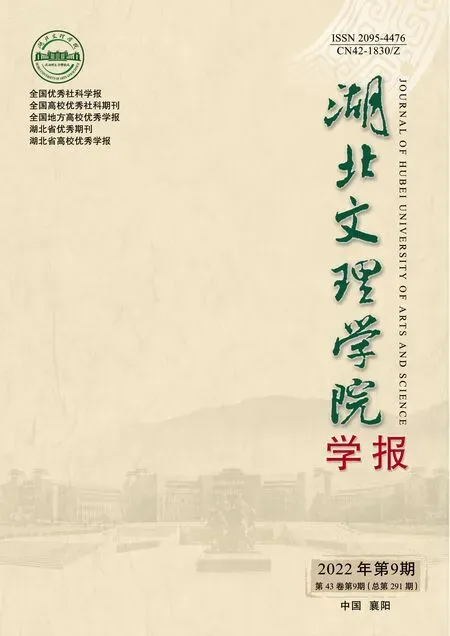论艺术审美图像的人文性及其当代嬗变
2022-11-21何正刚
何正刚
(四川音乐学院 艺术学理论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21)
人类的艺术欣赏,主要依赖于视、听这两种感官。在常见的艺术种类(如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建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电影等)中,除音乐是纯粹的听觉艺术外,其余皆是作用于视觉或同时作用于视听的艺术形式。纯粹的视觉艺术(包括雕刻、绘画、书法、摄影、建筑等)通常被统称为美术。对美术作品来说,由于其艺术形象就是通过点、线、面、体、块、色彩、肌理等造型元素,经由特定艺术手段创造出的视觉图形,因此在艺术欣赏中,所谓图像,往往专指美术作品的艺术形象。
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感觉之一,人对世界的认知经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感知以及随之产生的视觉心理。因此在生活中,人们为了增强头脑对信息认知的反应强度,会产生一种将非视觉的信息拟化为视觉信息的心理倾向。这种“视觉化”心理现象,在艺术欣赏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艺术的表达与抽象的概念陈述不同,它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人的情感,这就要求欣赏主体必须以形象性的思维接受来自艺术的信息,即运用形象思维将知觉“图像化”,从而使其“具体可感”。所以对艺术欣赏来说,“图像”作为一种属性特征不仅仅局限于美术,任何艺术形式都具有“图像性”,其作为艺术美的呈现形式即是艺术审美图像。同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艺术的人文性质需要经由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即通过审美活动得到体现,因而艺术审美图像就成为了承载艺术品人文内涵的重要载体。
一、艺术审美图像人文性的表现
说到艺术审美图像,首先必然提到美术。作为通过物质材料创造静态艺术形象的视觉性艺术,美术作品的感性形式即直观的画面形象。在西方,图像学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研究方法,就来自研究者对于视觉艺术的描述及阐释——20世纪初,德国文化史学家瓦尔堡(Aby Warbur, 1866—1929)将美术作品的主题与内涵放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开启了现代图像学研究领域。而后,美籍德裔美术史论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建立起了完善的图像志和图像学研究框架。他在1939年出版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inIconology)一书中这样说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宗教和一种哲学学说的基本态度,这些原理会不知不觉地体现于一个人的个性之中,并凝结于一件艺术品里”[1]。
作为图像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潘诺夫斯基的美术史理论研究的基石就是人文主义。他指出,人们在进行艺术欣赏活动时,艺术作品的外在形式最容易引起欣赏者的注意,但艺术是一种人文学科,艺术品作为“需要得到审美体验的人造物”[2],其根本意义是在于通过“表象”来承载“本质”。例如对一幅油画的欣赏,从画了什么到怎么画的,再到为什么这么画,这一系列体认过程,既有自然、常识性的内容,又有程式、习俗性的内容,更有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史的内容,这便是艺术美的人文属性。因此,潘诺夫斯基强调对美术作品的画面形象进行深度阐释,主张在艺术审美图像与哲学思想、人文观念之间建立广泛联系。
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在我国传统文化思想里面也可以找到依据。我国古典美学体系中,“言”“象”“意”是三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先秦文化典籍《周易·系辞上》里提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3]这里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指用单纯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有局限性,所以“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便是提出了“象”的表达方式。虽然此段内容一般是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但它同时也具有艺术理论上的价值。在审美范畴内,“象”即艺术作品的感性形式,它由具体的艺术语言铺陈开来,是个体观察之下的客观反映;“言”则是艺术作品中具有指代含义的部分,它指向人的思想意图;而“意”就是艺术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它既包括外在直观的“象”,又蕴藏“象外之趣”的惊讶与感动,构成了艺术美的完整内容。因此,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於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4]这里的“言”,可以看作是艺术家的一种主观性表达,其目的在于传达内容和输出理念,是对于艺术作品主题的昭示;“象”则可以看作是艺术作品的一种客观性表现,它既是艺术的外在形式本身,又包含艺术家观察事物的方式以及对世界实物映像的一种反射,是对于艺术作品存在的昭示。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想要拥有“意味”“意蕴”“意境”,那就必须使“言”和“象”相辅相成。所以,“言”需要通过“象”才能进行有效传达,而“象”则因为“言”的存在具有了“象外之意”。这个“象外之意”中的“意”是可以升华至“天人合一”的“意”,即一种“旨意”“天意”,它代表着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至高的人文追求。
可见,无论是潘诺夫斯基理论中的“图像”,还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的“象”,都指向艺术之美是由“眼睛”到“精神”的发展。这体现出艺术审美图像象征性的独特价值,凝聚了艺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意义。
除了视觉艺术,由于“视觉化效应”的存在,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不包括歌剧、音乐剧等带有综合性质的音乐艺术形式),不仅可以给欣赏者带来听觉上的愉悦,还能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空间,让人在脑海中产生基于现实条件的丰富画面感,包括音乐解释的画面、音乐烘托的画面、音乐与画面顺遂等等,这便是音乐审美图像。具体说来,就是由节奏、旋律、和声、音色等音乐要素构成的听觉语言,通过听觉刺激引发欣赏主体的情感共鸣,促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内心某种相关联的生活感受与生存体验重新组合,生发出具体的“可视化”感受。而这种音乐审美图像的出现,又会进一步巩固、加强和深化音乐欣赏者的审美体验。
不同于视觉艺术对图像信息的直观呈现,音乐审美图像需要欣赏主体通过想象力在自己的脑海中生成,同时由于音乐语言本身的非概念性以及听觉本身的抽象性,就使音乐形象在转化为具体图像的过程中有着极强的可塑性。同样一首乐曲,出于不同欣赏者在民族、职业、年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文化修养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生成完全不同的图像;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欣赏同一首音乐作品,其心中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景象。这是音乐作为一种极其抽象的艺术形式,其审美图像不同于视觉艺术、视听艺术的鲜明特征。
虽然音乐审美图像具有多维性、复杂性等特质,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因为即使再卓异的想象力也要受限于实践经验,音乐的创作、演奏、演唱、鉴赏都来自于人的现实生活,所以音乐审美图像的生成,是在相同的大前提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它绝不可能超出人类“观念史”的范畴。例如,波兰钢琴作曲家肖邦(Fryderyk Chopin, 1810—1849)创作的《降E大调辉煌的大圆舞曲》(Waltz No.1 in E-flat Major, Op.18),作品描绘了一个华丽的舞会场面,对于欣赏者来说,也可以将其想象为一群人嬉戏玩闹的场景,还可以演绎成小动物们在草坪上蹦跳、追逐的画面等等。这就是音乐审美图像的不确定性特征,但华丽而欢快、充满生命活力是这首乐曲的总体形象,这个总体形象则具有相对确定性,若离开这个相对确定性来看音乐审美图像,即是“对牛弹琴”。如果有可能把活泼、欢欣的听觉体验等同于残酷血腥、阴暗恐怖的战争场面,那音乐形象的相对确定性全无,也就不会有什么“审美图像”的问题存在了。因此,从人文视角来看,音乐艺术的审美图像在本质上与视觉艺术相同,即通过审美体验,将抽象的文化概念具象物化,以此实现人对于自身的反观,以及对于自我的“确证”。
除直接作用于视觉的美术和直接作用于听觉的音乐外,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等艺术形式是同时作用于人类的视、听这两种感官,被统称为综合艺术。这类艺术,其审美图像既不同于静止的美术画面,也不同于非直观的音乐画面,它是一种具体的运动着的图像,同时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特征。以电影艺术为例,电影审美图像即是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的结合。具体表现为,时间性不能脱离空间性,因为电影语言的展开只有通过无数具体画面的连接与转换才可以完成;空间性更不能脱离时间性,因为电影画面的叙事、表达等诸多功能都必须在一定的运动中才能够实现。因此,电影审美图像是运动进程之美与造型结构之美的统一,这是电影作为一门视听艺术的重要审美特征。
对影视与戏剧这类综合型艺术来说,文学性是其基础。因为任何戏剧影视作品的创作,都是以编写文学剧本作为第一道工序,并以此作为二度创作的根本依据。所以,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惟有综合艺术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文学本身作为一个大的艺术类别,由于是采用语言这一实指符号(1)从广义上来说,人类主动创造的有具体涵义的事物,或是原本存在的但被人类赋予新涵义的事物,都可以称为“符号”。从狭义上来说,“符号”即人为设定的一种象征物(用来指称和代表其他事物)或一种载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人类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记号”,人们能够利用语言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表意与传达系统。艺术也属于这一类符号形式,但与语言有所不同,语言是推理的符号,艺术则是表象的符号。作为基本的媒介和手段,因此在审美特征上与视听艺术其实有着明显的区别,与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更是有着重大区别(2)从表意的性质来看,语言具有实指性,图像则具有虚指性。因此,所谓文学审美图像,体现出文学的语言事实上是一种“虚指化”语言,即语言具有了图像的隐喻性功能,成为一种“语象”。这种意指功能上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学艺术规律的独特性。。
作为利用口语或文字形象地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主观情感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在表面上虽然是用眼睛看的,或是由嘴里读出来听到的,但文学既不是视觉艺术,也并非听觉艺术或综合艺术,而是语言艺术。这是因为,单纯的语言或文字并不构成文学作品,只有符合文学本身艺术规定性的语言、文字,才可以称为文学作品。所以,生成文学审美图像的关键不在于看或者听本身,而在于欣赏主体脑海中的想象、联想、逻辑、记忆、直觉等多种思维活动的综合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审美图像有着与听觉艺术相似的特性,但由于文字表达本身的逻辑性、细致性以及对世界万物高度的概括性,因此除抒情性的诗歌作品外,文学欣赏中的画面感要比音乐审美图像更为具体和立体。而抒情诗由于偏重情感抒发并且注重音调的运用,含有强烈的音乐性元素与非逻辑性的想象,所以它带给人的欣赏感受会相对偏向于听觉艺术,由此生成的画面感也就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
我国古代有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生动地体现出文学审美图像的人文内涵。拿偏重于抒情性的诗歌来说,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浪漫的人文画卷,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5]在这首五言绝句中,既有个人也有大自然,“鸟”“云”“山”的景象是诗人对于“游”的体认,传统道家“飘逸”的文化内涵正蕴含其间。至于叙事性为主的文学体裁,以清代奇才曹雪芹的举世名作《红楼梦》为例,在这部长篇世情小说中,对于主要人物之一王熙凤的出场有这样的描写:“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6]这段华美的语言,很自然地在读者脑海中描画出一个浓墨重彩、满身珠光宝气的美艳女性形象——那身着锦绣衣裳的王熙凤好似就站在你面前,她所散发的华丽气质,不仅是人物身份地位的体现,也是对宗法社会下这一“末世女强人”内心活动的昭示。
综上所述,作为艺术的形象性特征在审美活动中的生发,“图像”体验使艺术作品所涵盖的信息能够以更具吸引力、更易于记忆、更能引起情绪共鸣的方式被人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相较于其他人文学科更能体现出“人性”,而艺术审美图像就是一扇能够很好地了解人以及人类文化的窗口——将艺术作品呈现出的艺术形象置于人类各种境遇的潜在关系之中,置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类思想建构活动的相互作用之中,以此构建起完整的人类文明的观念范畴,包括人对于时代、民族、政治、哲学、科学、宗教等诸方面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解释。所以说,艺术不仅仅是“唯美”的产物,它更是“意义”的产物。艺术作为一种表征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使艺术作品成为了符号功能与人文价值的有机整体。
二、艺术审美图像人文性的当代嬗变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愈来愈快,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愈发倾向接受具象化的信息。因为接受抽象的信息需要脑内调用相应的概念进行运算、还原、加工,而接受具象的信息就使这一过程变得容易,甚至直接没有这一过程,从而节省了人们本就不多的精力。这一现象反映在文化层面,就是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以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即“读图时代”:在网络世界中,图像以其直观性、具象性的优势成为一种“通用语言”,日益打破传统语言文化的理性模式;在现实世界里,充斥着大量被包含在图像中的文字内容,形成一种由视觉引导的文化解读模式,画面成为了文字表述的先行者,以此贴近人的“感应性”。对此,我国不少学者有过相关论述。例如,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曾指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三个文化形态我们在文化学上经常把它叫做电子媒介的文化,也就是当代的文化,……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越来越趋向于图像的传送,……就是视觉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7]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也曾说道:“文化从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变为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以往的文化多以语言为基础进行传播,视觉文化传播时代,文化正趋向于多元化,文化传播由以语言为中心开始转向以形象为中心。”[8]7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当今时代称为“视像时代”“图像社会”“电子时代”等等[9]5,他们的表述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在说明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形态正越来越由视觉化的呈示方式构成。
从实质上来说,所谓读图时代并不是指文字或语言文化已消失不见,而是对于视觉文化成为文化主导形态这样一种趋势的强调,它是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模式的一种命名,其核心是一种突出直观感知的文化运作方式,它的出现“跟消费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或者说是消费社会的产物。”[7]而在当代消费社会中,除“图像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符号化”(3)“符号化”即是把一个事物变成符号。例如,人们用“熊猫”(符号)表示熊猫这种动物(事物),当你看到“熊猫”一词时,就知道是在表示这样一种生物,而不需要你真的亲眼看见一只熊猫。在这里,作为语言符号的“熊猫”这个词是“能指”(signifier),作为具体事物的熊猫是“熊猫”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signified),同时也是这个语言符号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曾指出:“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体;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从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10]这段话说明,在消费社会,“消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产品物性特征的占有,而变成对产品形象价值的占有,即通过符号化操控,实在的物被赋予“意义”,使产品的符号价值盖过使用价值而成为消费的焦点。
所以,在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下,符号和图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符号成为一种视觉表征,图像则成为基本的表意符号。这一状况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就是“艺术审美图像符号化”。前文提到,艺术是一种表征人类文化的符号系统,好的艺术作品应当是符号功能与人文价值的有机整体。而所谓艺术审美图像的符号化,事实上就是突出了艺术作品的符号功能,人文价值则成为符号功能的附属品。因为从实用属性来看,人文价值往往需要调动人的理性判断力以及想象力,经由知识与生活的一系列验证,才能得以生成实现;而符号本身即可以作为某个事物显现出的主要信息特征的标记,这十分契合读图时代追求快捷、简便的社会文化语境。所以,在当代听觉艺术中,视觉性元素被大量融入,从而让一首音乐作品与某种画面形成固有绑定,使本来应该由欣赏主体自己在脑海中生成的个性化音乐审美图像变得模式化、统一化,进而符号化。例如在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创作的商业性音乐中,为了市场宣传而制作大量画面精美的音乐录像,其原本虽然是利用图像手段来补充音乐所无法涵盖的信息与内容,但随着对艺人外形外貌的重视超过音乐本身,这种“音画”开始转为“画音”,即从画面的角度去理解音乐,而不是从音乐的角度创作画面,艺人的形象在此替代了本应由欣赏者自己构建的音乐审美图像,使其变成一种标识偶像明星的符号。而在视觉艺术方面,由于其本身就可以直接观看,因此创作者往往会通过美术作品将某一具体图像不断地运用、锤炼,以促使其成为一种符号。例如萌发于20世纪中期的波普艺术(Popular Art),作为一种主要源于当代通俗文化的美术形式,其创作特征即是直接借用商业社会的各种文化元素将其图像化,并大量运用复制、印刷、拼贴等手段不停强化这种表现,从而使图像本身符号化,进而在大众文化领域产生持久的影响力。至于文学艺术,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像与文字一起参与文学叙事,此情况不同于“文学插图”,它是图像成为了文学文本的有机构成,甚至直接承担起叙事、抒情等功能;二是小说的影视改编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很多经典小说作品,俨然已成为影视文化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这些都使得文学审美图像与欣赏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脱节,读者对文学信息的接收由“阅读”转为“观看”,而这一内在的文化逻辑转变,又进一步促成了文学审美模式的重塑,即“图像文化所张扬的感官美学、平面美学、仿真美学对文学来说极具蛊惑力。……以身体感官、性意识的张扬为表征的欲望化叙事、以历史意识消退后的当下体验为表征的表象化叙事、以营造超真实的历史类像而借以表达怀旧之情的虚拟化叙事,携带着时尚化的符号特征在文学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9]153。
可见,当代的艺术创作特别善于把艺术审美图像的某一特征元素进行提炼,将其经过符号化操控,以获得传播上的优势。至于人文性那种对内在精神深度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与消费文化对快速传播的要求相违背,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压制,这便是当代艺术审美图像人文性的嬗变。这一变化,是时代语境变迁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新的艺术创作手法的运用,并促进了艺术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更加广泛的传播。但同时,艺术作品也变得愈来愈通俗化、简单化,这其中有利也有弊,而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则需要人们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
三、对当代艺术审美图像人文性嬗变的反思
人何时成其为人?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当代学者朱青生曾说道:“只要是一个人,沉思反省,可以上达千古之边界,那里,人成其为人。沉思和反省可以通达之处,则为人文。不能逾越的边界即是非人的暗昧分界,人不能体验存在,也不能形容生命,因为人的问题,不能分享于动物,更不能穿透物性。人文越过与物质和动物的本性的界限开始,因此,人非草木,人非禽兽。”[11]298他更指出:“人本来不是‘人’,只有透过修养和教育,经由艺术和人文,方能成为真正的人。”[11]299显然,这里的“真正的人”,指的“不是作为活着的人,而是作为人文的人”[11]299。
人生而为人,却不够为人,所以人需要人文教育。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都十分重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例如我国孔子提出的“礼乐相济”思想、古希腊柏拉图提倡“理智的艺术”等等。确实,艺术帮助人成为人文意义上的人,其效果往往要好于枯燥的直接说理,因为有艺术审美图像作为人文内涵的载体,它作为艺术品的一种特征属性或艺术美的一种呈现形式,十分符合人在本能上对于接受感性形象的偏爱。所以,艺术作为一种人文学科,除了具备一般人文学科都具有的认识、改造等社会功能外,还拥有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功能,这体现出艺术独特的文化意义。而这样的特征优势,亦正好切合了当代社会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内在要求。或者说,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表象符号功能以及审美娱乐功能,使艺术天生就有作为商品的商业价值存在,并在今天这个以消费文化为基础的读图时代中表现得尤其显著。
不可否认,由于当代艺术审美图像的符号化对普通大众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因此它在消解艺术深刻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精英阶层对文化解释权的垄断,促进了更为公平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这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看到,读图时代的文化普遍有着强烈的商业属性,它所张扬的感性思维模式以及对人类本能欲望的推崇,一方面颠覆了旧有文化形态的话语霸权,一方面也在被市场逻辑所支配和利用。这其中,艺术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丰富多彩的创作理念被浅白性、消遣性抹煞,艺术变得肤浅化以至庸俗化,商业价值成为衡量一部艺术作品好坏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这对于艺术本身来说,无疑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 1874—1945)曾指出,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和科学一样,科学家是各种自然规律的发现者,而艺术家也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各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们全都知道艺术的这个特殊任务和特殊才能。列奥纳多·达·芬奇用‘教导人们学会观看’这组词来表达绘画和雕塑的意义。……歌德写道:‘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和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具体化。’[12]”在这位文化哲学的创始人看来,我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第三个世界”,而艺术即为我们隐喻了这个“新的王国”:艺术由自身所提供的形式丰富了人类对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并通过艺术作品引导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相较于单纯的感官愉悦和市场价值,人文价值才是艺术之美最根本的依托。正是由于人文性作为艺术审美图像背后的内容与内涵,才使得艺术作品能够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进而成就艺术史与人类文明史的同步和互文,这也是艺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根本性意义所在。
纵观艺术自身的发展历史,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等各门类艺术的审美图像共同构成的多姿多彩的表现空间和强大感染力,一方面为艺术作品的人文内涵提供了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让艺术作为商品的商业价值始终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和重要性会有所不同。无论东西方,传统的艺术观念都十分强调艺术的人文属性,商业属性则被排斥在经典艺术理论的视野之外。这一状况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消费社会的确立而发生转变,物质消费以前所未有的影响极大地刺激了艺术活动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艺术作品的性质,使艺术审美图像传统的人文性遭受到严重打击。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艺术为何”与“艺术何为”的问题。
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艺术的发展归根结蒂要受到时代环境制约,但艺术也必须保持自身对于时代的反作用力。在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只有通过调适、互补,在艺术审美图像的人文性与符号化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生态空间格局,使艺术审美图像不仅能够给人带来美的愉悦享受,更能够给人以美的智慧启迪,才能让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在当代真正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益。试想,如果艺术作品只具有符号功能,那么艺术只剩下某种工具属性,其最终必然会被语言这种推理性符号所取代;如果艺术创作只源于生活而没有高于生活,即艺术与生活完全重合,那么最终消亡的必定是艺术,而不可能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