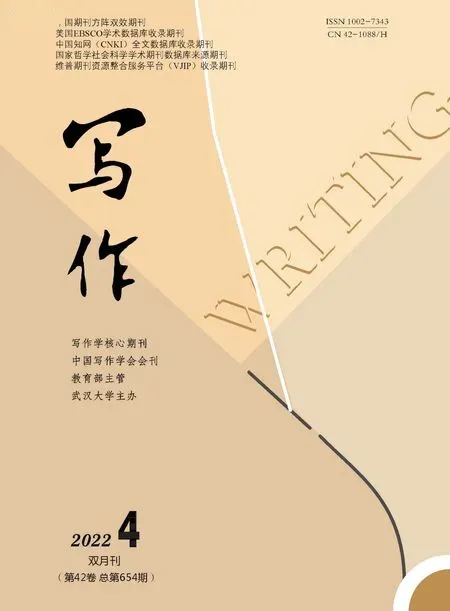於可训小说《猖日》的民俗狂欢化书写
2022-11-19王仁宝邓国飞
王仁宝 邓国飞
在先秦诸国之中,楚国以其重巫好鬼的文化特质而有别于中原正统,巫文化被视为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地“人神同位”的宗教观念认为:“神灵是具有亲和力的,也有人的需求和愿望,只要对神灵施以恩惠,就可以受到神的庇护。”①徐文武:《楚国思想与学术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②王逸撰:《楚辞章句》,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18-820页。“乐诸神”,即娱神,希冀神灵欢乐而不再降灾异于人间,猖日放猖即是对神灵施以恩惠的方式之一。作为上古巫文化的鲜明遗迹,与“猖”有关的民间信仰在长江以南的楚国旧地如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多处保存下来,具体表现为“五猖会”“游猖”“跳猖”“打猖”“供猖”“唱猖”“放猖”等民俗活动。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如鲁迅的《五猖会》以浙东乡村迎五猖神赛会日③五猖会主祀五通神,其性质与猖日放猖相通,都是娱神娱人的狂欢式节庆活动。“所谓迎神赛会,是指在固定的日期,由某一社区居民共同祭祀某位神灵,并且迎接神灵巡行当境以求消灾赐福的习俗,在祭神与神灵巡游的过程中,社区民众进行各种祈祷报赛活动,同时还举办有大型的歌舞表演以娱神娱人,整个社区都处于一种狂热欢庆的气氛中,这类活动总称为迎神赛会。”卢国龙、汪桂平:《道教科仪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9页。为写作背景,废名的《放猖》、於可训的《猖日》都将湖北黄梅乡下“放猖”旧俗作为描写对象。
於可训小说《猖日》,用类似笔记体小说的叙述方式再现了猖日放猖的全过程。猖日是五位猖神降临人间,驱晦纳祥的日子;也是村民们追击土地神,尽情发泄释放的日子;还是青年男女互诉衷情的难得时刻。猖日里人与神在狂奔、游荡、嬉戏、打斗与抢夺的过程中都获得了身心最大程度的释放,一年来积累的隐秘情绪此刻可以尽情发泄,难言包袱也可以就此卸下。释放与发泄过后,剩下的就是矗立在天地酣畅淋漓、无所羁绊的人的形象。放猖是对乡间原始野性力量的展示,重在对日常秩序的打破与突围,它演绎着现代社会业已丧失的具有生命力的传奇。小说《猖日》是於可训对乡间旧事的追忆,也是对已逝民俗的挽歌,其中包含着对现代工业社会下人类思维向度单一化的隐约不安。
一、娱神之日——神对人的任性游戏
於可训笔下的猖日首先是娱神之日,体现为神对人的任性游戏。《康熙字典》释义“猖”为形声字,从犬,昌声,昌亦表意。“猖”有狂骇、猖狂之意,即纵恣狂妄,不尊法度。屈原《离骚》即有“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①王逸撰:《楚辞章句》,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之句,批评桀纣狂妄放肆、乱政误国。民间传说猖神是屈原《国殇》中牺牲的士兵亡灵,非常态的死亡方式让他们身上多咒怨暴戾之气,因此猖神极易祸害人间,摧残生灵。猖日放猖,最初的目的为娱神祈福,消灾除难。村民们主动邀请猖神下凡,放纵神明让其尽情狂欢,满足猖神的一切愿望,使之体验人间的繁华与美好。他们希冀此后的一年中猖神不再祸害人间,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猖日里五猖的任何行为都为村民所纵容,五猖也抛弃了往日以泥塑金像的方式被供奉在五猖庙中刻板凝固、正襟危坐的形象,有了具体的肉身人象。五猖不再以惯常神明应有的端庄严肃的面目出现,而是在人间自由奔跑,任性游荡,肆意游戏。猖日里五猖的活动类似于巴赫金所分析的狂欢式节庆活动,具有“非日常”“非官方”特征,巴赫金认为具有诙谐因素的节庆活动“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与第二种生活”②[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猖日的节日狂欢,是神明获得愉悦的日子,五猖来到人间这“第二世界”,享受他们的“第二种生活”。五位猖神是猖日的主角,他们卸下了往日的庄严面具,展现出另类迥异甚至逾越规矩的一面,而这一切都因猖日这特殊的节庆之日变得合法化了,让神明愉悦恣肆、放任其游戏人间,实在是猖日这一娱神之日的应有之义。
於可训详细记述了村民们娱神的全过程,《猖日》开篇便描写了猖神进村之前村民为迎接猖神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猖日来临,村民将猖神迎接到人间,这是与上天沟通的隆重仪式,任何细节都不可怠慢。“女人掩上门,关上窗户,把一样样东西夹进被窝,或压在枕头底下,也有放到柜顶,或搁到榻板下面的。做这些事,要背着自家的男人和小伢。男人多心,小伢嘴快,都不宜窥见她们的秘密。”③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6、46-47页。女人们给降临人间的五猖神准备贡品,这一过程是神秘而严肃的,要掩门关窗,背着旁人,与神明的沟通决不允许被意外打断,猖日神秘的气氛便被如此渲染出来。男人女人们将一切准备好后,五猖便进村了。五猖是由本村或邻村的壮年小伙子扮演的,他们“穿戏服,着朝靴,画花脸,持钢叉,威风凛凛,像关公秦琼”④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6、46-47页。。人与神之间的界限被村民用特异的装扮鲜明地凸显出来。五猖进村后人与神的交流是庄重而严肃的,甚至是寂静噤声的,一切都在人神之间的会心与默许中悄然发生。画过花脸的猖神“再没有人间的自由,即是不准他们说话……他们已经同我们隔得很远”⑤废名:《放猖》,《废名散文》,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2页。。天机不可泄露,神秘是猖日的主色调,连平日里最为顽皮的小伢都察觉出了此日氛围的不寻常之处,他们主动寻找藏身之地,安静地观察猖神的一举一动。
乡民们放任五猖在村里自由行动,五猖游荡在村子的大街小巷,无需顾忌人间的规矩。他们可以随意进入家家户户的房门,甚至是未出嫁女子的闺房,他们可以胡翻乱找,无所约束。凡是在村民家里遇到看得入眼的贡品,皆可随手取走。对村民提供的贡品有不满意的,五猖还可以在所猖之户搞恶作剧,以玩笑的方式略微惩戒一下不够虔诚的人家。村民们不再以日常秩序规范要求五猖,而是要最大程度使五猖愉快,只要他们在人间这一天过得开心,猖得恣意,村民们就达到了其娱神目的,以求神灵护佑、驱灾纳福。猖神既是在战争中惨遭屠戮的士兵亡灵,也是民间建庙供奉的神明,需要履行神明的职责,承载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真诚向往。村民放五猖进家门,是为了让五猖驱赶藏在家中阴暗角落中的阴气、晦气、霉气,“他们的屋子才有地方装得下猖日留下的热闹和欢乐,他们才能大胆地领受这一年中的吉利和喜庆。”①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8、47页。因此,村民为之准备的贡品,也是对五猖为人间驱赶咒怨的犒劳和奖赏,是人主动与神签订合约的一部分。村民们通过使神明快乐而实现人世间的种种祈盼,娱神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
二、娱人之日——人对神的追逐嬉弄
猖日既是娱神之日,也是娱人之日,村民们在此日通过嬉弄神明来获得身心愉悦,实现娱人的目的。平日里村民辛勤劳作、供奉土地、虔敬真诚,不敢有丝毫怠慢。而在“非日常”状态的猖日里,不仅神明可以恣意妄为、任性游戏,村民也一改平日对待土地神虔敬尊崇的态度,转而对之嘲笑嬉弄,进行一场轰轰烈烈“打土地”的集体狂欢。因此在本质上,放猖是一种“娱人”活动,人们借助猖日狂欢氛围突破日常秩序规范,通过对土地神的追逐嬉弄释放长久以来的压抑和束缚,在精神上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和满足。在这场神人追击战中,神与人原有的神圣化等级关系被暂时取消了,颇近巴赫金在“狂欢化”理论中所指出的狂欢节“降格”特征:“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层面。”②[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8页。对土地神肉身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神明高高在上、俯视人间庄严形象的嗤笑和蔑视。猖日的狂欢精神,即是同一切自我隔离和自我封闭相对,同一切抽象的理想相对,同一切无视大地与身体的自命不凡相对。猖日的狂欢是全民性的,也是接地气的,在这难得的日子里,村民们来到村口这一公共区域,暂时放下正经严肃的说辞,有意抛却抽象缥缈的理想,去奔跑、蹦跳、追逐、喘息、投掷、嬉笑、喊叫……去体会身体接触泥土时踏实与安稳,去经历打破规矩时的激动与快乐,去感受生命存在之最原初的意义。猖日的“娱人”性质,并非指肉体感官上的快乐,更是通过类似于游戏或戏剧的形式展现精神层面的愉悦。“在狂欢节上,生活本身在演出”③[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8页。,在这场没有舞台、没有栏杆、没有演员、没有观众的演出中,每个人都可以出演最真实的自己,摘下面具、卸去盔甲,在节庆活动所营造出来的“第二世界”中对神明尽情嬉弄,肆意欢乐。
小说《猖日》解释了猖日“打土地”的缘由,土地神需护送五猖到其所辖各村,到村口后村民不允许土地神进村干扰五猖的放猖自由。责任心极强的土地神执意进村监管五猖,于是土地神就与村民发生了一场进退攻防战,村民称之为“打土地”。“穿破衣,涂锅烟,着草履,系草绳,摇蒲扇,邋里邋遢,像济公和尚”④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8、47页。的土地神在外形上与五猖可谓有天壤之别,他注定成为猖日村民们玩耍嬉弄的对象,村民有意识地矮化土地神形象,也是在为今日自己的叛逆与狂欢寻找心理上的合法性,“土地菩萨换了凡人的打扮,穿戴了凡人的衣裳鞋帽,显得不那么庄严。”⑤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7页。“打土地”的场面异常激烈,村民们摆动身体,弯曲手臂,将手中的泥块飞射向土地神,土地神为躲避击打而无休止地奔跑,整个过程伴随着嬉笑和欢呼。终于土地神被击倒在泥土之上,“打土地”的游戏狂欢达到了最高潮,村民对于神明的嬉弄也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完全地释放了自我,酣畅淋漓,彻头彻尾。此刻原有的身份秩序化为乌有,村民们在猖日狂欢中随心所欲地张扬个性,尽情展现生命活力,身心获得完全的愉悦。猖日“娱人”的目的得到实现。在村民看来,他们平日给土地菩萨烧香磕头,现在轮到土地菩萨牺牲了,因此跟土地开开玩笑,打打闹闹,不用担心亵渎神灵。村民们甚至唱起了顽皮的黄发小儿才会歌唱的咒语。往日稳重严肃的成人蜕变成总角孩童,他们不再需要用往常的规矩来约束自身,今日可以尽情放纵,恣意狂欢。这是一场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狂欢,具有“全民性”的特点,个体的狂热融入在集体欢闹的海洋中,这是极放肆而又极安全的狂欢,有着传统与集体的双重保护。
鲁迅的散文《五猖会》记录了浙东乡间神赛会日的风物人情。鲁迅笔下的五猖会与黄梅湖乡的猖日风俗有异,但人们渴望躬逢盛会、参与狂欢的心情是相通的。五猖会就是一场打破日常秩序的节庆狂欢,人们通过来到东关这样一处有着梅姑庙和五猖庙两座“殊与‘礼教’有妨”①鲁迅:《五猖会》,《鲁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页。庙宇的公共空间,参与这种妇孺不许,士人不屑,只有游手好闲之人才感兴趣的热闹集会,表达对日常秩序的不满,渴望在此日打破宗法礼教的束缚,获得身心的愉悦。鲁迅此文虽以《五猖会》为题,而着墨最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不是五猖会的狂欢场面,却是作为孩童的“我”在父亲的要求之下现场背诵《鉴略》,终于被工人簇拥着登船却对东关五猖会的热闹意兴阑珊的情节。作为散文集《朝花夕拾》的第四篇,《五猖会》是鲁迅“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②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83-184页。。此时的鲁迅先后历经女师大风潮、“八一三惨案”,不久后还与“现代评论”派展开论战。鲁迅面临着年轻生命被屠戮,自身罹患重病、辗转流离、陷入纷争等外在层面的巨大生存困境;内在精神层面上,有感于自身受到父亲的压制而错失了一些童年乐趣,激愤于封建势力对国人灵魂的压迫。
《五猖会》中的父亲是抽象了的“父亲”,迎神赛会具有颠覆礼教传统的狂欢化色彩,指向与正统专制文化相对的另一精神空间。但宗法势力蓄意要阻止人们进入这“第二世界”享受“第二种生活”。文中以儿童身份进行第一人称叙述,讲述者有限的视角更凸显了处于弱势地位“我”的痛苦无奈。在外界“他者”绝对权威的暴力压制下,“我”表面顺从但内心“诧异”,文本的深刻内涵在多重张力中得到体现。鲁迅《五猖会》借民俗引发对1920年代中国社会和其自身经历的深切思考,具有不可撼动的文学史、文化史地位。鲁迅《五猖会》与於可训《猖日》各自拥有独特的审美体验,相对来说,於可训小说《猖日》由于外在压迫力量的完全隐退实现了对现实秩序的彻底打破,为读者带来畅快饱满的阅读感受。但也正是打破秩序的目标实现地过于顺利,文章缺少了鲁迅《五猖会》所具有的文本张力。尽管如此,於可训《猖日》勇于打破禁忌的美学与社会学价值无需质疑。
三、狂欢之日——人与人的纵情破忌
1947年,返回北大重执教鞭的废名于《中国新报·文林》发表散文《放猖》,记叙家乡黄梅放猖的民俗,后收于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八章《上回的事情没有讲完》中,列于莫须有先生名下,承接第七章《莫须有先生教国语》的内容。废名笔下的“我”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没有直接参与猖日的狂欢,也没有亲身体验猖日“打破”秩序的愉悦,他通过观察猖兵们的活动来间接感受猖日的狂欢氛围。“我”处于日常生活和狂欢节庆之间的中间地带,他意识到猖日的“非常态”特征,却又不能于之有切身体会,因此感到“寂寞之至”①废名:《放猖》,《废名散文》,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330-331页。。与於可训《猖日》相比,废名《放猖》似乎重在单向度的神对人的游戏,缺少人对神反向的嬉弄,猖日娱神的效果大于娱人。
《放猖》原本是废名抗战时期在故乡黄梅避难担任国文教员时出给学生的作文题目,废名回忆:“作文的目的是要什么事情都能写……我出的作文题,都根据于儿童的经验,从小在乡间所习见的风俗习惯,我都拿来出题目。”②废名:《放猖》,《废名散文》,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3、330-331页。废名在《莫须有先生教国语》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莫须有先生告诫学生:“作文要写自己生活上的事。”③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9页。废名注重学生散文习作的真实感、经验性,要求其尽量来源于生活,表述要清楚、明白、自然,例如《送油》《放猖》这样写地方风俗的散文,应该首先把风俗介绍给读者,“令异乡人读之如身临其境一目了然。”④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莫须有先生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9页。《放猖》选用儿童视角进行第一人称叙述,写孩子有限视角能看到的世界,孩子理解力能达到的地方,真实地将儿童在狂欢节庆中略显懵懂的“未完全参与”感表达出来。作为儿童的“我”对于放猖仪式产生的敬畏、羡慕、寂寞之感,本就是《放猖》行文所着重突出的。充满真实感与个体经验性,这正是废名要求学生散文习作所应该呈现出来的审美效果。由此相较於可训《猖日》的彻底狂欢姿态,废名《放猖》多出一层含蓄美学的意味。《放猖》在审美选择上也符合废名一贯的内倾化文学观念,在废名看来“文学是梦”,指向内心世界,因此与外在世界始终隔了一层,保持着叙述距离感。内倾含蓄是美,大开大合亦是美,废名与於可训用不同的方式将黄梅放猖民俗展示给读者。
在情节设置上,相较废名《放猖》,於可训《猖日》对于男女爱情的描写更为细致大胆,将猖日的狂欢延续到人与人之间。猖日里青年男女不再需要恪守礼教之大防,此日他们可以无视禁忌,纵情享乐,表达爱意,自此猖日狂欢才算完整,神与人都实现了全方位的“打破”,人间的声色与生命力得到尽情展现。於可训用细腻的笔触大方地向读者展示猖日里有情人之间无需言说的默契,当扮演猖神的小伙子在所猖之户“摸着了一些体己之物,如一双布鞋、一副鞋垫、一条汗巾、一块垫肩什么的,就急忙收藏起来,留待偷情约会时面酬心上之人……但凡摸到这些体己之物的,藏的人取的人,必定都心知肚明,同为五猖的伙伴也没有不识相的,会去拆穿这里面的小把戏”⑤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面对姑娘大胆的爱意表达,小伙子们心领神会,他们将原本神明降福的仪式转变成示爱求偶的活动。对村民们来说,人间现世的欢乐才是最值得追求的。或许穿着五猖装扮的年轻人多少还碍于神明的威严,当放猖的仪式结束,青年男女迎来了他们最为珍贵的温存时刻,延续猖日狂欢的余韵。
“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的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⑥[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於可训将狂欢节的广场置换成了月色下的打谷场与草垛。乡间打谷场以天为盖地为庐,拥有居室屋檐下不具备的清新空气与自由氛围,空间上的广阔与时间上的契适相配合,构成了青年男女“打破”礼教束缚、挣脱秩序规矩的完美场域。元贞姐姐与猫伢、元贞六哥与淦生媳妇两对有情人在这里不拘行迹地亲密接触,上演了猖日里动人的一幕。扮演土地神的猫伢此刻正躺在元贞姐姐的怀里,安静而温顺,元贞姐姐显得更为大胆,却也因几句情话就羞红了脸。比较而言,扮演猖神的元贞六哥与长年寡居的淦生媳妇大胆放开得多,他们毫无顾忌地释放天性,表达爱意,甚至不在意是否会被窥听,这份不容于名教礼法的感情在这夜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容许与体谅,於可训借猫伢的口说:“猖吧,猖吧,一年难得有这一回。”⑦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於可训设置性格温驯谨慎的猫伢在猖日扮演被人嬉弄的土地神,让热情大胆、奔放洒脱的元贞六哥担任游戏人间的猖神,他们各自的性格与其承担的角色特征有一致性,也与他们各自在打谷场上的言行相映照。元贞六哥白天作为神明嬉弄人间,此刻则以凡体肉身尽享尘寰欢乐,无论是做神还是做人,他都要猖得尽兴肆意。猫伢在放猖仪式中主动扮演土地神被人们奚落嘲弄,在元贞的姐怀里仍旧温驯安分、懂事知礼。当元贞的姐为猫伢的不解风情而怅然,“猫伢嘻嘻一笑说:‘我是土地,不能乱猖’。”①於可训:《猖日》,《乡野传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或许是最初的身世与性格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角色选择,在放猖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也产生反向作用。由此,猖日狂欢下的“第二种生活”还有加深主体自我确认的作用,具有面向未来的积极意义。猖日的狂欢并非纯粹破坏式的“打破”,而是“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②[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以放猖为代表的民俗活动既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人们的心灵有释放作用,还对日常生活产生积极引导。
於可训通过小说《猖日》为读者展示乡间所蕴含的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野性力量与大开大合的原始生命力,以猖日的狂欢呈现出不同于单面一维线性生活状态的多样人生向度,引导我们思考当下看似理所应当的思维模式背后隐藏的诸多问题。不仅小说《猖日》,收录在於可训《乡野传奇集》中的其他篇目如《归渔》《腊戏》《元宵》《书场春秋》等都通过追忆已经逝去的风俗民情、奇人异事为我们构建起一个与现代工业社会截然异趣、充满野性传奇的“第二世界”,在其中可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抽离与反思。当然,由于社会背景、写作年代与作家经历的不同,鲁迅、废名、於可训各自要讨论的重点有异,作品所要揭示的主旨和呈现出来的风格也大为不同。带着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深切思考与强烈人文关怀,以及彻底的狂欢姿态与决绝的破禁立场,於可训为我们书写了一场猖日的盛大狂欢。其小说《猖日》呈现出的独特美学风格,与鲁迅《五猖会》、废名《放猖》共同丰富了放倡民俗书写的文学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