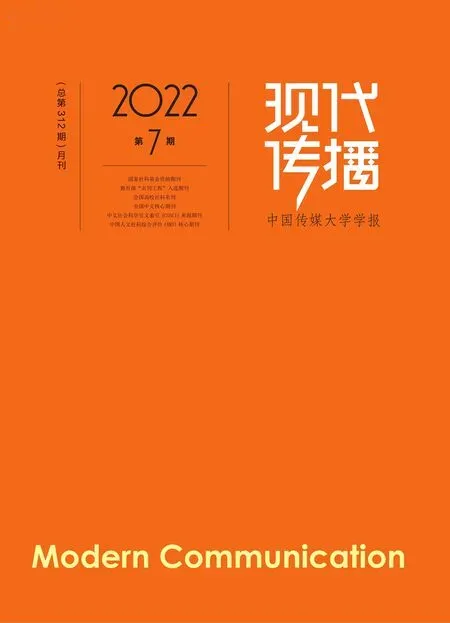启蒙现代性、共同体意识与视觉景观想象*
——文化空间视阈下的长城影像叙事与文化传播
2022-11-18巩杰李磊
巩 杰 李 磊
一、问题的提出:影像叙事如何建构和传播长城精神形象和文化身份
长城关乎民族象征、纪念碑性、传统符号、人类精神传承和历史文化记忆,甚至具有全球性和宇宙化的面向与内涵。关于长城全面具体的研究就显得极其重要又势在必行。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几个重要的方向与问题。
一是借助影像媒介和文本,重构原来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空间,如何对长城本体性进行全方位的认知?对长城本体的认知是首要的出发点,也是极其重要的认知观念。从本体而言,长城空间是方位、地理、历史、文化和生态的结晶体。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域外视野来看,“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①。长城作为边疆防御的空间建筑和符号象征,建构了中华民族边疆的地理空间界限和视觉空间标识。因而,我们在谈及长城时,就要从地理空间定位出发,充分认识长城作为边疆地理防御设施的重要属性和作用,尤其要把长城还原到北方和西部边疆的历史地理文化空间中进行考察和审视。
二是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纪念碑性和历史文化记忆如何被不断地塑造和传承?影像媒介对长城的立体呈现,更加全面逼真地表现中华民族精神和纪念碑性,从而引起现代人对历史文化的记忆,唤醒民族精神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文化基因。
三是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和视阈下,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人类文明的标志性建筑,能够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这就要更好地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以此来保存和唤醒民族历史记忆和重构全人类的文化记忆。同时,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进一步明确,应该受到全世界更好、更完备的保护。
四是从文化空间视阈来读解和阐释长城的影像叙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认知意义、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关于长城的传媒艺术和文化研究,有从先锋艺术角度和视觉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但是目前缺少从文化空间视阈对长城影像叙事作品的相关研究。我们要重新认识长城的空间意义和功能,对“一带一路”倡议语境下影视媒介中的长城空间生产和影像叙事进行详细读解和阐释。这也意味着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新技术条件下,对作为传媒艺术的影像作品,如何更好地重塑长城的文化符号、影像空间和精神形象,以及对如何更好地传播与传承长城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参照。“长城结果是一种令人着魔的幻象,它现在已经习惯性地深深地嵌入了中国和西方学术和老百姓的想象之中。”②长城影像叙事的时代转向,也可以看作是长城话语史和长城观念史,因而为学术研究和人们的文化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
本文重点要研究的是从何时开始,影像叙事中的长城具有了现代启蒙的精神力量;也要重点探讨长城影像叙事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文化审美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和内涵;同时讨论长城影像叙事作为一种视觉景观想象,又如何被纳入全球化的消费语境进行体验和审思。
二、孟姜女传奇故事影像叙事中“砖石长城”与启蒙现代性建构
长城作为一种建筑空间是中国西部和北方边塞的标志,它不仅是一种地理分界,也含括了时间的绵延与空间的交叠。传统文学艺术中的长城空间积累了边疆交锋的历史意象,是古代诗人在杏花烟雨的江南,对秦汉边塞的想象构建。影像叙事作品延续了文学艺术,尤其是孟姜女传奇故事的主题内涵和叙事范式,是“征夫怨边”与“闺妇思君”两种叙事视角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容颜离别尽,流恨满长城”的空间叙事意象和意蕴表达。同样是传媒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因其媒介生产的时间和本体差异,在影像叙事中也存在着不同点。通过不同的叙事时空呈现出“砖石长城”的空间建构,以及对启蒙现代性的强烈诉求和真切询唤。
(一)电影影像叙事中孟姜女传奇故事及“砖石长城”空间的启蒙现代性
孟姜女传奇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根据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孟姜女传奇故事的叙事走向因隋唐时期长城作为边疆屏障才开始与“闺妇”和大众情感进行了关联和缝合。③著名的理论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说:“传奇模式提供出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在传奇作品中,男主角英勇,女主角美貌,反面人物是十足的恶棍。”④在孟姜女传奇故事的理想化世界里,年轻美貌的女主角孟姜女和英俊书生范杞良(范喜良)相爱,范杞良却被秦始皇征为劳役去修筑工程浩大的万里长城以防御匈奴。而作为反面角色的秦始皇则是十足的暴君,孟姜女在长城寻夫并坚决反抗,投河自尽,以死抗争,争取人生和爱情的自由。长城成了统治者实施“暴政”和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也是人们争取自由与幸福的阻碍力量,具有了阶级剥削和意识形态压迫的刻板印象。“砖石长城”空间及其意象以反例和反证的方式,体现着现代启蒙精神和启蒙现代性诉求。
从媒介考古的角度看,电影是最早书写孟姜女传奇故事和呈现长城空间的影像媒介。遵循历史脉络就其要者而言,首先拍摄孟姜女传奇故事的影片当属邵醉翁导演、胡蝶主演的《孟姜女》(1926)。在袁牧之导演的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有金嗓子周璇对长城婉转缠绵的低吟浅唱:“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筑成长城长,侬愿做当年小孟姜。”电影插曲《四季歌》伴随着长城影像的镜头闪现,让故事和长城得到了更好的视听传播。由吴村编剧导演、周璇主演的《孟姜女》(1939)则关注到了长城的空间呈现和现实问题。当时有人撰文道:“孟姜女寻夫将上银幕”,这是抗战非常时期“国产电影的畸形发展”⑤。“它的中心意识显然在努力表现‘除奸报国’。”⑥这种改写与抗战时期的社会现实和话语语境是密不可分的,对惊醒汉奸、振奋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孟姜女争取自由和幸福的启蒙现代性,也体现在周诗禄导演的香港粤语片《万里长城》(1949),周诗禄编剧、导演的《孟姜女》(1955),屠光启导演、李丽华主演的《万里长城》(1957),台湾地区梁哲夫导演的《孟姜女》(1959),韩国权英纯导演的《秦始皇和万里长城》(1962),香港地区林柯导演的《孟姜女哭倒长城》(1963),台湾地区姚凤磐导演的《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1970)等影片中。沙丹导演的黄梅戏戏曲片《孟姜女》(1986)中白雪覆盖的长城成为人性压迫的象征,孟姜女哭倒长城象征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正如片尾的唱词:“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电影艺术通过更加节约化的时间和更为影像化的叙事张力,凸显“孟姜女哭长城”的叙事逻辑和影像魅力。孟姜女作为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中国新女性的原型”⑦,呼应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思潮和实践。长城作为一种被“摧毁”和被“解构”的反证,具有警示、启迪以及反向的询唤功能,激发国人对压迫的抗争、对人性解放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建构和彰显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国家现代性的精神需求、民众共情和启蒙现代性的迫切要求。
(二)电视艺术影像叙事中孟姜女与“砖石长城”空间的启蒙现代性
作为电视艺术的电视剧相比电影而言,有了更大的篇幅和体例,依照连续剧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更适合去讲述完整的传奇故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剧成了呈现孟姜女传奇故事最好的传媒艺术和叙事文本。在《长城故事》(1990)、《孟姜女》(1996)、《秦始皇》(2001)等电视剧中,孟姜女传奇故事和长城空间的呈现得到了较为全面宏大的叙事表达。神话/爱情网剧《九尾狐与仙鹤》(又名《孟姜女》)(2005)等呈现出拟像化的长城景观和反抗精神,以及对爱情和自由精神的追求。电视剧《秦时明月之万里长城》(2012)、动画电视剧《孟姜女》(2012)、越剧电视剧《孟姜女》(2013)等,使得这一题材的传奇性和虚构性大为增强,更加迎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和消费需求。孟姜女故事和长城空间影像叙事由“征怨”向“闺怨”的转换,也透露出人们审视长城的角度由政治向道德方向的变化:“从政治角度来看,长城不仅意味着阻隔,亦意味着和平;从道德角度出发,长城则代表着专制、残暴,最终还代表着政治失败。”⑧这样恰切地印证了“孟姜女哭长城”这一原型故事在叙事上的“道德批判意识”和表意上的“启蒙现代性”的密切结合。
总之,通过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孟姜女传奇故事及其影视叙事文本,我们发现长城除了具有军事防御作用以外,更具有了道德批判与负面价值的话语言说。长城话语被建构为阶级压迫和人性束缚的象征,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阻碍力量。因而,长城是一种砖石构筑的实体,也是一种象征和符号,更加凸显出人的身体、权力、生存与自由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空间视阈审视长城影像叙事与文化传播,虽然存在历史还原、民间传说与神话想象等叙事时空的断裂,但是这些影视作品试图弥合和修复消失已久的民间记忆和道德谴责与批判。长城空间充满强烈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也体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人通过这一传奇故事,对人性与爱情、觉醒与启蒙、反抗与自由等共同价值的强烈追求。这充分彰显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现代性诉求,凝聚为宝贵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的长城”话语下长城空间影像叙事的民族精神共同体建构
“孙逸仙率真地开始将长城变成一种民族的进步象征。”⑨在国内首先将长城与民族精神象征关联在一起的是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长城成了被卒然摧毁的军事防御系统与被重建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更具体地说,把长城定位为一个民族身份的不可动摇的象征,是在日本军队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后才被广泛传播开的。”⑩长城形象和象征的这种转变,也见证了以“废墟”空间存在的长城,具有了著名学者巫鸿所说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以及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地变成“英雄式的丰碑”,又如何成为建构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永恒象征。
(一)“血肉长城”与民族精神共同体建构
长城从人道主义和启蒙现代性中挣脱出来,成为主张积极抗战救亡运动和重振民族精神的标志。“长城的形象被重新构造,成为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式的纪念碑,并迅速在抗战期间的各种大众媒介和艺术作品中出现,几乎成为抗战的象征性标志。”长城纪念碑和英雄丰碑形象的确立在美术(版画/木刻)、戏剧、摄影、电影等大众媒介和视觉媒介中迅速涌现,这也揭示出传媒艺术在建构长城可视的英雄形象、重构人们的历史记忆、唤醒民众爱国主义精神方面的强大力量。“这是任何纯粹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所不能达到的。”
1933年4月梁中铭发表的《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一文,首先提出了“血肉长城”这一观念。在同一期《时事月报》上,一篇名为《到热河去》的札记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长城本为我国工程浩大之防边工事,数千年来仍未变其性质与地位。……陆军军器之进步,已远非笨拙之长城所能济用,今已进至人的长城时代,动的长城时代,非死的砖石的长城时代了。”“人的长城”“动的长城”“非死的砖石的长城”就建构起中华民族精神焕发的“新的长城”不屈不挠的伟岸形象。
有学者指出:“山河破碎的大变局下,存续了两千多年的长城,应救亡图存的时势之需脱胎换骨,成为集体意识空前统一的现代中国的象征。这一象征的固化与传播同早期国产电影密切相关。”作为一种现代影像媒介艺术,1935年摄制的电影《风云儿女》是现代视听媒介明确塑造和呈现“新的长城”形象和观念的发轫之作。其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中所歌唱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对这一形象和观念的视听形式的有力表达。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著名歌曲流行开来,1949年后成了新中国的代国歌,后来被正式确定为国歌。电影中呈现的长城拍摄点位于北京八达岭长城,电影不仅用影像片段指代了万里长城的庄严全貌,还将长城转喻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符号象征。其后,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华艺影片公司筹拍的救亡电影《关山万里》虽然未能拍摄,但由编剧潘孑农作词、刘雪庵作曲的主题歌《长城谣》却传唱开来:“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新的长城”的内外形象与故乡和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建构的内在关联性。同样,1938年候曜未能拍摄完成的电影《血肉长城》更加凸显了这一主题内涵。电影中并没有出现“砖石长城”,长城成了抵御外辱的象征,人们用身体筑就了一道永不坍塌的“血肉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民族精神共同体的确切象征。
与之形成同构的是来自国外视野的长城影像叙事与表达。著名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1938)中有意识地导演了人们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壮观场景。这是对长城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一次域外视野下的重现和重构。在美国导演雷伊·斯科特(Rey Scott)的纪录电影《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1941)中,林语堂在其导言中说:几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民在长达万里的边境线上修建了雄伟的长城,以此抵抗外敌的入侵。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但他们仍然需要面临一堵新的长城——那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外敌时坚强不屈的英雄精神”。同样,在具有国际视野的美国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役》(1944)中,长城也成为抗战时期不屈不挠的、具有血肉之躯的民族精神共同体的真实象征。
因而,可以明显地看出,抗战时期国际视野对“血肉长城”的影像呈现与重构,与国内视角形成了一种共情与同构。电影作品中的长城空间叙事,通过“人的长城”和“血肉长城”的呼喊,旨在唤醒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建构民族精神共同体。
(二)“钢铁长城”与民族精神共同体建构
关于“钢铁长城”最早的提法,根据学者吴雪杉的考证,“铁的长城”这一概念在1933年就出现了。在1937年,“铁的长城”开始被广泛传播。胡绳在其1937年10月出版的《后方民众的总动员》中写道:“全国人民在同一的意志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结成一座铁的长城,这才是我们的抗敌战争的政治基础。”1938年廖冰兄发表在《抗战漫画》上的《筑起我们钢铁的长城!》,以视觉艺术的形式见证抗战,塑造民族精神共同体。这是视觉文化形式对“钢铁长城”形象的历史描摹,而“钢铁长城”的影像叙事则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抗战胜利后及新中国建设时期,随着国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重构,以“血肉长城”为标识的民族精神开始让位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指导的民族精神。随着军事力量的崛起和军工科技的发展,以“钢铁长城”为标志的新的民族力量开始被唤醒。电影中的“钢铁长城”被赋予了象征和隐喻含义。电影《长城新曲》(1975)赋予了长城新的内涵和意义。“片名《长城新曲》,既寓意人民解放军‘钢铁长城’,又寓意故事发生地:燕山之麓,长城脚下。”在著名导演李俊执导的电影《南海长城》(1976)中,人们反击和围剿“海鲨特遣队”的流寇和特务,在南海上筑起祖国“钢铁长城”不可侵犯的威严。电影《祖国啊,母亲》(1977)中最后的长城影像呈现,凸显了幅员辽阔的祖国的壮丽河山,以及实现祖国统一和多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电影《吉鸿昌》(1979)片头的长城影像呈现,是“钢铁长城”般民族精神的真切象征。纪录电影直接以《钢铁长城》(1981)为片名,使得这一寓意更加明确和凸显。此后摄制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1982)、《干杯,女兵们》(1985)、《长城大决战》(1987)、《战争子午线》(1990)、《黄河绝恋》(1999)等影片中,巍然屹立的长城彰显了民族形象的新崛起和“钢铁长城”一样无坚不摧的“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长城具有了“纪念碑性”和“英雄式丰碑”的特征,是民族希望和未来的象征。
“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象征符号、神话传说、价值观念镌刻在一种自然面貌之上,并服务于现代政府和国家的发展。”因而,作为“自然面貌”和风景空间的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和精神图腾,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现代价值集体认同的“文化试金石”。“风景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于是,进入影像媒介视阈下的长城风景和空间也成为一种重要的“风景政治”。因而不难看出,长城开始由本体性的“砖石长城”向指代性的“血肉长城”和“钢铁长城”的质性转变,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新的长城”空间叙事形象。影视作品通过旧的“砖石长城”的摧毁和“新的长城”(“人的长城”“血肉长城”和“钢铁长城”)的诞生,来激励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影像叙事通过实拍与意指的结合,以比拟、象征和隐喻为修辞手法,塑造长城空间新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和民族伟力,充分彰显了长城的符号化特征及其“英雄式的丰碑”和“纪念碑性”。
四、全球本土化视阈下长城影像叙事的文化审美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无论是文明意义上的长城,还是民族意义上的长城,都不能单从中国内部生发出来,而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只有在全球性的目光下,长城的‘古老’与‘伟大’才能凸显出来,长城才能够首先被欧洲,然后才是中国来自东方文明的代表,才能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其他世界民族交相辉映。”
进入新时期,纪录片中的长城书写重在再现长城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记忆,是对长城全方位、立体性的影像空间呈现,注重长城作为一种地理空间的本体性价值和意义。长城空间纪录片试图在弥合风景、记忆与历史,通过地标符号、国家记忆、身份认同,进一步建构民族文化象征和文化审美共同体、世界眼里的中国文化地标和人类共同体意识。
(一)国内文化视野下长城纪实影像的文化审美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在文化精神和文化审美上寻找一个标志性、纪念碑性的民族标志建筑来确立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长城无疑成为这种精神价值的承担者。除了文字描写和叙事,长城很快就被纳入到影像叙事视野之下。1979年由沈杰等拍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长城》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长城纪录片。影片以航拍的方式呈现出长城的地理风貌和雄姿,试图探索建构一种文化审美共同体。1981年由殷培龙执导的科教片《万里长城》以科普的形式介绍了长城的历史、位置、风貌及传说,重点展现山海关、八达岭、嘉峪关长城的结构特点。长城影像引起强烈反响的是1991年刘效礼导演的《望长城》,被誉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里程碑”。在拍摄手法上,打破了传统的电影纪录片手法,强调实景拍摄、现场收音,又通过探访者的行动和语言,引导观众观看画面,具有身临其境之感。纪录片以长城为能指符号,唤醒民族的文化历史记忆,彰显民族文化的历史感和自豪感。
进入新世纪以及新时代以来,国内拍摄了多部关于长城的大型纪录片,开启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视阈下长城的新定位和新发现。总长为194集鸿篇巨制的纪录片《远方的家:长城内外》(2015)围绕着长城遗址所发生的故事展开,通过王昌龄的诗句“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体现出这部作品的诗意品格和文化审美特质,进而对万里长城进行了全面探访和文化审美共同体形象呈现。在《长城:中国的故事》(2015)中,作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纪录片全面记录了长城的地理、工事、历史、文化。尽管西方学者说:“长城隔开了神话时代和现实时代。”但是,纪录片将长城融入到全球本土化视阈中,重新定位长城的地理多样、历史久远和文明交流,告诉世界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万里长城。正如解说词所说的:“长城拒绝征服,但从未拒绝交流。”把游牧和农耕文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抛却以中原文化和汉文化为中心的传统理念,从民族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上来重新审视不同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从文化空间和文化地理学角度来审视,纪录片中的长城“已然杂糅了现实性、物质性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和想象性、概念化的‘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而成为一种‘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并成为“性别、种族、阶级等各种权力关系的角力场”。长城已经失去其军事防御和作为国族边界的功能,成为遗留下来弥合了人们“集体记忆”的建筑空间、文化遗产、视觉形式和历史象征。于是,从历史地理、文化基因和人类文明的角度来全面认识长城空间、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等问题,纪录片中的长城叙事自然而然地升格成文化审美共同体和人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密码。
(二)西方文化视野下长城纪实影像中的文化审美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意识
尽管西方人早期拍摄了大量的长城摄影和纪录影像,但长城并未完全纳入全球化的文化审视和视觉符号呈现体系。早期域外纪录片体现出长城的国际化视野和神秘性的探寻,夹杂着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偏见和对古老神秘中国的奇观化想象。自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方人开始重新审视长城及其空间本体。新世纪以来,长城再次进入西方创作者的视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拍摄的《中国长城》(2008)以域外视野使用了情景再现、电脑CGI特效和航拍等拍摄手法对长城进行了探索和揭秘。此后英国BBC则更热衷于拍摄中国的长城,产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BBC纪录片《美丽中国》(2008)之《风雪塞外》呈现了美丽而气势磅礴的长城空间和长城内外人们的生存历史。《中国长城:尘封的历史》(2014)再次以英国长城学者威廉·林赛探索长城为线索,根据长城考古的新发现揭秘长城的建造悬念和生存故事。《揭秘长城之魂》(2016)以探访者的视角和行走,结合科学研究和CGI动画,揭秘长城的内部构造和军事秘密。《又见长城》(TheForgottenWall)(2017)以外国人的视野,讲述被人们遗忘的箭扣野长城和城墙脚下赵氏一家的故事。《慢速飞翔旅程:中国万里长城》(ASlowOdyssey:TheGreatWallofChina)(2019)这部史诗般的冒险探索纪录片,从东海的老龙头开始到达气势恢宏的嘉峪关,见证了长城砖石、墙壁和瞭望塔等标志性的长城空间。
总之,国内外纪录片中的长城空间呈现,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视野,但却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全球本土化视阈,在表达效果上达到了一种共情。国内纪录片通过全球性反观和审视本土性,使长城空间的影像叙事从孟姜女民间传说的启蒙现代性、抗战时期激发的民族精神共同体的现实需要中释放出来,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对峙与割裂中超脱出来,成为建构文化审美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象征。西方文化视野下的纪录片拍摄,试图在全球性中关照和介入本土性,在某种程度上抛却刻板的“东方主义”好奇和想象,通过长城来探寻中华文明的神秘性和蕴含的人类文明基因。长城成为人类文化遗产和人类共同体的标志性建筑和核心意象,具有了全人类性的时代特征和未来诉求等复杂多元的文化面向。
五、全球化和消费化语境下长城影像空间叙事的视觉景观想象
随着民族文化的重新建构和世界文化的凸显,长城进入了全球化的文化审美和消费视野,也变成了“东方主义”“反纪念碑性”(anti-monument)、消费化与奇观化的空间景观杂糅,甚至具有了超越全球化的宇宙化超人类景观面向和视觉景观想象。
(一)动作/恐怖/惊悚片中的长城影像空间叙事的视觉景观想象
在当代艺术和媒介融合时代,视觉艺术使长城空间叙事变得进一步景观化和消费化。在以动作、恐怖、惊悚和爱情为主要类型的长城题材电影中,长城的空间内涵在消费化语境下出现了明显的消解,甚至呈现出从“鸦魔”到“怪兽”的魅惑性的魔怪面孔。
还原历史的时空语境,中国香港导演王星磊执导的悬疑/恐怖/惊悚片《鸦魔》(1975),是最早呈现出长城的魔怪面孔的影像。古代民间传说中成千上万的乌鸦随机攻击和杀害居民,村外的长城成了鸦魔的栖息地和庇护所。同样,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长城》(2016)中,电影齐聚了打怪兽、盗火药、炫爱情等元素的全球性符号。火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神秘的力量”,西方人对火药的觊觎与盗取绝不是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之举,而是深深打上了西方“列强”盗窃原罪的烙印。在长城上展示的东方女性的“身体”与“功夫”,以及与西方白人的爱情体验和幻想,让长城在“装置”“火药”“怪兽”“身体呈现”“情色展示”等方面,成为由来已久的“东方主义”的视觉景观想象和刻板印象。电影中的长城不再是一种“纪念碑式”的精神象征,而是一个依靠景观和特技制作出来的精巧的遍布机关的“装置”。作为一座“反纪念碑性”的衰朽的躯壳,艰难地抵御着怪兽对人类的凶猛入侵。
同样,在好莱坞大片《毒液:致命守护者》(2018)中,不明外星物质共生体入侵中国地标建筑——长城,在全球化的消费视野中,长城继成为“打怪兽”的壁垒之后又成了主体遭受侵害的对象。因而,长城进一步被东方化、想象化、景观化和消费化。
如果说张艺谋的《长城》是一种“自我异域化”的“东方主义”镜像,那么好莱坞的《毒液:致命守护者》无疑是西方白人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偏见,对长城以及中国全域“反纪念碑性”的凝视和想象。
(二)爱情/家庭/伦理片中的长城影像空间叙事的视觉景观想象
在爱情/家庭/伦理类型片中,长城成了类型惯例的景观象征和情感想象。这些爱与不爱的柔情与承诺,让长城成了一个情感迷离并具有魅惑性的附属物。在王正方的电影《北京故事》(1986)中,被拆除的城墙和长城成了电影呈现和表意的主要空间场景,也成了从美国归来的华人对古旧中国认同的标志性建筑。在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2》(2010)中,大全景俯拍的长城城垛是秦奋斗口中“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的地方,慕田峪长城成了一种消费性十足的关于爱情的视觉景观想象。电影《追爱》(2011)中的嘉峪关长城,如同电影的英文名字GreatWall,MyLove所表达的那样,台湾地区人到大陆看长城,长城与爱和远去的故乡关联在一起,具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深情凝望和视觉想象。
因而,爱情/家庭/伦理片中的长城影像叙事不再是民族精神和“纪念碑性”的文化符号,而是被有意识地、无情地消解。此类电影是对个人爱情和故乡情怀,以及“他者”意义上的“景观”和“风景”的深情凝望和视觉景观想象。
(三)影像装置艺术与媒介艺术宣传中的长城影像空间叙事的视觉景观想象
影像装置艺术(video installation art)作为一门以影像、空间、互动、装置以及观念的输出为表现形式的艺术,从录像艺术到移动影像,从数字艺术、装置到表演艺术和诸多难以定义的独特作品,均由技术提供丰富多样的创作手段。新技术打破了传统电视、电影的线性叙事模式,以超链接的媒体整合及立体拼贴手法,成为多媒体艺术的链接方式,通过观者参与、互动以及对其经验的开放,为观者提供了非线性的审美体验。
1988年被誉为“行为艺术之母”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中国创作了行为艺术作品《情人·长城》(TheLovers)。默里·格里格尔导演的纪录电影《中国的长城:在边缘的恋人》(1988)就是对这一声势浩大的行为艺术的全面记录,第一次让长城成为一种具有跨文化视觉消费的爱情景观想象。2019年9月,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的“焦点”版块展出《情人·长城》风格独特的彩色照片、绘画以及双频录像,现场录像首次在中国呈现。《情人·长城》将长城空间、装置、影像(双频录像)、行为艺术体验等结合起来,具有很强烈的先锋艺术特征。1988年10月,温普林在长城上举行了以“告别20世纪”为主题的大型行为艺术活动“包扎长城”,成为电视艺术片《大地震》摄制的主要组成部分。青年/行为艺术家在长城上彻夜摇滚、狂欢,还有各种行为艺术表演和表达,像极了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 Rock Festival)。长城被解构为一种行为艺术、影像装置、视觉想象与身体体验的先锋性后现代景观。
作为媒介艺术宣传作品,在宁瀛导演的宣传片《长城脚下的公社》(2002)中,“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一旅游实体景观酒店,只是对酒店场景的一次影像符号的空间再现,成为电影拍摄的场地和取景地,这就使得长城被解构成一种纯粹的消费景观,其“纪念碑性”的价值和意义被完全消解。同样,2015年好莱坞大片《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在长城上举行了主题为“长城之巅 原力觉醒”的商业宣传和预告片首映活动。长城虽然不是影片拍摄和再现的空间,但“长城作为一个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空间,承载和见证了好莱坞电影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商品的本土化宣传”。
这种关于长城的影像装置艺术和媒介宣传片,通过参与宣传、空间重构等方式在不断消解长城的纪念碑性和精神内涵,具有行为艺术和奇观化的影像特点,使得长城具有了“第三空间”“东方主义”“反纪念碑性”和视觉景观想象等异常复杂的文化面向。
总之,在全球化语境下,长城一方面被全球化体系所认知、重构和传播;另一方面则被消费化、奇观化的景观呈现所消解和剥离,具有了“反纪念碑性”的视觉形象和空间面向。长城成了消费视阈下的“景观的想象”和“想象的景观”。这种双向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张力,无不反映出长城叙事话语的延异、矛盾和驳杂。此类影像作品/行为艺术中呈现和传播的长城视觉空间是对民族精神、历史印记、共同心理、文化记忆和审美共同体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消解和解构。
六、结语
将长城纳入到全球化的话语重建和文化形象体系中,长城成了中西文化对比、凝视与思考的一种具有差异性的象征物,进而凸显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中华文化在比对凝视与多元化想象中进行身份和属性认同。这就需要从能指符号和虚幻影像的悄然蜕变中奋力警醒,以影像的再生产来抵抗过度的商业消费化和视觉景观化、奇观化的臆想和想象,重新建构长城影像的真实面向,以期获取更多的民族精神共同体认同和价值认同,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更好的观念和理论支持;也要努力探寻符号化、图像化的长城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下,建构人类共同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文化艺术生态理念中新的人类文明传播与文化传承价值。
注释:
① [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9页。
②⑦⑨ [美]阿瑟·沃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石云龙、金鑫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286、281页。
③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歌谣周刊》,1924年第69期,第6页。
④ [加]诺思洛普·弗莱:《原型批评:神话理论》,载叶舒宪编选:《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85页。
⑤ 未名:《孟姜女寻夫将上银幕:国产电影的畸形发展》,《至尊》,1936年第6期,第3页。
⑥ 《电影批评:〈孟姜女〉乙下片》,《电声周刊》,1939年第10期,第490页。
⑧ 侯艳:《唐代诗学中的长城意象》,《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