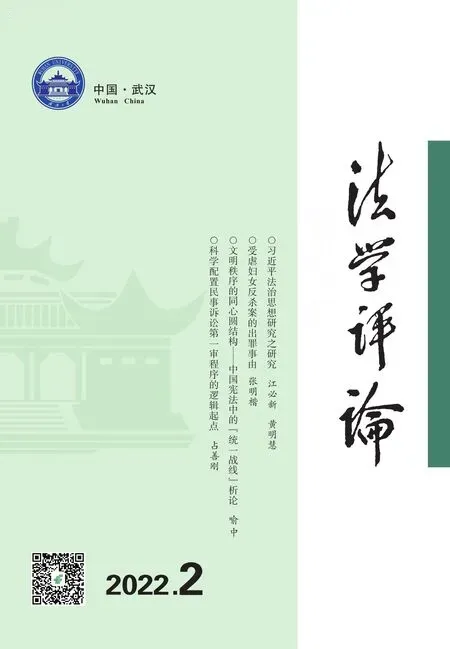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研判*
2022-11-17叶欣
叶 欣
引言
在法理上,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与患者知情同意权利密切相关。就我国现有立法来而言,诸如《医院工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均设有医方告知义务或患者知情同意权条款,但均未对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判定做出明确、统一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医疗方面相关的司法解释在一般意义上对知情同意权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能否直接作为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之判定依据,尚需法理支持。
在理论界,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患者知情同意能力及其判断标准问题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有学者认为患者的同意是有效医疗行为的前提,而患者之同意能力则是其同意之有效性的必要条件;(3)参见黄丁全:《医事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视野,根据发达国家通说,认为确定患者同意能力不宜以民事行为能力为判断标准,而应以是否具有对同意之内容、意义和效果的理解能力为依据;(4)参见季涛:《谁是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有学者认为介入性医疗活动涉及的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理论上并不需要其具备行为能力,而只要患者具有对相关诊疗行为的风险、后果必要的辨识能力和理解能力即可;(5)陆青、章晓英:《民法典时代近亲属同意规则的解释论重构》,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亦有学者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出发,认为医疗领域通常推定未成年人没有医疗决定权,限制了未成年人的权利,尤其是未成年人已具备了对其疾病与医疗真正理解、判断、决定的能力。(6)参见李燕:《未成年人医疗决定模式的民法典解读》,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3期。
综合既有研究成果,有关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界定多与民法上的行为能力、意思能力等相勾连。鉴于医疗风险之特殊性,有必要在学理上将患者同意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行为能力或意思能力区分开,从而为医疗实践中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之判定提供理论支撑。其本质而言,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独立判定说之要义有二:一是尊重患者自身意愿和同意权,二是最大限度规避医疗风险——从同意的阻却违法性角度来说,医方有效告知患者医疗信息及方案后,由具有知情同意能力的患者自由选择、自主决定、自担后果,在有效保障患者权利的同时,也阻却了医方医疗行为可能的违法性。对于医患双方而言,对知情同意权能力的判定标准处置得当,意味着可以进一步促成医患关系达到更加和谐、互信、共赢的良好情境。
一、患者同意能力论说
在一般意义上,能力是指判断特定的个体是否具备必要的认知、决策、情感和实践技能,从而能够充分完成特定任务(如驾驶),或做出特定决定(如拒绝医疗治疗)。(7)Moye, J. and Braun, M.,Assessment of capacity. In P. Lichtenberg (Ed.), Handbook of Assessment in Clinical Gerontology, 2nd edn, 2010,p.581. San Diego: Elsevier.在民法上,“知情同意能力是一个关于智力属性的复杂概念,通常被模糊地被称为‘能力(competence)’。虽然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衡量决策能力,但对于能力的标准,即使是成年人,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标准。我们只认同一点,即所选择的任何能力标准都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标准。这意味着我们将接受决策者的各种能力,但将寻求建立一个底线,低于这个底线,潜在决策者将被取消资格。”(8)King N.M.,Cross A.W.,Children as decision makers :guidelines for pediatricians .The juournal of pediatrics, 1989 ,July ,Volume 115,p.12.据此,患者知情同意能力是指了解医疗信息和风险、做出医疗选择并予以表达的能力或资格。目前,理论界对于患者同意能力性质的论说主要有行为能力说、识别能力说、意思能力浮动说等观点。
(一)行为能力说
行为能力说之要义在于:将行为能力状态作为患者能否行使同意权、接受医方告知的判定条件。比如,有学者认为患者的同意能力标准“应当要求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且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9)周友军:《论中国侵权法上的知情同意规则》,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患者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属于“不能”向患者说明的情形;(10)杨丽珍:《“告知后同意”:〈民法典〉第1219条第1款的解释论展开》,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如果患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医疗机构就必须向其本人履行告知义务”。(11)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但是,参照行为能力类型的划分标准判定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既过于硬性僵化,也无法契合医疗实际。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从理论性的维度看,行为能力一以贯之的全有或全无的类型化,在医疗领域中已经暴露出不合时宜的问题。“与行为能力不同,判断同意能力具有情境化的特质,需要结合具体诊疗场景进行个案考察。”(12)同前注③,陆青、章晓英文。因此,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之判断标准应当遵循具体化、个案化之原则;其二,从现实性的维度看,即便是同一主体,若配置相应的行为能力判定标准,其自主决定也将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在医疗领域,基于患者利益保护的考虑,对于其知情同意能力,需要具体细致的判定方式,而不宜简单地套用民法上的行为能力标准。“在一般性医疗行为,依其智力的成熟状态,已足以识别医疗行为之性质,亦即可以理解同意内容、意义和效果,即应认为有同意能力,至于是否达到一定之年龄,或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人均非必要条件。”(13)同前注①,黄丁全书,第218页。对未成年人而言,也应当根据不同性质的行为划分不同的判定标准,更有利于其利益的保护。“对于诸如遗嘱、收养、医疗决定等领域,法律可以设立特殊的行为能力判断标准,以更大限度地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思自治。”(14)彭诚信、李贝:《民法典编纂中自然人行为能力认定模式的立法选择——基于个案审查与形式审查的比较分析》,载《法学》2019年第2期。
(二)识别能力说
顾名思义,识别能力说的要义在于:主张以识别能力作为医疗同意能力的具体判断标准。如德国通说认为:“允诺是被害人对自己权益的处分,故不能完全适用民法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原则上应不以行为能力为要件,而应以个别的识别能力为标准;”(15)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亦有我国学者认为:“既然受害人同意能力应适用识别能力来判断,医疗决定在性质上又属于受害人同意,那么医疗决定能力理应适用识别能力标准;”(16)孙也龙:《医疗决定代理的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同样认为:“病患之同意能力系于病患个别之识别能力而非行为能力。在病患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但欠缺辨别是非善恶之判断能力时,仍因无识别能力,而无同意能力。反之,在病患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只须具有识别能力,仍得为有效之同意。”(17)陈富聪:《告知后同意与医师说明义务(下)》,载《月旦法学教室》第82期。
但是,识别能力标准也不宜适用于医疗领域中的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主要理由如下:其一,识别能力有着不同的适用场合,且分别蕴涵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比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识别能力通常被认为是与侵权责任能力相关联的概念,大多适用于侵权行为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境,“无识别能力者,不能认识其行为的危险,进而在行为上有所选择或控制,因此,不应使其负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保护无识别能力的行为人”。(18)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3民终5298号民事判决书。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将识别能力直接指称侵权责任能力,即为在法律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和后果的能力。“侵权行为责任的成立,须以识别能力为必要,无识别能力者无责任能力”。(19)同前注,王泽鉴书,第257页。但是,医疗领域中的患者知情同意能力是关涉患者作出医疗上的选择和决定是否有效的问题,一旦对患者产生不利影响时,是否可以达到阻却医方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效果。其二,识别能力的基准设定较高,若在医疗领域中采用识别能力标准,势必徒增患者知情同意能力判定门槛。比如,日本法在判定是否设立监护时,使用的是“辨识事理的能力”一词,它与意思能力不同,“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能力,因为它要求在有意思能力的同时,……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利害得失并依照经济合理性为意思决定的能力。”(20)彭诚信、李贝:《现代监护理念下监护与行为能力关系的重构》,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4期。但在医疗领域中,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之判断,无须具备充分认识后果的辨识能力之要件,因此,患者知情同意能力与侵权法上的识别能力在构成要件上存在明显差异。
(三)意思能力浮动说
意思能力浮动说的要义在于:医疗决定能力比照意思能力而决定,而不是参照行为能力,并根据所需决定事项面临的风险而浮动调整。比如,Appelbaum和Gutheil认为:当医疗行为危险性高,意思能力的判别则越严格;当医疗行为之危险性低时,意思能力的判别则较为宽松,即以浮动基准判断之;(21)Appelbaum PS, Gutheil TG. Clinical handbook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2nd ed.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1991,p.224.Shulman等认为若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越复杂,对于实现其个人意愿就更需谨慎,因此确认他的认知功能或情绪稳定度的标准则会越严格。(22)Shulman K.,et al.,Contemporaneous assessment of testamentary capacity,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2009,21:3,p.435.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意思能力是指能判断自己行为可产生何种结果之精神能力,或称心智能力,是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的基础,与决定能力本质上相同,每个行为所需之意思能力(判断力)不一致,有无意思能力的判断是依照行为种类与个案事实个别判定,而非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23)王敏真、黄诗淳等:《关于意思能力受损病人之医疗决策——如何在自主、代理、最佳利益及医疗品质间取得最佳平衡》,载《临床医学》2019年第2期。
意思能力浮动说关注到患者能力变化的情景,但同样不宜适用于医疗领域。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意思能力浮动说未明确区分成年患者与未成年患者的类型化不同。依附于患者的同意能力会发生动态变化,与定型化的行为能力之间也会发生渐次分离,并非固化恒定的状态。不同年龄层次的主体可能不一定体现出与年龄成正比的意思能力状态。在医疗过程中,成年患者与未成年患者在不同时间、阶段或受药物作用影响,其医疗同意能力情形也会出现差异。“意思能力是一种事实上的心理内在,应就具体人、具体行为进行具体判断”。(24)常鹏翱:《意思能力、行为能力与意思自治》,载《法学》2019年第3期。但是如何判定既符合医疗实际又具有可操作性,仍需要予以进一步的研究。其二,未明确区分医疗领域所需的同意能力与一般事项所需的意思能力。需要考量医疗事项与一般事项在性质上的区别,因为医疗事项主要涉及患者的人身性利益,一般事项涉及范围则较为广泛,还包括财产性利益。纵观我国《民法通则》第13条、《民法总则》第21-22条、《民法典》第21条之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则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何认定方面也是依循个性化判定模式,但并未明确区分财产管理行为和人身利益的行为。
二、知情同意能力独立说何以必要
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独立说之要义在于强调:将患者知情同意能力概念从民法上的行为能力、意思能力以及侵权法上的识别能力区分开来,形成专门适用于医疗领域的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理论,从而为环设知情同意能力判定基准的具体化和专门化提供理论支撑。
(一)法理层面:有利于医疗决定效力的认定
在我国,行为能力大概率的反映了意思能力状况,亦就是说行为能力的存在是为了实践操作的简便易行,大致吻合民事主体意思能力的现实情态。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不能等同,即不论是否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能力有可能并不一定与行为能力一一对应。(25)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页;李永军:《从〈民法总则〉第143条评我国法律行为规范体系的缺失》,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1期。。而在医疗领域,亦不能简单地出于操作简便的考虑,而是需要基于个性化的判定和尊重个人自主权的立足点,对知情同意能力进行考量和评价。
其一,就行为效力而言,是否具有知情同意能力决定了患者在医疗方面的同意行为是否有效。一般的法律行为领域,遵循的是行为能力判定标准,但也存在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特定样态下缺失意思能力的情况。“即使某项允许行为是由完全行为能力人作出的,该项行为也并非就一定有效。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首先就有关此项侵害行为之必要性和危险性向病人作出说明。所以,即使病人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只要他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其作出的允许行为也应当有效。”(2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即使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出的医疗决定行为有可能无效。因此,在医疗领域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和慎重对待,对知情同意能力的判断进行弹性化的识别,不可一味的僵化适用行为能力标准。
其二,就主体利益而言,是否具备同意的能力不应囿于年龄、智力、精神状态的界限,即使是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宜可以针对个别情形进行认定,其作出的医疗决定行为属于有效,则能够较为切实的保障其利益。亦就是说,即使是未成年人,或是受到监护宣告的人,仍然可能具有医疗事项的同意能力。“正如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特定情形下会对特定行为没有意思能力一样,无行为能力人也会在特定情形下对特定行为具有意思能力,这其实是行为能力和意思能力关系的常态表现。”(27)同前注,常鹏翱文。结合德国民法领域的案例,“如果根据一名未成年人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成熟程度,能够衡量侵害行为以及同意侵害的意义和后果,那么由该未成年人表示允许即可。”(28)同前注,[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162页。但是,这种同意行为必须以对医疗行为的必要性、风险性与可能的危害性作出说明为有效前提。
(二)价值层面:有益于患者自由意志的保护
相较于行为能力而言,知情同意能力更能深度彰显医疗法律的核心价值:尊重患者自由意志,注重保护患者权利。在传统的行为能力制度层面,尤为关注的是交易安全的问题,注重的是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已有学者指出带有限制过度的色彩。(29)参见朱广新:《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立法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为分析对象》,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都曾被质疑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在医疗领域对于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则更不宜僵化的直接套用行为能力进行判定。
其一,知情同意能力的独立更加符合“承诺阻却医疗行为违法性”需以本人同意为前提的要求。承诺行为在医疗领域具体体现为知情同意,但患者承诺针对的是医疗行为而非医疗结果。经过患者本人同意的医疗决定,因其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使得医疗行为消弭了可能存在的违法性。“惟承诺乃系指对医疗侵袭本身,而非指其结果。未成年人如意思能力已臻成熟,其承诺即得认为独立有效。”(30)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未成年人同样可以参照意思能力判定其承诺的有效性。
其二,知情同意能力的独立更加有利于体现自主决定的意愿。从患者切身利益出发,考虑患者需求,进而保护其最佳利益,这是知情同意权设置的价值基础。“每一个人都有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决定权,皆可接受或拒绝医疗。此权利专属于病人本人,任何人(如家属、医师)都不得违反病人意愿,对其强行进行医疗处置。”(31)同前注,王敏真等文。回归患者本人意思对其知情同意能力进行实质性的认定,得到患者的自主配合,从而能够较好地完成医疗事项,更加符合患者自身的实际需求或最佳利益。同时,也有利于防止法定代理人滥用代理同意权,不会基于代理人的价值观作出决定或选择,即使是所谓的“最佳利益”,也有可能违背了患者本人的意愿,从而引发其他不必要的纠纷。关于医疗事项的切身性和重大性,对于患者本人而言毋庸置疑,故其本人是否接受的意愿和选择理所当然的应当得到尊重和保障。
三、不同患者同意能力判断之分殊
对于部分特定的民事主体,虽然欠缺完全行为能力,或者是年龄、智力或者是精神状态、体力耗弱等因素,判断能力或许不是那么的充分,仍有可能依据其尚余的能力予以决定,在医疗方面相应的权利也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和保障。比如,对于成年患者而言,当出现反应异常或不合情理时,其知情同意能力之初始判断需要进行具体而微沟通,并须依赖医生的临床判定;对未成年患者而言,基于法律价值之效率与公平的立足点,如果涉及的是重要的事项或面临死亡的重大风险,则须采用严格的行为能力标准;若面临较低的风险,则允许采用较为宽松的能力标准予以衡量,亦即是将医疗行为分类型而适用不同的能力判定标准。
(一)成年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
已有较多学者提出未成年人应当归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类型中,(32)同前注,参见彭诚信、李贝文。既然提倡在未成年人的法律行为方面应当逐步放开对其以保护为名的限制,那么举轻以明重,即使设立了监护的成年人,同样应当由其自主决定作出选择。
其一,不论精神状态、身体障碍等因素,对于成年患者宜一概先以能力推定(33)英国《意思能力法案》(Mental Capacity Act 2005)首要原则即能力推定原则:当事人在被证明不具意思能力之前,都有法定权利决定自身事务。参见谢宛婷等:《意思能力丧失之病人的医疗决策——英国意思能力法案给台湾的启发与省思》,载《医疗质量杂志》2016年第5期。为原则,个案审查为例外。同意一种潜在的道德观点,即精神能力不应影响法律行为能力,即所有人,不论其能力和其他特征如何,都应作为人受到充分和平等的尊重。(34)Jillian Craigie et al.:Legal capacity, mental capacity and supported decision-making:Report from a panel ev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2018,p.5.“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看,患者医疗决策能力并不总是需要评估的,通常患者都是被预设为有能力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可以证明某些可以辨认的精神缺陷已经使该患者没有能力做出决策。”(35)肖健:《医疗知情同意的道德基础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就考量判定的顺序而言,首先适用能力推定为原则,符合大概率的公平要求和效率的价值追求。“判断能力由智力能力与意志能力两要素组成。它是一个依具体案件进行评价的相对概念。有无判断能力是被推定的。成年人原则上有判断能力,主张成年人无判断能力者,须负举证责任。”(36)朱广新:《民事行为能力类型化的局限性及其克服》,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1期。该文认为“未成年人原则上无判断能力,认为自己有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证明。”但本文认为超过一定年龄标准的未成年人宜区分医疗行为的类型来进行相应同意能力的判定。因为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进入到司法程序后方才涉及,如果在医疗过程中能够及时的具体确定患者的判断能力,则更能节约司法成本和避免事后判定的不准确。
其二,不论是医生评估抑或是司法裁判,在对成年患者能力可能进行否定评价时,宜参考其个人价值观及偏好等因素,综合判定其知情同意能力。通常而言,可以推定患者具有合理性、常规性的决定能力,那么,何谓合理性?一般来说,只有当病人拒绝医生推荐的治疗方案或者选择另外其他治疗方案时会遭受到能力质疑。(37)参见王丽莎:《成年精神障碍者的行为能力》,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5月。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价值观和偏好对一个人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可能是一个人进行决策推理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与价值观和偏好一致的决定可能表明此人具有能力,尽管价值观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能力的变化。如果一个人的决定超出了公认的规范性标准,那么价值观和决策之间的一致性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兴趣”。(38)S. McSwiggan et al.:Decision-making capacity evaluation in adult guardianship: a systematic review ,p.382.在特定情形下,患者的决定异于一般人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其价值观、个人偏好则更加值得关注。
其三,如患者被设立了成年监护,亦应当保障被监护的成年人的独立化,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最大化和处理自己事务的独立性。《瑞士民法典》第19条c款规定“有判断能力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自主行使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权利;但法律要求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不在此限”。(39)于海涌、赵希璇译:《瑞士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瑞士法认为是否具备判断能力并不是行为能力的划分标准,除特定情况之外,有判断能力即使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仍有权行使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权利。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法总则》第35条第3款后一句“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在解释上获得与《瑞士民法典》第19条c款一致的法律效果,被监护人即便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亦得独立实施与其人身性质高度相关的法律行为。(40)参见孙犀铭:《民法典语境下成年监护改革的拐点与转进》,载《法学家》2018年第4期。我国《民法典》保持了与《民法总则》一致的立法内容,同样可以由监护人保障并协助的行为仅限于财产上的行为,而不包括身份行为,那么医疗上的知情同意权俨然具有身份行为的性质,并不适宜由他人进行代理。所以,即使是设立了监护人的成年人,其在医疗方面的意思及意愿,也应当受到尊重和保障。现代监护制度的设定目的绝不是为了限制其权利与自由,而是旨在从协助和辅助的角度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被监护人之利益,应赋予其处理事务的独立性。“在知情同意方面,不仅应当获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且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辨别能力,适当听取其意见,并应尊重其有具备能力时对于参与试验性治疗所做出的在先意见。”(41)满洪杰:《论成年被监护人医疗决定问题:以被监护人意愿为中心》,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二)未成年人的知情同意能力
结合我国实际和立法现状,未成年人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之判断宜做如下考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原则上由法定代理人的替代同意进行医疗行为的所有决定。对于非重大性、危险性、侵入性的医疗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全部推定有知情同意能力。对于具有重大性、危险性、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年满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法定代理人予以辅助、补强,例外需要考量评估其能力状态,尽量考虑其自主意愿及意思,如具有知情同意能力的标准则可以完全自主决定。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从立法趋势来看,不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国内法均呈现出了尊重未成年人意愿的发展趋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赋予了能够形成自己见解的儿童在所有影响其事务的事项中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42)参见朱广新:《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体系性解读》,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我国《民法典》第35条强调了监护人在作出有关的监护决定时,需要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这不仅是法院的裁判案件的规范指引,也是监护人履行日常监护职责的行为指引,但在实施过程中究竟如何把握,则需要由监护人初步衡量和掌控的。
其二,从必要性来看,未成年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在医疗方面未成年人的意思自治应更加得以保障。虽然未成年人而言,心智尚不完全成熟,能力状态不具有稳定性、持续性,但随着年龄、智力的增长,而处于渐进性、阶段性的状态。“即使是幼儿,也应被看作是一个具有自主意思并享有基本权利的市民,只不过,鉴于其身体与精神的渐趋发展性、非成熟性,未成年人是一个需要特别保护与照料的‘成长中的市民’。完全否认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明显已严重违背《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要求。”(43)同前注,朱广新文。有学者认为:“一些儿童可能有能力作出一些决定,许多儿童可能能够代表他们对决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44)King N.M.,Cross A.W.:Children as decision makers :guidelines for pediatricians,The juournal of pediatrics, 1989,July ,Volume 115,p.12.
其三,从判定方法来说,考虑其心智的成熟情况,未成年人的知情同意能力认定,应当确定一个最低年龄标准之后,再区分不同类型,如重大医疗事项原则上以法定代理人为辅助,非重大事项一般则推定未成年人有权自主判定。“对于重大医疗行为,通说认为未成年人需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与行为能力制度相同。盖此时未成年人思虑未必周全,而须辅以法定代理人之判断也。”(45)同前注,陈富聪文。需要分不同的医疗行为,实行同意能力与行为能力部分分离的做法。“惟在重大医疗事项诊疗上(具有侵入性质、副作用较大、或效果不确定等影响生命、身体、健康重要法益之重大医疗事项之同意),则需病人具有行为能力。”(46)吴志正:《谁来说明?对谁说眀?谁来同意——兼评医疗相关法规》,载《月旦法学杂志》2008年第162期。这一模式较为适宜未成年人的情况,对于重大性、危险性、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原则上需要法定代理人予以介入、辅助、补强。
(三)特殊患者的知情同意能力
在医疗领域,对于精神障碍者应当适用与其能力相适应的评价机制,来帮助其实现生活正常化。在法律行为方面已经有学者提出不再将精神障碍者划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围。“成年精神障碍者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来保护其权益,不仅消除了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夹带的限制过度的问题,而且为他们随精神或意思能力的逐渐恢复而随即、自由地过上正常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47)同前注,朱广新文。
其一,在理念方面,基于保证精神障碍者社会生活正常化和自主决定的价值理念,应当保障身心障碍者具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自主决定能力,使其具有无差别的社会融入感。这既是人权基本精神的体现,也是医疗行为切身性的要求。《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283条第1款明确规定医疗决定不允许代理原则:“(1)就医疗行为而言,只要残疾人具有认识和判断能力,只能由其本人表示同意。否则,则应当取得享有处理该事务权限的管理人的同意。”(48)周友军、杨垠红译:《奥地利普通民法典》(2012年7月25日修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亦即认为,即使作为身心障碍者,在医疗方面同样有作出相应决定的能力。“完全监护制度没有意识到,残疾人的能力在不同时间下、生活中的不同领域往往是有区别的,而这一规律对所有非残疾人也同样适用。”(49)Robert D. Dinerstein,陈博译:《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中的“法律能力”——从监护制度到协助决策制的艰难转型》,载《反岐视评论》(第一辑),第68页。这意味着:医疗上的同意决定行为只是法律行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应当以行为能力某一方面的缺失,而否定其它方面的能力之存在,比如知情同意能力。
其二,在路径方面,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具体评估和鉴定工作,在极大程度上,依赖医疗过程中的医生的主动介入和耐心询问,从而使得医生能够深入了解患者的潜在偏好、价值观和核心信念。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改变了附在残疾这一标签上的无行为能力的法律推定,并要求所有残疾人享有作为人权法事项的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推定,(50)同前注,Jillian Craigie et al.文。确立了“法律能力人人平等”原则,要求成员国以协助决策模式全面取代替代决策模式,最大限度地尊重残疾人的意愿和偏好。(51)同前注,彭诚信、李贝文。亦有学者认为:“痴呆症患者应该被允许在他们有能力的范围内参与医疗决策,即使他们被宣布为无能力的。”(52)Ganzini L, Volicer L, Nelson W, Fox E, Derse AR. Ten myths about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J Am Med Dir Assoc. 2004;5(3 Suppl):263-7.那么,如何进行具体认定呢?可能需要医生具备更高的专业度和更为细致的沟通,“无能力的声明不应否定患者的偏好或愿望。临床医生可以通过在讨论中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帮助缓解由认知缺陷引起的混乱。如果可行的话,医生应该和病人就一个具体的医疗决定进行不止一次的交谈。”(53)S. A. Kleinfeld et al.:The Capacity to Make Medical Decisions,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Issue 145,2019,pp.29-30.
四、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阶段性认定
在实践中,对于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认定分为医疗阶段和争议阶段,分别由医生进行评估和司法裁判者予以判定。
(一)医疗阶段:以医学评估为手段
在医疗阶段,医学评估具有及时性、专业性的特点,能够较为现实的反映出患者同意能力的实际状态,具体而言:
其一,在评估主体方面,宜确定诊治医生评估知情同意能力的权限。诊治医生评估具有现实可行性、及时性与客观性。在现实可行性方面,已有学者指出:这些关于决策能力的艰难判断应该由患者的主治医师做出;常规的精神科会诊或法院介入既不可行也不可取。(54)Thomas Grisso and Paul S. Appelbaum:Assessing Competence to Consent to Treatment: A Guide for Physicians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11.事实上,由诊治医生而非转介精神科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进行评估,“治疗医生的优势可能是更熟悉患者和可用的治疗方案”,(55)Paul S. Appelbaum, M.D.:Assessment of Patients’Competence to Consent to Treatment,November 1, 2007,p.1837.其优势地位能避免引起患者的反感和处境的尴尬,既顺理成章又符合情理。“鉴于有效知情同意的能力要求,评估患者的决策能力是每一个医患互动的内在方面。”(56)同前注,Paul S. Appelbaum, M.D文。可见,身体方面的检查与能力评估属于医疗卫生人员在临床工作中应具备的常规技能,而医疗卫生人员的基本工作事项,包括对患者的心智、意识、思维、情绪、表达力、判定力等方面的检查与观察。在及时性方面,医生的评估能够较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患者的能力状态。患者情况瞬息万变,时而清醒抑或时而昏迷,可能处于意识迷失或混乱状态之间,则需要医生在须臾间作出判断。在客观性方面,为求准确、客观衡量患者的真实状态,在医疗过程中医生的评估鉴定不容缺失。即使事后采取司法认定,仍需进行医疗鉴定,但难以保证鉴定结论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因此,确定主治医生在特定情形下的评估权,既能应对医疗情况的复杂多变,又具有诊断的便利性与专业的可信度。
其二,在程序启动方面,诊治医生评估患者知情同意能力需要遵循必要的启动条件。“有效的同意必须是知情的、自愿的,并且由有能力决定治疗方案的个人提供。因此,在征得患者同意或接受患者拒绝之前,医疗从业者必须评估患者的决策能力。”(57)Ladislav Volicer, MD, PhD, and Linda Ganzini:MD Health Professionals’ Views on Standards for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Regarding Refusal of Medical Treatment in Mild Alzheimer’s Disease,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2003, p.1270.是否必须评估,应以是否达到触发启动评估程序为必要条件。如果患者接受医方的建议或方案,则不是一概需要进行评估,而是当患者提出异议或拒绝时,则需要启动评估程序。这一评估程序的并非自始需要,以首推患者具备同意能力为一般原则。如此,既不会增加医方的负担,又能体现尊重患者权益和操作效率性的考虑。
其三,在实施判定方面,若患者对于常规的治疗方案表示拒绝或异议,需要说明理由,并由临床医学专家鉴定或诊断其精神状况后,就其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进行判定和评估,符合医学上的正常标准的,进入医疗领域的后续就诊及治疗。另外,“考虑到病人的精神状态可能会出现波动,因此他或她的能力水平,以及剥夺病人决策权的严重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病人被认为没有能力的,应该至少在不同时间进行两次评估。”(58)同前注,Paul S. Appelbaum, M.D文。对于那些评估为没有同意能力的情况,需要遵循再次进行核查评估,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二)争议阶段:以司法裁判为基准
在争议阶段,知情同意能力的判定宜遵循如下模式:一般情况下,医疗上的决定能力以“全有”为法律拟制,全面推定有能力为原则,以个案审查作补充。即当患者作出拒绝同意的决定,并且异于一般人的通常选择时,需要考虑启动相应的审查机制,结合个人价值观、个人偏好等进行综合判定其知情同意能力,法院应推定成年人具有知情同意能力。而对于未成年人,在特殊情况下,区分不同的医疗行为的类型,即针对重大性、危险性、侵入性的医疗行为,需要例外考量评估其能力状态。具体应注意以下方面:
其一,当医患双方就同意能力发生争议时,则需要由法院介入进行裁判。我国学者认为:“判断决策者是否具有知情同意能力,需要决策者的沟通能力、理解信息能力、评估与选择能力有机结合,更需要依赖于判断者的‘实践智慧’”。(59)陈化:《生命伦理学知情同意能力问题探究》,载《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可见,司法判断者需要进行综合认定及运用实践智慧予以司法裁定。司法裁定环节可以借鉴和参考诊断过程中的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评估结果及依据,以便洞察医疗阶段患者能力的变化。
其二,医学评估是前置程序和认定基础,司法判定是最终结论和司法确认。在医疗事务这种既有利益切身性又具有高度专业性的领域,尽可能由患者来决定其有关的医疗事项,同时知情同意能力的判定与评估也有赖于医方的深度参与、细致沟通与有效交流。法院在医学评估鉴定的基础上,参考患者本人的知识背景及水平能力、价值判断作出上法律效果的认定,得出最终的法律上的知情同意能力的判断。
结语
知情同意能力因其在医疗领域中所具有的个性化、特殊化的适用情境,宜遵循实时、动态、弹性的认定模式,实现患者知情同意能力的准确定位、精准评估,这既有操作的可行性,又极具人性化与正当性,期待对推进建设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