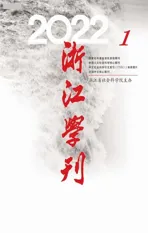披着黑格尔外衣的皮尔士:实用主义内涵之探析
2022-11-17程都
程 都
提要:皮尔士声称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奇怪的方式复兴了黑格尔哲学。通过对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同异)的澄清,为理解前者的内涵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二者共享了两个基本立场:世界之可理解性的基础是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念论,以及世界的发展过程是借由某种中介而产生的连续进程。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拒绝第三性(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足以构成世界,而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拉开了距离。与黑格尔哲学相比,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承诺世界具有的可理解性基础的同时,对绝对理性的范围加以适当限制,并对理性和世界的发展持更开放的态度。
在谈及皮尔士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在古典实用主义阵营中,皮尔士继承了康德,尤其关注理性-认识论问题,杜威则继承了黑格尔,聚焦于历史-经验整体论。国内著名实用主义学者陈亚军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是具有代表性的。(1)陈亚军:《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鸟瞰实用主义的路径分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6年第3期。阿佩尔对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验解读也使得将皮尔士视为康德阵营的观念得到更多的支持。(2)K. Apel, Charles S. Peirce: 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 trans. Michael Kroi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p.ix.皮尔士的文本和相关理论表述也都支持这一普遍看法。然而,皮尔士又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哲学复兴了黑格尔,尽管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尽管穿着奇怪的服饰)。”(3)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18.“实用主义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是紧密的联盟。”(4)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89.鉴于我们当下对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学理上的理解,皮尔士的话似乎会让我们陷入这样一种疑惑:难道我们误解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皮尔士自己的陈述,那么重新考察一下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就是澄清这种疑惑的最好方式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讨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来进一步理解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真实意蕴。
一、“思存同一”的观念论
皮尔士对黑格尔的亲近或许首先始于他们哲学中的观念论倾向。这一点将在我们对皮尔士的观念论内涵的澄清中逐渐得以显明。在皮尔士学界,皮尔士对观念论的主张一开始被认为与其实用主义哲学并不一致,随后又被认为是从唯名论发展到实在论的过渡状态,直到最近一个世纪,学者们才慢慢接受,观念论至始至终都是皮尔士哲学的底色之一。(5)M. H. Fisch, “Peirce’s Progress from Nominalism Toward Realism,” The Monist, Vol. 51, No. 2, 1967, pp.159-178. Lane, R., Peirce on Realism and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9-83.皮尔士曾在前后提出过两种不同观念论论述,二者都与皮尔士所提出的实用主义准则(Pragmaticism Maxim)息息相关。而黑格尔的观念论将为理解皮尔士对观念论的不同论述之间的融贯性,提供一个关键性解释。
首先,实用主义准则是一种方法论原则,目的是澄清一个概念的涵义;该方法同时也是皮尔士所致力于的科学探究(或真理探究)的方法论原则。人们所熟知的实用主义准则被表述为如下形式:
考虑一下,我们构想的概念的对象可能有什么可构想地实际后果的效果,那么我们对这些效果的构想,就是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所有构想。(6)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58.
皮尔士在时隔30多年后解释,为何要在该定义中多次使用“构想”(他用了5个concipere的派生词)一词:(1)他的实用主义方法所运用的涵义对象被限定在“理智意旨”上,(2)为了避免试图用知觉、图式或任何概念之外的东西来解释概念。皮尔士的解释强调了实用主义方法所关注的是可理解性问题,而不是经验证实性问题。此外,皮尔士在后期一再强调一个概念的涵义不在于它现实的效果,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可构想的可能的效果。他将意义的效果由“现实”变为“可能”,将完成时变为将来时,这一点将成为皮尔士实用主义哲学的关键特征之一。
当我们把实用主义方法运用于“实在”这个概念上时,就得到了皮尔士对观念论的第一个主张:实在作为一种独立于认知个体或群体的存在,它事实上就是所有的探究活动无限持续之后所达到的终极意见的对象。(7)C.S. Peirc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Volume 3,1872-1878, ed. C. J. W. Kloesel, M. H. Fisch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8.这就是莱恩(R. Lane)所谓的皮尔士的“基本观念论”(basic idealism)。(8)R. Lane, Peirce on Realism and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0.对皮尔士来说,只要我们的探究活动持续的足够久,最终的实在总会被我们的认知所表征;只要我们对所有实在之效果进行探究,我们终究可以得到关于实在本身的知识。并不存在完全无法被表征的现象背后的“实在”或物自体。皮尔士说到:“这种实在理论立刻就拒绝了物自体这一观念——一种独立于心灵对其概念的所有联系而存在的事物。”(9)S. Charles Peirce, 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 Volume 2,1867-1871, ed. C. J. W. E. C. Moore et 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469-470.就此而言,皮尔士的观念论不是别的,就是主张实在或所有实在之物都是可思的、可为认知所把握的。康德那不可知的物自体和某种先验的范畴,在此被拒绝了;实在并非不可通达,我们通达实在的方法是采取实用主义式的经验探究方案,即通过实在所产生的效果来认识“实在”。
而皮尔士对观念论的第二种论述来源于实用主义方法对“信念”这个概念的运用,以及他宇宙论学说的部分洞见。皮尔士说到:
……实用主义教导说,任何信念作为心灵表象的‘涵义’,都在于它所隐含的行为习惯的特征。(10)C.S. Peirce, The Charles S. Perice Papers, mircrofilm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hotographic Service. With the reference numbers by Richard Robin, Annotated V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MS [R] 318:10-1. (因其文献的特殊性,以手稿编号进行引用;下同。)
其中“习惯”一词是皮尔士对实用主义内涵之阐释的另一关键。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澄清概念之涵义的方法,强调从“可能的效果”来理解某个概念的实际涵义。而所谓的“可能的效果”事实上暗示某种一般倾向(tendency):当某些条件满足时,某个结果就会发生。在皮尔士的宇宙学理论中,作为一般倾向的习惯不仅体现在人类的行为上,还普遍地体现在所有自然物的领域:
我用“习惯”这个词,……指任何持续的状态,不管是人的还是一个物的,这种状态在于这样一种事实——任意一种特定的时刻,人或物都会,要么是肯定会,要么仅仅是可能会,以特定的方式表现。(11)C.S. Peirce, The Charles S. Perice Papers, mircrofilm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hotographic Service. With the reference numbers by Richard Robin, Annotated V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MS [R]673:14-15.
从皮尔士对习惯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习惯”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行为习惯,二是物的行为习惯。而这两个含义背后蕴含的观念是,习惯是一种活动的普遍模式。实用主义方法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模式,才能提出通过效果去理解概念的涵义,或根据行为去理解行为的动机或信念,更进一步地,才能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探究自然界中事件发生的原因。因为不光人具有习惯,所有自然物也具有相应的“习惯”——即它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在一份手稿中皮尔士写到:“只要自然过程是可理解的,自然的过程就等同于理性的过程,存在的法则和思想的法则就必须实际上被视为同一个。”(12)C.S. Peirce, The Charles S. Perice Papers, mircrofilm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hotographic Service. With the reference numbers by Richard Robin, Annotated V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MS 956.心灵和物质本质上是一元的,这就是被皮尔士称为的“客观观念论”:“关于宇宙的一个可理解的理论是客观观念论,物质是退化的心灵,根深蒂固的习惯则成了物理法则。”(13)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6,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20-21.
那么,皮尔士关于观念论的两种表述(基本观念论和客观观念论)有何种联系呢?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立场,基本观念论与承认独立于心灵而存在的实在论是一致,但客观观念论与这种实在论并不融贯。另一方面,有的人将二者视为完全不相关的立场,基本观念论是皮尔士对待认识论的一贯立场,而客观观念论是他宇宙论中泛神论的体现。(14)R. Lane, Peirce on Realism and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0.
本文认为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原则恰好为理解皮尔士这两种表述不同的观念论,提供了一个逻辑融贯的解释。实在本身的可认知性或可理解性正是“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这一命题在认识论上必然推论。黑格尔的观念论正如泰勒指出的那样,不是“笛卡尔主义或经验论者的‘观念’,即作为心灵的内容的观念;而是指同柏拉图的理念形似的东西。”(15)泰勒:《黑格尔》, 张国清、朱进东译, 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这意味着黑格尔的观念论并不限于人类认知心灵,而是使人类心灵得以认知的可能性条件。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观念论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是“精神的现实,是精神在其自己的因素里为自己所建造的王国。”(1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6页。这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就认识而言,是承诺这个世界具有可理解性,或者说承诺一切都是“理性的”;二是就本体论而言,认为世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理性(精神)自身发展的中介或过程,是理性认识自身、实现自身的环节。黑格尔的观念论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通过辩证法阐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并以此驳斥现代哲学的二元分裂。“这种最高的分裂, 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 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 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页。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出来的世界理性形式,既表现在大自然中,也体现在人类活动中(即历史中)。而实用主义方法阐释的“习惯”,也不仅在能动的主体中,也在被动的自然中。因此,皮尔士的两种观念论不过是“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原则”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层面的不同表述罢了。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方法预设了思维与存在(心灵与自然)的同一性原则。而正是基于该原则,皮尔士和黑格尔的观念论都拒斥了康德那不可知的物自体。因为对康德来说,理性只是人类的认知能力,而对皮尔士和黑格尔来说,理性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结构。在这样的观念论体系中,不可能存在不可理解的事物自身。而观念论的本质便是认为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可理解的,也必然是可理解的。对皮尔士来说,实用主义便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最有效的方法。
二、中介化的连续进程
观念论表明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宏观上的亲和性,而通过对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我们会发现实用主义和黑格尔观念论的一个微观且至关重要的共识,也即世界的发展过程是借由某种中介而产生的连续进程。这一发现会揭示出皮尔士实用主义另一个不为人重视的特征——对中介性的强调,同时也将揭示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连续论(synechism)的紧密联系。
有趣的一点是,黑格尔和皮尔士对中介原则的阐述都与其对直接认识的批判有关。黑格尔在《小逻辑》中阐述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三种态度的时候,分析了各种形态的直接知识:对天主的直观认识(耶柯比的信仰),对真理直接的、清楚分明的观念(笛卡尔的我思)等。在黑格尔看来,这些持有直接知识的观点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只坚持孤立的直接知识,而否认任何中介性也能包含真理。但这应该被斥为一种片面的、有限的关系。因为不管是数学理论的产生,还是宗教信仰的拥有,这些过程的“知识的直接性不但不排斥间接性,而且两者是这样结合着的:即直接知识实际上就是间接知识的产物和成果”(18)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真理虽是真的,但它也需要证明自己是真的,真理证明自己的方式便是以自己为中介,而达到自己。这样一种被中介过的真理才是黑格尔的绝对真理。
类似的,皮尔士对直接知识的批判始于对笛卡尔式的直观认识和直观能力的批判。在1868年的“对几种所谓人类具有的能力的质疑” 一文中,皮尔士细致地审查了人类是否可以拥有直接的知识和直观的能力这两点,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提出“除了借助符号,人无法思维”这一贯穿其整个哲学生涯的观点。
在之后,皮尔士基于对符号的理解,给出了一个符号学的实用主义定义:
实用主义最初是以格言的形式被宣布的,……这次则是以直陈语气表述:任何符号的整个智性要旨就在于理性行为的所有一般模式的总和,该理性行为会由于对该符号的理解而发生,并有条件地依赖所有可能不同的情景和欲望。(19)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93.
这意味着,实用主义不仅可以理解为阐释“对象-概念-涵义”或“信念-习惯-行为”之间关系的原则,甚至可以表述为“符号-一般模式-效果”之间相互关联的原则。而无论哪一种都暗示了与黑格尔相同的一个洞见:中介化。对此,皮尔士明确地说到:
实用主义将概念视为一个心灵符号,或在其塑造的对象与涵义之间的中介,或该对象通过概念所能产生的效果之间中介。(20)C.S. Peirce, The Charles S. Perice Papers, mircrofilm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hotographic Service. With the reference numbers by Richard Robin, Annotated Vatalogue of the papers of Charles S. Peirce,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67, MS [R] 320:5-7.
实用主义的三种阐释都包含一个中介化的三元结构:就概念的涵义而言,有“对象-概念-涵义”,就信念的内容而言,有“信念-习惯-行为”,而就符号而言,有“符号-一般模式-效果”。所有三元结构都揭示了实用主义的更根本的观念:意义的阐释、行动的实施以及符号的意指活动都需要“中介”的参与,没有哪一种活动是一种直接被给予的。
实用主义方法指出一个符号的涵义是该符号所造成的所有行为或后果,这事实上也就是皮尔士对符号本性的定义——符号总是指向自身之外的东西,而符号指向他物的方式是通过作为中介的诠释项来实现的。用实用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符号通过某种一般模式来产生特定效果,这种一般模式可以是人的习惯或自然的法则。在这符号三元结构中,符号本身就相当于黑格尔的直接性,其自身不包含任何实质的内容;而行为或效果就是黑格尔的否定,它是对直接性的现实化或否定;习惯或法则就是符号和效果的合题,前两者在此得以统一。也正是在这种中介化的三元结构中,黑格尔和皮尔士同时看到了世界、意识或精神持续发展的不断进程。
在此的连续性不是指黑格尔在谈连续与离散的辩证关系时的连续性,而是其整个哲学所呈现出来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统一性,另一个是整全性。统一性体现在黑格尔对各种二元对立的综合:精神与物质、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存在与非存在、有限与无限等等对子,在黑格尔那里都成了同一主体的不同阶段。就它们属于一个主体而言,是同一,就其本身是对立的而言,是差异,最后统一起来的便是有差异的同一。黑格尔会认为绝对地说来只有一个主体,那就是“绝对”;而其他具体的主体都不过是绝对的不同阶段,这便是整全性——它之外再无他物。而达成这种统一性和整全性的主要手段便是中介化过程,即不断自我扬弃、不断自我发展的过程。通过扬弃的中介活动,使简单的直接性变成了包含间接性的直接性,使得静止的实体成为一个活动的主体;总之,中介性使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而这种发展的因素在“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概念中都可以找到”。皮尔士曾经评论到“宇宙每一处都渗透了连续性的生长”这一点就是黑格尔的秘密,也正是皮尔士赞赏黑格尔的地方之一。在皮尔士自己的哲学中,致力于在不连续中寻求连续,在二元关系中寻求三元关系的就是连续论(synechism)。
而对皮尔士来说,连续性与一般性是同一个东西。(21)例如他说:“真正的一般性就是一种基本的连续性,而连续性无非就是一种完美的关系法则的一般性”。 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6,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117.在连续性内,不同的部分和个体因某个因素(通常是规律性)联结成一个整体,例如“地球上的所有事物都受重力影响”这一观念就将植物、动物和无机物这些不同的个体联系起来了——它们都受重力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皮尔士的连续性是对离散的个体起规范作用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一般的规范法则,实用主义原则才可以起作用,我们才可以通过某个概念产生的行为或效果去理解该概念的涵义。皮尔士关于连续性的论述还揭示了它另一个特征:流动性。在连续性的关系中,一个东西可以脱离它原来的规定,而进入另一个规定。例如原来我们认为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但现在我们认为太阳才是。正如黑格尔所主张的一切具体事物都是绝对发展的某个阶段,没有任何一个具体之物可以静止地保持自身。基于连续性的这种特征,皮尔士会说:“可错论是连续性原则的客观化。因为可错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即我们的知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总是在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连续统一体中游动。”(22)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70.与黑格尔的想法一样,皮尔士也并不将这种流动视为绝对地分裂,而是作为一种向实在(或绝对)的推进。这一进程以皮尔士的符号学术语来表述就是:一个符号带有一个诠释项,而每一个诠释项本身也是一个符号,并以另一个诠释项而指向另一对象;由此,这个意义的链条就可以无限延伸下去,并且最终形成一个网络,直至达到一个终极的诠释项,也即一个绝对心灵(Absolute mind)。可以说,皮尔士是以符号过程来阐述黑格尔用概念辩证法所阐述的进程。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不难理解为何皮尔士会被黑格尔吸引。观念论是二人哲学理论共同的底色,而中介性是他们哲学主张的共同洞见。而在实用主义的符号学定义中,实用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一致的洞见和异曲同工的效果,都致力于揭示一种自我发展的连续进程。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皮尔士和黑格尔哲学在形式上还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即三合一的结构。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一结构与皮尔士的符号三元结构如出一辙;皮尔士本人也明确地将黑格尔思想的三个阶段对应于他的三个范畴。(23)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8, ed. W. Bu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170,194.
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皮尔士在赞赏黑格尔的同时,也有意地强调他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不同之处,并且在他看来,这些不同之处足以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与实用主义区分开来。
三、 理性的限度与开放的未来
事实上,就在皮尔士对黑格尔观念论表示青睐的下一刻,他便说到:
然而,它(实用主义)通过严格拒绝第三性(黑格尔将此降级为不过是思维的一个阶段)足以构成世界,或甚至认为第三性自我就足够这一点与绝对观念论切割开来。要是黑格尔坚持前两个阶段是三合一之实在的独立的或独特的元素,而不是对前两个阶段持有轻蔑态度,那么实用主义者可能已经将他视为其真理的最大的维护者了。(24)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5, ed.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89.
皮尔士这里所说的三个阶段,也即他的三范畴: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皮尔士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他的三元范畴,其中,从本体论上说,皮尔士的第一性指的是可能性或潜在性,第二性指的是个体性或现实性,第三性指的是结合了二者的一般普遍性或必然性。它们可对应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无规定的存在(纯存在),有规定的现实存在(定在),以及具有无限规定的观念或理想存在(自为存在),或者是对应于个体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辩证运动的正、反,以及合题的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皮尔士是在指责黑格尔忽视了他的第一性和第二性范畴,或者说,忽视了理念辩证运动,忽视了初始的可能性和过渡的现实性阶段。
如果说皮尔士与黑格尔在观念论和中介性概念上的共识,揭示出实用主义对世界之理性基础和中介化连续进程的承诺,那么皮尔士所认为的与黑格尔的分歧又会揭示出实用主义的什么特征呢?
(一)无法被穿透的现实个体
在皮尔士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是三种不可彼此化约和还原的基本范畴。它们之间具有不断演进的关系,但是在本体论上,它们具有同等地位。首先,在皮尔士看来,黑格尔对第三性(即概念)的阐述已经非常好了,“但第二性的要素,即硬事实,在他的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25)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 ed.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77.皮尔士的第二性范畴指的是蛮力作用、实存的个体和事实。表面上来看,皮尔士那作为第二性的个体与黑格尔作为否定的特殊性具有相似的特征:(1)都是某种现实化的东西;(2)我们对个体认识都只能是从外在行为或效果而来。黑格尔甚至说出过一段极具实用主义的话:“其实,说个体自在地是什么,不外乎指它的动作行为是什么,而个体所面临的外在环境,也不外乎是它所作所为的后果,并且可以说就是个体自身。”(2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册),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2页。就在这相似性中,却隐藏着二者对个体性认识的根本区别。
黑格尔对个体性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1)个体性是普遍性的现实化;(2)个体化的原则是规定性(或否定性),而规定性本身又是普遍性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个体性的理解,特殊性(即个体性)和普遍性在黑格尔那里才得以统一。因此,按黑格尔的个体性,决定一个个体的是其所具有的规定性,例如决定苏格拉底的是,“男人”“生活在希腊”“善于辩论”“塌鼻”等等一系列属于苏格拉底的属性。但皮尔士并不认为决定个体是其各类一般属性。因为对他来说,一般的规定性是属于第三性(当规定是潜在的时候就是第一性)的,如果个体是由其属性决定的话,那么这相当于说第二性可以还原为第三性;同时,这也将导致三个基本范畴中的第二性范畴变得不再是基本的。而皮尔士的整个范畴理论都建基于三个范畴的基本性和不可相互还原性。如果将规定性视为个体性原则不为皮尔士所接受,那么皮尔士是如何理解作为第二性的个体呢?
皮尔士继承了邓·司各都关于此性的分析。(27)J. F. Boler, Charles Peirce and Scholastic Re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3, p.52.决定一个个体的不是其属性,而是个体独有的此性(haecceitas或thisness)。此性最根本的特点是不可分性和单一性,从认识论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可被概念所把握。同时,皮尔士更清楚地指出了个体另一特征:“它的实存,就其存在而言,不在任何性质中,……人们并不是在对其性质的知觉中认识它,而是在触及其此时此刻的坚持(insistency)中认识它,这就是邓·司各都所说的此性;要是他没说的话,那这也是他一直摸索的东西。”(28)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6, ed.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216-217.可是,这样理解的个体(第二性)会给皮尔士造成严重的困难:个体性似乎从根本上来说成了无法认识的某种东西,或成了物自体。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皮尔士和黑格尔的一个共识之一便是摒弃康德物自体,现在皮尔士自己似乎又将之召了回来。皮尔士要回答的是这样一个二难困境:如何在保持第二性或个体的独立性的同时,又承诺一种普遍的可理解性。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的符号学阐释对解答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洞见。符号可分为基本的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每一种符号都可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征对象。象征符是一种规定,而指示符却不是一种规定,而只是对一种现实存在的不可回避的承认。现实个体之存在可以通过指示符被表征,而不必被象征符的概念所表征。正如波兰学者欧勒斯基(Mateusz Oleksy)所阐释的,“在皮尔士事业的晚期,不可知个体的困境被这一理论所缓解了:一个个体的此性(thisness),不同于其是性(whatness),它是某种我们可以指示,却不能描述的东西。”(29)M. Oleksy, Realism and Individualism- Charles S. Peirce and the Threat of Modern Nominalism, Netherland: John Benjamins, 2015, p.50.因此,皮尔士通过符号的指示作用保留了对个体独特性的通达方式。皮尔士坚持个体的绝对不可分性和单一性,我们普遍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穿透它,因为它的此性只可指示,不可描述。个体属于指示符的领域,而不是象征符的领域。而这种只可指示的此性就现象学上而言,就表现为一种独立于任何规定性的蛮力或抗力。对皮尔士来说,普遍的概念(第三性)所无法穿透个体性的存在(第二性),尽管概念可以以一种中介方式连接不同的个体,但它永远也不能吞并或组合而成一个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尔士指责黑格尔没能给第二性(特殊性或个体)一个独立于第三性(普遍性或精神)的地位。
通过对第二性范畴的强调,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相对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哲学来说,似乎在有意的限制概念或理性本身的范围。尽管一切都是可知的,但是并非一切都是通过概念而得知的。另一方面,将现实个体与普遍概念等量齐观,也让实用主义方法在概念分析之余,更加重视经验性分析,这也即皮尔士一直提倡的科学探究之路。
(二)难以被规定的不确定性
对皮尔士来说,除了来自个体的顽强抵抗,概念或精神的自我发展还有来自偶然性的挑战。第一性范畴所蕴含的绝对偶然性或纯粹可能性使得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皮尔士对黑格尔忽视第一性的指责,首先明显地体现在他对黑格尔自由概念的不满上。
黑格尔说“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着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又是一个全体,这全体中的每一环节都是构成概念的一个整体,而且被设定和概念有不可分离的统一性。所以概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30)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302页。由此,黑格尔赋予了概念三个根本的特征:(1)概念发展完全是自己的辩证运动,并遵循自己的辩证逻辑;(2)任何事物的生存与毁灭都是绝对自身发展的环节;(3)概念绝对地包含一切在内。这其中蕴含着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自在自为地规定”就是概念的自由原则。如果一个东西它包含一切存有,在它之外别无他物,而在它在内又不无任何一物,这样的一个东西难道会不自由吗?从它不可能遭受任何阻碍来说,它当然是自由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是被自身规定的,被其自身发展所规定的,任它无限发展,它还是它自己,它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成就也就是自我同一。“自由正是在他物中即是在自己本身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创造者”。(31)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宋祖良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4年,第77页。起点和终点早已给定,途径如何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或历史的问题。这是自由的,但这同时也是必然的。早在黑格尔的同时代,谢林就曾表示过黑格尔的那种自由——自由即必然——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概念的外化如果这么顺利成章(这么符合逻辑),那么这根本不是自由。(32)王丁:《论晚期谢林“启示”概念的三重内涵》,《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对皮尔士来说,那个“纯零”(pure zero)不是那全然没有任何否定的东西,而是一种无限自由的状态,没有个体,没有主体与客体,也没有规律,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必然地被产生。(33)C. S. Peirc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6, ed. ed. C. Hartshorne & P. We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148-149.这样一种状态是在逻辑之外的,是在理性的辩证运动之外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为之后的概念的发展提供机会(chance)或可能性(possibility)。这样一种完全偶然的领域也被皮尔士称为偶发论(Tychism)的领域。根据皮尔士的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尽管是一种包含内容的逻辑,但是就其本质还是一种演绎的必然逻辑;但皮尔士的逻辑强调一种开放的、猜想的逻辑。逻辑的起点不是一个确定的命题,也不是一个自身就包含结论的前提,而是一个猜想。虽然猜想可以被逻辑所包含,但其本身的存在却是在逻辑之外,或说理性之外。跟黑格尔一样,皮尔士也坚持这个世界是理性的,并且终将被理解;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这种理性的发展不是通过辩证逻辑达到的,而是通过经验的探究。在皮尔士的形而上学中,世界从起点来看,是始于偶然性,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机遇;从终点来看,朝向未来,充满了期待与希望。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的图景相比,皮尔士的探究逻辑显得更加开放和自由。
其次,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对自由和开放性的强调也注定会导致对创造性的重视,而这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强调统一性或同一性又构成一个差别。当黑格尔表示“实体也是主体”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似乎就回答了各种对“黑格尔的秘密”的猜测。诚如黑格尔学者们所指出的,黑格尔对各种现代性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洞察,并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对这种二元分裂的克服和整合。因此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所致力于的是从事物本身的同一与差异来展现事物以及思维的统一。辩证法确实为差异性和同一性提供了很好的统一方案,但是皮尔士看来,这一方案忽视了生产性或创造性。这种生产性不是正反运动就可以达成的,正反运动最终不过达到的是真实的同一(包含差别),但并没有产生真正新的东西,因为一切都不过是精神自身的自我认识过程。而实用主义所持有的开放未来让皮尔士不得不将探索新事物视为哲学的重点,哲学不光要逻辑一致的理解整全,还要致力于去拓展所理解的整全。实用主义的符号观赋予了符号以生长的特性,符号不停地谋求诠释而指向对象,诠释本身作为符号再寻求诠释,如此延伸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便是最核心的动力——任何诠释的拓展都预示着新事物和新理解的诞生。
如果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是一个必然过程,那么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所承诺的世界之发展就是由不确定性驱动的开放过程,因为它不光受到现实个体的蛮力抵抗,还有偶然性的意外参与。对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来说,“绝对”并非是某个囵于逻辑(理性)的东西,而是使一切理性探索得以可能,并自身无限开放的过程。
四、结 语
综上,我们可以说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分享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和中介化的连续性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中的普遍三元结构。这一系列的特征使得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黑格尔哲学表现出极大的亲和性。如果说世界的可理解性、精神的发展过程(自我意识)和宇宙的生成是所有伟大哲学家的共同事业的话,“谢林认为这一切都是通过中立的点之间的颠倒而得来的,而黑格尔认为这是通过辩证法而来的”(34)平卡德:《观念论的遗产》,马肖、陆凯华译,《世界哲学》2015年第5期。,那么皮尔士就是借由实用主义方法,让科学探究持续进行,以及符号的无限生长来实现的。
皮尔士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吸引,并且他最终的哲学旨趣与黑格尔也基本保持一致。但实用主义毕竟不是绝对观念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内涵在与黑格尔哲学的对比也更加明确。在关于自由和未来发展的趋势等论题上,实用主义通过对特殊性或个体性地位的强调,以及对世界之发展的未来持开放态度而与绝对观念论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一方面展现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虽承认世界本质上的可理解性,但并不认为理性本身就可以述说完一切。理性的界限一方面在于承认第二性范畴之现实个体的蛮力存在,另一方面展现在实用主义对逻辑必然性之外的偶然性的强调,这让实用主义拥抱一个更接地气的(可经验的)、开放的、不确定的未来。如此看来,相对于杜威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内化吸收,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确实仅仅是披着黑格尔外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