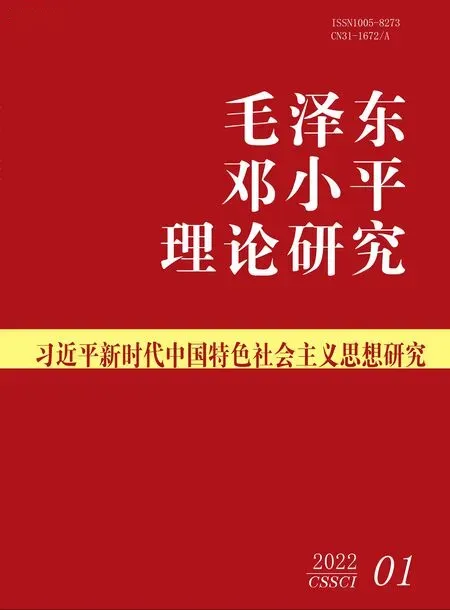乡村文化难题破解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实现研究透析*
2022-11-17任映红
任映红
In Feb.2022,the 19th“No.1 Document”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focuses on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The document emphasizes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of farming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as the value of“cultivating the roots and casting the soul”.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problems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need to be solved: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multiple impacts on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 misconduct challenging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weak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im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etc. The major way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es: meeting the cultural needs of farmers and correct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combining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and paralleling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inheriting and revitalis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novating effective platforms and carrie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civilisation.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第十九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强调“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1]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2]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以惊人的速度趋于消亡,传统文化失去载体,文化建设主体缺位、文化供需失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等,使农耕文化受到多重冲击,造成一系列乡村文化难题。进入新时代,深入探讨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路径,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城市化进程中凸现乡村文化建设难题
“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3](p.25)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也是振兴传统农耕文化的契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战略与新举措,一经提出就成为研究热点,学界或从宏观政策层面,或从中微观角度,对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做了深度解读和研究,如乡村振兴要有三气,即人气、财气、生气;以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目标,应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风尚;要抓住“钱、地、人”等关键环节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农耕文明精华凝聚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更是受学界深度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一是努力探寻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提出要在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重建乡村文明,提高村民主体性和积极性,实现民众自身文化价值的体现和延续;二是提出乡村文化转型的依据与构想,在世界文化转型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变动转型之中的中国乡村文化传承与新创造;三是提出乡村文化转型的依据与构想:从文化生态转到文化心态,从文化实践转到文化自觉,从简单思维转到复杂思考,从节庆仪式转到文化记忆,从孤芳自赏转到大众创造。在文明深处思考乡村振兴,指出“乡村振兴,文化为魂”;四是提出古村落保护与“活化”的方式等;五是指明要通过乡村文化振兴,赋予乡村生活以价值感、幸福感和快乐感,才能激发起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并努力振兴乡村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也揭示了乡村振兴中面临的文化缺失与缺位现象,阐述了不同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意义及实施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三农”问题提供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解决思路。无论政策设计还是现实观察都彰显了文化的力量。面对当前一些农村凸现的文化难题,迫切呼唤优秀传统文化回归重建,发挥“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笔者及所在团队在不同地域的调研中发现了当前一些乡村逐渐呈现出的五方面文化难题。
第一,乡村结构“空心化”,乡村人才“短缺化”,突出表现为城市化狂飙突进,青壮年离土离乡,乡村人口锐减、老龄化,人气不旺;田地撂荒、农业没落;村容沧桑、布局落伍;盲目撤村并居,传统村落快速消亡,故土故园、残存记忆及乡村传统文化正在失去载体,呈现出衰弱凋敝状态。现实中,传统村落呈现两种消亡状态:一种是“显性消亡”:如基层政府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重视不够,传统村落大量被撤村、并村、合村,被实施“村改居”,喜欢按城市小区来搞民房集聚改造,图新图变、一拆了之,原有的延续千百年的村落社会共同体瓦解消失,农耕文化传统无法存续,或苟延残喘或灰飞烟灭,“大量未纳入保护范围的村落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存在‘有乡村没乡愁、有新房没灵魂’的现象”。[4]针对这种现象,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立足村庄现有基础开展乡村建设,不盲目拆旧村、建新村,不超越发展阶段搞大融资、大开发、大建设”,[1]果断叫停乡村的“建设性破坏”“破坏性开发”。另一种是“隐性消亡”:村庄还在,但从物理形态到社区形态,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人口单向流向城市,人力资源短缺化问题突出,农技人才青黄不接,适应农村新业态发展、文化建设的人才严重匮乏,农民教育培训不系统也不及时,“学农不务农”现象突出,农学生不流向农村等,直接造成乡村产业发展滞后,吸纳就业能力弱、留人难。
第二,乡村价值“虚无化”,农民“身份低微化”。乡村具有生产价值、生活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几千年来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农业生产就地取材、自给自足,辛苦劳作中潜藏温暖和诗意,农民有内心的充实和满足,难怪古人会吟诵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熙熙然如登春台,且道承谁恩力”(宋·释智遇《偈颂二十四首其一》)这样充满美好自足寓意的词句。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价值开始“虚无化”。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曾对乡村衰败深感忧虑,都市导向破坏传统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造成农本价值解体,农村农民被遗弃,农民难以在乡村生活中获得价值认同、意义和乐趣,这样会造成中华文明“失根”“失魂”“失血”,农村“文化失调”。他认为应通过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通过文化重建乡村价值和乐趣,来解决农村农民问题。[5]在城市化浪潮中,留守农村务农甚至变成“没本事”“没出路”“保守落伍”的代名词。这种“价值评价落差”对农民心理打击是全方位的,从根本上削弱了农村价值链,让农民的社会“身份地位”日渐“低微化”,精神失落的农民难以从做农活、田园生活中找到价值意义,难以感到幸福安静、自我满足和自豪。部分农民回流返乡,大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不是自愿“叶落归根”。
第三,文化建设主体“虚置化”,文化建设内容“单一化”。体制内的农村文化建设主管部门是县文化局,直接指导管理乡镇综合文化站(以下简称“文化站”)。文化站的基本职能是提供社会服务、指导基层和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与村(社区)宣传文化工作队伍一道,共同构成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然而,一些地区的乡镇机构改革后,文化站常常“有站无人”,工作人员被抽调、借用现象突出;而体制外的文化建设主体(如广大农民、乡贤能人、民间艺人、文化服务志愿者、乡村文化爱好者等)的作用没有得到重视和发挥,文化建设主体“虚置化”严重影响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组织和开展。在农村基层,往往把文化建设理解为“送文化”“放电影”“跳广场舞”,这样的理解片面单一,难以认识到文化建设的责任和作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少,文化场所缺乏、开展活动少,文化人才欠缺等因素,导致农民文化生活贫乏,无处可去、无戏可看、无书可读。行政主导下的“送文化”活动把握农民文化需求不够精准,存在“我以为你喜欢”“我想给你什么”而没有深入调研农民“想要什么”“我能给什么”,文化服务不接地气,农民参与热情不高;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过于“节日化”“商业化”,往往有形无神,常态化的文化活动组织少,一时的热闹繁华过后归于冷清寂寞。
第四,乡土传统文化“断裂化”,乡村道德体系“碎片化”。传统村落文化体系逐渐崩塌,引导约束功能减弱;乡村社会传统价值信仰消解,“守望相助”伦理观断裂;农民原有的人生理念、生活方式、习俗习惯被打乱,引导规范缺位,社会关联度下降,农民伦理共识消减,传统美德丢失,失范行为滋生。如农村出现子女不赡养老人,老人成为家庭的“负资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贫困孤独老人自杀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精神孤寂内心失落,不少人就在封建迷信、宗教活动中寻求精神寄托,有的甚至陷入邪教误区。传统乡村道德体系呈现“碎片化”,加之资本下乡的自负肆虐,独特的“乡土性”日益流失,修桥铺路,水利兴修,无人牵头;红白喜事,贫弱相邻,无人帮衬。天价彩礼,水涨船高,甚至有人因不堪彩礼重负而酿成血案;熟人社会,礼尚往来,但人情风、攀比风越刮越盛,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大操大办,极大加重了农民经济负担。一些农村尤其是城郊接合部、城中村,站街招嫖、聚众赌博、制毒贩毒吸毒,犯罪团伙寻衅滋事、闲散人员聚众斗殴;封建迷信邪教问题沉渣泛起,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治安稳定,影响乡风文明建设。
第五,基层组织“涣散化”,乡村治理“灰色化”。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如有的村委办公室因办公经费不足干脆关门,村主任随身带着公章“流动办公”,各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活动停滞、内耗严重,村干部说话没人听,干群关系疏离,群众满意度低等。一些地方农村基层被有钱有势有劣迹的“社会强人”所控制,“混混”当家,恐吓管制、威逼利诱,在诸如此类“灰色化”治理下,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舆论纠错机制弱化,乡规民约失去约束力。
二、村落共同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功能
乡村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一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之源头和重要依托。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了“共同体”(Gemeinschaft)理论。[6](p.1)“共同体”是自然形成、整体本位的、小范围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大范围的;“共同体”是古老、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现代的。[7]“共同体”是在情感、依赖、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密切联系的有机群体,如亲属关系(血缘共同体)、邻里关系(地缘共同体)、友谊关系(精神共同体)等。[8](p.292)村落是生产生活空间,也是秩序关系空间,更是文化情感空间,其中,农耕文化就是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它以独特的价值规范、道德准则约束行为,维系心灵精神秩序和乡村社会秩序。
中华文明绵延5000余年,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共识和情感归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9](p.313)作为乡土中国的重要载体,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超越单纯的经济考量,对其精神和历史文化价值应给予充分珍视。[4]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注重乡村农耕文化的价值实现、传承活化,应是文化振兴的重中之重。
第一,以文化力量和人力资本等措施助推“产业兴旺”。文化是乡村产业、乡村旅游的灵魂和核心。文化软实力可以转化为经济硬实力。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对“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力量进行过深层思考。习近平把文化的力量比喻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10]产业兴旺需要人力资本,有文化才有乡愁、才有人气,才能培育并留住村落精英、种植大户、大学生创业者、本土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新农人、退伍军人等,吸引农民工返乡回流,兴办产业或拓展新业态。传统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脉流淌、民风质朴,吸引着城里人来文化旅游、体验传统叙事;推动三大产业融合,实现城乡融合;实现公共文化设施共享,追求生产、生态、生活、文化要素的融合;优化地理标志认证,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加大农产品品牌培育,吃得放心、品出难忘的“文化味”;乡村通过“文化联姻”,突破行政区域藩篱,突破传统产业边界、区域空间边界和要素功能边界,让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在村落这一场域内高度关联起来,打造一体化发展的乡村振兴共同体。
第二,以“天人合一”与和谐共生等理念推动“生态宜居”。“天人合一”阐述的是天人关系。《易经》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天人合一,多指人与道合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则将天人关系与治国理政相联系,有天人合德思想,将天地之道内化为人德,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1]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在自然界中,天、地、人各有其道,感通对应、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生态宜居必须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些农村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生活垃圾遍布,农药农膜过度使用等,对环境造成多重夹击;管理不到位,出现“盲区”,容易出现所谓“公地悲剧”。生态宜居重在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提升环保意识,根据乡村自然资源禀赋有选择性地发展经济、文化旅游产业,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在村庄规划、传统村落保护、人居环境整治中,在景观设计风格、建筑空间布局上,用好乡村传统文化遗产,形成民居、道路、农田、山林、水系的和谐共生格局,形成生态宜居、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
第三,以中华传统美德和人伦秩序等主张维护“乡风文明”。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根”在乡村。勤劳节俭、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都是备受珍视的传统美德。习近平强调:“家庭人伦等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农民进城的大迁徙中受到了冲击。这个冲击不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泯灭良知人性。”[12]传统村落文化是以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原生态农耕文化,蕴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培育文明乡风重在塑形铸魂,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3]在当前一些农村地区,道德滑坡,公序良俗失效,给社会埋下重大隐患。维护乡风文明,重在移风易俗,大力倡导敬老孝亲、长幼有序、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守望相助的人伦秩序,勤俭持家、淳朴敦厚、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村规民约”,并以各种形式加以宣传、固化和内化,树立起良好风尚;要净化社会风气,整治黄赌毒、封建迷信,坚决抵制陈规陋习。
第四,以优秀传统习俗和自治善治等方式实现“治理有效”。习近平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3](p.260)费孝通将传统中国称之为“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以农为本,城乡之间没有鸿沟,躬耕陇亩也能怡然自乐,农民淳朴善良,村落自治有序。费正清曾感慨道:“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14](p.21)从村里走出去的乡贤精英愿意告老还乡,有的带回新理念和新技术,有的则以见识学养成为民间权威,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活力和新秩序。乡村要振兴,治理须有效,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3](p.25)“深入开展市县巡察,强化基层监督,……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打击‘村霸’。防范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和影响”。[1]只有着力于重构道德信仰空间,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中的“自信、有序、淳朴”等,才能促进乡村善治。
第五,以美好生活和民生福祉等手段增进“生活富裕”。“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3](p.35)也是乡村振兴的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心理体认、信仰追求,成为体现全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尚书》有关于“五福”的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生活的美好。《礼记》称福为“备”,意思是生活完善。个人完善、天下大同、宇宙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美好生活奠定的三维基础。[15]“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十四五”规划纲要,展望了2035 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美好愿景。创造美好生活、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既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又要“保障物质生活”“增加农民收入”;既要“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条件”,又要“提升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既要“仓廪实衣食足”,更要“知礼节知荣辱”。个人生活富裕、全民共同富裕,是实现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
三、乡村文化振兴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实现路径
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现代价值,积极探索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已迫在眉睫,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满足农民文化需求,纠正文化供需失衡。有效供给的前提是了解需求、满足农民内在诉求,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有: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形成乡村文化空间;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办好乡村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主旋律,坚决扫除黄赌毒、封建迷信、邪教、诈骗等社会丑恶现象,形成乡风文明风尚;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及弘扬,形成文化纽带,“记得住乡愁”;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根据本土文化特色形成特色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需要纠正农村文化建设供需失衡问题,解决好“谁来提供”“提供什么”“怎么提供”“机制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创新”五大问题,提升文化供给的质量效率。一是解决“谁来供给”,塑造一主多元的文化供给主体。在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乡村文化的供给者和消费者基本同体,自娱自乐。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成为文化供给主体、主导力量。为满足农民多层次文化需求,要着力培养农村各类文化人才,形成以政府为主体,村落精英、民间组织、草根民间艺人、志愿者、文创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文化供给体系,避免政府唱“独角戏”“剃头挑子一头热”。二是解决“提供什么”,塑造丰富多样的文化供给内容。目前政府的文化供给多为文化“大锅饭”。随着农民文化需求逐步提升,供给方式需要精确瞄准供给对象,以合适的方式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乃至“小众”的文化需求。目前,农村多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农家书屋的书就要考虑这些群体,多采取接地气的举措。同时,文化有“文野雅俗”之分,扎根生活的传统民间艺术广受欢迎,可以多提供,如南戏、社戏、采茶戏、越剧、黄梅戏、评剧、川剧、秦腔、河北梆子、说书、鼓词、皮影戏,等等。三是解决“怎么提供”,塑造可接受的文化供给方式。传统单向的政府文化供给方式,基本上按照自己的固定模式设计去输出,不太注重可接受性。实际上,文化供给方式要注意可选择性,如文化项目的“菜单式服务”很受欢迎。四是解决“机制如何构建”,使文化供给机制持续有效。创新文化供给体制机制主要包括联动体制:乡村振兴中,文化建设要纳入政府工作和考核指标体系,文化和经济联动;互动机制:政府文化供给体系多提供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提高参与度,形成政府大力引导和群众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激励机制:政府文化直接供给、间接供给和乡村文化自我供给相结合,可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激励乡村文化骨干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能迅速把握、敏感捕捉文化需求信号,文化产业以市场为纽带,及时提供适应农村特点的文化产品。五是解决“制度如何创新”,深化文化制度创新和供给。农村不缺潜力、农民不缺智慧,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去生长发挥。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农民干事创业的热情,迸发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转化和乡村振兴的制度伟力。
第二,继承和创造结合、保护和开发并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价值实现,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一是继承和创造结合。习近平多次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3](p.33)要弘扬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极富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物质和精神、行为和制度多向互动,使思想、情感、利益互促互构,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二是保护和开发并行。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13]对待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应超越被动、静态的保护,在不损害村落整体形态的前提下,重新规划和修缮,完善功能、优化环境,提高宜居程度,使其得到保护性开发、发展性保护。[4]大凡能保存至今,有文化底蕴、有人气、有看头的传统村落,多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名村。如隶属广东佛山的松塘村,是闻名遐迩的“翰林村”。松塘村每年民俗活动多,有正月初四巡游、二月初二土地诞、六月廿四关帝诞、八月十五中秋烧番塔、九月九重阳敬老、孔子诞祭孔奖学庆典、翰林文化节等活动,仪式古老又有新的内涵,不断激励年轻一代读书上进,造福桑梓。保护性开发的传统村落,往往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追寻精神家园,触摸那久远的淳朴厚重的传统文化,感受那通行天地间的真善美。城里人忙于打拼、赚钱、追梦、逐富,但丰裕的物质生活未必能带来心灵的充盈,到远离都市喧嚣的乡村寻找曾经的精神家园,重温传统乡村精神,可以寄托乡愁乡思。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传统民居、宗祠庙宇、村舍炊烟、乡音方言、乡规民约等,都要悉心保护传承。
第三,传承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当前,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传承活化,创新平台载体十分重要。
一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经过几千年积累与沉淀,传统村落蕴含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有物质形态的历史建筑、宗祠、古宅,也有族谱家训、乡规民约、民间艺术、民间传说、民风习俗、非遗文化、节庆文化、祭祀及其衍生文化等。这些文化资源加以合理开发推介,可使沉淀的传统村落文化发挥作用。同时,应当尽量将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进一步品牌化、特色化,吸引更多人进入并沉浸其间,得到更多人尊重和认可。二是推进传统文化活化发展。习近平强调:“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6]“活化”即唤醒(arousal)、激发(excitation),“就是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传承保护中发展创新,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文化表现形式,焕发精气神,提升文化自信”,[17]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又赋予其现代之魂。传统民俗是乡愁的载体,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可以通过工艺体验、创意IP、文化表演、乡土美食、节庆民俗活化起来。三是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乡风文明建设都需要平台载体。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平台开展对象化分众化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创新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源,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1]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准把握当前农村文化难题,开出了治理“药方”。在乡村文化平台建设方面,全国各地有许多探索,如浙江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分批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至2021 年4 月,全省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7804 家,500 人以上的行政村覆盖率已超过90%。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已拓展到70%的县(市、区),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5万余个”。[18]又如,广东全省涌现了“粤书吧”、智慧书房、读书驿站、“邻里图书馆”等1900多家新型阅读空间或文化空间。[19](p.289)这些举措使千家万户得到文化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文明素养。
面对当前一些农村地区存在的诸多文化难题,要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载述历史,承载乡愁情缘,传承文脉,使其担当起耕读传家、道德教化、文化教育、凝心聚力的重任。全社会要形成共识,共同守护传承、弘扬转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实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田野沃土滋养而枝繁叶茂,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厚重底色,永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