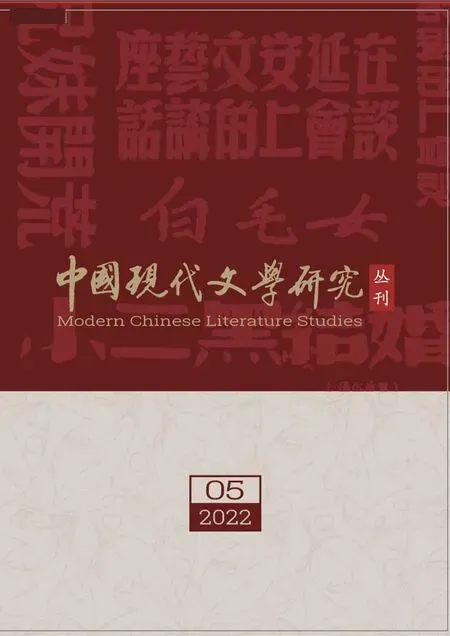“置身”的探寻:现代中国游记文体观论析※
2022-11-16苗帅
苗 帅
内容提要:游记将作者在现实世界中基于“身体—主体”的“置身”经验作为一项基本要求,对弃置身体以试图深探纯粹精神或与之相反将身体对象化的文学观构成挑战。现代中国游记文体观在晚清、1930年代前后、新时期以来等关键时期各具特质和新质,人们关注的往往不在“游记何谓”,而在“游记何为”,因此现代游记文体远非一项文体论题,而是一种思想论题。以“置身”的游记文体哲学为轴心,将有助于理解诸种现代游记文体观的生成逻辑及其是非功过。
晚清以降,朝廷遣使和有识之士自发的域外之游成一时之盛,域外游记由是蔚为大观;与此同时,国内交通亦渐发展,及至民国已颇可观,“纪游之书,所出日多”。①周钟岳:《旅行江浙直鄂日记·序一》,陈秉仁:《旅行江浙直鄂日记》,昆明市立职业中学校商科实习商店1928年版,第1页。悠久的游记传统和充满新变的现代环境,使得现代游记散文一方面固守着游记文体的根本特性,另一方面更趋多元的游览方式则不断开拓着游记的题材、样式和文体功能。然而,“游记何谓”始终言人人殊,这既源于游记自身携带的某些特性,也与现代以来的思想变迁以及文学场中的观念博弈息息相关。
一 “置身”:游记的文体哲学
现代作家虽有大量“游记文章”,却对“游记文体”时有贬抑。如《赤都心史》实为纪游之作,瞿秋白却着意声明不可以游记视之:“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①瞿秋白:《赤都心史·序》,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2~3页。几年后,杨钟健的游记《去国的悲哀》出版,王德崇亦序之曰:“本书的作法与普通的游记略有不同,普通的游记常是一种起居注式的日记,取材但求其详细而不加以客观的审择,此书则在各种事物之中,抽精撷华,其关系重要者无不赤裸裸的描写出来,其关系个人日常行止者则所述甚少。”②王德崇:《去国的悲哀·序》,杨钟健:《去国的悲哀》,平社出版部1929年版,第2页。两人均将“普通的游记”视作枯燥平浅的记录,而对游记文体的“成见”实则大不相同。对瞿秋白而言,游记文体的枯浅在于无法抵达自我内在真实,以留下一份“心理记录的底稿”;在王德崇看来,游记文体的弊陋反而在于视角总限于作者己身,难以进行“客观的审择”。如果说瞿秋白认为游记不过是通讯式的记录,王德崇将游记与“起居注式的日记”约同,那么梁启超对游记文体的认识则更趋近于山水记和亭台记——这种认识符合更多人的印象。他在《新大陆游记·凡例》中称:“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自己则在书中将此类“无关宏旨,徒灾枣梨”③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1页。之言悉数删去,凸显其与传统游记的不同风貌。
不难发现,上述三人虽然对一般的“游记文体”均有微词,但彼此的“游记文体观”大相径庭。这些关于游记文体的驳杂印象,究其实质是不同的人将游记诸种不同的“可变因素”——如起居注式的顺时记录或山水记式的模山范水等——误作识别这一文体的不变要素。米哈伊尔·格洛文斯基的说法颇具启示性:“不变因素是鉴别体裁的必要因素,可变因素属于可能性因素,它们之间的合作并非心血来潮或出于偶然;正是这种合作关系决定着体裁的运作方式。④米哈伊尔·格洛文斯基:《文学体裁》,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修订版),田庆生、史忠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页。”这提示我们,一方面应当尽可能确定游记文体的那些不变因素,正是此类因素标识了游记存在于“文体之林”的独异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这些南辕北辙的游记文体观也不应一哂置之,它们提示了读者在此类文体作品的阅读中往往真正关心以及作者常常倾注更多心血的内容。
关于“不变因素”,目前人们基本达成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以游踪、游观、游感作为界定游记的三种要素。稍有差异的是,人们对三要素的命名尚不统一。冯光廉以“游踪、景物、观感”称之:“一篇典型的游记,应该包括游踪、山川景物的描写,游人的观感等内容。”①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8页。并在分析康有为的《奈波里》时明确以此为辨体标准,称其“在写法上完全合于一般游记的规范,游踪、景物、观感三要素皆备”②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8页。。王立群的观点也是:“游踪、景观、情感是游记文体的三大文体要素。”③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与冯光廉的命名方式基本一致。稍后,梅新林、崔小敬在《游记文体之辨》一文中则采用了“游程、游观、游感”的说法,虽然根本上与冯光廉、王立群等人的观点一致,却增添了一层更为自觉的认识:“根据游记由‘游’而‘记’、以‘记’纪‘游’的文体特点,当以游程、游观、游感加以概括更为妥贴。”④梅新林、崔小敬:《游记文体之辨》,《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这一细微的认识增进对辨体实践却有实际意义。
以余秋雨散文的文体性质为例,《文化苦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散文集有时被视作当代游记散文较具代表性的作品。特别是在刘锡庆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中,新时期以来大陆游记散文作家仅列两位,即贾平凹和余秋雨。⑤刘锡庆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454页。然而余秋雨散文的文体归属尚需进一步讨论。如果以游踪、景观、情感三要素而论,余秋雨此类散文的确三者兼备,但这些文章又与人们对游记文体的一般印象存在出入。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中勾勒出余秋雨散文的一种基本模式,即“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⑥朱国华:《别一种媚俗——〈文化苦旅〉论》,《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朱文本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但这一模式的归纳基本符合实情,特别是提出“故事”这一首要因素,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那种文体印象偏差产生的原因。从具体文本来看,如《柳侯祠》一文两处述及游踪,一处是开篇“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一句,另一处是临近篇末时叙写“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及所见。⑦余秋雨:《柳侯祠》,《收获》1988年第5期。此外则是对柳宗元故事的铺叙和感喟。如果抽离两处游踪叙述,整篇文章会是一篇独立的历史人物随笔,且完整文意亦无删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作者的实地游览活动,依然可以完整成文。《道士塔》中有一句:“我见过他的照片”①余秋雨:《道士塔》,《收获》1988年第4期。,这构成了余秋雨散文写作的一种基本隐喻,即他的目光聚焦于某种历史“照片”,而非主体的“游”中所见,这意味着作家的现实游踪与文中展示的“观”“感”呈现出断裂状态,“观”并非“游之观”,“感”亦非“游之感”。因此,余秋雨的散文根本上属于历史随笔而非游记,与其说他的作品扩展了游记的边界,不如说是扩展了历史随笔的边界,即作者通过“身临其境”来完成史话叙述。人们对余秋雨的批评往往关注其史实谬误,也从侧面表明历史故实才是余氏散文的命脉所系。对余秋雨散文文体的辨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游记”文体的边界;同时也提醒我们游记的三要素为什么有必要采用“游踪”“游观”“游感”的表述,而非泛化的“游踪”“景观”“情感”。换句话说,游踪不仅是游记三要素之首,而且是轴心,对游观、游感具有直接的生发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游记文体的独异性在于必须将作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游历活动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游”作为一种行动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项核心标准来整合一种文体,是因为其自身独具的意义空间,它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身体向陌生领域的开拓来生成新的“置身”经验。“置身”经验的力量在于,它一方面对抗着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分并试图探索纯粹心灵而将身体弃置一旁的观念,另一方面区别于那种将自我或他者身体视作一种被安置于客观空间中的物质性存在的认识。
换句话说,只有借由“身体—主体”,空间才能被重新激活。所谓“重新”,意在强调让这一次体验构成的空间从上一次体验构成的空间中解放出来。落实到文本现象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大钊八游五峰山,先后作有《游碣石山杂记》(1913年)、《五峰游记》(1919年),两篇游记不仅环境、心绪不同,游观、游感各异,甚至语体上也经历了由文言到白话的变化。
由此也可以发现,“置身”不仅包含一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一组身体与时间的关系。而后者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前面提到的两种形态的“重游”,无论是不同的人还是同一个人,不同时间里的身体均各自独异,这些差异性身体在同一区域里的“置身”活动不会生成相同的体验,也因此,游记写作的可能才会在有限的实存区域空间中释放出无限性。
第二个层面是,在一次的游历中,不断位移的身体在不同时刻上生发出的体验,构成了一段游程中体验的集合。此类散点体验在付诸书写时,往往使游记文章以某种顺时的方式加以结构,其中又以日记形式最为常见。俞樾对以日记为游记的体式定型过程曾有扼要的梳理:“文章家排日纪行,始于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然止记登岱事耳。至唐李习之《南行记》,宋欧阳永叔《于役志》,则山程水驿,次第而书,遂成文家一体。”①俞樾:《栈云峡雨日记·序》,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第1册,重庆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应当说明的是,以日记为游记的文体交互不只是一种经验性的传统,究其实质这一现象根植于“置身”的时间之维。1936年,钱公侠和施瑛曾选编日记和游记作品,合为一册《日记与游记》,这次编选实践再次印证了为游记文体与日记文体划出明确界限本身就是一项不切实的工作,编者解释:“本篇中的材料,有许多不能够分出究竟是日记还是游记,因为纪游的文章,有的以日月为经,以地方为纬,硬为分排,实在何必多此一举。比如胡适的《庐山游记》、郁达夫的《西游日录》全是这样的东西。”②钱公侠、施瑛编:《日记与游记·小引》,启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郁达夫采用日记体纪游实际正是出于一种文体上的自觉,他曾表示:“游历的行旅者,遇到了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要想把眼前的印象留下,可以转告他人,并且日后也可以唤醒自己的追怀,记日记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③郁达夫:《再谈日记》,《文学》1935年第5卷第2号。这意味着,将日记与游记联结在一起的,不仅是排日记事的缀文方式,其内源性动力,正是这一“把眼前的印象留下”的初衷,或说对于个体经验真实性的维护。而在游记散文那里,正是“置身”这一基本要求,塑造了那种真实性,这会使我们想起梅洛-庞蒂说的:“体验揭示了在身体最终所处的客观空间里的一种原始空间性,而客观空间只不过是原始空间性的外壳,原始空间性融合于身体的存在本身。”④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6页。我们在此申述的“置身”过程,实质上也正是这样一个不断去蔽的过程。
二 “置身”的有效性问题:晚清域外游记的限度
晚清域外游记因深刻联结着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实践,后世的基本评价多取其正价。但细究具体的游历活动和游记写作,人们却往往难以真正满意,症结在于外游者“置身”经验的有效性问题。周作人和钱钟书先后指出了问题的两个方面。1935年,周作人在批评王韬的《扶桑游记》时认为:“他自己只是‘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别无一点关心。”①周作人:《王韬的酒色烟》,《益世报·读书周刊》1935年7月4日。他的不满在于,王韬虽身居文明之邦,耳闻目见、持笔成书,而行为思想仍不改名士派其旧。周作人对游记作品价值的评判标准无疑是严苛的,在他看来,有效的“置身”经验应当达致思想的新变,成为内在自我革新的契机。如果说周作人为“置身”经验的有效性设置了一条高线,那么钱钟书则谈到了一条底线,即在陌生环境中的游历者、考察者能否真正看懂并如实描写情事本相,而晚清域外游记显然有诸多内容低于这一底线。钱钟书指出:“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吹捧自我,所写的旅行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谈》——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②钱钟书:《〈走向世界〉丛书序》,《人民日报》1984年5月8日。
影响晚清域外行旅者“置身”经验有效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过去的游记写作中一个颇为罕见的困境成为此时域外游记作者集体面临的问题,即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作为传统游记表现对象的山川风物或风土人情,而遭遇了一种更高级别的且具有对抗性的文明——这一经验以及由此带来的自卑心态对于古代中国的域外行旅者几乎前所未有。徐勤劝告梁启超勿为游记的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凡游野蛮地为游记易,游文明地为游记难。子以尔许之短日月,游尔许之大国土,每市未尝得终一旬淹,所见几何?徒以辽豕为通人余笑耳。”③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凡例》,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1页。所谓“野蛮”“文明”不过是相对而言,参照系是自己所处环境的文明程度。正是在这种势位结构中,才有了恐“以辽豕为通人余笑耳”的敏感心理,这种担忧本身不无道理,说到底,这是对身处落后文明的国民——包括上层知识分子——是否有能力真正理解先进文明的怀疑。除了主观的理解能力,“以尔许之短日月,游尔许之大国土,每市未尝得终一旬淹”的客观限制也影响着游历者的认识。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国至外洋者未始没有像容闳那种浸透于西方文明的人,为何仍“所记述浅率居多”?①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2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容闳或其他久居域外的学习、生活者,记述见闻并非一项必要的任务。因此迟至1909年,容闳才以英文写出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其中虽缕述早年赴美见闻,但一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记而只是追述生平的回忆录,二来也并非以中文写作、意在供中国人参考的指南。而由官方派遣的使臣,虽然只能作走马观花之游,却有记录程途的义务,因此留下大量考察游记。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薛福成就在上报总理衙门的咨呈中表示自己即是按照“贵衙门咨行‘具奏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一片”的要求,“一路访察外洋各埠情形,随所见闻,据实纂记”的。②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9、63,63页。应该说,正是“随时记载”的政治任务及日记咨报制度直接催生了当时大量详细记录在异域见闻、起居、事务的出使游记。有意味的是,日记咨报制度的确立距离郭嵩焘《使西纪程》毁版事件过去仅半年,这提醒我们,官方主导的游记写作及呈报一方面出于清政府及时了解各国事机的需求,另一方面强力的意识形态作用也压抑着对于“置身”经验的有效书写。
除了日记咨报的制度因素,晚清域外游记写作的内源性动力则来自传统士人的“立言”理想和“日知其所亡”的修身道路。晚清域外游记作者对自家游记的文体认识常与“日知录”联系在一起,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凡例》中自述:“窃谓排日纂事,可详书所见所闻;如别有心得,不妨随手札记,则亭林顾氏《日知录》之例,亦可参用。”③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9、63,63页。载振的《英轺日记·凡例》中也称:“是书仿黄氏《日钞》、顾氏《日知录》体,纪事之馀,稍参论议。”④载振:《英轺日记·凡例》,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页。无论是薛福成游记还是载振游记,就体例而言都明显与顾炎武《日知录》相去甚远,相合处大概只在“纪事之馀,稍参论议”的一般写法和文章经世的精神底色。清末向国初经世思想的反顾一如王国维所言:“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⑤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文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页。作为桐城派“中兴”人物的曾国藩在“考据”“义理”“辞章”的桐城家法外又增一“经济”,对朋辈和后生都产生重要影响。而彼时人们对域外游记文体功用的学理性认识,即由这一脉络生发而来。在奉派出使并撰有游记的官员中,后期桐城派理所当然地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曾纪泽以及为载振作《英轺日记》的唐文治等均属此列。
如此,晚清域外游记这一充满新质的文类被平稳地安置于传统学术和士人精神的延长线上。应该说,作为传统学术的内部变革的桐城派“经济”思想,为书写异质文明、蕴含着借由外部文明变革内部文化潜在力量的晚清域外游记提供了学理支撑,与此同时也规定着外游者(主要指官方遣使)“置身”经验的精神限度,或说理解异质文化的思想“前结构”。
三 “置身”选择与文体政治:小品游记与报告游记的观念博弈
1930年代前后关于游记文体的言说与实践,成为不同文学观和政治观博弈交锋的象征性符码。言志思潮主导下的游记文体观以小品文为游记正体,与此同时,左翼人士则有意将新兴的报告文学树立为游记文体的理想样态。择取自我精神为“风景”的小品游记和择取“社会相”为“风景”的报告游记,在不同的“置身”方式及其书写的选择中,前所未有地开拓出游记的文体政治意涵。
1957年,沈从文为《旅行家》杂志作《谈“写游记”》一文,表达了自己对游记文体的基本看法:
“文以载道”,在旧社会是句极有势力的话,把古代一切作家的思想都笼罩住了。……个人文集,也总是把庙堂之文放在最前面,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①沈从文:《谈“写游记”》,《旅行家》1957年第7期。
所谓“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未必符合实情。实际上,游记散文历来是中国古代散文中数量颇丰、成就极高的门类,柳宗元之永州八记、苏轼之前后赤壁赋、徐霞客游记、晚明游记小品、桐城游记古文,不仅是游记文的代表,几乎也同时展示了中国散文的主要成就。①这里使用的“散文”概念指现代文体观念中的“散文”。而这些游记作品历来在散文史上获致的评价,恰恰提醒我们:“‘文以载道’的主流文统”往往无法彻底地“把古代一切作家的思想都笼罩住”。沈从文有失公允的论断显然基于文学革命以来反对“载道”的现代文学观以及后来周作人提出的“言志—载道”二元文学史观。
游记被当成一种“言志”的文体须与小品文的发展结合来看。1945年周作人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忆及1922年在燕京大学教授国文,“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②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5页。,并将胡文作为“说理的序文”的代表,俞文则作为“叙景兼事的纪游文”的代表。③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4、65页。但需要指出的是,俞平伯《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作于1925年4月13日,不可能在1922年讲授。周作人的这一记忆失误颇有意味,他在回忆中对《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有意或无意的抬升,实际联结的是关于小品文的言说。1925年5月4日,也就是写作《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的半个多月后,俞平伯致信周作人,表示收到对方寄来的《文饭小品》一书。《文饭小品》是晚明王思任的小品集,其文公认以游记最佳。俞平伯在信中略谈了一些体会,基本也是就其中的游记文展开:“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雁宕小记’起首数语,语妙天下。非此不足把持游‘雁宕’之完整印象。读此冥然有会矣。”④俞平伯:《致周作人》(1925年5月4日),《俞平伯全集》第9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可以说,周作人在俞平伯游记中看重的,正是俞平伯激赏王思任小品中的“明人风姿卓越处”。
1934年周作人又具专文谈《文饭小品》,与周氏同期的很多文章一样,此篇也是向被他称为“载道派”的左翼人士进击的文字,并且在文末明确了这一意图:“盖王谑庵与此载道家者流总是无缘也”⑤周作人:《文饭小品》(续),《人间世》1934年第10期。;此后周作人在论“游记最有新意”⑥周作人:《重刊〈袁中郎集〉序》,《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1月17日。的袁中郎小品,乃至论清人舒白香《游山日记》的“闲情”⑦周作人:《说闲情》,《宇宙风》1935年第4期。与“私人的思想性情”①周作人:《风雨谈·游山日记》,《宇宙风》1936年第8期。时,也都是基于这一“言志—载道”的二元框架。而在二十年后的新中国谈论游记文体的沈从文,其基本思路沿袭的仍是这一话语资源,可谓静水深流。而沈从文认为古人将游记“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也正是因为选择性地将晚明小品一类的游记,而非桐城古文一类的游记视作游记文的主要形态。
提倡小品文几乎无法绕过游记文体,这只要翻看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就能发现,被言志派视作近代文学之始的明人小品,大多都是纪游之作。阿英在分析1934年的文学动态时也指出游记文与小品文的伴生现象:“伴着小品文的产生,一九三四年,游记文学也是很发展,几乎每一种杂志上,报纸上,都时时刊载着这一种的文字。就已经编印成书的说,主要的已有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巴金的《旅途随笔》,郑振铎的《欧行日记》。”②阿英:《小记二章·游记文学论—— 一九三四文学小记之一》,《海市集》,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33页。
阿英提到的三人中,在游记散文创作方面,尤以郁达夫为世所推崇。可以说,1930年代之所以被认为是游记的全盛时代,除了作品数量可观,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以郁达夫游记为代表的、能够显示现代游记散文风貌的作品。郁达夫彼时有“游记作家”之称,同在1934年,郁达夫登休宁白岳山后有诗四首,第四首写道:“养生无物只烟霞,游记居然号作家。一事堪同坡老比,我行稍过浙西涯。”③郁达夫:《登白岳齐云仙境,徘徊半日,感慨系之,因不上黄山,到此乃西游终点也》(四首之四),《民国日报·越国春秋》1934年4月11日。郁达夫提醒我们,他是将自己的游记放在以“坡老”苏轼为代表之一的游记传统中看待的。更具体地说,郁达夫是将自己的游记归入小品文之列,在1933年的浙东之旅前,他在给钱歌川的信中告知:“我不日将去杭江路一带游行一次,小说做不出,或可为写一点杂感游记之类的小品。”④郁达夫:《致钱歌川》(1933年11月5日),《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这“杂感游记之类的小品”便是四天后从启程之际就开始动笔的《杭江小历纪程》以及稍后所作的《浙东景物纪略》。次年,郁达夫在《屐痕处处·自序》中又有相似的自白:“我的每次出游,大抵连孙文定公那样清高的目的都没有的,一大半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因而写下来的游记,也乱七八糟,并无系统。”⑤郁达夫:《屐痕处处·自序》,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2页。虽然言辞自谦,实际也是将自己的作品区别于“赋得的文学”,而归入“即兴的文学”。虽然郁达夫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存在明显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却基本相契,这种契合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尤为鲜明地体现出来。郁达夫称:“袁中郎集的不见流传者(乾隆中被禁毁),当然又是清初馆阁诸公的袍巾头巾,在那里作梗。”与周作人倡晚明小品、反对“方巾气”可谓同声相应。又说:“至于公安一派在文学上的革命功绩和历史,已有周作人先生提倡在先,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说。”①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人间世》1934年第7期。更可见周氏的直接影响。
可以看到,1930年代前后游记小品的兴盛主要是在彼时兴起的言志文学思潮下发生的。以周作人为首的言志派作家借用晚明资源并掀起晚明小品热,纪游作为晚明小品的重要主题,使得游记成为言志文学思潮中一种特殊的文体资源。其影响力辐射蔓延,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游记小品创作,更重要的是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游记文体观,这从当时郁达夫关于自己游记创作心态的言说中可以见出,也是为什么后来沈从文会得到一种与文学史事实存在偏差的印象,即游记因疏离了“载道”文统而“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
小品式游记的赓续发展很快招致左翼人士的批评,穆木天出言讥讽:“现在,想以小品文统制一切文艺者有人,抄古书作文言者有人,与之成为三位一体的,就是游记之盛行。”穆木天实际并非反对游记文体本身,“主要地要看现在的游记中,所反映的是什么,什九,怕不是江上的清风就是山间的明月,游记中作详细的社会生活之描写的,怕是少数”②原刊作:“……所反映的是什九,什么,怕不是……”系误排。。但面对这一现象,穆木天还是干脆主张不必再写游记:“我们似应当把写游记,作自传,抄古书,等等的工夫,拿出来给中国介绍翻译点世界文学名作。”③穆木天:《谈游记之类》,《大晚报》1934年6月21日。
与穆木天将游记视作一种已经被污染的文体而直接放弃不同,茅盾的策略则是争夺游记这一文体资源:“我们也要写游记。我们要用满洲游记、长城游记、闸北战墟游记等等来振发读者的精神。”④茅盾:《关于小品文》,《文学》1934年第3卷第1号。阿英对此也持相同意见,“要求‘新的游记’的产生”⑤阿英:《小记二章·游记文学论——一九三四文学小记之一》,《海市集》,北新书局1936年版,第136页。。所谓“新的游记”,即在游记中确立新的表现对象,将传统游记中的自然风景改变为“社会相”①“社会相”一语可参考举岱的《游记选·题记》:“古人旅行,山轿蹇驴,竹杖芒鞋,时时刻刻都拥在自然的怀抱中,所以感觉最亲切的是自然,体味最深刻的也是自然,游记最好的题材便只有自然风景。现代人的旅行却不同了,凭借轮船火车的便利,走遍各地各国的都市;而在大都会中,人的活动常淹没了自然,于是‘社会相’又代替了自然风景成为游记最好的题材。”文化供应社1942年版,第5页。的现代风景。这样的声音在当时颇为盛行。孔另境在《游记种种》中也主张:“此后的游记应该把范围扩大到社会的游记方面去,那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类游记了。”关于这“扩大到社会”的“第三类游记”,他补充道:“这种职业的游记——其实是视察报告——现在正在发达起来,在报章杂志上不断地看到这类文字的登载,这是很可喜的现象。”②孔另境:《游记种种》,《申报》1935年6月19日。这里所说的“在报章杂志上”不断出现的“视察报告”是指当时正在兴起的报告文学。而茅盾要人们作“满洲游记、长城游记、闸北战墟游记等等”,也正与他对报告文学的倡导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概念,很多符合“报告文学”特点的作品最初都只属于另一种文体,而游记又是报告文学先导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1930年陶晶孙翻译中野重治《德国新兴文学》一文,首次使用“报告文学”这一汉语译名,并且出现在这一句子中:“刻羞③即捷克记者、报告文学家基希。可说是新的型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有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④中野重治:《德国新兴文学——简略的解说》,陶晶孙译,《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这里已可窥见“随笔纪行”在报告文学行列中的重要位置。对中国报告文学理论起步有着重要影响的另一位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川口浩则对报告文学与旅行记、风土记的关系展开了更详细的阐述:
近代的散文,最初以旅行记及风土记的形式而出现,以后几经变迁而至今日。在此,我们应得注意散文这种文学形式,在它产生的当初,已经带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的色彩。譬如在德国,一般的被认为德国近代的散文之滥觞的海涅的《旅行记》,曾以辛辣的笔锋,批判了旅行所及的地方的人物和制度等等。可是后来散文这种形式占有了支配的地位,形式的本身接近了完成的领域,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却了最初之特征的社会批判的特质,现在,以这种被近代的散文遗失了的精神而再生的,就是所谓报告文学!⑤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也就是说,散文中那种着眼于现实社会的旅行记和风土记,正是报告文学的生根之处。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以及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这类游记后来也均被追认为报告文学作品,并成为报告游记成果的重要“形象展示”。
应该说,言志派强调“自我精神”表现与左翼偏重“社会相”再现的两种“置身”经验书写立场,在游记文体观上最终落实为小品游记和报告游记的文体之争。这与其说是文学实践的差异,不如说是理念设计的博弈。此间真正的问题已溢出“游记何谓”,而指向“游记何为”,由此空前地拓展了游记文体本身的观念负载能力。
四 “置身”新变与多元游记观:“旅游文学”与“文化游记”
无论是“走向世界”还是通往无人涉足之地,现代工业都使行旅者的游踪以不可思议的程度延长了,钱歌川说:“近百年来所谓天险,大都被机械文明所克服,轮船、汽车甚至飞机几乎无往不利,于是乎秘藏在四川的名山大川、古代遗迹,我们也常有机会去领略浏览,或凭吊了。”①钱歌川:《四川之行·序》,葛绥成:《四川之行》,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1页。应该说,近代以来游记文学的发展根本上源于这种出游方式的变革。
192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独立为中国旅行社,成为首家国人自办的商业旅行社,此举标志着中国现代旅游业的真正开端,中国第一份旅游刊物《旅行杂志》也于同年创刊。杂志延请包括张恨水、郁达夫、胡适、秦瘦鸥在内的诸多名家撰稿,意在以文字促进商旅。与现代旅游业息息相关的游记文字开始在这份刊物上源源不断地涌现。但此时尚未出现后来所谓的“旅游文学”概念,这个词汇迟至1980年代才随着当代“旅游热”逐渐兴起。当然其首要价值并非借之创造新的文学体类,而是用以开发新的旅游资源。
“文化散文”与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两个概念有高度重合性,因此人们有时也以“文化大散文”称之。1992年贾平凹在《〈美文〉发刊词》中首倡“大散文”,旨在“扫除浮艳之风”,“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②贾平凹:《〈美文〉发刊词》,《美文》1992年第1期。这一主张源于对日益脱离现实精神的文学趋势的不满,因此其所呼唤的“大”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正需以更广袤的天地以及由此开拓出的更开阔的历史襟怀、现实视野和生命体验作为支撑。以此为基础,1999年《美文》又标举“行动散文”,更加自觉地将“行动”与“大散文”理念的构筑相联系。黄宾堂、龙冬在具有宣言性质的《让散文行动起来》中倡导走出书斋的“户外生活”①黄宾堂、龙冬:《让散文行动起来》,《美文》1999年第1期。。对此人们不免疑惑:“行动散文是不是新游记?”另一位发起者穆涛明确否定了这一看法,在他看来,混同两者乃是对“行动散文”遗神取貌的误解。②穆涛:《稿边笔记:再谈行动散文》,《美文》2001年第9期不过,与前述瞿秋白、杨钟健等人对“游记”概念的贬抑不同,穆涛并不拒斥“游记”。他对游记的认识几乎不附着价值色彩:“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有了想法和心得,记下来就叫游记。”③穆涛:《稿边笔记》,《美文》2005年第5期。然而也正因游记范围的宽泛,它与“行动散文”不免有无法交叉的部分,这主要表现在“游记散文的写作主体可以是一个贵族。他可以乘飞机坐豪华卧车住高级饭店,去抒发高贵的农家乐或是田园风光之类轻飘飘的情感。‘行动散文’作者的行动本身就应该与下层人一样,去吃苦尝酸,去披肝沥胆,去流泪流血”。④杨爱平:《“行动散文”与散文行动》,《当代文坛》2003年第2期。
实际上,黄宾堂和龙冬对“行动散文”所要求的“户外生活”早已有明确界定,即“用田野的方法接触自然和实际”。此间渗出的模糊的人类学意识,在马丽华那里则十分明晰,她称《西行阿里》“起因和结果都归结为与人类学家们一次愉快的旅行”,《灵魂像风》中“观念的变化的表现是,无师自通地具有了影视人类学的意味”。⑤马丽华:《西行阿里·修订版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格勒是与马丽华同行阿里的“人类学家们”中的一位,他为马丽华冠以“人类学散文作家”⑥格勒:《西行阿里·序》,马丽华:《西行阿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之名,并在这一意义上将其置于摩尔根的流脉上看待。⑦格勒:“今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已成了我们了解昔日印第安部落民族的必读书。此时此刻人们多么希望多有几部像《古代社会》这样的书,但已后悔莫及。如果再过一百年后,凡对阿里的过去感兴趣的后辈们是否也会责怪我们为什么不多出几本像《西行阿里》这样的书呢?很有可能。”见《西行阿里·序》,第9页。
相较马丽华的“被指认”,张承志对“摩尔根道路”的追寻更为自觉,他说:“我们的人文地理,期盼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回归求知的本来意义。首先成为社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①张承志:《〈人文地理〉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思想》(下),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13、412、411页。可以说,“民众的立场”是理解张承志“摩尔根道路”意涵的关键。张承志将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视作“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和“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②张承志:《〈人文地理〉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思想》(下),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13、412、411页。有意思的是,张承志虽然将人类学家摩尔根视作理想人物,却对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深致不满。这在对“田野”一词的态度上尤为显明,他认为:“把人、文化主体、人间社会视为‘田野’,是令人震惊的。”③张承志对此有详细解释:“因为对这个术语更熟悉的考古学界,还有地质队员并非如此使用这个词汇。在我们守旧的观念里,只把地层、探方、发掘工地;把相对于室内整理的那一部分工作称之为田野。我们从不敢对工地附近的百姓村落,用这个术语来表述。”见张承志《〈人文地理〉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思想》(下),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隐匿在“田野”语词背后的是对“文化的主体,即民众,从地位到态度”的“傲慢”。④张承志:《〈人文地理〉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思想》(下),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13、412、411页。由此必然出现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文明的阐释者,不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而是高奥的学科原理和教授训练。”⑤张承志:《〈人文地理〉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思想》(下),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13、413、412、411页。这使得民间社会、不同文明中微妙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被一套统一的调查术抹杀。在《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一书的小引中他自述本书的举意:“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⑥张承志:《鲜花的废墟:西班牙纪行》,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可以说,张承志的“民众立场”和“摩尔根道路”中内蕴着一种对“参差—统一”“边缘—中心”紧张关系的焦虑。
张承志游历实践中的现实精神和民众立场,与“大散文”鼓呼的“现实感”⑦贾平凹:《〈美文〉发刊辞》,《美文》1992年第1期。和“融入具体的社会生活”⑧穆涛:《稿边笔记:再谈行动散文》,《美文》2001年第9期。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关注内外之辨,旨在“走出狭窄的内心后花园”⑨穆涛:《稿边笔记:再谈行动散文》,《美文》2001年第9期。;前者则在“边缘—中心”的思考与经验中,以边缘文化作为心灵探寻的起点。而同样置身边缘之地,张承志和马丽华对摩尔根道路的实践也依托不同的学科背景,马丽华对人类学的选择和张承志在“人文地理”概念下的方法论思考,呈现出两人游历活动的不同思想底色。
当这些基于不同观念的游历书写均被归入“文化游记”时,“文化游记”概念极强的容纳能力得以显现,同时其有效性也难免遭受怀疑。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化游记”内部已经形成丰富参差的世界,因此对于我们而言,真正的任务并非不断“合并同类项”,而是析出“文化游记”的不同路径,并维系乃至增进其多元性。
结 语
游记文体观一向歧异杂陈,今人普遍接受游踪、游观、游感三要素说。游记将作者在现实世界中基于“身体—主体”的“置身”经验作为一项基本要求,对弃置身体以试图深探纯粹精神或与之相反将身体对象化的文学观构成挑战。晚清域外游记成就有限与“置身”的有效限度相关。1930年代前后言志派与左翼择取不同的“置身”经验及其书写方式,以小品游记和报告游记作为不同文学观、政治观对弈的象征符码,开拓出游记的文体政治空间。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交通和旅游业的成熟,“旅游文学”概念兴起;创作方面则以“文化游记”为大宗。二者呈现出殊异的“置身”形态,前者是作家现代行旅体验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共旋;后者则一面在身体上借力现代出行方式远游,一面在精神上不断反思现代困境,由此形成一种具有张力的“置身”体验。当代游记及其文体观尚保持着开放性和新的可能性,但可以确信的是:对游记文体新路径的探索,根本上依然是对新的“置身”经验及其书写方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