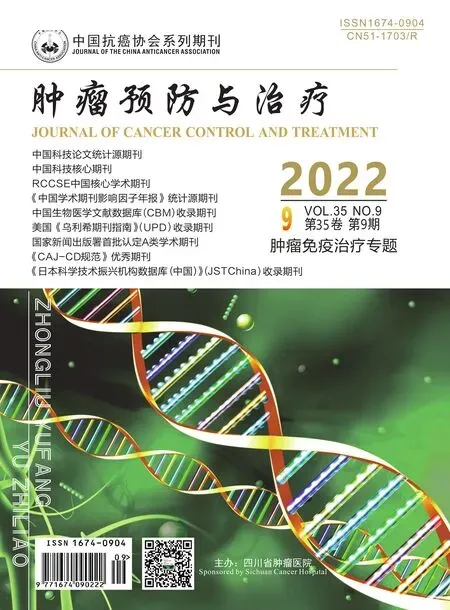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进展*
2022-11-15李蓝星张音洁金永东
李蓝星,张音洁,金永东
610054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医学院(李蓝星); 610041成都,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肿瘤内科(张音洁、金永东)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尤其是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负担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全球肝癌发生率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近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全球癌症最新数据,2020年全球肝癌新发人数为905 677,位于全球恶性肿瘤新发人数第6位;死亡人数为830 180,位于全球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第3位。我国肝癌新发病例人数为410 038,位于我国恶性肿瘤新发人数第5位;死亡人数为391 152,位于我国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第2位[1]。在我国,肝癌的筛查、早诊早治、临床诊治规范化及全程管理尤为重要。肝癌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以及HCC-ICC混合型,三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分子特征、临床表现、病理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2]。其中HCC是最常见的肝癌类型,约占总体的90%[3]。在我国,肝癌患者确诊病例中,约70%为中晚期患者,且超过一半患者无法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4]。因此,对于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uHCC)患者,系统性的药物规范化治疗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随着索拉菲尼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新药相继应用于临床实践,uHCC的治疗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IMbrave150研究是全球首个证实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显著优效于索拉非尼,开启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模式在uHCC的探索之路。本文针对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不可切除肝细胞癌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合阐述。
1 靶向治疗在uHCC一线治疗盘点
1.1 SHARP研究 & Oriental研究
2008年SHARP研究探讨索拉非尼对比安慰剂用于既往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晚期HCC患者。研究结果提示,索拉非尼和安慰剂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分别为10.7个月和7.9个月(HR=0.69;95%CI:0.55~0.87;P<0.001),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mPFS)为5.5个月和2.8个月(P<0.001);客观有效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分别为2%和1%[5]。2009年Oriental研究探讨了索拉非尼治疗亚太地区晚期HCC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发现索拉非尼组和安慰剂组的mOS分别为6.5个月和4.2个月(HR=0.68;95%CI:0.50~0.93;P=0.014)[6]。
1.2 REFLECT研究
2018年REFLECT研究对比仑伐替尼与索拉非尼在uHCC患者一线治疗疗效,基于mRECIST标准评估,仑伐替尼和索拉非尼组mOS分别为13.6个月和12.3个月(HR=0.92;95%CI:0.79~1.06),mPFS分别为7.4个月和3.7个月(HR=0.66;95%CI:0.57~0.77),ORR分别为24.1%和9.2%(OR=3.13;95%CI:2.15~4.56)[7]。
1.3 ZGDH3研究
多纳非尼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ZGDH3研究对比多纳非尼与索拉非尼一线治疗不可切除或转移性HCC的疗效,发现多纳非尼和索拉非尼组mOS分别为12.1个月和10.3个月(HR=0.831;95%CI:0.699~0.988;P=0.0245),mPFS分别为3.7个月和3.6个月(HR=0.909;95%CI:0.763~1.082;P=0.0570),ORR分别为4.6%和2.7%,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分别为30.8%和28.7%[8]。
2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用于uHCC的历程
2018年是肝癌治疗领域的一道分水岭,从索拉非尼一枝独秀迈入新药百花齐放的局面。肿瘤的发生发展与免疫逃逸密切相关,通过激活不同的免疫抑制途径来逃避免疫监视,最具代表的检查点负性调节信号通路就是程序性死亡受体(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及其配体PD-L1通路[9]。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通过阻断检查点蛋白及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阻止T细胞失活,而发挥抗肿瘤作用[10]。HCC是一种慢性炎症诱导的肿瘤,可以表达多种抗原介导免疫反应。在过去的十年中,基于调节免疫稳态平衡的免疫治疗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探索,并在HCC中显示出有效的结果[11]。抗血管生成药物是uHCC治疗基石,通过促进树突状细胞成熟,上调T细胞的迁移和功能,逆转组织缺氧引起的免疫抑制细胞的表达等调节免疫微环境[12],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治疗HCC时可使血管正常化和免疫重建之间建立正反馈回路,且在小鼠实验中能够看到肿瘤退缩程度更大、有效率更高的现象[13]。2019年3期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究IMbrave150重磅来袭,全球首先采用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模式,推动uHCC治疗进入新时代。
2.1 IMbrave150研究
IMbrave150研究探索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uHCC患者。初步结果提示,mPFS分别为6.8个月和4.3个月(HR=0.59;95%CI:0.47~0.76;P<0.001);12个月生存率分别为67.2%(95%CI:61.3~73.1)和54.6%(95%CI:45.2~64.0);3级和4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eatment-related adverse events,TRAEs)发生率分别为56.5%和55.1%[14]。2021年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胃肠道肿瘤研讨会(ASCO Gastrointestinal Cancers Symposium,ASCO-GI)上公布研究终点,mOS分别为19.2个月和13.4个月(HR=0.66;95%CI:0.52~0.85;P=0.0009;ORR分别为29.8%和11.3%(RECIST 1.1标准),35.4%和13.9%(mRECIST标准);在亚组分析中,中国人群mOS分别为24.0个月和11.4个月(HR=0.53;95%CI:0.35~0.80)[15]。
IMbrave150研究是全球首个证实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抗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优效于索拉非尼。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人群亚组分析中,中位生存期延长至24个月,推动uHCC治疗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2 ORIENT-32
ORIENT-32研究探索贝伐珠单抗类似物联合信迪利单抗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uHCC疗效及安全性。研究结果提示,mPFS分别为4.6个月和2.8个月(HR=0.56,95%CI:0.46~0.70;P<0.0001);试验组总生存期明显长于对照组,中位生存期未达到,对照组mOS为10.4个月(HR=0.56,95%CI:0.46~0.70;P<0.0001)。在安全性方面,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有32%和19%患者出现严重TRAEs;最常见的3/4级TRAEs为高血压(14%和6%)、手足综合征(无和12%);与治疗相关的死亡(2%和1%)[16]。
ORIENT-32研究是全球首个证实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信迪利单抗)联合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类似物)优于索拉非尼的研究。相较于IMbrave150研究,ORIENT-32研究入组的人群中94.5%是HBV相关HCC,65%以上患者曾接受过肝动脉栓塞化疗(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更符合中国人群特征,也进一步证明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模式可行性和优效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NMPA)已正式批准“双达组合”用于既往未接受过系统治疗uHCC患者的一线治疗。
2.3 RESCUE研究
RESCUE研究是国内多中心2期临床研究,探索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既往未接受系统性治疗或一线靶向治疗进展/不耐受的uHCC患者。研究结果提示一线治疗队列ORR为34.3%(95%CI:23.3~46.6),mPFS为5.7个月(95%CI:5.4~7.4),12个月生存率为74.7%(95%CI:62.5~83.5);二线治疗队列ORR为22.5%(95%CI:23.3~46.6),mPFS为5.5个月(95%CI:3.7~5.6),12个月生存率为68.2%(95%CI:59.0~75.7)。安全性方面,77.4%患者出现3级及以上TRAEs,最常见的不良话反应为高血压(34.2%)[17]。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项关于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一线治疗进展或不耐受的晚期HCC临床研究中,反应性皮肤毛细血管内皮增殖(reactive cutaneous capillary endothelial proliferation,RCCEP)是最常见不良反应,217例患者中有145例(66.8%)出现了RCCEP[18];而RESCUE研究中RCCEP的发生率显著降低(29.5%和66.8%),研究者认为VEGFA/VEGFR-2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RCCEP的发病机制,卡瑞利珠单抗诱导的免疫反应的重新+激活打破了血管生成促进与抑制反应之间的平衡,从而导致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过度增殖[17]。2021年ASCO大会上RESCUE研究公布了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结果,一线队列的mOS为20.1个月(95%CI:14.9~NR),2年OS率为43.3%(95%CI:31.3~54.7);二线队列的mOS为21.8个月(95%CI:17.3~26.8),2年OS率为44.6%(95%CI:35.5~53.3)[19]。
RESCUE研究提示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阿帕替尼联合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同样能够达到不俗的疗效和可控的安全性。近日,恒瑞医药公布全球3期SHR-1210-Ⅲ-310研究(NCT0-3764293)“双艾组合”对比索拉非尼在uHCC一线治疗达到主要研究终点,目前NMPA已受理“双艾组合”晚期HCC一线适应证上市许可申请,具体数据预计在2022年9月欧洲肿瘤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ESMO)上公布,期待为uHCC一线治疗再添“中国证据”。
2.4 COSMIC-312研究
2021年ESMO会议上公布了COSMIC-312研究中期分析结果,这是一项探索卡博替尼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对比索拉非尼/卡博替尼一线治疗uHCC的全球多中心3期研究。试验共纳入837名患者,按2∶1∶1随机分配接受卡博替尼联合阿替利珠单抗组(C+A组)、索拉非尼单药组(S组)及卡博替尼单药组(C组)。研究结果显示,根据RECIST 1.1标准,C+A组、S组、C组的ORR分别为11%、3.7%、6.4%,DCR分别为78%、65%、84%;C+A组与S组mPFS分别为6.8个月和4.2个月(HR=0.63;99%CI:0.44~0.91;P=0.0012);mOS无显著差异,分别为15.4和15.5个月(HR=0.90;96%CI:0.69~1.18;P=0.438)。HBV亚组中,mPFS分别为6.7个月和2.7个月(HR=0.46;95%CI:0.29~0.73);mOS分别为18.2和14.9个月(HR=0.53;95%CI:0.33~0.87)。在安全性方面,C+A组、S组、C组出现3/4级TRAEs分别为51%、30%、52%,其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手足综合征、高血压、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及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升高。与治疗相关的死亡率分别为1.9%、0.5%和0.5%[20]。
基于3期CELESTIAL研究,在既往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HCC患者中,卡博替尼相比安慰剂,显著改善OS(10.2个月和8.0个月)和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5.2个月和1.9个月)[21]。2019年1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卡博替尼用于先前接受过索拉非尼治疗的晚期HCC患者。2022年3月Exelixis生物公司宣布COSMIC-312研究最终结果以失败告终。
2.5 KEYNOTE-524研究&LEAP-002研究
2019年ASCO上公布了1b期试验KEYNOTE-524的结果,探索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uHCC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在通过剂量限制毒性阶段后,纳入100名既往没有接受过全身治疗晚期HCC患者,中位随访10.6个月,ORR为46.0%(mRECIST标准)、36.0%(RECIST 1.1标准);中位缓解持续时间(median duration of response,mDoR)为8.6个月(mRECIST标准)、12.6个月(RECIST 1.1标准);mPFS为9.3个月(mRECIST标准)、8.6个月(RECIST 1.1标准);mOS为22.0个月。67%患者出现≥3级TRAE,3%患者出现与治疗相关的死亡[22]。
基于KEYNOTE-524研究令人惊艳的试验结果,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搭配的“可乐组合”已经被《CSCO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0》推荐为晚期HCC一线治疗策略选择(2B类证据)。全球多中心3期LEAP-002研究进一步探索“可乐组合”对比仑伐替尼联合安慰剂一线治疗uHCC患者。然而,2022年8月3日默克公司发文宣布LEAP-002研究失败,具体数据尚未公布。“可乐组合”在uHCC被寄予厚望却黯然退场,笔者认为LEAP-002研究的失利与HBV感染导致的HCC入组的患者比例低可能相关,基于不同病因导致HCC患者分层治疗和方案选择值得进一步研究设计。
2.6 其他
2021年ESMO摘要938P展示KN046联合仑伐替尼治疗uHCC的2期研究,根据RECIST 1.1标准,21例可评估患者的ORR为57%(95%CI:34.0%~78.2%),DCR为95%(95%CI:76.2%~99.9%)。根据mRECIST标准,ORR和DCR分别提高到76.2%(95%CI:52.8%~91.8%)和95%(95%CI:76.2%~99.9%)。在安全性方面,64%(16/25)患者发生TRAEs,20%(5/25)患者发生≥3级TRAEs。8%患者发生了与KN046相关的≥3级TRAE,包含1例肺炎、1例血小板降低[23]。KN046联合仑伐替尼显示出较高的缓解率及有效的安全性,双免疫联合靶向治疗在一线uHCC治疗显示出极具潜力的抗肿瘤活性。
2021年ASCO-GI上摘要306展示派安普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8 mg)一线治疗uHCC的1b/2研究。根据RECIST 1.1标准,29名可评估患者的ORR为31.0%(9/29),DCR为82.8%(24/29);mPFS为8.8个月,mOS尚未达到。安全性方面,最常见的TRAEs是AST和ALT升高(38.7%和35.5%)、血胆红素增加(22.6%)、虚弱(22.6%)、血小板计数减少(19.4%)和皮疹(16.1%)。16.1%(5/31)患者发生≥3级TRAEs[24]。派安普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在uHCC中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疗效和可接受的安全性。基于此研究的结果,目前派安普利单抗联合较高剂量安罗替尼(10 mg)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uHCC的3期随机研究正在进行中(NCT-04344158)。
2022年ASCO-GI上展示了多项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或转移性uHCC的单臂研究结果。RENOBATE研究探索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一线治疗uHCC的疗效及安全性,根据RECIST 1.1标准,21名可评估患者ORR为35.7%;mRECIST标准的ORR为35.7%;mPFS为5.5个月,未达到mOS。安全性方面,最常见的TRAEs是手足综合征(33.3%),皮疹(28.5%)和脱发(23.8%)[25]。另一项GOING研究探索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在uHCC一线治疗进展后的用药顺序及安全性分析,研究设计分为队列A(索拉非尼一线治疗进展组)和队列B(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进展组),队列A患者前2个周期接受瑞戈非尼单药(160 mg/天,用3周/休1周),第3周期开始增加纳武利尤单抗(240 mg,两周一次)。本次大会上公布的是队列A的中期分析的安全性,可评估的30名患者中,10名(33.3%)出现3级TRAEs(没有出现4/5级的TRAEs)。常见的TRAEs包括手足综合征(56.6%)、虚弱(43.3%)、腹泻(36.7%)等;疗效方面数据尚未公布[26]。瑞戈非尼和纳武利尤单抗都是uHCC二线治疗的指南推荐,RENOBATE研究和GOING研究都聚焦于此。有趣的是,RENOBATE研究探索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在uHCC一线治疗的可行性,而GOING研究探索一线标准治疗失败后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在二线治疗联合的用药顺序管理及安全性。上述的研究结果提示,一线瑞戈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具有潜在的高效抗肿瘤活性,二线瑞戈非尼序贯纳武利尤单抗联合瑞戈非尼顺序组合具有可管理的安全性,为后线治疗提供多样性选择以及用药管理安全性的先例,期待后续更大样本的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摘要435探索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HCC的2期单臂研究,根据RECIST1.1标准,52名可评估患者的ORR为32.7%(17/52),DCR为78.8%(41/52);mRECIST标准下的ORR为46.2%(95%CI:32.2~60.5%),DCR为94.2%(95%CI:84.1~98.8%);mPFS为9.9个月(95%CI:5.5~11.0),mOS尚未达到。安全性方面,25.9%患者出现≥3级TRAEs,11.1%患者出现≥3级irAEs,没有出现与治疗相关的死亡事件[27]。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作为晚期HCC一线治疗显示出有希望的抗肿瘤活性且安全性可控。目前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对比索拉非尼(NCT04723004)及特瑞普利单抗联合仑伐替尼对比仑伐替尼(NCT04523493)一线治疗晚期HCC的随机3期研究均在进行中,期待进一步研究结果。摘要436是探索度伐利尤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uHCC的2期单臂研究,共纳入47名患者,根据RECIST1.1标准,10名可评估患者ORR为21.3%(95%CI:10.7~35.7),mDoR及mOS尚未达到。安全性方面,70.2%(33/47)患者出现TRAEs,10.6%(5/47)患者发生严重TRAEs,包括胃溃疡穿孔、腹水、肝肿瘤破裂、肌酐升高和肺炎[28]。基于此研究结果提示度伐利尤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潜在的治疗价值,目前3期EMERALD-2研究(NCT-03847428)探索度伐利尤单抗单药或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高危复发的治愈性HCC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正在进行中。
除上述临床研究外,索拉非尼联合纳武利尤单抗(NCT03439891)、替雷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NCT04401800)一线治疗uHCC患者的多中心2期研究等均在招募中。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uHCC治疗必将迎来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3 靶向及免疫治疗联合局部治疗在uHCC临床探索
uHCC除了全身系统治疗外,局部治疗也尤为重要,临床上常用的局部治疗包括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选择性体内放射治疗、局部消融技术等。局部治疗可导致肿瘤细胞的缺血、坏死,从而刺激肿瘤相关抗原和新抗原释放并被抗原呈递细胞摄取,从而改善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具有协同作用,可以增强抗肿瘤疗效[29]。
LTHAIC研究是国内2期前瞻性单臂临床研究,旨在探索仑伐替尼和特瑞普利单抗联合HAIC,一线治疗晚期HCC疗效。试验共纳入36名患者,86.1%的患者有门静脉侵犯,27.8%有肝外转移。中位随访11.2个月,主要研究终点6个月PFS率为80.6%;mPFS为10.5个月(95%CI:6.21~14.79),mOS未达到。RECIST1.1标准评估ORR为63.9%(95%CI:40.9~73.0),mRECIST标准评估ORR为66.7%(95%CI:43.3~75.1),其中5名患者(13.9%)达到影像学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8名患者(22.2%)转化为可切除的疾病状态,其中1名达到病理CR。最常见的TRAEs为血小板减少症(13.9%)、AST升高(13.9%)和高血压(11.1%),总体毒副反应可控,且未出现与治疗相关的死亡[30]。LTHAIC研究人群中,中位年龄为49岁,中位肿瘤大小为11.2cm,年轻且肿瘤负荷大是入组人群的主要特点,有效率较单一的系统治疗明显提高,再次显示多维度综合治疗模式的优效性,靶向免疫系统治疗联合局部治疗三联模式以其优异的疗效且可控的毒副反应为晚期uHCC患者提供又一可行的治疗方案,尤其是对肿瘤负荷较大,年轻且一般状态较好的患者,提高了降期转化手术治疗的可能性。尽管不同治疗模式转化率大相径庭[31-32],多项研究结果表明uHCC转化成功后,与初诊可接受手术根治性切除的患者预后无明显差异[33]。值得注意的是,石明教授团队另一项3期RCT证实,相较于经TACE而言,HAIC在uHCC患者中显著提高mOS(23.1个月和16.1个月;P<0.001),ORR(46%和18%;P<0.001)以及转化为可手术切除率(23.8和11.5%;P=0.004)[34]。
LTHAIC研究是uHCC从系统治疗向局部联合系统治疗模式转变的试金石并展示出极具潜力的价值,但仍需更大样本量3期RCT进一步证实三联治疗模式的疗效及安全性。石明教授团队正在开展3期RCT(NCT05198609),探索HAIC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和阿帕替尼对比卡瑞利珠单抗和阿帕替尼治疗uHCC疗效及安全性;另一项作为壁报展示在2022年ASCO-GI上的TALENTACE研究(NCT-047126430)正在进行中,探索TACE联合“T+A”对比单纯TACE在不可治愈性HCC患者疗效评价[35]。局部联合靶向及免疫治疗模式是未来uHCC探索的重要方向,期待更多临床研究为三联治疗模式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学证据。
4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uHCC面临的挑战
4.1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的潜在生物标记物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已经被广泛认可作为uHCC治疗的一线新选择,目前全球3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有效率在11%~30%之间,但并非所有接受联合治疗的患者都能达到预期疗效。生物标记物是预测和评估疗效的良好指标。
4.1.1 PD-L1,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和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 近年来,PD-L1表达作为预测疗效指标在多个肿瘤中得到广泛应用[36]。然而,在接受免疫治疗的HCC患者中,PD-L1的预测价值仍然有待商榷。一方面,多项研究结果显示PD-L1状态与治疗有效性之间的结果不一致。CheckMate-040研究中对PD-L1表达进行了回顾性评估,采用了1%的肿瘤细胞表达作为PD-L1的截断值,结果发现PD-L1状态与纳武利尤单抗治疗没有关联性[37]。KEYNOTE-224研究发现,PD-L1阳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的有效率更高[38]。另一方面,用于评估免疫治疗有效性和PD-L1状态关联性差,即使PD-L1表达呈阴性,部分患者仍然从免疫治疗中获益[39]。此外,PD-L1检测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异质性[40]。因此,目前PD-L1表达在HCC患者中的预测价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TMB定义为特定基因组区域内每兆碱基对(Mb)体细胞非同义突变的个数,可以间接反映肿瘤产生新抗原的能力和程度,已被证实可预测多种肿瘤的免疫治疗疗效[41]。尽管TMB被认为是一种潜在可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标记物,但是在肝癌中的临床价值仍有争议,因为大多数的数据来自样本量较少和显著选择偏差的研究[42]。TMB-H被认为≥10个突变/兆碱基DNA(mut/Mb),由基因测序试剂FoundationOne CDx(F1CDx)确定并获得FDA批准,与PD-L1面临同样的问题,TMB检测结果很大程度受检测方法和试剂盒的影响。近期一项研究结果提示,不支持将TMB-H作为免疫治疗所有实体瘤的生物标志物,包括FDA批准的10个突变/Mb的阈值[43]。TMB是一种正在不断研究发展中的生物标志物,对于如何衡量TMB,目前尚没有达成共识。TMB与其他肿瘤免疫治疗相关标志物联合应用,或能提高免疫治疗疗效预测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但具体的联合策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44]。相对于单一TMB-H或PD-L1阳性,TMB-H且PD-L1表达阳性的患者可能接受免疫治疗的疗效更优[45]。DNA MMR系统广泛存在于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的生物体中,是细胞进化中高度保守的修复机制。临床上主要通过免疫组化方法检测MLH1、PMS2、MSH2和MSH6蛋白。MSH2/MSH6异二聚体通过构象变化与初始的DNA错配碱基相结合,而MLH1/PMS2异二聚体负责切除被标记错配碱基序列和校对合成新的DNA链。若一种或多种蛋白质不表达或功能失调,则该状态称为错配蛋白功能缺失(mismatch repair deficiency,dMMR),相反则称为错配蛋白功能完整(mismatch repair proficient,pMMR)[46]。MSI定义为肿瘤组织的微卫星由于重复单位的插入或缺失,导致微卫星长度的改变引起一系列现象,根据微卫星状态可分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低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low,MSI-L)、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ility,MSS)。在多种肿瘤中,dMMR和MSI-H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90%~95%)[47]。dMMR/MSI-H肿瘤微环境表现为新抗原呈指数级增加,导致大量淋巴结细胞活化和对免疫治疗高度敏感性[48]。KEYNOTE系列研究结果提示,在先前化疗后进展的dMMR/MSI-H肿瘤患者中,帕博利珠单抗表现出令人惊喜的结果,2017年5月FDA批准帕博利珠单抗适用于所有dMMR/MSI-H的实体瘤患者,这也是首次FDA以分子标记物作而非肿瘤类型作为获批适应证[49]。dMMR/MSI-H作为免疫治疗特异性标记物在临床上被广泛认可,但是TCGA数据库显示肝癌MSI-H只有0.8%~3%,远远无法满足临床需求[46]。
4.1.2 基因测序 在过去十年间,基因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助力推进肿瘤分子图谱构建,为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了新的方向[50]。在HCC预测与免疫治疗相关指标中,最具前景的是WNT/β-连环蛋白。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是一种高度保守且受严格控制的分子机制,可调节胚胎发育、细胞增殖和分化,WNT/β-连环蛋白通路的异常可以促进肝癌的发展发展[51]。研究发现WNT/β-连环蛋白通路激活突变和野生型的HCC患者mPFS分别为2.0个月和7.4个月,mOS分别为9.1个月和15.2个月。在WNT/β-连环蛋白突变亚组中没有观察到免疫治疗获益,而50%的野生型对免疫治疗药物有效,WNT/β-连环蛋白突变认为对免疫治疗不敏感,且比野生型的患者预后更差[52]。临床前模型也确定了WNT/β-连环蛋白突变促进HCC发生发展,并参与逃避免疫监视[53]。动物模型中已经被证实WNT/β-连环蛋白突变促进HCC免疫逃逸和抗PD-1治疗抵抗[54]。WNT/β-连环蛋白在HCC中被认为是极具前景的生物标记物,但仍需要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DNA损伤修复(DNA Damage Repair,DDR)缺陷被认为是预测免疫治疗潜在的生物标记物,DDR通路负责DNA损伤后的识别、信号转导和修复,其功能异常可导致细胞的凋亡或基因组不稳定性的增加。多项研究提示,DDR通路突变与免疫治疗疗效相关性[55-57],但目前仍缺乏HCC相关的研究数据。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在肝癌免疫治疗中被认为是有潜在预测价值的生物标记物。一项研究中发现HCC中lncRNA MIR155的表达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和PD-L1呈正相关,或可作为潜在的免疫治疗预测因子[58]。其他研究也观察到了具有免疫相关特异性lncRNAs的HCC有更多的免疫细胞浸润和PD-L1、PD-L2以及吲哚胺2,3-双加氧酶1(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1,IDO1)高表达[59]。LncRNA作为联合治疗生物标记物仍需要被进一步验证。
4.1.3 肠道微生物群 肠道微生物群在生理上参与免疫等多种功能调节,一直都是研究的热门领域。由于肠道和肝脏密切联系,肝胆肿瘤发生发展被发现与肠道微生物群相关[60]。李艳等[61]研究者在小鼠模型中进一步证实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可以调节免疫微环境和抑制肿瘤生长,并且发现未折叠蛋白应答(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UPR)降低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发挥作用呈正相关,UPR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免疫治疗生物标记物。另一项HCC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收集患者治疗前后粪便样本进行微生物类群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肠道微生物群对治疗疗效产生重要影响,监测肠道微生物群动态变化可以为HCC免疫治疗结果早期预测提供重要依据[62]。尽管多项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疗效生物标记物,并且在免疫微环境和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离临床应用尚有一段距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4.1.4 抗药性抗体(anti-drug antibody,ADA) 人源化单克隆抗体的全身给药可能具有免疫原性,并引起不必要的ADA。IMbrave150研究中“A+T”治疗后,29.6%HCC患者出现对阿替利珠单抗的ADA反应。ADA可以通过降低血清浓度或中和抗体降低治疗性抗体的疗效。2022年ASCO大会上报道一项前瞻性研究,探索晚期HCC患者接受“A+T”治疗后高ADA水平的临床及免疫学意义。共纳入132例患者(研究队列50例;验证队列82例),研究结果发现,两组队列中高水平ADA组与低水平ADA组患者相比,缓解率分别为11%和34%,7%和29%,且PFS与OS更差。ADA水平与阿替利珠单抗血药浓度呈负相关。此外,还发现高水平ADA患者对“A+T”治疗缺乏CD8+T细胞增殖反应。ADA水平可作为免疫治疗疗效及不良结局的预测因子,但临床实践中如何区分不同抗体药物间ADA水平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有趣的是,ADA水平升高同样是机体耐药性的表现,如何解决肿瘤治疗耐药性的问题仍是肿瘤学的一大难题。
尽管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模式在uHCC中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目前临床上仍然缺乏良好的生物标记物。肠道微生物群和WNT/β-连环蛋白被认为是极具潜力的生物标记物,并且CTNNB1基因的突变导致WNT/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的激活已经在HCC免疫“冷”肿瘤中被证实[63]。期待更多HCC靶向联合免疫治疗中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帮助临床医生更好的做出临床决策。
4.2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耐药的分子机制及发展方向
4.2.1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耐药的分子机制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uHCC中已经被证实具有积极抗肿瘤活性,然而耐药问题仍是治疗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有研究基于细胞及分子特征针对HCC进行免疫及亚组分类,结果表明约65%的HCC表现为免疫“非炎症”类型,包括45%免疫“中间”亚型和20%免疫“排除”亚型。“中间”亚型表现为TP53突变丰富,染色体高度不稳定,与干扰素信号或抗原呈递相关的基因缺失;“排除”亚型表现为CTNNB1突变和免疫性荒漠化的特征[63]。简而言之,大多数HCC免疫类型及微环境表现为对免疫治疗不敏感,其特点表现为T细胞缺乏,抗原提呈不足,免疫抑制细胞浸润,包括髓系抑制细胞(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M2肿瘤相关巨噬细胞(M2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M2TAM)、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等,导致维持免疫耐受能力下降以及无法产生肿瘤免疫反应。免疫“冷”肿瘤是HCC免疫治疗原发性耐药的重要机制[64]。多项临床及动物模型试验中证实,抗血管生成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抗肿瘤治疗中发挥协同作用,能够推动免疫细胞向“冷”肿瘤渗透从而转化为“热”肿瘤。这种协同作用可能涉及多种机制,包括改善药物输送和免疫渗透的血管正常化,激活各种抗肿瘤免疫细胞亚群,以及抑制具有促肿瘤活性的免疫细胞类型(MDSCs、M2TAMs、Tregs)[65]。尽管联合治疗模式是逆转免疫“冷”肿瘤的一种有效方法,并且在联合治疗较单药免疫治疗的临床研究中看到显著的疗效提升,但是联合治疗在部分uHCC患者中仍表现为原发性耐药或在后续治疗过程中出现获得性耐药。事实上,耐药发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并且动态变化的,其中涉及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甚至内外因素叠加(表1)[66]。此外,HCC的异质性同样在在耐药中发挥重要作用。HCC与其他原发肿瘤不同,多灶性病变极为常见。虽然这些肿瘤在遗传上起源于相似的细胞,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多灶性病变和不同患者免疫检查点分子差异性表达是构成异质性的主要原因[67]。基于以上理论,有学者提出根据免疫渗透状态和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对HCC患者建立分层模型,可能有助于精准选择对免疫治疗敏感的患者[68]。

表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耐药机制
4.2.2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耐药的发展方向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uHCC治疗中的耐药问题是临床上的一大挑战,笔者就关于此问题提出逆转耐药潜在的发展方向。首先,PD-1/PD-L1抑制剂联合CTLA-4抑制剂可以提高uHCC患者治疗有效率并延长生存时间,抗PD-1/PD-L1和抗CTLA-4的组合不仅可以在启动期激活和增加CD8+T细胞,而且促进CD8+T细胞侵入肿瘤并抑制Tregs和MDSCs[69]。2022年ASCO-GI公布了3期HIMALAYA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上述理论,并在临床中得以实践。研究结果显示,STRIDE组(曲美木单抗300 mg联合度伐利尤单抗组)相较于度伐利尤单抗组和索拉非尼组,ORR分别为20.1%、17.0和5.1%,DOR分别为22.34个月、16.82个月和18.43个月,mOS分别为16.4个月、16.6个月和13.8个月[70]。值得注意的是,HIMALAYA研究中STRIDE方案采用的是曲美木单抗300 mg(仅首周使用一次)联合度伐利尤单抗(T300+D),原因是因为前期1/2研究中发现,相较于曲美木单抗(75 mg,每4周一次,连续使用4周期)联合度伐利尤单抗组(T75+D),T300+D显示出更高的ORR(24.0%和9.5%)和OS(18.7个月和11.3个月)以及更低的不良反应[71]。在循环淋巴细胞谱发现,T300+D组外周血中发现活化的CD8+/Ki67+T细胞数是最高的,进一步证实抗PD-L1联合抗CTLA-4抗肿瘤治疗的理论基础。研究者进一步分析T75+D组ORR和OS较差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单次高剂量的抗CTLA-4足够启动自身的免疫激活,重复多次的抗CTLA-4不会产生显著的启动效果,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低剂量抗CTLA-4无法启动自身的免疫激活[71]。由于STRIDE方案与目前使用的PD-L1/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作用方式不同,笔者认为STRIDE方案序贯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可能是逆转部分耐药患者一种潜在有效的治疗策略。
第二,局部治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是逆转耐药的可选策略。TACE可引起HCC内CD8+/PD-1+细胞和Treg细胞减少,同时促进了微环境内的免疫应答、炎性反应,与免疫治疗具有协同效应[72]。TACE同样具有强大的细胞毒性和缺血性抗肿瘤作用,可能促进栓塞诱导的局部缺氧环境,进而导致肿瘤中的新血管形成[73]。多项研究表明,TACE联合索拉非尼或阿帕替尼可进一步提高疗效[74-76]。TACE联合靶向免疫治疗可能是进一步提高疗效及逆转耐药的可选策略。此外,免疫治疗与射频消融或热消融联用,在治疗进展期肝癌中能够明显促进CD8+T细胞在肿瘤组织中的积累,呈现出较好的疗效[77]。抗血管生成可以调节肿瘤内部血管网络的成熟度,降低肿瘤内部的组织间压力,改善肿瘤内部乏氧水平,提高肿瘤的放射敏感性,阿帕替尼联合调强适形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在uHCC临床研究中显示出积极抗肿瘤活性[78]。同时,临床前模型提供了免疫治疗联合IMRT协同证据,免疫治疗和放射治疗都具有免疫编辑效应,可能使免疫系统通过放射增敏和持续的全身免疫反应发挥抗肿瘤效应[79]。多种局部治疗方法联合靶向免疫治疗在uHCC中表现出极具潜力的联合抗肿瘤效应,由于目前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临床实践仍需谨慎对待。
第三,肠道微生物群与免疫治疗被证实具有协同效应[80],肠道益生菌联合免疫治疗前瞻性研究首次证实肠道益生菌能够改善肠道菌群稳态,并增强免疫治疗效应[81]。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靶点被发现,包括SOAT1、p38γ、MOAP-1等[82-84]。肿瘤疫苗、溶瘤病毒也是促进肿瘤免疫原性和解决耐药性的潜在方法[85-86]。靶向免疫治疗联合其他新靶点药物可能是逆转耐药潜在的发展方向。
5 总结及展望
uHCC患者的系统治疗始于2008年索拉非尼在国内获批一线适应证,而索拉非尼作为全球首个多靶点抗肿瘤药物开启了靶向治疗时代。随后的10年期间,多种药物试图挑战其疗效均以失败告终,uHCC治疗步伐停滞不前。直到2018年,REFLECT研究表明仑伐替尼非劣效于索拉非尼,仑伐替尼成功破冰,一举打破了索拉非尼一枝独秀的一线地位。随着免疫药物发展,uHCC治疗迎来免疫新纪元,2019年ASCO上IMbrave150研究结果大放异彩,开创了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新模式,彻底打破靶向治疗在uHCC一线治疗的传统格局,促进了靶向联合免疫治疗探索的大爆发。2020年IMbrave150研究结果发表在全球生物医学顶级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T+A)作为uHCC患者一线治疗方案被国内外权威指南纳入优选推荐。2021年NMPA批准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类似物纳入uHCC患者一线治疗适应症。目前多项研究正在进行中(表2)。

表2 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在不可切除或晚期肝细胞癌临床研究进展汇总
除了系统治疗外,uHCC局部治疗尤为重要,局部治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模式展现出极具前景的抗肿瘤活性,在转化治疗方面尤为突出,期待更大样本量的RCT提供更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双免疫治疗序贯靶向免疫治疗,局部治疗联合靶向免疫治疗,靶向免疫治疗联合其他新靶点药物可能成为uHCC治疗新趋势和探索方向。随着对肝癌治疗的不断探索,以多手段综合治疗的全程管理模式被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肝癌治疗全程管理理念成为广泛的共识。虽然肝癌的临床治疗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无论是作用机制还是临床治疗过程中,仍有很多疑问尚待进一步解决,诸如局部治疗联合系统治疗的方式和时机如何把握,药物耐药后的序贯治疗如何选择,如何筛选出更多的分子生物标记物实现人群精准化治疗等。从2008年到2022年,从突破到传承,从探索到创新,从一枝独秀到百家争鸣,浩瀚星辰未来已来,uHCC患者治疗必将迎来百花齐放的新格局,期待下一个“十年”,逐步推进实现肝癌转变为可防可控“慢性病”的伟大目标。
作者声明:本文全部作者对于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出现的不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并承诺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资料等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可接受核查。
学术不端:本文在初审、返修及出版前均通过中国知网(CNKI)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学术不端检测。
同行评议:经同行专家双盲外审,达到刊发要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文章版权:本文出版前已与全体作者签署了论文授权书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