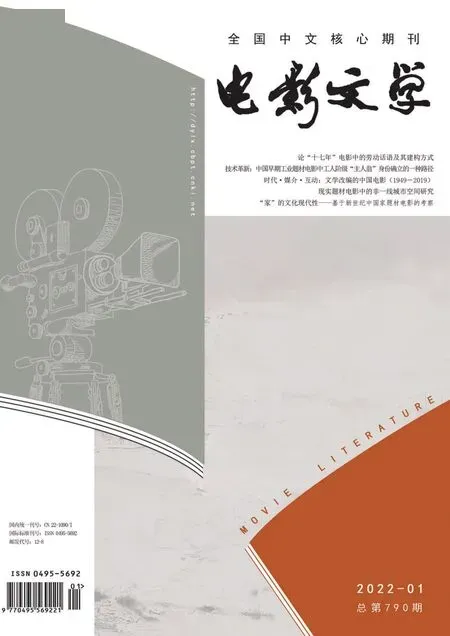史诗叙事、生态隐喻与转场的后现代性
——《远去的牧歌》中哈萨克日常影像解析
2022-11-13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21
郑 亮 郝 阳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远去的牧歌》以史诗般瑰丽的画卷、恢宏的草原景象为空间背景,讲述了胡玛尔带领的哈萨克阿吾勒(村庄)跨越四十年的转场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随着季节变换而不断迁徙,在与他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他们展现出民族特有的性格特质与生存观。身处改革的浪潮中,他们与数千年的游牧生活告别,饱含爱与乡愁走向定居。敬畏自然、爱护动物、珍视草场等是哈萨克民族独有的生态观的典型体现,在“人类中心主义”至上、金钱至上的当代社会,影片在漫长的历史语境中展现了哈萨克族一年四时的日常生活,像是一部哈萨克祖祖辈辈的民族生活史。影像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达,是出生、死亡、情感、工作等,围绕着转场的特殊生活方式,胡玛尔和族人的言谈、互动、所思、所为皆向世人传递着哈萨克人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的抉择。
一、史诗叙事:马背上的迁徙影像志
哈萨克族是世界上最早创造游牧文化的四大游牧民族之一,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是哈萨克族的生存方式,在我国的早期典籍中,如《西陲要略》《西域图志》《清实录》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哈萨克”与“游牧”二字相联系。甚至在民国晚期,在一些边政学者或民族学家的文字中提及“哈萨克”与“游牧”字眼时,仍然将二者相提并论。张焕仪在《天山南北风土漫谈》中说:“哈萨克族的一般生活需用完全仰给游牧。他们的财产则以牲畜的数目计算……”游牧是哈萨克人骨血中的一脉。影片《远去的牧歌》,便是以哈萨克牧民的一次转场开始,冰天雪地间,胡玛尔和其族人骑着马艰难前行。雪地苍茫辽阔,在零下三十五摄氏度的自然环境中,转场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影片一开场就交代了哈萨克游牧民族艰苦的生活环境。哈萨克人根据畜牧的需求,以及草场的草类、面积、气候和地势等因素,将不同自然空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在三地四牧场之间不断流转。影片所呈现的第一次转场只是千百年来哈萨克族生活的一个缩影。影片后续以十年为一个时间轴,分别记述了胡玛尔带领大家转向春牧场、夏牧场、秋牧场、定居的过程。影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开始,暴风骤雪中,胡玛尔与族人们正驭马前行。他们一边自救式地迁徙,一边在迁徙中对他人(羊皮别克)进行救助。也正是在马背上的迁徙中,胡玛尔的儿媳即将生产,人们在骆驼背上搭起帐篷,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在呼啸的狂风暴雪中,婴儿的啼哭声穿透自然的重重艰辛带给人希望,脐母为转场途中出生的“牧马人”(女孩)起名“博兰古丽”,意为“风雪之花”,这种希望的力量足以消解任何苦难和困境,哈萨克民族性格中的坚韧与毅力也在此体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骏马奔腾中,胡玛尔与族人转向春牧场。气温转暖,冰雪消融,流水潺潺,万物复苏,人们再次骑上马背,开始了又一次的迁徙。春牧场一派生机勃勃:小驼羔吸吮着母乳,母牛产崽,儿童们绽放笑颜,春牧场的一切都洋溢着昂扬的生命力。在河流水涨时,牧民们结束春牧场的生活,收拾家当,再次开始了向夏牧场的迁徙。
影片镜头转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夏天,长镜头与航拍下的草原青色连绵,鲜花盛开,胡玛尔与族人们再经马背上的迁徙,到达夏牧场。此时,草原上牧草丰盛,景色宜人,是各类牲畜的快速上膘期,人们也能在夏牧场得以休憩,饱尝羔羊肉与驼奶,走家串户,举行各种盛大仪式及民族色彩浓厚的文化活动,其乐融融。秋牧场与夏牧场一地两用,等到九月时,哈萨克游牧民们从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牧,秋牧场的植被已得到恢复,此时正值水草丰茂,人们居住在此,开始为牲畜配种。在春牧场与夏牧场,牧民们度过一年中较为舒适的生活,并为过冬做准备。牧民们随四时流转不断迁转,由此在草原上形成的游牧文化,是草原生态环境以及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选择、互相作用的结果,具有显著的生态意识,是草原人的智慧结晶。
哈萨克俗语说:“草地是牲畜的母亲,牲畜是草地的子孙。”哈萨克人十分珍视草地,也因此形成了一定的草地使用规则。影片中,在冬牧场放牧时,族人对胡玛尔说:“羊把草根刨出来了,到了夏天,这个地方的草肯定长得不好”,胡玛尔听后当即决定纳吾鲁孜节后立刻转场。此番话语也道出了游牧的根本原因——尽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原。游牧民们的生活与草地、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具有其特殊性,这一方面取决于游牧民们生活、生存的先决条件就是适应自然:牧民的牲畜生产及再生产是凭借天然牧场的饲料资源进行的。因此,无论是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是在对天然牧场适应性利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尽管游牧民族并非自愿选择迁徙,而是环境促使他们做出了“迁徙—适应”的举动,但这一行为在满足牲畜多样性、保证畜群食物量之外,也较好地保存了地表植物的覆盖面。从人类自身的短期利益来看,尤其是从生活的安乐舒适方面来看,游牧的生活并不适宜,但是,如果从生态及人类生存的长远意义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具有科学的依据,这一生活生产方式实际上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系统维持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游牧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前提下,由此衍生出的生活、生产方式,形成的生活技能都充溢着一种和谐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既彰显了游牧民们非凡的适应能力,又能够使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影片中的四季转场透露出了哈萨克游牧民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为人类应该持何种生态、生存观提供了借鉴思路。
二、生态隐喻:草场、羊群面对现代性
曾繁仁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下生态危机结合思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四个原则,即“尊重自然、生态自我、生态平等、生态同情”。他认为,“生态自然”尤其重要,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的首要原则。长期以来,人们以轻视和掠取的态度对待自然,然而,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人类对自然应该持有一种尊重的态度,有了尊重,才会有对自然的珍爱和保护。曾繁仁提出的人与自然相处的原则,在影片中哈萨克游牧民的生活中也有表露。从胡玛尔及其族人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出,哈萨克游牧民们的生活习惯是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他们日常生活的第一要务就是保护草原,草原生态的良性循环是游牧生活的基础。只有对自然葆有尊重与敬畏,才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哈萨克族对自然的尊重,一方面源于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另一方面源于游牧民族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以草地为例,影片中多次以航拍镜头俯拍草原,展现一碧千里的宜人风光,在美丽风光的背后,是哈萨克牧民们对草地的珍视与爱护。长久以来,放牧的草地上仅能看到羊圈的底子,人或畜几乎不会留下生活过的痕迹;每到一处新的草场,长辈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们讲解如何保护牧草、保护水源,如同呵护自己的生命般细心。影片中,羊皮别克告诉牧民们“山羊浑身都是宝”,养殖山羊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却遭到哈迪夏的反对,因为山羊吃草根,会破坏草皮;当胡玛尔看到有人在草原上四处寻找“冬虫夏草”和“贝母”时,厉声呵退他们,看着被肆意挖采过的草原,他痛心不已;因为“山羊的粪便碱性太大,太破坏草地”,胡玛尔与族人一道劝说羊皮别克不要鼓动大家养山羊,共同保护草原;后来,草原旅游业日渐发达,游客散去后,苍老的胡玛尔捡拾游客们留在草原上的垃圾……影片中,人们守护草原的情节俯拾皆是,这是草原上的民族尊重自然的充分体现。与草原人尊重自然截然不同的,是随着“祛魅”主义盛行,自然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人类借助科技手段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多,掌控感越来越强,自然成为征服、奴役的对象。人与自然的相处完全失衡,后果也接踵而至,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海洋污染、资源匮乏、某些物种濒临灭绝等一系列环境危机,给了人类当头棒喝式的警示。在浮躁的社会背景下,哈萨克民族尊重自然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利益主导的发展观的有力驳斥。从思想和学术层面来说,在过去三十年,以环境伦理广为人知的一般领域已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奠定了基础。以舒马赫的专著《小即是美》为灵感发起的一系列运动,如深层生态学、佛教经济学、深绿色宗教、动物伦理、生态女性主义等,已经为将大自然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为超越理想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在影片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曾繁仁先生提出的“生态同情”。因着哈萨克族对草原的特殊情感,他们对草场、动物等所有草原上的生命体衍生出一种由热爱而来的同情、怜惜。在这样的情感中,既有对游牧民族对草原上其他生命的敬畏,也是游牧民不以“人类中心主义”对待其他生灵的体现。影片中,在整个阿吾勒都即将动身转往春牧场时,哈迪夏一家却因为一窝无人照顾的雏燕而迟迟不肯动身,哈迪夏也为濒临死亡的母骆驼伤心落泪,怜悯失去母亲的驼羔,这种人与周遭非人类生命物体休戚与共的情感书写,在哈萨克原生态电影《永生羊》中也得到了充分表达。在叙事结构上,《永生羊》同样以四季牧场的转移为时间和空间背景,以羊这一动物贯穿影片始终。小羊萨尔巴斯是小哈力最好的伙伴;乌库芭拉在暴风雪中为小羊羔找奶;哈力成年后,用羊为奶奶的去世进行了献祭……影片借羊传达出哈萨克民族对生命的虔诚与敬畏,展现了哈萨克族的生态平等与生态同情。
无论是尊重自然、生态平等或是生态同情,其本源皆是因为哈萨克民族对自然的珍视。自然是人类的来处,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更是人类永享幸福生活重要的保障。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极其重要的一点,哈萨克人才能与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灵和谐相处。影片中采用DOCU-FICTION,即纪录加故事的样式,将草原的壮美与草原人的生活娓娓道来,如同一部壮丽的史诗。影片多次运用航拍镜头俯瞰草原,将草原风光秀丽壮美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如一幅悠长的画卷,成为观众所向往的“诗意的栖居”之境。
影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富有情感的表达,朴拙又细腻,极具诗意,颇有浪漫主义之姿。谛视当代文学、影视等各类艺术形式,不难发现,自然的呼吁再次盛行,文本和影像等媒介的传递启示着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启示着我们并不能仅用经济的字眼来衡量我们的福祉。浪漫主义的重返,是人类在“让资本蔓延,还是让地球黯淡”这一关键十字路口的选择倾向。正如加拉德所说:“我们在迅速地消耗那点仅有的、先天的希望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接受浪漫主义所赠予的对自然的珍惜和信心。”影片中的浪漫主义,还在于深描自然之美,广袤无边的草原,崇山峻岭中的森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给大地复魅的过程中隐喻着生态和谐、天人合一的现代化建设观,以及这一建设观当下、未来的图景。
三、转场之“后”:生活在别处与何处是家乡
影片中有多次“后”的表达——风雪之后、转场之后、定居之后等,这些镜头的切换都关乎哈萨克族生活的巨大变迁。对于后现代的“后”字,利奥塔如此解释,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后’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时性的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很明晰”,他据此提出,“‘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从影片之外的现实角度来看,在转场之后,定居之后,草原的传统容纳了现代性之后,人们要如何继续生活?面对现代性的侵蚀、传统的日益消解,草原人的身与心要归于何处?80后的新锐导演李睿珺在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给出了相似的表达。该影片充满了对生态文明的深切关怀,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内心的焦虑与迷茫,当面临文化、自然和社会等多重生态危机之时,当本民族的历史厚重感被现代化逐渐消解之时,当诗意、歌声和母语被渐次遗忘时,人们心中不禁发出疑惑:何以为“家”?影片中爷爷说道:“好多年轻人,卖掉牛羊,搬到农场种地。到处开垦耕地,到处打机井,井里的水也都干了……还有的去淘金,去了城里打工,再也不回来了……”爷爷在离世前,骑着马在草原上唱道:“绿色的草原呀,正在消失;奔流的河水呀,早已干枯。”让爷爷悲伤的,不仅是草原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更是当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经济来到草原时,人们内心所面临的危机。当传统遭遇现代,人们满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风俗的爱意与不舍,却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远去的牧歌》中的游牧民们同样面对这种两难的选择。影片中有这样的一幕,哈迪夏的小儿媳提议去城里打工,也想像别人一样拥有摩托车。哈迪夏的小儿子杜曼只得与哥哥巴彦商量,将母亲交由哥哥照顾,这无疑违背了母亲跟随老小生活的传统风俗。在兄弟俩对话的镜头中,前景是一匹马与一辆摩托车“相视而立”,象征着留守草原与进城做边贸生意,后景是争执的兄弟俩,巴彦希望杜曼能遵循传统,而杜曼一心向往城市与现代化生活。这一幕展现出了两重矛盾:一是留恋与出走。与老一辈哈萨克牧民对草原深切的留恋不同,多数草原年轻人渴望走出草原,渴望经济富足,向往安稳舒适的现代生活;另一重矛盾是以巴彦(马)和杜曼(摩托车)代表的民族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当繁华的城市生活吸引着年轻人出走草原进军城市后,民族传统将面临断层的危机。我们知道,现代对于传统的消解,多数肇始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蚀。纵观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人们远离了生养自己的土地与家园,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也导致了资本对人的异化。影片中的杜曼离开草原后,婚姻屡次失败,事业迷茫,人生陷入困顿,显然,杜曼并没有如他所愿般顺利地适应城市生活,成为游离在城市与草原重建地带的“他者”。影片也借此反映了一个潜在问题,即社会急速转型期间,个体如何重新建构起对自己身份的认知。
当代电影中标志性的地方建筑、风景、事物等已成为镜头叙事的惯常表达,而在《远去的牧歌》中,草原成为不断变换却始终如一的叙事空间,甚至成为本片潜在的叙事主线。格伦·A.洛夫认为,随着人们对生态思维的日益重视,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交叉领域的迅速整合,人文学科有层出不穷的新方法出现,如生态批评观点就认为“地方似乎随时出击,以恢复它作为至关重要的人文观念的地位”。草原这一“地方”,是哈萨克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草原与游牧生活某种程度上成为草原人的根。段义孚先生在《恋地情结》中提到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类普遍都具有恋地情结,在此处地与自然基本同义。他认为自然环境不仅繁育了人,同时也影响了人的时间观、世界观和宇宙观。自然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庇护。当人们涌向城市,便失去了自然的庇护,失去了根,失去了精神家园。人们失去庇护,难以掩盖精神的虚弱:人们游走于城市,却无法融入;流浪于荒野又无家可归,僵持着戒备来掩饰自我的非真实感。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规划牧民大规模定居,这一措施的出发点在于维护草原生态的平衡。影片中,为了进一步落实“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生态建设目标,为了“美丽的草原休养生息”,胡玛尔和他的族人们进行了最后一次转场——下山定居。事实上,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及全面退牧还草的政策,大量的哈萨克牧民开始了定居生活。不可否认,这一举措改善了哈萨克牧民的生活条件,促进了经济发展,对草原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如此一来,历史悠久的哈萨克游牧文化也受到了撼动,对于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来说,定居点的兴建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四季转场的生活方式,对传统生产方式也将产生极大冲击,当人们不再转场,那么与之相关的节日、风俗等也将失去其依附的基础,代代传承的游牧文化可能面临日渐式微甚至退出历史舞台的局面。政府为此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如创建文化保护区、制定文化保护规则等,希望能够以此使哈萨克游牧文化得到可持续性的保护,让草原游牧文化能够得以长久保存。从这一意义上说,《远去的牧歌》实质上也是一种“抢救式的拍摄”,以一种记录的方式保存了草原上鲜活的面貌,这样一种写实的方式以镜头诗意地记录,唤起观众的某种意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替中,草原的内在永远无法更改,那是悠扬的牧歌,也是草原精神的原力。
从影片结尾可以看出,国家愈发重视对于牧区草原的保护。这一变化也折射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们生态文明建设走过的历程,在发扬中国生态意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生态美学的路上我们仍在探索和努力,先进、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既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彰显,也是最能引起人们行为和价值观变化的途径。在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途径与发展之道,这是因为,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来都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我们探讨宇宙之奇妙、人生之轨迹、道德之约束。
屈光参差对弱视来说是公认的危险因素。所谓屈光参差,是指双眼在一条或两条子午线上的屈光力存在差异,人群中双眼屈光力完全相等者较少见,多数表现有一定差异。我国2011年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发布的弱视诊断专家共识中指出双眼远视性球镜度数相差1.50 D或柱镜度数相差1.00 D为屈光参差性弱视的危险因素[6]。屈光参差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有研究表明其和遗传机制有关,胎儿包括出生前的胚眼发育以及出生后双眼正视化进程差异等眼球发育平衡的因素如受到影响,将导致屈光参差的发生[7]。双眼轴增长速度不同,前房深度不同,角膜曲率不一致等均会造成屈光参差[8]。
其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化倾向在数千年前的中华文化中就已出现,具体表现为一种整体性观念:宇宙是一个生态整体,个人、家、社会、国家与自然都共生在这一个整体之中,有机地联结在一起。道家、儒家都有与这个宇宙生态整体相联结的主张,如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境界“逍遥游”,主张打破个体生命的局限,渐渐地同化进宇宙生命的整体;再如儒家的“万物皆备于我心”,将宇宙整体内化于个体之中,这一数千年前出现的生态化倾向几经演变,至今仍然保留在我国的生态文化观念中。中国的文化中,并没有类似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并不存在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宇宙等级模式。一切有形的物体或生命,是平等、相互依存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生态化理念,如崇尚自然、反对人为;对欲望倡导自然的节制态度;对于取用自然,保持着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在审美领域,自然物象被较多地选用,用自然的意象营造“意境”之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生态主义资源。因此,可以说,面对当前人类共同的困境时,我们所提出的“自然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实际是一种对传统的一脉相承,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生态观。
四、牧歌不辍:民族文化与非遗传承
除了对草原生命的敬畏,《远去的牧歌》中对于哈萨克牧民的生活全貌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影片用镜头对哈萨克游牧民们的生活、风俗、劳动、观念等进行了记录与再现,具有民族志的内涵。这样的记录其实是对草原文化的抢救性保存。影片制作团队谙熟哈萨克民族文化,大量的民族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也由此被导演不露痕迹地融入镜头中,在面临变迁的现代化进程中,影片很好地处理了遗产的地方性和传承形式。彭兆荣认为,任何遗产都有一个“地方性”,首先指遗产的“所在”,其次,在当下的全球一体化时代,遗产的变迁方式和变迁方向必然会被改变,即遗产的再地方化。下山定居建立新家,不仅是个体、族群的安定,也是文化遗产的安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中,传承需要人来维系,文化也需要适应新的形势迁入一个新的家园,因而,博兰古丽的回家也有了未来的意义。
关于文化,利奥塔认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在文化中不存在工作,不存在宗教虔诚,也不存在被人们作为表现而从事的艺术。类似的,不存在有教养和没教养的活动。没有必要通过专门的特殊仪式或庄重礼仪来证明存在着文化,证明它的性质。生活的全部就是这种证明”。影片中的细枝末节的生活记录其实就是哈萨克的文化遗产,在不断的转场中,季节更替,场景变换,但生活中的细节是固定的,驯鹰、毡房、刺绣、奶制品制作等在日常生活中的积淀组成了游牧文化。这些文化并没有专门的仪式,它融入在人们高兴时弹起的冬不拉里,渗透进人们喜悦时跳起的《黑走马》中,在哈萨克民族生活中一点一滴延续。
无论在影片或是实际生活中,伴随着牧民们转场的主要家当之一,就是便于拆装、易于转运的毡房。毡房“制作方便、质柔量轻、拆卸简便、极易搬迁,取材几乎全来源于大自然的树干(且不用大材)和自己牧养的牲畜的副产品等土产材料”,毡房是哈萨克游牧民们生活智慧的结晶,因其装饰美观、拱形的顶圈具有家庭乃至民族的象征意味,而成为哈萨克民族特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定居点的增多,根植于游牧传统的毡房的存在必要性面临消解。毡房似乎成为哈萨克族在婚礼等人生重要场合及传统节日重新搭建并展示一种民族集体记忆的方式,人们以此表达对传统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的追忆,但追忆的背后是切实的远去。
哈萨克族题材电影《永生羊》的导演同样巧妙地将哈萨克民族的文化融入镜头中,在最微末的生活日常中呈现哈萨克特有的魅力。当乌库芭拉在婚前遇到了歌王阿肯并芳心暗许时,她弹奏冬不拉琴向意中人诉说自己的情感;她改嫁凯斯泰尔,却不得不离开时,依旧用冬不拉琴传递无法言说的话语;在哈力的成年礼上,人们用冬不拉弹奏欢快的音乐,为少年的成长送上美好的祝福……冬不拉可以是草原人的各式情感的表达,是草原人的话语与消遣。冬不拉琴是哈萨克族最喜欢的艺术表现工具,其种类多样,琴身大多由整块木材雕凿而成,琴弦由羊肠或尼龙制成。中央民族大学冬不拉琴专业学生叶尔那尔依据自己对琴声的理解,将冬不拉的风格做以区分,他通过古代哈萨克汗国的三个玉兹(juz,哈萨克语“部落”之意)分布将冬不拉“奎依”(哈萨克语“乐曲”之意)进行分类:东部的大玉兹多以抒情、旋律性较强的作品为主;中部的中玉兹偏重于模仿动物、自然界等作品;西部的小玉兹由于靠近里海则多以快速、多变风格的作曲为主。此外,民间弹奏冬不拉琴的手势也与表现动物姿态有关,富于变化的弹奏手势形象地展现了草原上泉水潺潺、鸟鸣婉转、骏马奔腾的声音。冬不拉为草原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与乐趣,成为草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在2009年,冬不拉已被列入我国哈萨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中。
而令乌库芭拉一见倾心的歌王“阿肯”,也代表了一种草原上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草原上孕育了优美动人的诗歌,“阿肯”就是诗歌的创作、演唱和传播者。“阿肯弹唱”既有自弹自唱形式,也有两人或多人对唱形式,自弹自唱多是演唱民歌或演绎叙事长诗,对唱则常为即兴创作,具有比赛的意味,是一种比才斗智的活动,极具活力。阿肯对唱是一种民族特色非常显著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是口头文学艺术的精华和典型,是哈萨克族的“红楼梦”。因而,阿肯对唱其实也可以视作世界各地及其他兄弟民族了解哈萨克文化的重要途径。在2005年,阿肯对唱已被列入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舞蹈作为一种形式简单的娱乐方式、庆祝方式,已成为哈萨克族生活中最靓丽的一笔,哈萨克族舞蹈风格欢快幽默,能够为单调的草原生活增添色彩。在《远去的牧歌》中,舞蹈的画面多次呈现。当博兰古丽考上大学时,大家起舞为她庆祝,在欢庆那吾鲁孜节时,大家身着盛装,欢快起舞。在《永生羊》中,亦有多处舞蹈镜头。哈萨克族能歌善舞,传统的舞蹈形式简单,不受表演场地限制,常以草原或毡房为空间,在视觉上呈现一种环绕性。因此,舞蹈者与观看者之间距离较近,便于欣赏,具有某种互动性,同时观看者也能够感知到舞蹈者的情绪表达,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哈萨克舞蹈的内容覆盖较广,包含民间传说、劳动生产、民族风俗文化、与动物相关的舞蹈等,其中传统舞蹈“阿尤毕/哈熊舞”(与动物相关)、“卡拉角勒哈/黑走马舞”(民间传说)、“克模子毕/马奶舞”(民间风俗)等相继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然而,哈萨克传统舞蹈的根在草原上,当脱离了孕育它的土壤,传统舞蹈与自然、牧民生活的紧密联系渐次瓦解,由自娱性向着商业性或是某种功利性发展,失掉其淳朴本真的意味,“非遗”保护中的过度商业化或不当“指导”也使其原生态性难以保留。
五、哈萨克的歌声中有草有马
电影不能没有音乐,正如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绿色,哈萨克人的日子离不开草原和骏马。来自哈萨克的阿肯叶尔波利在歌里如此唱道:“涌动的山河,神圣的天籁,大自然世界,滋养着心灵,微风拂天明,山亲怀抱里,花木草醇香……”悠扬的冬不拉声随着歌者的低吟浅唱,仿佛草原的河流在缓缓流淌。然而,这悠扬的哈萨克歌声终究是渐渐远去了。
《远去的牧歌》不仅是一部民族史和民族心灵史,一部蕴含着深厚生态意味的民族志,一部既有转场、游牧迁徙又有定居的辩证的民族志,更是一部呼吁着人们关爱自然,关注我们的来处,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书写。从后现代文化语境来看,各类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的直观表现。大众文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开始日益追求短暂的感官快乐,审美逐渐世俗化。当代美学发展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感性主义,力图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而鲜少注重深层次内涵的挖掘,形成了图像狂欢的现象。
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症结与困惑,一种声音开始呼唤传统文化,期望从先哲处汲取精神的滋养,来填补现代人在面临社会转型时心智的失落与行为的无措。对于有生态意识的电影创作者来说,极有挑战的职责就是要培养观众对自然的关切与兴趣,这种兴趣的培养与呼唤,要将一种价值观深植于受众心中,让受众以一种长远的思维去取舍,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去生活。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精神生活的贫瘠让人们习惯于逃避思考,因此,当下的电影需要自觉地“担起一种职责,将观众指向一种与非人类自然的更深层、更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将人类意识引向对自身生活的环境的充分思索”。《远去的牧歌》便是这样的电影,影片在史诗般的叙事基调下,述说了哈萨克民族在追求真实与美好过程中的坚韧,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草原依恋的情怀,在记录了悠扬的民族变迁史之外,寓有更深层次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