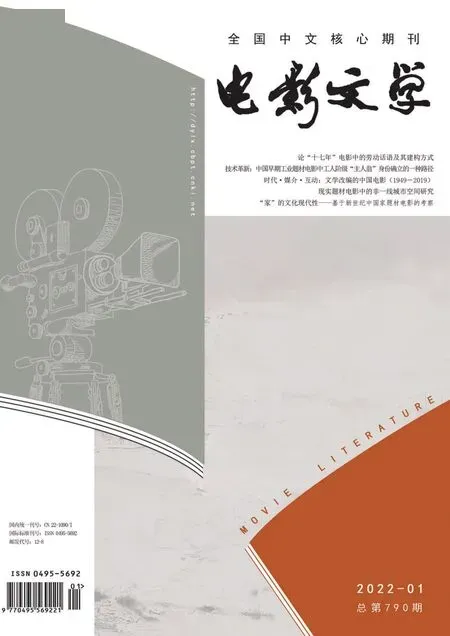鹏飞导演的喜剧性表达和悲剧化内核
2022-11-13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1130
董 莉 (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鹏飞,198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毕业于法国国际影像与声音学院导演系。2008年,担任蔡明亮剧情片《脸》的副导演。2013年,担任编剧的剧情片《郊游》获得第70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15年,执导剧情片《地下香》,该片获得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和芝加哥电影节新锐导演竞赛单元金雨果奖。2017年,执导的剧情片《米花之味》入围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该片于2018年4月在中国公映。2021年3月,执导的剧情片《又见奈良》在中国公映。从《米花之味》中对留守儿童、返乡者的展现到《又见奈良》中对不同文化的中间人、战后遗孤等议题的触及,鹏飞的影片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社会学性质,而在关注边缘群体的同时,他又通过朴实简洁的镜头语言,使所要描写的人或者物避免陷入奇观化的状态,从根本上对其生活中的困境进行描述。
在鹏飞所创作的影片中始终充溢着一种举重若轻的叙事风格。沉重的社会性议题被他有意地用幽默、温馨等元素进行包裹,从另一个切面缓解了话题的冲击力,使其融入日常当中。无论是《米花之味》还是《又见奈良》,影片的格调都是松弛的。但这种叙事手法并不意味着对话题严肃性的逃避。鹏飞对于社会议题的日常化处理,缩小了它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将一种远方的困境重新构建为确切可感的现实影像。
一、《又见奈良》:文化区隔下的寻亲之路
作为一部以日本战后遗孤为主要题材的电影,《又见奈良》就像它所聚焦的人群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着不被观众所接受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历史沉重的烙印。对于苦痛记忆的铭记于心或对于政治的漠不关心,都将日本遗孤置于一个长期不被关注的境地。因此,影片对于战后遗孤的呈现要经过多方面的考量。同时,这种风险还来自影片在情绪上的处理。轻浮的原谅或者肤浅的阐述,都将使影片滑向脱离实际的处境。而如何描述和呈现战后遗孤,事实上还与如何看待日本侵华战争密切相关,它是反战这一思想脉络在当下的延续。可以说,《又见奈良》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个难题。处理它,不存在任何取巧的方法。
于是,鹏飞在《又见奈良》中延续了此前《米花之味》中的叙事手法,即以轻松幽默的外壳来包裹沉重宏大的内核。影片在片头以一段时长两分多钟的动画影像来交代整部影片的叙事线索,沉重、惨痛的历史被色调明亮的画面和轻快飞扬的音乐所转置。关于国家、民族和战争的宏大叙事被移植到个体与个体间的母女之情上,成为影片一种在隐的话语。而影片绝大多数的幽默片段恰恰是来自这种在隐的话语。譬如小泽的前男友来到她的住处收拾物件时,陈慧明下意识地用俄语同他对话,并在告别时说出了俄语的再见(“noka”)。这恰恰与日语中的笨蛋(“baka”)同音。这种文化区隔下的巧合和小泽男友的郁闷自然令人发笑,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片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为何陈慧明会说俄语,为何她在异国的环境中会下意识地说起俄语?阿尔都塞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曾提出一个观点,即症候式阅读。文本中的空白、沉默和缺陷是潜藏在旧的问题体系中不被人意识到的新的总问题的症候。症候式阅读要求读者不仅关注文本中在现的部分,更要关注文本中未被提及、在隐的部分,并且这些隐藏在文本表象之外的内容往往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如前文提及,国家、民族和战争这一类叙事是影片在隐的话语。谈及近代中国东北的历史,必然绕不开日、俄两国。陈慧明本能式地用俄语应对,事实上潜藏着一段中国人民被压迫的苦痛历史。
类似的幽默片段在影片中可谓比比皆是。在寻访陈丽华的途中,小泽、陈慧明和吉泽三人偶然地来到了一对战后遗孤的家中,并受到了他们的款待。在吃饺子的过程中,遗孤夫妇为他们自弹自唱地演奏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此时,样板戏背后浓郁的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被淡化了,它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辨认标志,近乎与接收电视信号的大锅同构。“党给我智慧给我胆”这一句歌词的出现有着强烈的戏剧感和冲突感。这不是解放全人类的宏大叙事的延伸,而是一种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身份错置的反差感。于是,影片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进行了回望和梳理,对所谓民族主义的迷思进行了回应:出生并成长在中国的日本人究竟属于哪一边,侵略者的后代是否依然有着侵略者的天性。而随口切换中日双语的拖车司机更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违和感和喜剧感:前一秒是彬彬有礼的日式对话,后一秒是熟悉的东北乡音。这里可以引入帕克的社会距离的概念: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社会距离越大,相互之间的影响越小,描述的是个体或群体间相互认同、了解的程度,描述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政治地位、空间位置、文化背景、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差异。战后遗孤独特的身份赋予了他们与中、日两国的本土社会始终存在着的社会距离。他们被置于两者之间,始终无法对其缩进、消解。而演员的现实身份又凸显了电影作为一种影像媒介记录和承载历史的功能。讲着纯正中文、熟悉《智取威虎山》的遗孤们的孩子却只会说日语,未尝不是出于对其身份辨认的考量。
当然,影片最重要的仍然是陈慧明寻找养女的叙事线索。作为一代战后遗孤的故事对于主线来说,只是点缀。这又使得影片具备了公路片的特质,即通过旅途来接近目标,并以旅途中的人物和事件来对影片所要阐明的话题进行全景式的描述。拖车司机、交通警察等日本战后遗孤的出现,既丰富了影片的内容和层次,推进了叙事的发展,又从另一个维度暗示着陈丽华和小泽等人在日本生活的现实处境。不被前男友家人接受的小泽和血缘鉴定失败的陈丽华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因此,不难理解,在得知陈丽华死讯的那一刻,小泽为何在车上泣不成声。没有回报、没有结果的寻找便是陈慧明此行的答案。但她尚不知晓这一切。忘记揭开的相机镜头盖和不存在的胶卷分别从两个节点提示着答案。前者还有着些许的喜感,后者则是彻底的悲凉。有关相机的片段一前一后相互对应,更加凸显出喜剧和悲剧的互通。
而《又见奈良》用幽默来包裹悲剧的最直观表述便是陈慧明在奈良的湖中放生海螃蟹的一幕。此刻观众的莞尔一笑对应的是影片后续对陈丽华人生的逐步揭晓。海螃蟹无法适应淡水,只能死去,而陈丽华无法为日本所接纳,最终在公寓中孤独死去,这种主体形象的变更展现出影片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同时,语言作为影片区别文化的一大标志,也往往面临着失效的情况。陈慧明和退役警察吉泽在木椅上运用肢体进行的交流、陈丽华在信中提及的她和聋哑人管理员的友情反复佐证着语言既塑造了身份,又产生了隔阂。无声似乎是影片所要传递的最终氛围。在影片的片尾,三人各怀心事地走在夜里的大街上。吉泽思念着女儿,期盼着她的来信;陈慧明思念着陈丽华,不知她如今身在何方;小泽已明白一切,但她无法说出真相,并不由得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在日本的处境。此时,邓丽君的歌声响起,携带着三个人的症结一同步向夜晚的深处。人与人之间的短暂连接可以给予个体慰藉,但前方仍然存在着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求。正像信中的谎言可以短暂地安抚母亲,但生活冷酷的事实依然无法改变。
二、《米花之味》:现代变革下的母女冲突
在《米花之味》中,鹏飞便确定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举重若轻,拒绝奇观。云南山区在今天的中国正如20世纪的中国在世界中的面貌一般。但导演鹏飞有意地避免了奇观的贩卖,即通过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营造一种云南山区与现代都市之间的距离,进而将那里的一切陌生化、非日常化。在《米花之味》中,一切情感的脉络都是切实可感的。宗教、傣族的风俗并未使观众产生遥远感,并将其视作一种前现代的景观。从这个角度来看,《米花之味》是十足现代的。
而贯穿影片、支撑影片叙事的母女冲突也有着极强的可感知性。在有关留守儿童的题材中,儿童往往都是一种被遗弃、无助的形象,出走的家长们则面目模糊。这种塑造方式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譬如呼吁人们关注留守儿童,关注乡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迎来的种种阵痛。但它将个体概念化、扁平化,缩小了观众与人物的共情空间。同时,今日的留守儿童也与前十年大众的印象截然不同:“他们不怎么喜欢去外面,更希望当个本地土豪,不喜欢大城市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精神空虚、性格叛逆已成为当今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在《米花之味》中,母女之间的矛盾既受到地理位置和本地文化的制约,又具备着某种可通约的普遍性。母亲的长期缺席使女儿未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爷爷的放纵几乎使女儿任意妄为。相比和归来的母亲交流沟通,女儿更喜欢对着手机打游戏。母亲对她来说,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存在,是一个突然出现、毫不讲理的权威形象。她的叛逆源于缺乏父母关怀导致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敌我的辨认中,母亲、老师等人被下意识地划入了敌人的一方。越是管教,她便越是反抗。
但在影片中,这种反抗又被巧妙地消弭了。综观整部《米花之味》,观众难以发现任何强烈极端的冲突。女儿在面临斥责时,往往是默不作声的。当母亲没收女儿的手机,女儿并未大吵大闹。当女儿和同学在寺庙前打游戏时,母亲关掉了Wi-Fi,说,佛需要休息了,女儿未多言语。女儿以一种固执、承受的姿态化解了母亲的怒火。这种对垒恰恰暗示着她们对彼此理解的渴望。当母亲以家长的形象出现时,影片始终弥散着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乡村对外来者的抗拒,来自女儿对缺席者的埋怨,来自本土文化对出走者的不理解和污名化。而《米花之味》并未使这些情绪走向苦大仇深的地步。这得益于导演有意的松弛化、幽默化的处理。女儿事实上表征着传统的云南山区的文化,而母亲则表征着进步、现代化的都市文化。
那么,该如何弥合和化解母女之间的隔阂呢?影片给出的答案十分温馨,即理解本土的传统和接纳自我的过往。一同在锅中炸制米花,一同在钟乳石洞对着佛像起舞。这些片段彰显着母亲对于过往的集体文化的复归,亦表明了女儿对于母亲的理解。在影片中,母亲曾经脱下傣族特色的裙子,准备离开,但她又穿了起来。这可以视作现代变革下个体由彷徨走向坚定,亦是一个母亲对于女儿扎根生长的世界的理解。
结 语
鹏飞导演的电影有着一贯的克制风格。在轻松写意的镜头和幽默喜剧的叙事背后,他总是试图将沉重的社会议题日常化,缩小其与生活的距离,使人们能够深切感知人物的处境和命运。在鹏飞的视野中,留守儿童所在的云南和战后遗孤所在的日本绝不是阴郁、沉闷的,他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希望和闪光点。而正是这种掺杂着幽默元素的喜剧化表达,使他能够更为顺利地传达出影片的悲剧性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