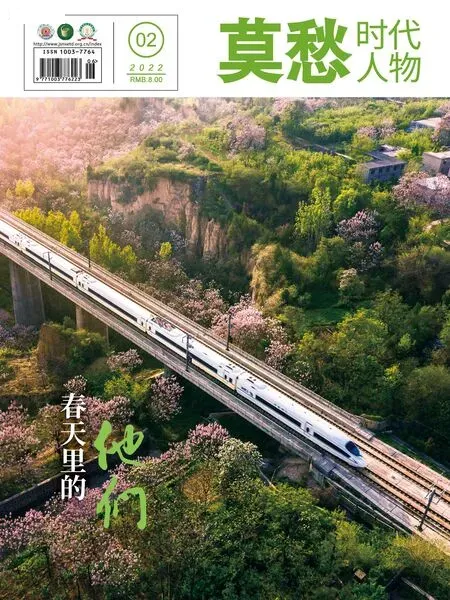怀旧,废墟上的徘徊
2022-11-11叶兆言
文/叶兆言
人之本性,难免喜新厌旧,怀旧却会有别样风光,会很时髦,会显得很有文化。十多年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老师曾经非常认真地问我,《南京人》中提到的那位老先生是谁,说这老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一针见血。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南京人》是我的一本旧书,他问的这番话是小说家笔法,是我伪造的,所谓老先生并不存在。董健老师很失望,做学问的人总是严谨,他向我打听出处,大概也是想在文章中引用,听我这么一说,只能叹气摇头。
我编造的这番话是什么呢,为什么董健老师会感兴趣?在《南京人》这本书中,我提到了民国年间有位老先生,说北京是个官场,就看谁官大;上海是个洋场,就看谁钱多。因此要做官,必须去北京;要挣钱,必须去上海。南京这地方什么都没有,做不了官挣不上钱,只能退求其次,老老实实做学问。老先生是文学加工的产物,结果董健老师信以为真,也引起很多南京人的共鸣。常常有人当面夸我,说这话有道理,说到了节骨眼上,说出了南京人的性格特点。有些在官场上混得不得意的人,甚至因为这番话,要与我结交,要跟我一起喝酒。
多少年来,作为一名小说家,我一直以偏重怀旧被读者所认同。不知不觉就成了遗老遗少,你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青年作家,已有人写文章将你归类老作家、老夫子行列。浑水摸鱼的怀旧让人多少占了些便宜,当然,有时也吃亏,毕竟老了会有过气之嫌。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怀旧可以用来励志,励志不等于得志,仅靠怀旧在文坛上打拼,显然没太大出息,也不可能会有更好出路。俗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一味怀旧,注定死路一条。小说家怀旧与史学家不一样,小说家可以想象,可以合理想象,甚至可以不合理想象。只要说得好,胡说八道并没有太大关系。
小说家们虚构人物,设计好故事,在史学家眼里是一堆幼稚笑话,错误百出漏洞无数。但是大家目的并无二致,都是温故而知新,就好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小说家也好,史学家也好,很少无缘无故地去怀旧。区别就在于方法不同,手段各异,真实标准不一样。
怀旧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小说家手中的利器,如何利用怀旧,怎么利用怀旧,有很多学问可以做。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想不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怀旧。简单地为怀旧而怀旧,显然会有创作上的风险,小说家的怀旧总是别有用心,怀旧必须要有情怀,要有理想,要有最起码的人文关怀。第二,必须告诉读者,小说中的怀旧往往是虚构,文学的真实从来就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换句话说,民国年间南京有没有那么一位老先生可以不重要,原话是否如此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接近真相。我的关于南京人的性格描写,显然带有理想成分,也就是说希望南京人是那样,我只是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南京人。
事实上,我们都明白那些最基本的道理,都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都知道真相并没有那么美好,南京人与北京人、上海人并没有那么大差异。现实是残酷的,很难让人满意,哪儿的人都想当官,哪儿的人都想挣钱,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说到底还是个文学人物,无怀氏之人与,葛天氏之人与,如果我们真相信五柳先生们确实存在,那也太天真了。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些差距,古人衔觞赋诗,只不过是为了以乐其志,也只能以乐其志,这一点,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早已经说得很清楚。南京夫子庙的秦淮河边有个桃叶渡,说起来,也是一个著名去处,有历史有来头。喜欢书法的人都知道,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叫王献之,字写得比他爹还好。这个王献之风流倜傥,有位爱妾叫桃叶,住在河对岸,他常常亲自在渡口迎送,并为之作了首《桃叶歌》: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
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
历史上的传说往往不靠谱,不知猴年马月,有好事的人怀旧,在秦淮河边竖了一块石碑,基本上就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故事给落实了。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都这么说,大家也就深信不疑,都相信桃叶渡就在秦淮河边。明朝有位诗人叫沈愚,觉得这事不能这样以讹传讹,下功夫去考证,得出桃叶渡绝不可能在秦淮河的结论,确切地点应该是在长江北岸的“桃叶山”下,那里的古渡口才是原址所在,因此也写了一首诗:
世间古迹杜撰多,离奇莫过江变河,
花神应怜桃叶痴,夜渡大江披绿蓑。
沈愚搁在历史上没名气,这首修正考订桃叶渡的小诗,自然没什么影响,知道的人也不多。结果就是,同样是怀旧,大家对真相都不感兴趣,王献之《桃叶歌》中明明白白写着渡江,短短一首诗中有三个“江”字,却非要视而不见,认定桃叶渡就在秦淮河边,就在今天大家都错误认定的那个地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怀旧中,真假有时候并不重要,将错就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择,这样的选择又会有什么样后果,这才是最重要的。选择性的怀旧完全有可能塑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毫无疑问,南京是一个滨江城市,然而它的城市建设,有意无意地总是沿着秦淮河在展开。多少年来,长江沿岸基本上都是破烂不堪,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江边,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滚滚长江显得有些宽大,好像小桥流水才更适合南京,“夜泊秦淮近酒家”成为这个城市最好的写照,醉生梦死灯红酒绿,很自然地就成为标签,结果便是,像刘禹锡这样的大诗人,完全可以不用亲临南京,完全可以不用体验生活,就能轻而易举地写出脍炙人口的《金陵五题》。刘禹锡在这五首小诗前面有自序说明,强调自己并没到过南京,他的怀旧基本上就是凭空捏造。桃叶渡与南京的关系大可一说,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个文人与爱妾的八卦,而且与这座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南京人喜欢说六朝古都,所谓古,也是怀旧的意思。可惜这个旧太遥远,说来说去,都是些不靠谱传闻。
南京几乎找不到什么货真价实的六朝文物,原因同样可以从桃叶渡说起。当然,这个桃叶渡不是秦淮河边那个伪造的假古董,而是长江对面的桃叶山古渡。想当年,隋炀帝杨广曾在此练兵。那时候的杨广年轻有为,还没被封为太子,他在桃叶山下秣马厉兵,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南朝。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在桃叶渡那端,杨广虎视眈眈地做着准备,而在大江这边,陈后主仍然在醉生梦死,“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很快隋兵渡江,六朝灰飞烟灭。“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隋文帝下令杨广将南京这个城池给废了,于是该烧的烧,该毁的毁,这也是为什么南京这个古城很难见到六朝文物的真实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南京真的就这么被毁了,它归镇江所管辖,城市地位大大下降。
一个城市繁华起来了,一个城市破落衰亡了,总会有这样那样原因,怀旧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探索这些原因。南京的繁华是它曾经是古都,南京的破落衰亡也是它曾经是古都,繁华的原因同样可以成为萧条的原因。对桃叶渡遗址的怀旧,有助于我们用一种别样的眼光打量南京,我们回忆往事,徘徊在历史的废墟上,感慨六朝繁华,流连吴宫花草和晋代衣冠,说来说去,所有的怀旧和追古,结果还是为了抚今,为了讨论当下。事实也是这样,对于这座城市的凝视,如果我们的目光始终只盯着秦淮河,只是关心它的兴衰,只是在意它的发展,显然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