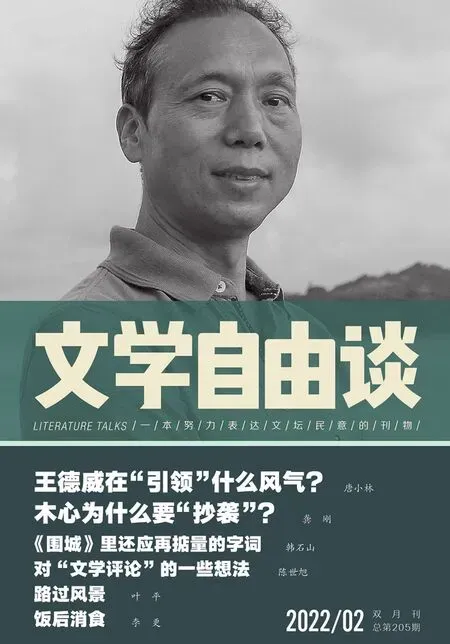路过风景(外一题)
2022-11-10□叶平
□叶 平
感觉中,上海浦东图书馆是我阅读体验中最舒心的读书场所,除了“高大上”的硬件设施,更有大学校园一样的人文环境,不经意间还会有意外的遇见:一个展览、一次讲座、一部大书、一位名人……
一次去茶水间时,路过一个走廊,抬头见一个门牌,上书“鲍鹏山工作室”,不由惊讶:我刚刚在读的《彀中英雄》就是鲍鹏山所著。他笔下的先秦两汉人物,多是我喜爱的,且文风机智风趣,语言犀利辛辣,胆识非同寻常。此书出版已近十年,还是很耐读——史料之丰富,考证之扎实,想象之瑰丽,以愚之见,比之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出道稍迟半步,似乎有了跟风、模仿之嫌,失去了“一夜成名天下知”的可能性。然而,毕竟是源头活水,虽出自一脉,却又自成一家。原来创新和原创的魅力就在这里。
实话说,在余秋雨之后,我读过不少历史文化散文随笔,鲍鹏山的作品是印象最好的。他没有流行的“穿越时空、宣染史料、自由飞翔”这种“三级跳”式的套路,更无“臆想加呓语、议论加感叹”“新瓶装老酒”的公式化模板,也没有好拿圣贤开道、卖弄学问、故作高深、文字生涩的学院派习惯;有的只是史学家的严慎和机智,更有哲人的视觉和诗人的激情,以及幽默风趣又不失深刻的个性化叙述。他后来由遥远的青海调至繁华的上海,成为上海开放大学教授,没有这些质地硬朗的作品垫底,应该是不可能的。
鲍鹏山是潜心研究先秦诸子的专家,出版《寂寞圣贤》《论语新读》《天纵圣贤》《绝地生灵》《先秦诸子十二讲》等著作,随后以《新说水浒》在央视“百家讲坛”走红。作为沪上文化名人,早已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了,浦东图书馆给他开工作室这种“双赢”的好事是很自然的了。
我在那扇门前踌躇不前,确认不会有错,沙发上坐着的那位看文稿的中年人,应该就是鲍鹏山了。另有两位年轻人在电脑前忙碌着,应该是他带的研究生也未可知。
“泰山”就在眼前,岂能有眼不识?敲门而入的冲动,在即将迈出脚步时戛然而止。我问自己:进去是要表达巧遇名人的崇敬和激动之情吗?是想求教历史随笔写作的秘诀吗?或是要合影留念、在朋友圈炫耀一回?这些显然与我的年龄和心境极不协调,所谓“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飞”。人应有自知之明,何况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尺短寸长都是有的。重要的是,“追星”除了满足虚荣心,毫无实际意义,而虚荣心又是读书人最忌讳的。说白了,读书、思考、写作都是个人的事,能否成名成家、史册留痕,更是个人的天赋和命数。
在读鲍氏《寂寞的圣哲》一书时,见有贾平凹写的序,知道这些文章在屡投不中后,被贾主编的《美文》连续发表。贾当时倡导大散文,正需要这样有历史洞见的作品。读者在认识《美文》的同时,也熟悉了鲍氏。贾、鲍之间,便有伯乐与千里马之谊。序中有个细节,说鲍第一次从青海去西安拜见贾时,送去一个古陶罐,应该是心仪的不凡之物,加上“人是黑黑的,言语不多,很憨诚的那一类”,很得贾氏喜爱。他把那个陶罐放在抬头可见的书架上,遂写下“罐者观也官也,得大者能大观,能大观者则大官”一句。一言中的,十多年后,鲍氏虽未成为紫袍加身的官吏,但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一时名气直追贾平凹,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
这是常识,学问是做出来的,文章是写出来的,半点虚假也会露怯。作家用作品说话是最有效、最牢靠的。靠傍名家、蹭权威、跑关系、资本炒作,也可得到虚名浮利,但结果一定是自取其辱。即使获了某个级别大奖、当了什么主席,也是飞得高,跌得重,成为笑话,被世人轻看,这种例子已经很多。
贾平凹和鲍鹏山都是靠作品说话的榜样。当年鲍若拿不出上等好作品,贾怎会投以青眼?以文章安身立命的书生,缘分和面子从来都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讨来的。伯乐和千里马的相遇是一种天缘,彼此都在寻找,走了很远的路,在某个拐弯处突然碰面,一见如故,然后相互成就,彼此荣耀。这么说,《美文》之与这卷书,贾之于鲍,不好说是谁帮了谁,应该是互为伯仲,彼此有缘吧!
由此想到,古代的人才举荐制要求很高,是对彼此眼力、学养、天赋、品德的双向检验。可惜那个任人唯贤的环境,早已被不堪的人心世相败坏殆尽,千里马和伯乐相遇的佳话,只能去历史的残卷里寻找了。以文坛来看,推荐文学新锐加入作协、进修学习、出版作品、获大奖的伯乐也不少见,但这伯乐多是加引号的,细心盘点一下推荐和被推荐者都是什么人就一目了然了。谁能说背后绝无资源寻租的供需利益链?怕是各有所图而已。至少也是认准了有回报价值的潜力股,不会做赔本买卖。
我在那扇门前徘徊着,纠结着进还是不进。若再年轻十多岁,能拿出让人家刮目相看的“硬头货”,我会毫不犹豫地进门去拜师讨教。可如今就不必了,一个奔六的老男人,既没有成为大众偶像的荣幸,也便失去了作别人粉丝的激情。人一生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见什么人,都是有特定时间和情境的,错过的就永远错过了,勉强自己等于为难别人。想到自己年轻时拜访名人被冷落,请人家签名被拒绝,至今还有羞辱感。虽说是人生苦短,“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也不知以后是否还有机会相见,即使有,如果不合时宜,宁愿“有眼不识泰山”,还是不凑热闹,落个内心宁静为好。
我这种“看客”心理,不少文人应该也会有的。内心总有一点阿Q式的小自信——别人行,我咋不行?与其仰望天空,不如自成风景;狮子的威武与小猫的可爱,小花的灿烂与大树的挺拔,就生命本身而言,没有本质区别。
后来的日子里,我多次路过那扇门,有时见鲍先生独自坐在那里阅读、思考、看手机,我却再没有敲门而入的闪念。我后来关注了鲍鹏山的公众号,那些最新发表的文化随笔,依然是风格独具、“开卷有益”,偶尔看看,会有见字如面的感觉。尽管他不知道,我曾多次悄无声息地路过他的门口,一厢情愿地见过他。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谁都活得心累。不去打扰,对别人和自己都是一种尊敬,特别是对那些名人。对一个作家最好的尊敬,就是默默地读他的作品。话说回来,作家“用作品说话”永远是唯一的“王道”,也是赢得世人尊重的根本。
所谓的自尊,其实很简单,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许多时候,赏景不如听景,相见不如相望。英雄不问出处,相忘于江湖是最好的。江湖大如野又小如笼,鹰击长空,鱼游江河,自有使命和宿命。是鹰是鱼,总会在天空或河流相遇。即使弱小如蚁,也有属于自己耕耘和栖息的一片沃土。
尴尬的阅读
我抱上两卷世界名著和几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东张西望。像饥饿的小鸟,在乱花迷眼中匆匆寻觅到几粒可食的果子,发现还有一个空位等着我,就悄悄走过去。两个埋头电脑的青年用眼的余光感到了我的来到,敏捷地让开已经宽敞的空位。我用微笑报以谢谢,然后从背包里掏出电脑、水杯和手机。他们应该确认我也是资深“书虫”,似乎在说:欢迎老朋友!多么难得啊,我们要挤在一起,度过愉快的一天了。
我这才敏感地发现,这群小弟小妹应该是00后了。他们边看书边敲电脑,还用笔作记录,应该是备考、写论文或做什么创意。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他们没有离开座位,甚至没见他们抬头望望窗外的天空。我有些心疼,那些因久坐而引发的疑难杂症,应该就是在这样的年龄,在这样的苦读中酝酿的。我真想提醒一句:小伙伴们,抬头望望天空,站起来走动一下吧!可又怎能说出口?
我从眼镜的浮光里,看到他们头上都压着一座山,他们挣扎着要爬出来,却怎么也不能。好在已经露出脑袋,明亮的眼睛看到了黑夜里的星光。
恍惚间,大而无“挡”的阅读空间,已幻化成一片鸟儿栖息的森林。各种各样的鸟儿飞来飞去,有的忙着建巢,有的在哺育幼儿,有的在寻找伴侣。大家随遇而安,各有所爱,各得其乐。
旁边那个男生走了,很快就有一个女孩来了。她生的娇小,明眸如月,向我点点头,旋即打开电脑,埋头书本,又画又记,像是有意要让我见证一株雪莲在身边静静绽放的奇观!我看一眼她读的书:《高等数字》《英汉对照实用手册》。
从过道往返时,见大家读的多是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经济、工业、生活类书籍,很少看到有人在读文学书籍,当然也没遇到怀揣诗人和作家梦的知音。
后来的日子里,我特别注意到这个细节,发现文学书库里的读者要少很多,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籍,除了中外名著、二战之后的外国小说、少数流行作家的作品,其他文学书籍的借阅率并不高,特别是当代文学,有许多书已经出版了五六年,还是崭新的。
这里的文学期刊几乎包括了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所有杂志,却极少有人翻阅。我浏览那些大刊名刊的目录,多是熟悉的老面孔和刚刚在文坛走红的新星,少见陌生的名字。我细心阅读了两位文坛“大咖”的文化散文,洋洋万余言,看似满纸锦绣,却是移花接木、东拼西凑,让人读得云山雾海,似乎想显摆自己宝刀不老、才华横溢,顺便要检验读者的智商和耐心。曾经对他们残存的一点好感被消磨尽净,取而代之的就是不屑。不禁想弱弱地问一声:这是何苦呢?难道节制一下发表欲就吃亏了吗?岂不知发表那种掉书袋的、华而不实的、自以为是的文章会自取其辱吗?这和那些天天在网上刷存在感、晒幸福的人有啥两样?
举目四顾,我在这里的文学阅读无疑是孤独的异数,甚至是尴尬、多余、不合时宜的。难怪有人说,“文学成了小圈子内的狂欢”,“文学成了一群既得利益者的盛宴”。更有难听的:“文学已经死亡”,“当代文学没有大家,也难出大师”。
失落的瞬间,感到了更多的欣慰:文学虽然关乎人类的精神世界,但一个“全民写作”和作家诗人泛滥的社会毕竟是畸形的,如同“全民娱乐”和明星满街跑的社会一样不可思议。再说,文学的衰落虽有时代变化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作家们没有奉献出与时代同步的优秀作品,让读者期待的热情不断降温,终于失去耐心。相信读者是聪明的,他们的选择永远是正确的。
饭点到了,我该去吃掉女儿特意准备的面包和奶茶,可又不见有人和我一样带着干粮。去楼下的餐厅,见还有一些空位。看到我的同桌们和那么多书友都不来吃饭,不知他们是忘记了吃还是真的不饿,我也就不觉得饿了。原来,读书之于“书虫”,真的是能充饥的。若有幸遇到一本好书,简直就是一场“秀色可餐”的艳遇,精神的魅力就是这样的万能和神奇!
我喜欢莫言、张承志、阎连科、余华,不亚于喜欢张贤亮、陈忠实和路遥。他们都是有独创特质的作家,而且和我一样,有过饿肚子和受歧视的经历,更懂得怜悯弱者,更透悟人性和人情。他们的文字里总有豪放之气和凛然之风,至少做不出自取其辱的蠢事。我虽不能望其项背,却也是气息相通。比之科班出身的批评家,我就是个围观的“乡下人”,除了喝彩,实在看不下去时,也会忘乎所以地吼几声,即使不合时宜,心里却也笃定。
常提醒自己:你可以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记得时间会给你画像,作品会给你作证,读者会给你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