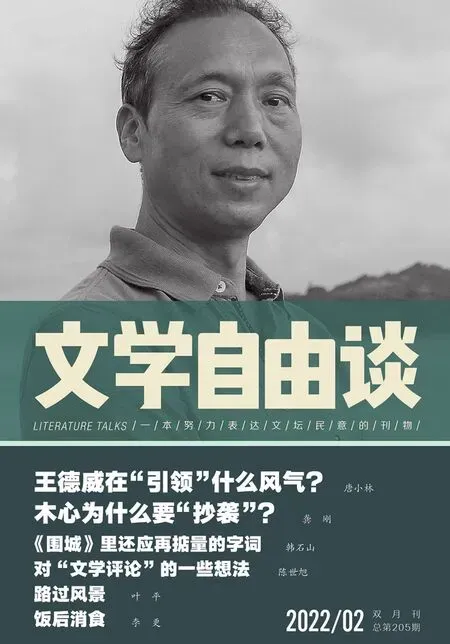我有一张“毛姆地图”
2022-11-10刘世芬
□刘世芬
早年读一本《世界文学名著速读手册》(方洲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名著丛中过,偏偏驻足于寥寥数笔的《月亮与六便士》。及至买来原著读完,当即“抛”下一众文豪,直奔毛姆而去。后来将他所有的中译本一网打尽,塞满了书房里满满两排书柜。
就在这个“毛姆专柜”中,有一本《湖畔恋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购自网上,封面署名“毛姆等 著”。那段时间,我对“毛姆”可谓饥不择食,忽略了那个“等”字,以为全书都是“毛姆著”。待书到手后,翻开目录,发现只有第一篇《湖畔恋情》(也译《池塘》)的作者是毛姆。当然,后面那几位作者也不能不算“著名”,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也读了他们的作品。然而却在想:编者为何没把作者写成“詹姆斯·乔伊斯等 著”,难道他们的“吸力”不足?
显然,这个问题有点个人化。事实上,我还真的被毛姆牢牢“吸”住了——倘若封面的作者换成后面任何一人,我与这本书很难有现在的缘分。
似乎不宜完全归结于名气,像后面的赫胥黎、厄普代克、乔伊斯,也难说他们的名气不及毛姆,但“为什么是毛姆”?
那就再让我“个人化”一回。读完毛姆所有的中译本,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幅“毛姆地图”——说毛姆是个十足的“驴友”,并不为过。
毛姆被“锁定”,固然因为他终生锲而不舍的人性钻探;在我看来,他的驴友特质,更令他的作品充满极具诱惑的异域性。
距离感从来都是产生美感的前提。作为一个天生的异乡人,毛姆拒绝同一,寻求多异——他的作品带给人的生存异质感总让人欲罢不能,呈现在他笔下的那些遥远奇异的地名、人名、植物、事物,因距离而充满神异的召唤。
就说这篇《湖畔恋情》吧,背景是西萨摩亚的阿皮亚,这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或许不是那么隔膜,但往前推二十年、五十年呢?我对其中浓郁的异域情调欲罢不能。加之《月亮与六便士》的合力“夹击”,2017年,在毛姆前往南太平洋一百周年之际,我从上海飞至日本东京,再飞越太平洋抵达波利尼西亚首府塔希提,沿着《月亮与六便士》的素材发生地漫溯……倘若不是受到疫情的影响,2020年我将开始探寻毛姆的欧洲足迹。
当初,毛姆立志写作后,开始的几个剧本遭到失败,他在日记中写到:“回圣托马斯医院复习一年,再找个船上的外科医生的差事干,至少有机会旅行。 ”
看到了吧,旅行,就是毛姆的出发点和落足点,也是他的生命写照。他的一生,是在认真地做着两件事:旅行和写作。
毛姆的一生,哦——足够漫长,差四十天九十二岁。无论生活在哪里,他总是一次次地向着这个地球的某个目的地出发。
出发,已经嵌入他的生命。毛姆在一个地方不能超过三个月,否则就会感到浑身不适。
“我很清楚,我总是渴望离开,渴望到国外去。”他对画家朋友杰拉德·凯利说,“其实,旅行时还不如在伦敦舒坦呢,但我就是无法克服这种推着我向前走的焦躁心情。”
比如这几个年份——
1908年,他去了瓦伦纳、马德里、君士坦丁堡、布尔萨、卡普里和希腊的科孚岛;
1909年,他去了巴黎、安特卫普、布鲁塞尔、法国南部、米兰、雅典和威尼斯,还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徒步旅行。这一年,他做好了去美国的计划;
1911年,他去了勒图凯、爱尔兰、巴利阿里群岛,秋天再去纽约。不过,这时他满脑子都是对远东的憧憬,“曼谷和上海的风景,日本的港口,棕榈树,蓝天,深色皮肤的人,东方的香气。”
1912年,他先后去了西班牙、巴黎、布拉格、马里昂巴德和慕尼黑。9月,其他人都回家后,他只身去了罗马。11月,回到伦敦后立即又去了纽约;
1916年至1917年初,他先是暂时放弃在瑞士的特工身份,又从美国前往南太平洋,此行佳作频频,《月亮与六便士》成为代表作。并在同年再次以特工身份进入俄国;
1924年,从墨西哥城去了尤卡坦半岛、哈瓦那、牙买加、英属洪都拉斯,最后来到危地马拉。从危地马拉城乘船到了印度支那的顺化,又经西贡乘船去了马赛;
1928这一年,毛姆主要是在旅行——丹麦、德国、奥地利、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姆摇身一变成为打入多国的英军间谍,开启了“行李上的生活”。在以“阿申登”为主人公的毛姆间谍小说中,摇曳多姿的地名连接起整个欧洲版图。他从每一个行程里“残酷”地榨取着写作素材,连乘客的眼神都不肯放过。
与当今跨海越洋的朝发夕至相比,毛姆时期堪称“慢生活”。可这远远不能阻滞毛姆那颗拥抱地球渴望放飞的心。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每年的出行仍保持在五到十次。毛姆同时期的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说,“毛姆让人想到一只贴满标签的旅行箱,只有上帝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毛姆的暮年,爱仆艾伦忠实地陪伴着他,而这种陪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一起旅行。艾伦也承认和毛姆生活在一起最有价值的就是有机会旅行:九十岁那年,神智时而不清的毛姆,依然催促艾伦上路……
毛姆钟情别处,也让自己时刻身在别处。
无论身在何处,首先让文学在场。整个人往那一站,就是诗和远方。于是,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热切关注的,除了毛姆的作品,更有他那旖旎多姿的旅途,甚至有时,后者胜于前者,这也直接导致他的作品与旅途难解难分。
当我通读毛姆之后,早就想写这样一本书了,梳理一下专属于毛姆的文学履迹。这些年,我读了国内毛姆作品的所有中译本(仅《月亮与六便士》就多达七个版本),其中包括九个版本的毛姆传记。其实,在我电脑桌上方的那张世界地图,早已被我标注成为“毛姆地图”——在这本书里,我并未完全依照时间顺序,而是按毛姆的旅行线路划定了不同的地理版块:欧洲、美洲、南太平洋、东南亚、东方,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赴瑞士、俄国、美国的特工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行李上生活”。
这本书同时也展示了毛姆迥异于常人的人生切面,比如《毛姆在一九五四》,集中展现了毛姆八十岁的精彩;《这一世,两个人》则揭秘毛姆与视若生命的两个英俊男孩:杰拉德·哈克斯顿与艾伦·塞尔传奇感人的一生……
我试图把这样一张属于毛姆的“世界地图”移植到文字里,感受他那精彩、跌宕、丰实的旅迹。
我愿循着这张“地图”,一次次缅想,一次次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