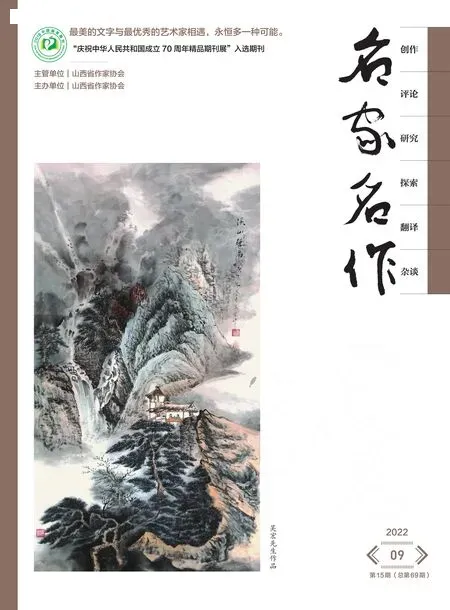浅析存在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
——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例
2022-11-10刘家昌
刘家昌
萨特的研究目的在于阐明和回答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 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被生理学作为身体研究,被心理学作为灵魂研究,被社会学作为共同体研究。”人类将人作为人类所认识的自然性质,就像其他生物的自然性质一样来探索;也作为人类所了解的历史来认识,通过对传统的带有批判性眼光的澄清,通过理解人在行动和思想中的意义,通过从动机、境况和自然现实中解释事件来认识的历史。人类的探索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不是关于人类自身整体性的知识。而萨特的这本书所要进行的正是这些研究的延展。但是与这些过往的研究不同的是,他尝试从更加切近于人的本质的深入视角出发,兼以对哲学史上种种与人相关的理论的回溯作为补充,由此展示出一幅关于人的画卷。
一、西方哲学关于人的讨论的回溯
萨特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的批评出发,阐明了一种“存在先于本质”(der Existanz Essenz vorausgeht)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存在主义是从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cortigo ergo sum)出发的,因此包含了一种绝对的主观性,从而无法认识他人,或者形成那种“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而天主教徒则是认为存在主义否定了上帝,从而失去了一种严肃性(Ernst),导致人的随心所欲而失去评判人的行为的标准。
萨特的论述就是从这两种批判中展开的。存在主义的内核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被论述为:“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这种学说还肯定任何真理和行动中既包含客观性的环境和人的主观性在内。”而接下来针对一些人认为存在主义“揭露了恶的一面”从而认为它是一种悲观主义,萨特将这种思想以及所谓的世俗智慧(die Weisheit dervoelker) 作为出发点,对存在主义作了否定性的表述,他认为存在两种存在主义,即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他们的共同观点都是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存在与行动而决定的,即哲学是以主观性(Subjaektivitaet)为基底的。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别。
雅斯贝尔斯所讨论的人作为世界上的实存,是一个可识别的对象。例如,他认为:“在关于人的自然理论中,它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形式;在精神分析中,它被理解为各种无意识的组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它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劳动生产的生物,通过它的生产,它以一种假定的完美的方式获得对自然的控制和共同体。”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理解了人类的一部分实际发生的事情,但从来没有理解整个人类。在将这些理论提升到对整个人的绝对认识的过程中——他们都做了这件事——他们忽视了真正的人,并使那些相信这些理论的人产生关于人的种种知识,最终使人性本身达到了灭绝的边缘——人的存在。这意味着雅斯贝尔斯所批判的是一种将人仅仅作为不同理论的客体进行研究的方式,但却忽视了真正的人本身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存在仅仅是存在本身的一种样式,即此在(Dasein),但是这种此在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定在”,即人的此在是具有特殊性的,它能够以自身的实存的可朽的肉身去追问那个无限的不朽的存在本身,它不是宗教所指向的上帝,而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沿袭下来的一种理性的对象。但同样的,这也预设了一种属于理性视域内的先天的人类范畴。
二、萨特探求人的存在的路径
萨特并未追寻上文中所提的两者中的任何一条路径,因为他认为两者都是有缺陷的。他选择在它们之间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更接近人的方式,并且由此最终阐发出他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他首先通过裁纸刀的制作和人的形成进行对比,人在创造裁纸刀时必然知晓它的用途,或者说它的某种本质,故裁纸刀的存在是被本质决定的,制作先于存在。而人的出现若是从宗教的视角出发,则是上帝的神圣理性赋予了人与人的本质。而在无神论者那里,“人性”(Menschliche natur)的概念依然暗含了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观点,从自然性质(natur)一词中就可清楚明白地感知到。而在康德那里,这种普遍的人性被推向极端,先天的(a priori)范畴或者是先验的(transzendental)范畴更是表明了人生来便具有某种特定的本质。
但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认为有一种人的现实性(menschliche Wirklichkeit)存在,它取代了上帝的神圣理性先于人的本质而存在——首先有人的存在,而后人碰上了自己与他人,之后才给自己或者说人下定义(赋予本质)。主观性也在这里体现,人除了是自己认为的那样之外,什么也不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人首先是存在,这是人认识自己的真实面目并完全承担自己选择的责任。人完全(voll)承担责任不仅仅意味着承担自己选择的责任,也意味着替所有人选择并承担责任。所谓的人的主观性是指人具有自由,但也指人无法超越人的主观性。
实际是,这种观点表明人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接近自己的:“以被研究的客体的身份与所有研究都无法接近的自由的实存。”在一种状况下,人类把人言说为一个对象,在另一种状况下,人类把人言说为一个非对象性的人,当它本真地产生自我意识的时候,它就意识到了这个作为非客体的人。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无法穷尽对它的认识,而只能在思想和行动的起源中去体验。从根本上说,人比他自身所能知道的更多。当人认识到对自己的要求时,人也就意识到了来自自身的自由。是实现它们还是逃避它们,这取决于人们自己。从严格意义上说人们并不能否认,人们决定了一些事情,从而决定了人们自己,而且人们对此负有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选择、决定、责任等人类的行动所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性,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主体都被植入了人这个普遍概念,但是它又并非是由某种普遍性的本质而生成的,这种人的普遍性在后文亦有论述。回归人的选择,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在为所有人做出选择,在人塑造自己形象的行动中(人也仅仅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构造自己的形象),他同时也在塑造一个他认为的人应当成为的形象。这个形象的人对于与他同处于整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是适用的。我所做出的选择同时代表了一种倾向的构造,即人应当如此,而这也是一种我对所有人承担责任(表态)——它可以和康德所说的“你应当如此行动,仅仅按照你同时也愿意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则那样行动”的道德律进行对比。在塑造自己时,我也塑造了全人类。
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海德格尔所说的Angst即人的畏。这里的畏来自人为全人类所作出的抉择,当人为自己做出抉择时,他也为全人类作出了抉择,而人是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由此,人便产生了一种重大的责任感,而且它是无法逃避的。那么倘若有认为了逃避这种责任感而求助于决定论或者用一种“并非人人如此”的态度来为自己开脱,那么就将陷入一种“自我欺骗”。但是一个人在作出抉择时将永远需要意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这种烦是无法解脱的,由此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我如何具有一种为所有人做出抉择的承担责任的资格的?
三、萨特对人的存在的讨论
萨特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亚伯拉罕的痛苦”作为例子,一个天使命令亚伯拉罕杀死自己的儿子,“任何人都会盘算:第一,他是不是真正的天使,第二,我是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但遗憾的是,人们永远地失去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是由主观性决定的。可以认为,克尔凯郭尔所引用的《圣经》中的这个隐喻是对某种上帝的指引进行的自我反省,以至于他不断地确证自己被握在上帝的手中:通过他所做的事情,通过在世发生于他身上的事情,他听从了上帝的种种安排,但他经历了每一件事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引导他的不是有形的指导和明确的诫命,而是通过自由本身的指导,自由本身决定了自己。这同时也意味着不存在能够证明这种上帝的指引的证据,它所导向的结果就是:人的抉择是完全凭借自身的被迫的自由而做出的,同时也就像在全人类注视下做出的那样,这显然是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又成为人类行动的条件之一,由此又引出了听任(verlassen)的概念。
由于不存在一种世俗的道德,也不存在一个呈放着道德价值的理性天堂,所以人类也无法在自身之外找到一个评判人类行动的价值标准了,人是自由的,或者说人就是自由,没有人能为人类提供这样一些价值和命令使人类的行为成为合法化——人类的自由是一种被迫的自由。人的存在并非自己创造的,但是当人类被抛入这个世界时,人类就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人类是任何人,是每一个个体或者是人类共同体,人注定拥有自由。人类没有任何帮助,却无时无刻要发明人,人的未来是人自己决定的。没有任何一种伦理学的抽象准则可以适用于一切境况为人类提供帮助,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构造自己,情感和一切脑海中认为人自身之所是之物皆是虚妄的本质,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行动,即每一个个体为全人类作出的选择,我所承担的责任所构成的。这就是听任,就是决定人类存在的是人类自己,人类注定承担这种行动的痛苦。
换言之,在世界上,那些将人类打倒在地的巨大力量想要吞噬人类:对未来的恐惧,对失去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恐惧,对各种不祥的可能的担忧。但是在面对死亡时,面对这个人的可朽性的终极体现时,人类也许可以获得一种信念来对抗它们,即使在最极端的,无法解释的,最没有意义的状况下,这种信念也会让人平静地死去。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就是:“人的永恒现象就是人成为人自身的过程。”
总而言之,萨特认为,由于上帝不复存在,人类也没有先天的本质(a priori Gewesen),所以人的价值或者本质要依靠自己来发明,生活在没有人行动之前是没意义的,它的意义依赖于人的行动而赋予(暗含了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可能性)。
最终,萨特将整个讨论引向了人道主义的一种解读,它并非是指某人对人的特殊发明而感到自豪并以此肯定人的价值。而萨特最终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的人道主义在于人首先是处于一个“被抛入世界”的状态,同时人也需要将自己抛离自身。同时也要以此为路径去追求超越的目的,这才是人“本真的”(eigentlich)存在。人类需要重新解放自己、找到自己,并意识到并不存在一个上帝替人类决定这一切。人类是自由的,他们必将自由选择自己,从而必定为自己的选择或者行动而负责。
四、萨特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暗合之处
萨特认为的绝望是“人类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人类的行动可以通达的可能性之内”。我处于各种可能性之中,但是我并不依靠那些和我没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因为我无法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对其产生改变。正如笛卡尔所说的“征服自己,不要征服世界”——人类不应怀着希望而行动。我也无法依靠他人,因为人是自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应该放弃行动,我首先应该承担责任,然后按照我承担的责任行事,“凡是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把握”。而针对无所作为论,存在主义哲学采取了与之相反的态度,它提出人只能是人所意图成为的那样,人除却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也不是,除却他的生命外,什么也不是。存在主义因此而是一种严峻的乐观主义。而针对一些先定的本质论,他也提出了人没有先定的本质,而是由自己决定(英雄和懦夫是由于其行为而成为的,并非天生的)。
可以看出,萨特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有一定的暗合之处的,这在梅洛庞蒂的《意义与无意义》一书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哲学只有在它保持抽象,让自身局限于概念和虚假的理性存在并掩盖那些实际的人际关系时才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应当是现实的存在,是以实践为其方式的存在。行动意味着人的自由,是人实现并最终成为自身的过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明确提出了“对人来说,根本就是人本身”。人需要在自己面对自然和世界的庞大力量时进行无畏的、勇敢的实践去改变世界,以此才能赢得属于人自己的尊严和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人的主体性力量的确证。
纵观西方哲学史乃至于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讨论,他们大多忽视了人的现实实践的力量,可以说,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也正是他以“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方式走出的一条与传统哲学家不同的道路。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这里,他同样地重视人的行动——实践,这恰恰表明了一种伟大思想之间的默契,即对于属于人的光辉的确证,这种确证所依托的正是属于人的实践活动。
五、结语
萨特作为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体现了一种立足于人的在世的行动的本质。这种本质摒弃了神学和各种遮蔽,它所通达的是一种属于人自身的抉择与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本质的重新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