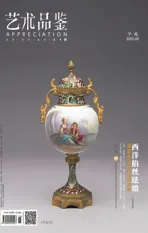分析舞蹈编创中的意图传达
2022-11-08宗怡然淮南师范学院
宗怡然(淮南师范学院)
自吴晓邦先生将“新舞蹈”的概念引入中国后,为“反映现实主义题材”的中国“新舞蹈”事业迎来了一片生机。随着大量舞蹈佳作的涌现,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在“新舞蹈”背景下诞生的舞蹈作品均在一种“题材为先”的创作指针下传递着某种强烈的情感意图。这也正是吴晓邦在《编导法与创作法》一文中所坚持的“突出人情、人性”的创作理念的现实体现。于平教授在《“表意优先”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绿色通道——由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评奖引发的思考》一文中,针对吴晓邦先生的创作理念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指出,吴晓邦先生曾强调“突出人性、人情中情感与理念表达”的“创作法”,从而更直接地表现中国人的现代生活,而这些理念的产生在于要求中国的舞蹈创作要“表现人”而不是“动作的花拳绣腿”。基于以上的背景分析,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当下的舞蹈创作,若仅是囿于形式主义下的技巧化表现而不表达任何情感意图,仅是见“道”而不见“器”,以表意不明的身体语汇去诠释那些概念模糊的形而上内容,那么此类作品定是无法满足观者的“期待视野”,更谈何唤起观者的情感共鸣。
一、舞蹈调度的意图传达——《阿齐力》
“舞台调度作为舞段的‘结构骨架’往往成为显示动作语义的‘语境’,它与舞蹈动作语汇的不可剥离性使之也被视为‘舞蹈语言’本身。”若从诸多舞蹈调度的样式中进行梳理可归为两大类,一是直线调度,直线调度又可分为纵线、斜线、交叉线、横线等,直线调度在视觉审美上给人一种强烈的压力及力度感。二是曲线调度,在“曲形”调度的基础上又可衍生出半圆、曲线圆、圆、S 弯等图式。从视觉体验上看,“曲线”调度较之于“直线”调度更为柔和,同时,“曲线”之下的“圆形”图案在其自身历史语境的笼罩下往往被编导们用于民间舞“生命”“中和”等相关的题材创作中。其实,若从两种调度样式的相同性上看,不论是前者彰显力量的“直线”调度,抑或后者承载信仰的“圆形”调度,两者皆在一种“虚幻的力的意象”构造下承担着表意的使命。因此,本章节以“直线”中的“纵线”调度作为研究舞蹈调度的对象之一,以此揭示出“纵线”调度中所隐藏的“视错觉”审美特征。
关于视错觉,视错觉是人们在认知事物时,基于经验主义或不当的参照所形成的“对事物的存在状态、所感觉到的客观真实与事物本质的客观真实不相同的知觉印象”。在近几年的舞蹈创作中,很多编导善于利用舞蹈调度的“视错觉”功能给予观者一种审美上的“误读”,例如,家喻户晓的《千手观音》,张伟东、许瑾的《剪纸姑娘》等作品中均有体现。因此,笔者在创作作品《阿齐力》时,同样采取了这一“视觉错位”的创作手法。与之不同的则是,《剪纸姑娘》是以一个静止的图形样式在“视觉错位”的审美“误读”下塑造了“双人一体”的人物形象,而笔者对于《阿齐力》的创作则是在“流动”的纵线调度中利用“视觉错位”营造出一副“千手幻象”。这样的好处是区别了舞蹈构图与舞蹈调度两者间在其表现形式上的不同。结合作品,“阿齐力”是维语的音译,意为“绽放”,同时也象征着一群花季般维吾尔族姑娘青春的绽放。作为新疆代表性之一的维吾尔族,该民族受丝绸之路的文化影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基于这一文化背景,笔者在创作《阿齐力》这部群舞作品时,便是以维吾尔族的传统“灯舞”为基础进行大量程式化动作的重置与消解。首先,为了有效地突出维吾尔族姑娘内心深处这一虔诚的民族信仰,笔者在其传统维吾尔族“赛乃姆”的风格动律中进行了动作的拆解与重置,并在这一“程式化”的风格动律中融入了很多生活化的动作。如,双手合十的祈福动态,围圈“传灯”的递进动态等。同时,为了凸显维族姑娘的纯洁,彰显维吾尔族姑娘内心深处对于民族信仰的虔诚,笔者除了建立舞蹈动作的互文性外,还通过舞蹈调度的语境营造,去传达作品的舞蹈意图。其中,在剧中的中间部分,笔者在一个流动的“二龙吐珠”的双线调度上形成了一个“纵线”队形。与此同时,在这一“纵线”队形上,笔者通过一种遮蔽式的视觉错位透视出“一人”在前的“千手”幻象。而在这“千手幻象”的视觉呈现下隐喻的则是维吾尔族姑娘内心深处对于信仰的民族情结。(见图1)由此可见,通过笔者对其纵线错视的“缩距”运用,以此拉开了舞台空间的深度距离,将原本那个属于正方体的舞台空间在“视觉错位”的有效遮蔽下给人一种“咫尺千里”的审美体验。由此,伴随着美轮美奂的双臂画圆,再通过“视觉错位”的有效运用,由此形成了一种“近低远高”与“近大远小”的透视力效。综上所述,舞蹈调度作为表达作品情感,彰显作品审美的符号媒介,它通过精妙绝伦、整齐划一的图式构造赋予了舞蹈作品在其空间形式上的美学价值。与此同时,正如玛莎格莱勒所言那般,“舞蹈的魅力在于,它揭示的不是一般的生活情景,而是‘人类灵魂深入的景象’”。

图1 群舞《阿齐力》剧照(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二、舞蹈语境的意图传达——《汉韵》
语境(context)一词最早是在语言学领域出现,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在他的《算数的基础》中提到“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词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这段话就是说,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词的含义之时,必须将它放置在一个连续的语句之中进行解读,否则便会出现“断章取义”的现象。如此一来,舞蹈艺术在进行表意时实质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由于舞蹈艺术在物质媒介上的特殊性,致使观者在对其动作语义的解读时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同时作为创作主体的编导,当进行某种舞蹈意图的传达时,在动作语言的表意上也会出现一种偏差的现象。因此,对于舞蹈语境的有效营造逐渐成为众编导“说好故事”的重要依托。回顾当下舞蹈作品在语境营造层面的创作现状,能够发现,当下的舞蹈作品在舞蹈语境的烘托与帮衬下不仅明确了舞蹈动作的情感意图,同时,在接受主体的观者层面也逐渐将原本仅属于“空中楼阁”的舞蹈艺术带回到了大众身边,使更多接受群体走进剧场,感受一场来自心底的情感共振。由此,在肯定舞蹈语境的价值之余,我们则需思考“如何从一种‘规定情境’的舞蹈语境中提炼出与之对应身体动作”,这是当下编导理应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鉴于此,笔者以自己的原创作品《汉韵》为例,通过对其作品“袖舞”语境下“中和”文化观的理念传达,以此论证出舞蹈语境的意图传达所具有的审美特征。(见图2)

图2 群舞《汉韵》剧照(图片来源:个人原创作品专场《锦瑟无弦》)
从商代的“巫舞舞袖”、周代的“以袖为仪”、春秋战国时期的“长袖善舞”、汉代的“翘袖折腰”、隋唐的“宽衣大袖”,直至近现代戏曲舞蹈中“水袖”,可见“袖舞”早已成为中国舞蹈发展史中的重要文化之一。随着“袖舞”文化的不断演变,与之对应的“袖舞”形态呈现出一副千姿百态的模样。因此,汉代“袖舞”的身体形态在传统文化语境的长期规训下由此形成了一种“中和之美”的舞蹈文化观。不难发现,在近几年的舞蹈发展中,人们对于“返古”“复古”的一度痴迷,使中国舞蹈界刮起了一股“汉舞之风”。随着“汉舞”佳作的不断涌现,一大批高产的舞蹈作品迅速出现在各大城市的剧场中,有的甚至成为一些电视节目的专栏,如河南卫视的《舞千年》之《凌波微步》,《相和歌》等。由此可见,以“返古”之名进行“袖舞”复现的当下的舞蹈创作,与其说是打破艺术与生活藩篱的重要媒介,倒不如说是当下人们心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出的“回音”。《汉韵》是一部以“袖舞”为媒介进行“身体”探索的群舞作品,由于“袖舞”作为汉文化的一种符号,一经呈现,必然会使该作品形成一种浓郁的汉唐语境,而这种因舞蹈语境形成的作品表意像一把双刃剑左右着作品的价值走向,稍有偏差,就会落得一个注重形式的悲惨境遇。
由此,为了规避这种创作偏离,有效地在“袖舞”语境中传递出一种“中和之美”的文化理念。笔者在“袖舞”的基础上以“圆”为身体路径,通过一系列“甩袖”“绕袖”“缠袖”等动作编创以此进行着舞蹈意图的传达。
三、结语
综上所述,舞蹈意图作为一个符号,它既是作品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生成作品“意义”的重要载体。因此,当我们试图通过舞蹈作品进行情感的传递时,舞蹈意图的有效传达便成为众多编导创作前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我们知道,有关舞蹈意图的传达方式实质有多种,可以说,但凡是呈现于舞台上的任何舞蹈语言皆能起到表意的作用,而当对众多表意途径进行分析后能够发现,很多进行表意的手段不是使舞蹈作品陷入了一个“故事”的泥泞,便是因外部因素的介入让本该作为舞蹈本体的“身体动作”让位于其他媒介。鉴于此,笔者认为,舞蹈意图的有效传达首先应建立在编导对于舞蹈本体所持有的深刻认识上进行的舞蹈创作,尤其是对于舞蹈单一动机的有效捕捉。接着,在明确舞蹈单一动机之后,通过一系列意义相符的舞台调度将原本抽象化的舞蹈意图进行可视化、形象化的审美呈现,最终使舞蹈意图在一个充满意象的语境氛围中以一种直击心灵的审美体验进行文本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