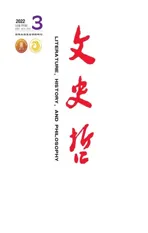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
——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2022-11-08谢丽萍郭台辉
谢丽萍 郭台辉
现代政治身份的观念建构,是中国知识界探讨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议题,可以围绕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展开论述,比如“国民”“公民”等。“国民”曾一度是令人振奋并充满期待的高频词,迅速进入社会大众的日常表述,并与“公民”表述紧密关联。晚清时期的“国民/公民”被识别并定格为政治身份概念,进而与现代国家构建紧密联系起来:从身份构建角度出发,国民是国家与社会成员在直接关系中形成的政治社会身份,构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从观念转型角度出发,“国民”表述与现代化转型息息相关,只有“国民”用以对译西方citizen时,才算引介了西方现代公民身份的观念,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政治身份转型。
政治身份研究属于认同研究(identity)的问题域,既有大多数研究是在现代国家构建的总体框架下,基于国家认同立场来讨论政治身份观念问题。在晚清中国的问题域中,原有的知识体系不足以解释世界时局的变化。以国家构建与认同为前提预设的“国民/公民”身份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式认同,很少触及现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的传统伦理,也掩饰了由晚清中国“礼崩乐坏”所带来的身份焦虑问题。虽然“国民”与“公民”概念经常混用,语义也多指国家成员并强调议政的权利,但二者的意涵仍略有区别。以康有为的著述为例,“公民”指传统意义上的“为公之民”,这与从个体出发的“国民”之现代语义相矛盾。这说明,异域观念与制度不容易替换与改造本土长期形成的身份观念与制度体系;相反,传统观念在外来危机来临时依然充满生命力,并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直至晚清时期,“天民”表述仍为士人与大众所熟知的身份概念,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体系中十分重要,在民国之后却被选择性遗弃,没有进入现代国家构建与认同问题域的概念集群。因此,理解“国民/公民”的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有必要转换视角,以“天民”叙述为线索,关注传统身份向现代转向的伦理之基。那么,同样作为重要的身份概念,传统色彩较浓的“天民”与现代新兴的“国民/公民”有何关联?
近年来兴起的概念史研究,通过概念表述研究微观层面的细微变化,旨在洞察宏观层面思想观念的大转型问题,但在实际上存在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其一,很多外来概念在晚清中国无法直接找到可直译的词语,因此需要创造新词或者意译,以更准确地表达所指代的新观念,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彼此概念体系天然的非互通性。晚清中国士人如何基于传统观念形态改造自身观念,同时吸纳和转化外来观念,便是概念史研究需要正面回应的问题。其二,已有概念史研究一般把近代概念追溯到梁启超,而鲜有讨论甚至提及康有为的相关论述,从而在客观上抬高梁启超的思想地位,但这不符合二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真实位置,也切割了师徒之间的思想关联。实际上,从康、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近代“民”的身份想象与构建存在激进化的逻辑。其三,由“国民”概念切入身份构建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更着重于现代政治意涵的使用语境。由于受到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西方史观影响,这些研究在选取概念表述的材料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诸如“天民”等传统概念,即使这些概念因应本土语境变化而转型。其实,直至晚清时期,“天民”概念甚至也常与“公民”共同使用,其中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典型。
本文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兼顾共同出现的“国民/公民”表述,首先论证“天民”与“公民”在大同至公理念中乃一体两面的表述,以打破现代国家构建的“国家认同”主流观点;然后回到“天民”概念在《大同书》之中的思想语境,发现政治身份观念的伦理基础;再根据传统人伦的解释,确立“独立”与“平等”作为政治身份的伦理特质,论证道德优先性的身份构建逻辑,即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为政治主体。通过理解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与价值基础,本文发现近代身份观念建构过程中所需面对的传统伦理式微难题。唯有经过反思并重构作为中间环节的传统伦理体系,从中理解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现代政治意识生成的隐性韧劲,完成现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的艰巨任务,才能展示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连贯性,才可回应西方现代性理论所忽略或遮蔽的中国议题。
一、“公民”与“天民”:大同至公理念的一体两面
有关近代中国的“公民”概念的研究,往往追溯至康有为1902年所作《公民自治篇》,通过其中的关键词“议政”与“忧国”来论证“公民”表述的现代意涵:“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人人皆视其国为己之家,其得失肥瘠皆有关焉。夫家人虽有长幼贵贱,而有事则必聚而谋之,以同利而共其患。”实际上,从晚清时期的历史语境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康氏所言的“人人有议政之权”是回应清政府“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早在1895年康有为等应试举人“公车上书”,已开创士人公议之风气。所谓“民者,无位之称”,即“民”指不在职位之人,而“公民”之说旨在表明不仅仅是士人,不在职位之人也应当关心政治局势;“为公”则强调了视国为家、同利共患的意义。这种推己及人乃至天下为公的思路,可从《礼记·礼运》中寻得其思想资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大同至公”理念,在康有为《大同书》中则展现得更为明晰,并将“公民”与“天民”的意涵与语境联系在一起:
据乱世:民服于旧国;升平世:人民渐脱旧国之权,归于统一公政府;太平世:无旧国,人民皆为世界公民,以公议为权。
据乱世:专为一国者为小人;升平世:为大同者为大人;太平世:人人皆大同至公,是为天民。
上述内容出自康氏所列制的内含上百条目的《大同合国三世表》,书中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三个阶段: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并在最终阶段太平世多次共同出现“公民”与“天民”表述。“公民”与“天民”共同呈现“大同至公”的理念,以此承袭传统中国“公”观念所包含的“天”“自然”“条理”“多数”“均”“连带”“共同”“利他”“和谐”等有关共同、总体、自主的种种含义,指向人类社会“平等”的终极状态,达成公平的终极境界。康氏于《礼运注》中解释:
故只有天下为公,一切皆本公理而已。公者,人人如一之谓,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分等殊异,此狭隘之小道也;平等公同,此广大之道也。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在康有为的论断中,“私”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私与独占的含义,而是“分”“等”“殊”“异”所代表的贫富差异与人种的自然殊异等等,即各种差别、等级、位阶。因此,实现“天下为公”与“大同世界”的思路便是消除“私”,即消除一切差异。“大同至公”理念指向“平”“等”“公”“同”状态,即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差别,人人皆有应有之物、应有之权。只有立足于上述核心理念,才能切实理解《公民自治篇》中“公民”之视国为家、同利共患的意涵。
从创作时间上来说,康有为《大同书》撰写于1901到1902年间,与《公民自治篇》的发表时间相差无几。“大同至公”理念指代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含义,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与“公民”直接相关的公举、公议、自治等意涵时,不可忽略其背后蕴含人与人之间无差别的伦理价值追求。“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因此,在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公民”与“天民”的表述如硬币之两面:“公民”承担职责与行为的政治意涵;而“天民”承载独立与平等的价值底色,为“公民”铺垫伦理基础。
二、天民观念的逻辑起点:“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
由前文可知,康有为对身份认同的论述蕴含“大同至公”理念,明显超越了现代国家的认知与思维范畴,而“天民”因人人皆为天生之民,尤为强调“独立”与“平等”两大价值理念。康有为的理想社会形态是消除差别,无所谓公私区别,每个人的生存境况均相同,不存在因条件差异而被区隔的界限。这是《大同书》描述的思想核心,思路是经由“破九界”最终实现“太平世”:(一)去国界,合大地;(二)去级界,平民族;(三)去种界,同人类;(四)去形界,保独立;(五)去家界,为天民;(六)去产界,公生业;(七)去乱界,治太平;(八)去类界,爱众生;(九)去苦界,至极乐。“天民”作为贯穿康有为大同思想的重要身份概念,为何在第五章“去家界”一题中进行重点强调?
窃谓女之与男既同为人体,同为天民,亦同为国民。同为天民,则有天权而不可侵之;同为国民,则有民权而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职而不可失,同任国职而不可让焉。
……公民则天职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同为天民,同为国民,与女子为公民,又于男子无损也。何事摈之而侵天界乎?女子亦何可让天职,舍国责,而甘受摈哉!
故天下为公之世,凡属人身,皆为公民,而有国合众,女子亦在众民之列。若行有玷缺而才不能供国事者,则无论男女,皆不得为公民。否则以女子为公民,可骤添国民之一半,既顺公理,又得厚力,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将欲为太平世欤,以女子为公民,太平之第一义也。
以上内容出自“去家界为天民”一章,共同采用了“天民”“国民”“公民”概念,旨在解释男女性别不应有尊卑之分。多数关于近代“民”的研究也引用该段落,但只取康氏对“国民/公民”的使用,而忽略一并使用的“天民”表述所呈现的男女平权思想;另一方面,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天民”,却只将其放在性别与家庭的论域中进行解释,并没有往“女性为公之民”的路向展开讨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呈现“九界”分裂之苦,正是描述人类社会高低位阶关系的九个层次,指出从当下苦难的“据乱世”过渡到完美的“大同世”的必经途径正是“破九界”,且破除“九界”的路径有其先后次序:
“欲急至大同,最难则在去国。”“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夫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天之生人也,使形体魂知,各完成也,各各自立也。此天之生是使独也。”
由此可以往前推演,要先实现男女平等独立(“破形界”),才能破除夫妇父子之间的依附关系(“破家界”),然后才能“破国界”,最终逐渐走向大同。
康有为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更早体现在其《教学通议》讲述礼教伦理的缘起之时,康氏《教学通议·原教》借助传统经典解释人类社会起源,引用了《易经·序卦传》和陆贾《新语》,其中所体现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类似涟漪式扩散的差序格局,就是传统的人伦秩序:
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羲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有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再者,纵观《大同书》全文关于“天民”的表述,我们可知,男女与家庭论题只是“天民”的小语境,“破九界”与“大同世”实为“天民”的大语境,并以“平等”与“独立”作为典型的核心理念。诸如“以天之公理言之,人各有自主独立之权,当为平等”等言可见之于全书。在对“破九界”的描述中,康有为处处强调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显然,在《大同书》讨论“民”的诸部中,应当存在着互文用法,亦即康有为所讨论的“民”,既指代“天民”“人类”“公”“众”以及“独立”个体,也称作共生于“大地”之民。如果我们不能体察不同表述背后所蕴含之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便无法准确把握“天民”“国民”“公民”等基础性概念所共同回应的身份认同问题,更难以发现《大同书》所言“一切平权从男女平权始”的重要意义。
因此,虽然“天民”主要出现在“去形界保独立”(性别)与“去家界为天民”(家庭)两部之中,但不能由此认为,“天民”之说仅仅适用于性别与家庭论题。我们在理解“天民”时要意识到,“破形界”与“破家界”是“破九界”以实现“大同之世”最为关键的环节,而“九界”之诸界并非各自分离的平行界限,破除九界有先后次序,而“形界”与“家界”便是要最先破除的界限。在《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的最后一章“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中,康有为便直接点题,强调男女人权的重要性,并在文中连连发问:如何破九界并实现大同之世?对种种疑问的回答均指向“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康反复感叹,一切美好均出于“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在《礼运注》中,康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嵌入自己的大同理想,对“大道之行也”文段进行修改与再诠释,其中修改的内容就包括将“女有归”之“归”改为“岿”,释义为“岿者,巍也。女子虽弱,而巍然自立,不得陵抑。各立契约而共守之,此夫妇之公理也”。“归”的本意取“嫁”,但康有为将原本女性“得嫁”之意涵改为女性“自立/独立”之意涵。男女关系是中国传统人伦秩序之基础,对于理解“天民”尤为重要。
可见,康有为所遵循的社会结构认识是基于儒家传统的人伦秩序与三纲伦常,而男女之间的平等与独立,不能只是单纯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而应该作为“公民/天民”身份的逻辑起点。因此,在晚清“礼崩乐坏”危机的问题域中,康有为主要回应传统伦理式微所呈现出的身份焦虑问题,这种“家国天下”的世界观把伦理与政治秩序统一纳入宇宙观之中。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在近代中国政治观念转型的显性线索中,同时也存在传统伦理重塑的隐晦线索。从晚清的蔡元培、秋瑾、刘师培、何震等提倡“女子复权”运动,到“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都不能简单地视作照搬或学习西洋的模式与经验,因为在伦理关系观念上存在着从性别到家庭再到君臣国家的逻辑次序,并一直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观念基础。
因此,康有为提倡“公民/天民”身份的概念集群,都是针对原有伦理世界观不足以解释时代进步的大问题。这为我们重新理解近代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即把论证基础立足于伦理关系的重塑,“独立”与“平等”作为天民身份观念的两个伦理价值,显然不能依据西方现代观念体系和国家构建思维框架来解释,既不能通过西方的个体理性思维来认识人之“独立”,也不能通过其自然法传统来论证人之“平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既脱胎于传统又具备转型意义的“独立”与“平等”伦理观念?这需要我们回到康有为思想中的人道与人伦语境。
三、“独立”与人道苦乐之说:顺人性合天理的“天民”
在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天民”之“天”取自“自然”“本性”之义,“天民”理所当然地享有天权,“天民”之“独立”体现在人人享有自立、自主、自由之权。康有为将其所了解到的西洋知识转述为自己对天权的理解:“自立”可以解释为平等交往,“自由”是指对行为意愿的满足,“自主”是不受来自外界长上之力的欺压。“独立”之释义意涵体现了康氏对西方现代观念的认知方式:他通过带有“自”字的三组词呈现人之自觉,在“天人之辨”传统观念限域内完成“人之自我发现”的论述。其中的相关表述可见于康氏《论语注》《大同书》《中庸注》等多本著作:
女子与男子,同为天民,同隶于天……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
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但圣人姑别其名称,独以王者为天之子,而庶人为母之子,其实人人皆为天之子也。
子赣不欲人之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为天之生,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
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其有交合,亦皆平等。如两国之交,若有一强一弱,或附属之,或统摄之,即失自立之权,或如半主之国,或如藩属之国、奴隶之人矣。
人人有天授之体,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故凡为人者,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宴飨可以自乐,出入可以自行,交合可以自主。此人人公有之权利也。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不得自由之事,莫过于强行牉合。
康有为虽没有明确解释自由、自立、自主的含义,但是《大同书》之“去形界保独立”描述了自立、自由的具体表现。其中,根据引文表述,“自立”之权体现为康有为以两国之交来类比人与人(更明确地说,是强调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交往状态;“自由”之权则具体表现为,人人都有学习、发表言论、出行、用餐、交往等自由。显然,“自立”之权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状态,而“自由”之权则体现为出于自身意愿而非外界强力约束的行为。
“自主”之权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直接作为六条“公法”的第一条出现,该词的表述与传教士的文化传输工作有关。早在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中,“自主之权”就常与“主权”“权利”等词互换使用。此外,康有为早年吸收西方知识,主要来自《万国公报》所刊西方传教士的文章,“自主之权”在其中也是一个常用词。康有为在与张之洞展开互相批评之时,也提出了自己对“自主之权”的理解:
若夫人人有自主之权,此又孔、孟之义也。《论语》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言己有主权,又不侵人之主权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也。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有立达之权,又使人人有之也。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人人直接于天而有主权,又开人人自主之权也。其他天爵自尊,藐视大人,出处语默,进退屈伸,皆人自主之。《易》曰:确乎不拔,《礼》曰:强立不反,贵自主也。故《春秋》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明父不得杀子;书天王杀其弟佞夫,明兄不得杀弟;书卫刺其大夫买,明君不得杀臣。以人皆天生,虽君、父不能专杀之也。
地球各强国,人民无不有自主之权者。其有长上,以力压之者,无不死败。此又揽近百年事而可见。
显然,康有为将“自主之权”与“孔孟之义”结合起来,通过提出人之关系“其有长上,以力压之者,无不死败”,反证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正当性。
康有为还经常提到“天民直隶于天”,这里的“天民”可以理解为,以“天”为其存在根据、以“天”为渊源的“天生之民”。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已经写明“实理”与“公法”条目,人类发源于“天地原质”,各具一魂,因而有自主之权。人类平等是一个几何公理,共享同一套法则。康有为从人类发源上强调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并以此为公理。康有为强调“民”与“天”的关系,是基于他对当时社会关系的判断。从上述引文的语境可见,“自立”“自由”多见于男子在社会地位上压制女子的内容,“自主”多见于强国压制弱国、君主压制平民等作为反例的内容。康有为从“女有归”到“女有岿”的刻意修改,也是基于他对女子依附于男子的从属关系的批判。甚至在“破九界”的思路中,康有为否定民依附于国家的观念。既然归属于某个人的情况则称之为“私”,那么何之谓“公”?那便是前文所交代的,人与人无差别,消弭所有从属关系。民/人的独立性意味着,并非依附或从属于某一个体或团体,人与人的共同点乃在于均同归属于“天”。
“天理,圣人犹裁成辅相之,故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也,是天理二字非全美者也。”康有为所言“天人为一体”的天民,其所欲反思的正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本位观念: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之源在于“天理”,人在现实中存在的欲望和情感必须接受“理”的规范。康有为的“人道”之说则认为,“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即关注人间苦疾与安乐;而“破九界”在于破除九界给人所带来的苦疾。因此,康氏之“天民”,其“直隶于天”,意在“非隶属于他人”,天理与人欲并非相互违背,恰恰是浑然一体。康氏以“人道”为“天道”,这与程朱理学之天理观有所差异。康氏在“大同世界”中强调,人道之去苦求乐,人人之安乐,通过自立自由自主之人欲来实现,人人为天之子,无所谓依附于他人之说,此为人之独立性的体现。
康有为对“天民”平等身份的独立设计,意在破除社会中的依附关系。康氏将独立平等视为“顺人性合天理”,以人本无私的人性设定,破除九界之私,构筑一个完全无私的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康有为之“人的独立”实为“不从属于他人”的意思。这是一种被动意义上的独立,强调对人的霸占不具有合理性,与西方着重于从个体理性的主动能力视角阐发人之独立性的现代性解释有所不同。细考康有为关于“独立”解释背后的思想体系,他对于人之本源性的讨论在于“人欲”,而非“理性”。即便康有为关于“智”的讨论,也是指人对“仁”的感知、认识以及实现的能力与责任: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财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然知而不仁,则不肯下手,如老氏之取巧;仁而不知,则慈悲舍身,如佛氏之众生平等。……孔子之仁,专以爱人类为主其智,专以除人害为先。
在康有为的思想语境中,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体现是“合天人为元仁”的本体论,而非西方启蒙时期所强调的人之理性认识论。无论是人类发源与世界本源的讨论,还是人人受九界之苦的描述,抑或是最为完美之大同世界的设计,“天民”一直贯穿于道德伦理论域,因此“公民”亦不能纯粹作为政治主体进行理解,在公养、公教、公恤此类逻辑在先的人道问题中,“公民/天民”呈现出道德主体的优先性。
四、“平等”与人伦秩序重建:消弭等级区隔的“天民”
康有为展示的“天民”独立性,体现在破除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而非阐发个体理性能力。那么,在大同世界的语境中,“独立”与“平等”很可能是同义反复的概念表述。换言之,实现独立即实现平等,实现平等则实现独立。西方语境中的“个体”与独立性相关而与群体相对,而在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中,由于设定人与人的无差别性,“个体”消弭于“人人”的表述中。在大同世界中,“天民”就是“人人”,不存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张力。大同世界中存在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个体间的关系联结,即便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公-私”议题,在大同世界中也没有脱离开以社会关系为主导的认知方式。“私”的含义是“私有”归属关系的私、分等殊异的私,“公”是无从属关系的公、无差别的公。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体自身所扮演的角色与生存境况,因而,人人“平等”需要通过重建人伦秩序来实现。人伦秩序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即人有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根据《孟子·滕文公》记载,五伦之教自尧舜开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其早期作品《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氏基于五伦扩展到十种人伦关系的讨论,并从“夫妇之道”“父子之道”开始层层破除人伦关系对人的道德束缚。比如,夫妇门的实理内容:“今医药家已考明,凡终身一夫一妇,与一夫屡易数妇,一妇屡易数夫,实无所分别。凡魂之与魂,最难久合。相处既久,则相爱之性多变。”又如,父母子女门的实理内容:“原质是天地所有,非父母之所生。父母但能取天地之原质,以造成子女而已。……人于死后,其魂有自能投生者;……父母与子女,其质体亦互相轮回。”再如,“君臣门”的实理内容:“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以《实理公法全书》中的“父母子女门”为例,重置父子(父母子女)人伦关系秩序的意义在于,不再将父母视为“我”与其他人关系的来源,人类一切关系均由“天地”来衡量,而不再由“我之父母”来衡量。在传统人伦秩序中,父母子女是衍生其他关系的来源,比如“祖父母和我有关系,是因为他们是我父的父母;昆弟和我有关系,是因为他们同为我父母所生;世叔父和我有关系,是因为他们是我父的昆弟”。诚如吴飞指出,以生生之德为纲的中国哲学,其最核心的取向,正是男女交合与生儿育女之事。《周易·系辞下》的“生生十六字”(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将男女阴阳与万物化生之起源联系起来,并由此推演到父母生子的人伦次序。父母生子,是中国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也是一切人伦关系秩序构建的始点;而康有为想变革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父母生子为基点的人伦秩序观念,通过借用佛学投生轮回的观点,将父母与子女解释为可以交替轮换的角色,这样父母便不再是衍生其他人际关系的来源,只有“天地”才是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人类一切关系全部交由“天地”来衡量。只有这样,人际关系的缔结才不会受制于父母之命,人际关系的自由缔结才是人人平等的体现。这也是康氏为何一直强调“人”为“以天为渊源之天民”的意义所在。
对于康氏而言,“破形界”不仅仅破除性别的形体区隔,而且联动至破除夫妇、父子(家庭)、君臣(国家)等地位的殊异区隔。康有为前文提及其所言“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的逻辑,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涟漪式扩散的差序格局而展开。差序格局在传统中本是由亲密到疏远,而在康有为关于人伦关系的新定义中,却变得松动灵活,比如“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夫妇、父母子女、君臣等高阶位与低阶位的成对关系不再如传统所描述那般稳固,而是解释为可以轮换或替换的关系,而更为稳固的只有“天地”这个具有大而化之倾向的概念,人与人因为共处于天地之间而赋得平等性。
中国传统人伦秩序是“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合并在一起的差序格局。康有为的“破九界”思路是将传统差序的人伦关系一一破除抹平,在以“天”为终极存在的基础上,康氏主张设立无差别的“公”。在完成对破家界环节的讨论之后,在家-国-天下的递进层级上的破国界论述中,康氏也是在道义与原理上否定了“私国”即王朝的专制权力,将“民”从隶属于朝廷国家的独夫君主之民,转化为以“民”为主体的“人人”式国家的人民,最后成为“人人”共有世界的世界公民/天民。康氏的思路与近代西方的社会关系讨论存在明显的区别。比如,在家庭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方面,洛克和卢梭将“父-子”与“君-臣”两对角色分别置于两个不相关的组织系统,有着家庭与政治社会分庭抗礼的公私领域之分;而康氏重建人伦秩序的努力依旧遵循着家国天下格局。在这种传统的立体差序格局下,康有为旨在抹平纵向的高低位阶差异,并在结构上通过人伦的亲疏顺序逐步实现“平等”,即以消除私有的方式来实现“公”,最终通过“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的合并方式实现大同世界。唯有当社会组织形式破除了形成位阶关系的所有可能性,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独立。
康氏实现平等的思路是将有位阶之差的家国天下格局进行扁平化处理,这意味着,其“自由”并非承认私人权利的市民自由,而是一种无差别的自由自在观。康有为关于“天地”永恒的论述旨在论述其“平等”意涵为大而化一的平等,而不是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关于“同心圆”差序格局框架与消除附属私有的思路,并非在西方公私有别的观念框架下解释公领域,而是认为公私无别谓之“公”。这种消弭殊异的绝对平等理念来自其佛学研究。梁启超曾指出,其师康有为否定现存秩序,这与大乘佛教那种有机同一体的理想息息相关,旨在消除人际关系中的一切差异并追求界限的无等差。张灏也对康有为的思想来源作出相关分析,认为他受大乘佛教华严宗哲学的影响,华严宗世界观的核心是排斥包括今世和来世二元论在内的一切二元思想模式,追求激进的无差别同一境界。
康有为所处的晚清时代,谈论人的平等性始终需要在三纲伦常的语境中进行。士大夫们激烈抨击康有为的平等之说,认为颠覆人伦纲常会导致失序:“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孝弟为仁之本,在作者实无所用。一切平等,无所谓孝弟。无君之人,更不必言孝弟。”虽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长兴学记》之独立平等言论并没有《实理公法全书》以及后来的《大同书》《孟子微》等作品的观点那么激进明了,但也令士大夫担忧纲常的崩坏与伦理的堕落,这也从侧面呈现了构建政治身份始终无法忽略传统伦理的接受程度。人伦关系秩序不仅仅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还承担着社会伦理的功能,人在社会关系中承担的角色也附带相应的角色伦理,比如孝悌之道、忠义之道。在三纲伦常观念盛行的清季语境中,康氏所提出的平等,不可仅仅从西方平权观念的角度予以理解,还应视为危机时代重建传统人伦关系秩序的伟大尝试。
回到康有为的“天民”表述,甚至是回到“天民”的另一面——“公民”的表述,康氏赞颂人的独立平等,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性价值的引入与萌芽,而忽略了其历史语境。康有为所言“天民”的平等性有几个特点:第一,“平等”需要通过重塑人伦秩序来完成,始终脱离不了三纲伦常的语境;第二,强调破除人伦关系中位阶的不平等差异,消弭上下压制关系,平等的实现顺序从关键的男女与家庭关系开始,在家国天下的同心圆格局中逐步向外扩散;第三,“平等”指向传统大同思想与大乘佛教“合一无别”的无差别理念,旨在消除区隔,个体平等统归于“天”的一体平等之中,从而区别于近代西方之个人自然权利的讨论。
五、结语:现代性叙事所忽视的伦理之基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观念的构建基础在于传统伦理世界观的转型与重塑,既体现于“公民”背后的“大同至公”理念,也体现在“天民”“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的逻辑起点。“独立”与“平等”在今日往往被解读为带有西方现代性价值内涵的关键词,但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士人论述中则另有中国传统人伦语境:“独立”旨在强调人非他人之附属,在天人之辨议题中提倡顺人性合天理,这种“人”之自我发现,是“人欲”作为自然的发现,而非西方意义上个体理性能力的发现;“平等”旨在强调消弭等级区隔,在三纲伦常秩序中提倡破九界行大同,这种“人人无差别”的设定,是儒学佛学的一体平等,而非西方自然权利意义上的权利平等。在晚清有关“民”观念的论述中,“民”优先呈现为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这个逻辑顺位在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的主导下并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以国家认同为前提预设的“国民/公民”身份研究,难以触及现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之初关于传统知识的重新塑造。为此本文借助“天民”视角,回到晚清的历史语境,通过破除旧人伦关系来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思路,提出既往“国民/公民”研究所忽略的伦理基础。
“天民”作为一种身份概念,在同时期为士人熟知,在近代中国语境中十分重要,在现代语境中却被陌生化,在西方现代国家的观念与理论框架中也找不到合适位置。“天民”“国民”“公民”共同使用的情况,无疑反映出晚清士人对时局的复杂理解,这种关联为本文反思“国民/公民”身份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天民”表述一样,晚清时期的人伦重建语境中也能发现“国民/公民”表述,但由于国家认同视角的局限,政治转型的语境较少观照到相关伦理议题。因此,转换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伦理议题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其说发见伦理嵌入政治转型,毋宁说在自然伦理宇宙观中透见政治转型。
晚清中国现代转型的特殊之处在于,转型过程伴随外来文明的传播与武力入侵,本土思想即使不是出于内生性发展欲求而主动转型,面对新时局和新知识,仍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以至于所需厘清的议题更为复杂。在伦理视角下,本文对既往的现代性叙事提出两个值得继续商榷的问题:
其一是在现代国家观念构建主导下独有的国家认同解释问题(面向政治身份建构研究)。当前“从臣民到国民”的既有主流解释符合国家认同目的论,却无法很好地解释“反君意识”如何以及为何能够顺利对接“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在认同研究的问题域中,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研究需要回答“新的共同体如何生成”的问题。于晚清中国而言,“民族国家”并非不证自明、清晰明确的转型方向;那么,其逐步转型的过程则与中华文明传统思想资源以及彼时的世界局势和外来知识的相互融合息息相关。关注康有为“天民”论述背后的观念逻辑,能够发现康有为藉由西洋用词尝试对传统人伦知识进行重新塑造,以传统“公天下”理念来解释“视国为家、同利共赢”,在提倡“独立”与“平等”中,完成个体融入新共同体的论证,使得“天民/公民”带有融合凝聚的面向,而非锻造个体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面向。以此解释近代中国共同体认同观念形成的缘由,应该更具说服力。
其二是“外来概念背后思想观念的可转译性和可理解性”的预设问题(面向观念转型研究)。当外来思想观念并不能够直接转译和理解时,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晚清时期的“国民/公民”表述可否对译citizen的西式用法。现代西方citizen表述背后有自然法的思想渊源,基于“自然状态”和“政治社会”相对立的二元判断;而晚清时期的“国民/公民”表述恰恰把政治秩序置于自然伦理宇宙观语境,“人人有参政之权”在民直隶于天、自有天权的逻辑中得到解释。虽然这两种表述背后的观念无法直接对译,但都为“民应当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提供各自的合理性解释,因而“国民/公民”的提出依旧有其现代意义;只是其现代意义不在于从自然状态走向政治社会的契约精神,而在于面向“士人不得议政”禁令乃至“君为臣纲”的传统伦常基础。
基于伦理的思维方式能够为中国转型问题的思考提供更多解释思路。唯有通过理解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及其价值基础,才能深入发现近代身份观念建构过程中所需处理的传统伦理式微难题,进而理解伦理观念对现代政治意识生成的深远影响。因此,这种伦理视角并不局限于解读康有为的思想,还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随之兴起的家庭革命、无产阶级以及共产主义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