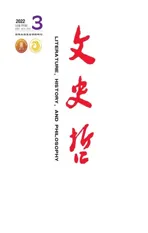儒家的现代化转型和新时代中国的理论构建
2022-11-08姚洋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0)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说:“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一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谈一下如何实现儒家的现代化转型,并由此构建中国新理论的问题。
历史上任何留存到今天的理论都是对当时主流历史进程的回应。今天我们谈儒家的现代化转型,首先是要回应当代中国发生的最为显著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并将在未来三十年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的?这是当代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关心的终极问题。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学者做出了许多努力,试图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并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制度转型、社会变革和政治转型的理论,为我们理解中国、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这些理论很少直接涉及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更很少将党的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发展新的国家治理理论。另一方面,官方理论滞后于党的实践,无法准确描述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成功实践。这些都是中国面对世界有理说不出的关键性原因。
一、从反传统到礼敬传统
之所以无法产生新的理论,是因为我们要么被国内的旧理论所束缚,要么被西方的理论所束缚。旧理论还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已经不适合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现实;西方的理论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总结,其中包含很多由西方经验形成的成见,也不适合当代中国的现实。要形成属于当代中国自己的理论,就必须跳出上述两种理论的束缚。在摆脱现有理论的条条框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对中国优秀传统的回归。
在哲学层面,党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中国务实主义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在认识论层面不承认永恒的真理,二是在实践层面以结果为导向,手段服务于目的。这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延伸。孔子不信鬼神,对学问和人生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世间没有永恒的真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是结果导向的,实践的手段要服务于目的。仁是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但在不同的场合,仁和不同的实践结合在一起。“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刚、毅、木、讷近仁”,等等。仁是最高理想,但实现这个理想的手段视情景而不同。就如“猫论”一样,目的比手段更重要。务实主义让党摆脱了以往的教条式实践,开启了改革的大门;务实主义也让改革者放弃毕其功于一役的震荡疗法,采取小步快跑的渐进道路,让中国的改革走得比苏东国家更平稳、更有效。
在政治领域,党回归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干部四化”起,不断完善干部选拔制度,使之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选贤任能的基础是儒家的人性论和对个人修养的追求。不同于西方单一的人性观,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孔子尽管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但相信“中人可教”;孟子相信每个人都有善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尽管认为人性恶,但相信通过“化性起伪”(《荀子·性恶》),人仍然可以成为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个人修养的最佳顺序和最高境界。儒家对个人修养的关注与墨家对贤能的强调相结合,就形成西汉以降中国官僚帝制的一个重要元素——选贤任能。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在国家治理方面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在今天西式民主向着民粹主义退化的当口,这个贡献显得尤其重要。
在经济领域,党放弃了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采取混合所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分配原则也从按劳分配转变为按要素分配。过去,我们常把这些转变说成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殊不知,中国早在北宋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和后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只在于没有产生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技术。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的回归,而按要素分配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贤能主义完全一致。奖励先进、惩罚懒惰、淘汰落后,既是市场原则,也是中国贤能主义的原则。
在社会领域,党鼓励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节日得到恢复,国学热、国风热此起彼伏。贤能主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体现在社会领域,能力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推动力。社会分层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可以为一个社会保持活力提供重要动力,怕的是分层的固化。放眼世界和中国历史,社会分层的固化和能力作为进入特定阶层的凭据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一个以能力为导向的社会不容易形成阶层固化,而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一定不会欣赏能力。现今中国社会的贤能主义虽然有走过头的地方(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领域),但总体而言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是中国对发达国家保持追赶态势的重要动力。
党的实践已经超越了理论工作者的步伐,如何将党的实践转化为新的理论,是摆在当代中国学人面前的重任之一。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回到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去,从那里开始新理论的构建。
二、儒家的现代化转型
从儒家思想出发构建新的理论,首先就遇到对待儒家的态度问题。社会上的儒学热,很大程度上是把儒家当作修身养性的学说来讲,而不涉及儒家政治哲学的一面。学术刊物发表的多数关于儒家的论文,则是把儒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不考虑儒家的现代意义。学界也存在复兴儒家政治哲学的努力,但其中也问题多多。多数理论停留在对儒家理想原型的构建之中,而没有与现实相勾连;多数研究也没有回应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主流价值;在方法论上,多数研究没有采取当代哲学的分析方法,从而没有改变“儒家没有逻辑”的偏见。许多人的一个顾虑是,儒家已经被定性为替专制辩护的政治哲学,今天谈儒家的复兴因而有重新为专制辩护的嫌疑。这个顾虑来自两个认识误区。
一个误区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误解。“专制”是描述中国古代社会时出现最为频繁的名词,但秦统一之后的中国,不能以“专制”来简单概括。如钱穆早已指出的,秦的统一实现了“化家为国”,即国家不再是国王一家的私产,而是属于天下的公产。自汉到宋的国家治理不是皇帝一人独大,而是存在皇权与相权以及后者所领导的政府之间的分权;到宋代,士大夫更是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而御史的弹劾和监督权也达到顶峰。如福山所指出的,西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接近现代意义的强政府国家,比西方提前了2000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秦之后的中国不应被简单地称为专制社会(更不应该被称为封建社会,因为秦已经结束了封建社会),而应该被称为“官僚帝制”,即皇帝与群臣共治的制度。皇帝代表治统,但由宰相和他们领导的政府实施治理权,这种理性安排是中国古代实现强大国家的原因。
历史地看,官僚帝制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西方出现过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但这种城邦只适合小型社会;况且,希腊半岛上那么多的城邦,也只有雅典实行过民主制度。西方也出现过罗马共和国,但它最终被帝制所取代。自一万年前进入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文明社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采取了君主帝制,而像中国古代社会这样理性的官僚帝制,是寥若晨星的存在。我们的先人不仅发明了一种近于现代的治理模式,而且为这个模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这就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经过他改造的儒家学说。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以天作为皇权合法性的来源;同时,他也强调皇帝作为天子所应尽的责任,以孟子“民为贵”的思想约束皇权。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官僚帝制延续了2000年就怪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回到董仲舒的时代,天人感应说为西汉以及此后一千年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社会和学界之所以长期把儒家和“专制”联系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明清政治的影响。然而,南宋之后中国政治走向衰退,总体而言是一个文明盛极而衰的结果,具体的导火索则是北方蛮族的入侵。儒家不应该为此负责。儒家在宋明时期的转型,与其说是导致中国政治走向衰落的原因,毋宁说是儒家为适应中华文明进入停滞期而进行的调整。
另一个误区是把儒家看作一成不变的、过时的东西,没有看到儒家学说中能够与现代价值相勾连的元素。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评价孔子的所有思想,是不公平的。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当时的主流观念,即便是与同时代的希腊先贤相比,也并不落后。如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与比孔子晚出生100多年的柏拉图相比,孔子并不更加相信君主的权力。在孔子之后的2000多年里,儒家被多次改造,在经历宋明理学的改造之后,更是遁入内心,不仅失去了事功的能力,而且也的确成为皇权的附庸。这正是我们要回到先秦儒家那里的原因所在。轴心时代的每一位先哲都至少参透了人的问题的一个面向,而儒家对人性的看法比任何轴心时代的思想家都更客观、更全面。儒家关于人性具有多样性、流变性和可塑性的观点,与当代心理学和灵长目动物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自霍布斯以降,西方的政治学说都建立在“人是自利的”这一个对人性的单一假设之上,由此产生的政府(国家)被想象为原子化的公民之间的一个均衡契约。沿着这一思想,西方建构起精巧的国家治理模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模式日益显露出来颓势,西方许多国家被原子化的民粹主义裹挟,有滑入不可治理性的危险。儒家的客观人性论具有极大的现代意义,为我们构建与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现代政治哲学打开了大门。
在西方文明兴起的历史中,曾经有过重新发现雅典的过程。我们今天也要重新发现先秦儒家,用现代哲学的方法发掘经典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并建构新的理论。就新的政治哲学而言,沿着儒家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人性走下去,我们就可以得到与自由主义民主很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潜能,但由于努力程度的不同,每个人达到的成圣成贤的高度也不同,政治安排因此应该奖励较高成就的人。据此,选贤任能应该成为具有宪法地位的制度。如此构建的治理模式排斥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但并不拒绝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决原则。儒家相信每个人具备相同的潜能,把个人修养作为君子的一个重要品格,同时也肯定个人通过努力而取得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尊重个人价值。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家秉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的中庸态度,因而为社会个体进行自我决策留出了自由的空间。儒家拒绝自由主义抽象的平等,接受建立在贤能基础之上的比例平等。这可能会让多数人认为,儒家不支持平等。但是,因为相信每个人具备同样的潜能,儒家不会拒绝旨在鼓励每个人发挥其潜能的平等措施,如教育的平等供给。事实上,这样的平等取向在现实中比抽象的平等更加可取。在政治领域,它防止了对平等的滥用,是民粹主义的一副高效解毒剂;在分配领域,它拒绝福利国家,而把注意力放在提高民众收入和其他基本能力上面,因而更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三、结 语
过去两千年里,中华文明经历了两次外来文明的大冲击,一次是佛教,一次是西方文化。我们花费了一千年才把佛教完整地吸收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宋明理学就是在对佛教的回应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现在还在第二次文化冲击之中。自1840年打开国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如对佛教的吸收一样,我们必须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来的价值吸纳进我们自己的文化之中。西方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力度远大于佛教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花费比吸收佛教更长的时间去吸收西方文化;当代人比古代人具备更多的历史自觉。吸收西方文化不意味着被动地去接受,否则就会像日本那样,在经济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在文化和哲学领域仍然是两张皮,不能产生新的理论。用一个比喻来讲,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用中国自己的思想资源为筐,有选择地去盛西方的文化价值,打造一只全新的美丽花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