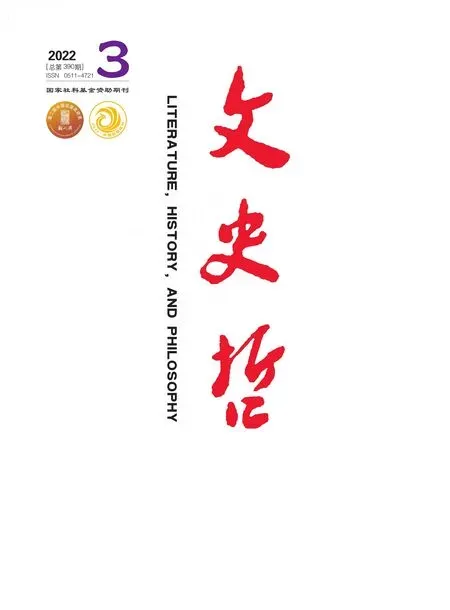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之圆通考释与谱系建构
2022-11-08李桂奎
李桂奎
在当今文论建设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其生吞活剥地套用某些体系化的西方文论,或口号性地呼吁“现代阐释”“现代转换”以及“现代重建”,倒不如遵从前人扎扎实实的考辨阐释路数,建构一套富有中国气派、东方气质的本土化、自主性理论谱系。一方面,相对于尚且拥有依稀可辨的谱系性的诗文理论、书画理论、戏曲理论而言,以各种序跋、评点、杂论以及小说话等形式存在的小说批评理论更多地给人以“寓目散评”“体系模糊”“碎片化”“拼盘化”等印象,因而期待借助古今贯通、中西打通等圆通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那些多元性、富有张力的术语进行考释,并通过探其语义源流,发其衍生意蕴,以滋补和增强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理论的元气和底气。另一方面,要将小说批评中那些相对松散的碎石瓦片建构成较为严密的理论谱系,也理应从最为基础的、具体的术语考释和阐发来做起。
一、古典考释及其与小说名实阐释之互通
众所周知,术语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构成要素,也是文艺理论言说或表达的工具。这里所谓的“术语”,既包括以往文艺理论研究中所谓的“称名”“概念”“范畴”“命题”等名堂不一的术语,也包括近年西方文论所谓的“关键词”意义上的术语。可以说,大多数文艺理论术语的命名是经过一番词汇遴选与长期文化积淀的,其意义指向大致有义理与艺理二端。在传统富有张力的“言意”观念下,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也大致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点展开。无论是望文生义的宏观概释,还是与时俱进的微观细释,都应尽量还原或拈用中国文论本色的诗性话语。从文体学与阐释学的双重视角看,“小说”固有的“说”“传”以及“演义”等术语的生发功能均可以与传统解释之学、传注之学、衍生之学形成某种呼应和关联,因而也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互通。
“考释”一词,最早见于清人阮元的《小沧浪笔谈》卷二:“篆文奇古,予为考释之。”尽管作为一个词语出现较晚,但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它却由来已久。大概从古代说文、释名、解义等方法启用,考释行为就开始了,至今仍行之有效。考,至少包括考其原始、考镜源流等内涵。释,既包括释其内涵、研精阐微,也包括新意生发等。在中国古代,以“解字”“释名”为名义的术语考释活动不仅源远流长,且历久弥新。其中,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著作开创了探求字义根源和阐释事物名、源的学术传统。考释之道看似并不复杂,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
由于术语的命名与创生至少应符合自洽性和有效性两条原则,因而术语考释也应以自洽性和有效性为旨归。传统形态的考释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打上了较为鲜明的经学印记。诞生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背景下的以分析古书章节句读为主的“章句之学”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不仅今文经学派自身颇擅此道,而且其“音韵”“文字”“考据”等注释经典的方略也常常被引入其他术语考释中,有效地发挥着文论衍生作用。可以说,包括小说评点在内的文学批评方式多生发于章句之学,许多文论术语释解“注重对文本的结构、意象、遣词造句等属于文学形式方面的分析,同时也不废义理和内容的考察”,在注重细微的注释和分析过程中,采取了“依经立义”“立象尽意”等言说方式。当然,汉代以来古文经学家所提倡的“我注六经”,即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今文学家所从事的“六经注我”,即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发挥自己的新见解,对考释法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就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实施而言,除了基本的字义、词义诠释,从命名视角阐释术语本身的意义、衍生的意义更为重要。依据传统名实文化,参照当今语义学阐释方法,从命名视角考释古代小说批评术语,有助于有针对性地考察古代小说作法及其文本审美规律。
历史地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典形态的考释法已趋于成熟。不仅儒家的章句之学已颇成气候,而且对佛教经论里出现的术语加以解说的“格义”法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其突出表现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汉代以来解经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考释之道。其中,《书记》篇明确指出:“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这里所谓的“解释结滞”是指解释行文中的不明之义,即刘勰在《序志》中进一步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这些方法皆旨在推原起源和演变,一言以蔽之曰“考”;这里所谓的“章”,即“彰”,所谓“释名以章义”是指从解释事物的名物入手,并进而将其含义放大,一言以蔽之曰“释”。基于此,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校勘学以及目录学的思想,就是对传统学术路数的精辟概括。总之,考释之“考”主要在正本清源、考镜源流,讲求文献依据;“释”主要在通过脉络梳理加以阐发诠释,讲求符合文化传统与历史语境。
再后来,历经延承今文经学解释方略的宋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洗礼,尤其是经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随后的叶燮等文论家的创造性发挥,考释法的义理考索与艺理思辨精神得到强化,滋养着方兴未艾的小说批评。到清代乾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为盛极一时的朴学,主要集中于文字学或考古学,尽管对以往的经世致用学术观念有所消解,但其所擅长的训诂、考订方法及其形成的求实严谨学风,对当今包括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在内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明清小说批评术语之考释接受了八股文阐释观念的影响,偏重于文法揭示,并显示出一定的重文字、音韵等训诂注释的特点。
当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与小说批评术语问题既可纳入阐释学视野来审视,反过来也可以用中国阐释学观念重新认识传统小说文体及其文本评语。刘勰《文心雕龙》在采取“释名以章义”方法进行文体辨析时常用“音训释名”。其《论说》部分是这样解释“说”字的:“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尽管在整个讨论中刘勰针对的是文体或文章,但我们不妨将这种关于“说”的阐释方法与“小说”批评术语之考释联系起来,由此进一步加深关于小说娱悦性的认识。再看,古代小说作品题名多含“传”“记”,固然是受史传文学影响使然,但也可以与传统阐释学中的“传注”结合起来看。关于“传”“记”“说”等方式的阐释学属性,李春青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注之学就是中国古代的经典阐释学。”“在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史上,‘传’是最早的阐释方式。”“除‘传’之外,较早的经典阐释方式还有‘记’和‘说’。”在古人多种多样的诠释观念中,除了用作小说篇目命名的“传”“记”“说”等术语之外,“演义”一词也含有阐释学与文体学双重功能。就“演义”一词而言,它也作“演绎”,一开始便是作为注疏学概念而使用的。作为一种方法,它常被用以解释词意,考证名物等等,自然被“考释”之法吸取借鉴。况且,在语义演变发展中,“演义”一词既保留了固有的“释法”之义,又具备了作为小说“文体”的特点。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曰:“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这种解释显然是针对小说创作融入更多虚幻、荒诞观念成分而言的。关于“演义”之原初,近代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看得较清楚:“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无论是“演言”还是“演事”,都具有推演阐释性质。早期“演义”的一种功能是,小说家依据经典来演说上世故事,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作适当的“增饰”。从阐释学视角看,“传述”“记述”“演义”自然都属于对原文本进行解说、解释、发挥的重要方法;而从文体史视角看,无论“传”“记”,还是“说”,又都是小说文体的某种重要形式或形态。这种创作方法与阐释方法的彼此呼应也为我们推动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工作开拓了思路。
概而言之,传统文论发展中形成的以文献考据与义理阐发为重心的古典术语考释法起源于“解字”“释名”,后在经学以及佛学等阐释观念影响下,形成刘勰所谓的“释名以章义”方法,再加其他固有的“音训释名”“以类证义”方略,皆对文论术语原初含义与后来衍生意义阐发具有普适性与长效性。就小说批评术语研究而言,古典术语考释方法可谓得天独厚:一方面,依托于“解字”“释名”“彰义”等常规术语考释,处于零散状态的小说批评术语可以得到整合、建构;另一方面“传”“记”“演义”等小说体式本身含有解释性质,自然与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存在天缘之合,渗透或寄生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自释中。如此说来,术语考释的过程也是一个小说理论不断生发、推演、提升的过程。
二、古典考释的现代化及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之实绩
作为抽象化理论概括的结果,各体文论术语中的很大一部分既生发于具体的各体文学实践,又期待依托考释不断地发扬光大。纵观中国文论研究史,人们在史的梳理与理论建构上常常以术语阐释为基础。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以及各种蜂拥而至的新思想、新方法的渗透和影响下,古典形态的术语考释得以脱胎换骨,并被广泛且有效地应用于各种文学批评史编写和文论研究当中。从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开始的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往往依托于对历代文论中富有活力的概念、范畴、命题等术语的考释。尽管一开始人们并没有采取“术语考释”或“话语阐发”等名义,但已显示出某种践行这种学术路数之实。直至近年,随着术语考释法的不断演进,新推出的“马工程”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仍主动选择立足于文论术语考释,其主编黄霖先生确定的编写理念是:“系统展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内容、重要范畴与基本术语,旨在梳理与彰显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为当前重建具有中国特色、又立足当今现实,并适应全球文化潮流的文论体系铺路。”尽管这是针对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普适性学术方法而言的,但对于传统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蓦然回首可见,20世纪上半叶,许多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一代学人,包括王国维、闻一多、郭绍虞、朱自清、罗根泽、朱光潜、宗白华、吴宓、陈寅恪、钱钟书、王瑶等文史学者,都曾凭着颇见功力的文论术语考释,一展开疆拓土的雄风。其中,王国维得风气之先,率先引领起从古典形态术语考释向现代术语考释的转型,不仅推出《论性》《释理》《原命》《释史》《释由》等文章,对古代文化中的几个核心术语进行了考释,而且还在《人间词话》中对其提出的影响深远的“境界”这一重要术语进行了重新命名、考释、建构。继而,在术语考释的现代化方面,郭绍虞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先是对“性灵”“神韵”“格调”等术语展开考释,写成《性灵说》《神韵与格调》二文;然后将其纳入《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等论著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构的奠基之作。随之,朱自清不仅对郭绍虞开辟的研究范式和治学方法深表认同与赞赏,而且还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1934)一文中指出:“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笔’‘道’‘贯道’‘载情’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些个术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强调懂得某些术语意义对懂得这些术语所处某一时代或所属某一理论家学说的重要性。继而,朱先生先后身体力行地运用语义分析和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对“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等诗论术语及其内在联系,展开较全面而深入的考释。后来汇成影响深远的《诗言志辨》一书。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朱自清所提到的各种标志性文论术语也陆续得到考释,代表性成果有,吕雪堂之释“风骨”(1915)、张寿林之释“神韵”(1928)、许群之释“意境”(1943)、傅庚生之释“赋比兴”“神气”(1945)等等。如此,经过王国维、郭绍虞、朱自清等一代学人的努力,古代文论固有的术语考释传统被大张旗鼓地从古典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对郭绍虞、朱自清等先生在现代学术史上所做的筚路蓝缕的更新换代的考释工作,陈平原曾纳入“关键词”视野审视,称之为“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为中心来构建批评史的研究框架”“借考证特定词汇的生成与演变,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这种从小处入手,以精密分析、仔细考辨为特点的术语考释方法及其在中国文论现代化与本土化过程中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再看,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基于术语考释方法的文论研究成果更是不绝如缕。颇具代表性者有,钱钟书的《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991年再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新增6篇文章)。前者长于通过引经据典并善于通过跨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等壁垒,对经史子集之文化符号及各种语词展开考论,不执着于术语考释却拓展了术语考释的方略;后者运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等方法,并借助对相关术语展开全面深入的比较,对《文心雕龙》中的各种创作论术语进行了严谨细致的考论,从而建构起“心物交融”说、“杼轴献功”说、“作家才性”说、“拟容取心”说、“情志”说、“三准”说、“杂而不越”说、“率志委和”说等“八说”理论体系。此后,术语考释法不仅成为打开“文心”的一把金钥匙,而且也成为开启“龙学”宝库的重要法门。特别需要称扬的是,童庆炳围绕其“文化诗学”理念,积二十多年之功,分别从语言之维、审美之维、文化之维三个维度,对《文心雕龙》中的“道心神理”“奇正华实”“会通适变”“因内符外”“循体成势”“感物吟志”“披文入情”等三十个具有命题性质的术语进行了深度考释与解说,汇集为《〈文心雕龙〉三十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显示出中西会通、古今贯通等现代综合研究的力度和水平。总之,现代学者们凭着较强的辨析、思辨意识和功力,围绕《文心雕龙》这一经典文论所展开的系列术语考释,发挥了引领学术转型的重要作用。
期间,在新的思想观念影响下,许多学者除了广泛关注“称名”“概念”“命题”等术语,还纷纷采取西方关于概括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观念,以“范畴”名义,对各种文论与美学术语展开系统研究。如,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精选了古代文论中的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意与境、体与性六对常见而又重要的范畴,既梳理其来龙去脉之“史”,又比照性地阐释其“意”。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按“心”“物”“感”“合”“品”及相互关系分五个系列,将收集到的近500条美学范畴放到整个中国古代美学与文化的思想体系之中进行把握,阐释了其基本内涵以及产生、演变过程。继而,各种以“范畴”命名的术语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如,蔡钟翔、邓光东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20种(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辑10种初版,2005-2006年第2辑10种初版)本着融会中西、古今会通、兼容并包的学术立场和实践理念,从“范畴”意义上梳理与阐释了感兴、意象、神思、格调、情志、知音等一系列美学理论术语。在此前后,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华书局2005年版)设立文德、文术、文体、文变四章,每章均择取其所属最为重要的概念、范畴,予以考辨和分析论述。这些研究成果既注重分门别类,又注意文化底蕴发掘。同时,人们还开始围绕“范畴”观念提出各种理论谱系或体系构建方案,并加以尝试。如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等文章倡导通过中外、古今文论比较研究来阐释并建构古代文论中的独特概念、范畴,并通过传统理论资源的汲取和利用,以实现当代文论话语谱系重建。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方法论》《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古代文论中的“原人”观念为核心,梳理、阐释了“情”“神”“意”“理”等范畴,影响也较为深远。另外,曹顺庆等人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版)从现代性意义上探讨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依经立义”“述而不作”等话语规则和意义生成范式。杨星映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古代文学理论要为当代人理解并运用,必然要进行阐释、介绍。所谓‘转换’,首先在于用现在的语言阐释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和体系,使当代人能够理解、掌握古代文学理论的特性和精髓。所谓‘重建’,是将其精华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打通古今,融会中外,从而建设新的中国文学理论。”此所谓“重释”“重建”云云,意思显然并非是强调推倒重来,而是注重重新发掘、重新梳理、重新搭建;所谓“转换”,也并非旨在腾笼换鸟,而是通过话语更新增强适用度和合理合法性。尽管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话语框架的约束,这些研究成果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系统梳理、明辨蕴涵的考释前功不容抹杀。
还有,随着西方“关键词”研究方法的引进,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阐释又开拓出一些新的思路。如,南帆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等研究成果为小说理论术语考释提供了参照和经验。张清华为《小说评论》开列的“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栏目立足当今,放眼传统,发表了关于“寓言”“传奇”“虚构”等关键词的释解,值得借鉴。另外,袁劲的《中国文论关键词阐释:方法、可能与局限》一文对以“关键词”观念研究古代文论研究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结,并提醒我们:“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以词语的遴选和类分为基础,以意义的阐释为落脚点。就方法而言,关键词的阐释只存在发掘文字根抵、梳理语义脉络、凝练方法启思等‘一般步骤’,而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公式’,也不存在非此不可的‘操作法则’。”在具体操作与实施过程中,术语考释的经验表明:它既不像各类辞典上的词语解释那样要求精准,也不像各种考试中的“名词解释”那样有相对正确的“标准答案”。小说批评术语考释自然也不求“一步到位”“一锤定音”,而是根据与时俱进的“一般步骤”逐步推进。
具体就小说批评术语与理论建构而言,学界也取得了一些实绩。首先是伴随各种小说批评史撰写,学人们推出了一些相关理论汇编与选释著作。如,曾祖萌等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黄霖、韩同文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著作曾涉及一些术语并展开过考辨注释。孙逊的《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范畴体系及理论贡献》(《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也已尝试对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加以宏观的把握和论述,从而为其《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编纂确立了纲领,并进而沿着这篇文章的逻辑思路加以分类和演绎。后来,黄霖、罗书华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的基础上撰成的《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对历代小说序跋、杂论、小说话资料进行汇编校释,并特别突出了某些术语之间的联缀性和系统性。
在各种小说文体、文法理论批评术语的考释及谱系梳理和建构方面,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曾依据当时的美学观念对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评点家所运用的各种术语进行过梳理,并从艺术赏析视角将各种理论阐释纳入小说审美体系。王先霈与周伟民合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则对上自明代洪武年间,下至晚清的各类小说理论进行过史的梳理和辨识,并进而从器识论、传神论、环境论、批评论、真实论、性格论、文料说、技巧论、鉴赏论等几个层面搭建古代小说理论体系。还有,宁宗一主编的《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小说学通论高度,不仅对先秦两汉至晚清的小说理论作了总揽式的博览,而且还从“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小说技法学”等层面进行了体系化建构。另外,王先霈等人编撰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致力于包括小说批评在内的各种术语阐释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源流以及脉络的历史性、系统性进行了梳理与建构,为进一步强化、深化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和谱系建构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古代小说理论术语考释的成果除了被穿插到文学批评史或小说理论资料的相关汇编著作之外,还有单篇论文。如,陈洪的《释〈水浒〉金批“因缘生法”说》(《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罗德荣的《为金圣叹“草蛇灰线法”一辩》(《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张方的《“传神写照”与“笔外神情”——中国传统小说人物论的一个相关阐释》(《理论月刊》2002年第6期),《“颊上三毫”:明清小说评点中的画论术语一探》(《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陈心浩、李金善的《“妙”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等等。此外,还有像赖力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和特点》(《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等论文,在梳理文学批评术语来龙去脉过程中,特别夹带着对“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一击两鸣”等小说戏曲形式技巧方面的术语的考释。
由此可见,术语考释,尤其是小说批评术语考释,成为现代学术的一道风景,令人驻足叹赏。当然,以往包括小说批评在内的文论术语考释工作也存在某些需引以为戒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有的将小说批评术语研究限定在“文体或文类的名词称谓”层面,有的简单粗放地用西方话语直接加以兑换,如将“绵针泥刺法”释为“讽刺”,将“背面傅(敷)粉法”释为“反衬”,将“欲合故纵法”释为“悬疑”等等,都存在某种误读、曲解以及简单化之嫌。在当今新的学术条件下,我们要注意纠正以往由“强制阐释”“过度阐释”“亏欠阐释”带来的偏差,对各类小说批评术语的原初底蕴、衍生意义以及升级意蕴进行新的要言不烦、推陈出新的考释与生发。
三、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中的贯通与会通
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过程中,为规避“分解”“稀释”等缺陷,我们要坚定地立足传统文化,不仅要以通观眼光来梳理术语的古今“通变”,而且要借鉴关键词、阐释学等相关理论以实现中西“打通”;不仅要做到跨学科“会通”,而且要做到跨文体、跨文类“融通”;不仅要把每个术语的语义释解得“贯通”,而且要借助架接整合使许多术语“联通”,从而达到“不隔”“入化”的“圆通”阐释境地。这种“圆通”性的术语考释既放眼传统文化语境与审美观念,符合言必问出处要理,又注意从通变性高度对各种小说术语的“义理”“艺理”展开全方位的考释,使之符合微观宏观相结合的学术之道。
首先,继续运行“推源溯流”“考镜源流”等古今会通观念,对小说批评术语展开历时纵向贯通的阐释。
要想把握某个术语的精髓,必须立足于刨根问底。在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中,着意运用“释名以章义”的这套古典考释方法,为术语考释达到“圆通”境地做好准备。有人将这种刨根问底的方法称为“工夫论”方法:“许多术语、范畴和命题,在古代都缺乏细致的解释,今人来研究它们,当然要从理论上把它们的内涵与意义阐释清楚。但是,这种理论上的阐释应该和工夫论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使得我们的阐释具有合法性和可靠性。”“所谓工夫论的方法,就是中国古代‘体——认’合一的方法。”为此,在对一个富含文化积淀的小说批评展开考释时,必须牢牢抓住其源头或根本做文章,而不能舍本逐末。如,关于“小说”这一术语,清代罗浮居士《蜃楼志序》曾释曰:“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这种术语解释工作不仅没有拘泥于字面意义,而且还把小说非关心“天经地义,治国化民”,注重“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事末理,有别于“瑰玮博丽”等宏大叙事,而趣向“一方一隅”俗语琐句等“小言”特点和性质,都一一揭示出来。如此从内容考辨到用语阐释的路数值得借鉴。沿此,我们奉行的“考释”之道自然并非仅限于字面含义的简单解释,而重在理论意蕴的生发。
在考察术语原初基础上,从古今延续的纵向维度,对各种小说批评术语所存在的嬗变承传、来龙去脉加以梳理,寻绎小说批评术语的源流衍变,以达成其语义衍生、衍变层面的解释。如,与上述罗浮居士注重阐释字义有所不同,在对“小说”术语考释时,明代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提出了所谓的“小说者,正史之余也”说,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则提出了所谓“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说,章学诚《文史通义》又提出了所谓“历三变而尽失古人之源流”说,他们各自围绕对“小说”性质的认知,对这一术语的发展和意蕴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历时梳理。
其次,借助“中外打通”“学科贯通”等学术理念,打开传统小说批评术语考释视野及共时“会通”新局面。
我们在对每一个具体术语进行考释时,既要通过纵向统释以“知变化之道”,又要通过横向通释以“知神之所为”,从而为每一个术语注入神气和活力。在现代学术背景下,要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化境”,必须在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中坚持以中化西,以今化古。换言之,要达到小说批评术语考释的“圆通”境地,就离不开跨文化、跨时空等圆通性研究。如何打通中西文论?对此,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曾基于其在《谈艺录》中提出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之学术理念,提出了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以求得共同的“诗心”与“文心”的学术之道,即“打通”。后来,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台湾学者黄俊杰的“经典诠释学”等皆值得借鉴。其中,成中英本着“中西互释与互通”观念,提出了这样一套理念:“‘诠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它可以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作出陈述与发言,表现诠释者心灵的创造力,并启发他人的想象力,体会新义,此即为理解。事实上,诠释自身即可被视为宇宙不息创造的实现。”通过跨文化视野的对话,形成涵盖古今中外的“打通”阐释。这些理念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已经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此不再赘述。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应该不再继续沿着将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及话语纳入西化小说理论体系那条老路走,特别注意避免继续将古代小说理论术语纳入西化“美学范畴”及“史论”之中,运用他者话语对其文体、文法术语进行阐释;注意避免将古代小说理论术语强拉硬扯到“典型”“情节”“性格”“人物形象”“结构”“叙述视角”“描写”“对话”等西化话语体系上。
就共时通释而言,其主要表现是对每一个理论术语进行跨文化、跨学科、跨文类等跨界链接和互释。在跨学科阐释方面,海外不少学者有自己较为独到的思考和建树,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术语多生发或借用于诗文理论、书画理论,因此应在其源流考镜上重视跨文类借境阐释及通变阐释。除了提出跨文化打通理念,钱钟书还曾指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既然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多从诗文、书画等其他前期文类理论发展而来,那么在文论术语研究中屡试不爽的考释方法经过调适和改进,也必然会更好地应用于小说批评术语考释。在这方面,谭帆所提出的“整体性原则”认为:“古代文论有其自身的民族性的理论体系,理论术语也有相应的系统,整体性原则就是要求研究者以系统为背景,确定某个理论术语在这个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因而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史’的意识,摸清理论术语的来龙去脉,同时又要注意术语的横向关系,即理论术语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所谓“横向联系”就是要打开古老的哲学、史学以及画学、建筑学等跨学科视野,与相关的小说理论及其他文体的跨文类视野,阐明其跨学科系统,进而从术语生成的共时性空间以及中外融通维度,达成知识层面的横向考释。如,笔者与黄霖先生合写的《中国古代写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一文借助现代语言学“态势语”理论、社会心理学“角色扮演”理论,从“表演”层面对其意义进行了发掘阐释,分析了其固有之“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的特征,对其从小说戏曲术语范畴被引入评诗、论画、谈稗的过程及其意蕴作了较为系统的考释。另外,张世君在其《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空间叙事理论探微》等论文基础上,推出《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不仅对金圣叹小说批评中的“忠恕”“格物”及其与佛教“因缘生法”融合的各种术语进行了系统考释性探讨,而且着意采取“细读归纳法”“比较方法”“还原验证法”以及“跨学科”等圆通性阐释方法,对“间架”“一线穿”“脱卸”“犯笔”“勾画和白描”“衬染与背面傅(敷)粉法”以及“字法”“句法”“章法”等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所谓的“叙事概念”术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和界定。这些概念性术语的释解所运用的建筑结构意识、戏曲段落意识、书法笔意意识、绘画图像意识、语言学修辞意识及其时间性与空间性观念,均值得借鉴。近年来,张晶的《阐释:作为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一文也倡言将“阐释”视为一种“古代文论的提升途径”,强调要注意这种阐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注释或校注之类,而是以原典文字含义为出发点,从美学、哲学、文化学或心理学等理论角度进行意义阐发或建构的过程”。小说批评术语考释自然也要借鉴这种执行理念。
再次,注重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与“文本本意”“文本原评”密切结合。由于许多小说批评术语生发于富有字法、句法之妙的具体文本,带有较强的文本针对性和依附性,因而只有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将批评术语考释落实到位。如,结合《少室山房笔记》中的相关论述,可以更好地理解胡应麟小说批评中的“传奇”“杂录”“辩订”等术语。又如,在阐释金圣叹小说评点所运用的“以文运事”“草蛇灰线”“横云断山”等术语时,就应依照其原始生发的文本加以解释。再如,结合明清小说所津津乐道的“画中人”传奇故事,可以更为有效地考释关于写人审美效果的“如画”“传神”“如生”“若活”等小说批评术语。另外,由于古代小说批评术语散落在各种评点、序跋、杂著或小说话中,因而要结合其得以生发、赖以生存的具体文本生态,考释这些批评术语。如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开头有眉批曰:“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这段文字一下子运用了十几条经过抽象提炼概括而命名的批评。对其意义之源,评点者脂砚斋明确指出这是“于逐回中搜剔刳剖,明白注释”的结果,仿佛如“考释”使然,旨在借此揭示“书中之秘法”,并指出小说文本所拥有的“草蛇灰线”等“诸奇”,以及其以“事则实事”为底色,以“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为追求等特点。可据此纳入当今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中。
同时,小说批评术语常常拥有自己得以生存的语境,前面往往有一些铺垫,后面也常常紧跟着一连串相应的阐发,据此展开的术语考释当最为准确有效。如,若对但明伦评《聊斋》所提出的“迷离闪烁、夭矫变幻之笔”这一术语展开考释,乍看比较晦涩偏僻,但只要联系蒲松龄《作文管见》所谓的“文贵转”与“文贵宕”以及其《与诸侄书》所强调的“避实击虚之法”,再结合但明伦评点中的解释性文字,就可迎刃而解了。原来,这个术语是对《葛巾》这篇小说所作的概评:“此篇纯用迷离闪烁、夭矫变幻之笔,不惟笔笔转,直句句转,且字字转矣。文忌直,转则曲;文忌弱,转则健;文忌腐,转则新;文忌平,转则峭;文忌窘,转则宽;文忌散,转则聚;文忌松,转则紧;文忌复,转则开;文忌熟,转则生;文忌板,转则活;文忌硬,转则圆;文忌浅,转则深;文忌涩,转则畅;文忌闷,转则醒。求转笔于此文,思过半矣。”由这段较为细致的分解评说可见,所谓的“迷离闪烁、夭矫变幻之笔”不过主要是讲的一个“转”字,大意指的是故事情节的转折、回转和转变,即曲折多变。
另外,除了纳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大合唱的个体术语考释、话语阐发,学人们还特别注重术语联通考释,尤其是注重借助传统文论家的术语互释建立术语群之间的关联。如,元代杨维桢《图画宝鉴序》曾经指出:“故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由此建立起“传神”与“气韵生动”二者之间的互释关系。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曰:“韵者,态度风致。”“气之精者为神。”由这种互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术语与术语之间的联通,而且这种术语链接有利于构架小说理论谱系。
总体而言,在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中,我们应通过兼顾作者、文本、读者几个层面的贯通新解,使得各个术语保持一定的个性和活力,为理论谱系建构凝神聚气。为了保证这种理论建构的有效、特效、高效,我们既要重视通过语境还原,以探寻原汁原味的本义;又要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加强义理阐发,将那些处于各种休眠状态的术语激活,从而达成从关键性术语的考释到观念性话语的阐发,再到学理性谱系的建构。
四、从类分式术语统合到统序性谱系建构
常理说,在分门别类地辨章学术基础上,从考释其意、考镜源流入手,进而通过脉络梳理、整合,可以达成新的小说理论谱系建构。据初步估算,散见于各种小说序跋、评点、小说话、杂论中的各种称得上“术语”的概念、关键词、范畴、命题等不下千条,有的是生发于书画的元术语或根术语,有的由诗文术语衍生而来,有的依附于小说文本自生自长。面对如此数量洋洋可观的零散的、碎片化的小说批评术语,我们应按照依类相从等原则予以梳理整合,纵横交互地实现其谱系性的系统建构。
首先,为保证摸排搜辑过程中的数量、质量及有条不紊,我们应从小说序跋、小说评点、小说话、小说杂论等形式入手,将各种批评术语提取出来,加以分门别类和统筹整合。关于中国文论的特点,刘若愚曾在其《中国文学理论》指出:“在中文的批评著作中,同一个词,即便由同一作者所用,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考释和建构中对相关术语分类、归类、整合。相对而言,小说批评术语既有碎片化零散实质,又有可整合的“统序”潜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用“求同”思维对各种术语的兼通功能和文本指意进行统筹概括,使之“以类相从”,具体操作和实际处理不妨参照黄霖在谈到“古代小说分类”问题时提出的“辨性质、明角度、趋大流”三原则;另一方面,又要用“辨异”思维凸显单个术语的特殊功能和独特意义;还要按照大小层级对各种术语归类整合,对同一家族的兄弟术语以及一脉相承的祖孙术语进行组合、整合,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大谱系。
具体而言,对那些名称不同但意义相似的术语,可以直接进入谱系建构程序,在谱系建构过程中顺带阐释。如,将金圣叹的“皮里阳秋”“太史公酒账肉簿”“史公笔”,张竹坡的“阳秋之笔”“春秋字法”“春秋笔法”等大同小异的诸般术语,直接纳入“拟史笔法”术语序列进行系统化考释;将金圣叹的“深文曲笔”“叙事微”“用笔著”,张竹坡的“隐笔”,脂砚斋的“曲笔”,哈斯宝的“必从远处绕来,曲曲折折”“史臣臧否之法”等等,直接整合到“曲笔”术语序列进行系统化考释;将李日华《广谐史序》、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张无咎《北宋三遂平妖传序》、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吉衣主人(袁于令)《隋史遗文序》、黄越《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小说“真假”“奇正”等问题的大同小异的术语,掇拾在一起,采取“组合并解”法加以整合互释、通解。对那些需要稍加阐释即可沿用的术语,如毛宗岗父子评《三国志演义》所谓的“起结”“照应”“关目”,张竹坡评《金瓶梅》所谓的“两对章法”,就不必专门解释。对那些诸如“截法”“岔法”“突然法”“避难法”“由近渐远”“将繁改简”“暗透法”“进一步法”“退一步法”“错综法”“倒卷帘法”“自难自法”等等字面显得明了、无须进行专门考释的文法术语,也可按照层级,将其归入相关、相似的术语系列来阐释、建构。
其次,在术语考释、整合过程中,除了关注“源”“流”,还要强化脉络梳理,在谱系建构中关注“义脉”“血脉”“命脉”等历时性之“脉”,以建立起某种历时性的“统序”。由于各种术语在应用过程中或被与时俱进地赋予某种新的意义,或自身生生不息地生出新的内涵,存在一个“古今”问题,因而,我们应以“通古今之变”的气魄对各种历久弥新的术语展开“通义”“史统”性的考释。同时,在立足于本土文论建设基础上,我们可借鉴西方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所提出的将阐释者现在的视界与历史上本文作者当时的视界融为一体的“视界融合”观念。通过自觉与古人、西方人对话,在话语融通、会通中完成术语考释。如,胡亚敏曾将布迪厄“场域”理论引入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探讨,既把某些术语的社会文化意义落实到具体初始、生成、延展、本土四个“场域”之中,又按照一定的发展轨迹将小说批评术语编辑成带有历史感的叙事,并把这种历时演变形象地称为“概念的旅行”。采取这种“历史场域法”,可有效地组结一系列小说批评术语宗亲、家族与群落。
再次,为强化层次性与立体感,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谱系建构还要特别讲究“共时性”的会通和“互文性”的联通。对此,前人也已踏出一条可行的路子。如,谭帆在20世纪80年代即意识到:“理论术语内在意蕴的多义性,形式组成的复合性以及外部构造的序列性是古代文论术语构造特征的重要方面。”近年,他把“从术语的解读角度梳理小说史”当作“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从文体、文法视角切入组建团队,对“小说”与“演义”“补史”与“通俗”“虚实”与“幻真”“奇书”与“才子书”等小说文体与文法术语展开集中考释。其系列研究成果已汇聚成《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又如,汪涌豪的《范畴论》(2017年再版时,题名《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曾以“小说范畴总结与重要范畴分释”为题,对“幻”“避犯”“白描”等几个重点范畴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考释,并进而对“诸范畴的联通及意义”进行了探讨,也在尝试走一条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统序特征”的综合考察,以建构严密的小说理论谱系的学术路子。无论如何,考镜源流、梳理脉络、统筹整合等系统化工程是中国小说理论谱系建构的必然创获。
概而言之,正如其他理论术语的考释及相应谱系的建构均非一蹴而就、一锤定音一样,中国古代小说批评术语考释与谱系建构工作也离不开动态整合,以及不断地圆通化提炼、系统化提升。在当今学术背景下,只有将各种传统小说批评术语的内蕴激活,使之成为中国本土化小说理论谱系建构的活力素,只有基于对各种小说批评术语的主从、共生、平行、互渗等族群关系进行系统化的类别区分、层级整合、脉络梳理,进而依托于对各种术语进行纵横交互的圆通性考释,才能使得中国小说理论谱系的建构工程牢不可摧,才能付诸有效应用并有望为全球化文论发展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