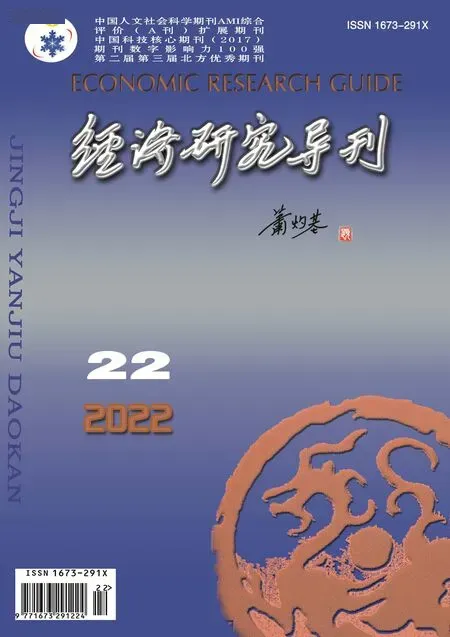新型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研究
——以“直播用工”为视角
2022-11-08张文涛
张文涛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00)
一、MCN 机构与网络主播间新型劳动关系概述
(一)“数字经济”下的直播行业
随着互联网迈进“数字时代”,网络直播越来越成为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方式。直播也作为一种劳动就业方式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同时新的劳动就业方式也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MCN”机构常与视频直播平台合作,进行受众群体评估、流量投放,协助创作者进行人设营销等,以获得收入。《中国MCN 行业发展白皮书》称,“MCN”是新兴商业组织,从事热点内容产出、网红培育、流量获取变现活动。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直播行业网红“内卷”化效应出现。在严峻的行业形势下,大小主播为了寻求发展纷纷选择与MCN 机构签约,随之“主播—MCN—直播平台”的商业模式逐渐成熟。
新型就业模式的出现,也给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方式带来了极大挑战。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对于维护新型就业劳动者方面发文指出,对于在形态上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典型情形的,但用工方实际上对劳动者进行了劳动管理的,用工方应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认用工方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在实践中,MCN 机构与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纠纷的案例日益增多。由于实践中劳动从属性的认定标准模糊且相关劳动法律滞后、新型劳动关系认定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大肆出现。
(二)直播用工新型劳动关系认定司法实践出现分歧
近年来,网络主播申请确认与MCN 机构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不断增多,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根据双方的合同性质加以甄别并通过合同双方的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判断双方构成劳动关系或者普通民事关系,但因缺乏统一的司法指导判例以及司法解释,往往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1.〔2021〕苏0302 民初230 号:法院认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涉案合约虽名为《艺人独家经纪合约》,但根据该协议约定的内容,以及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地点、时间、报酬计算办法等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主要条款。虽名为经纪合同,实为劳动合同。
2.〔2021〕桂0403 民初2036 号:法院认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主播需接受原告的专业培训;不得私自在任何平台进行直播,不得自行选择直播地点,必须在MCN机构指定的平台、地点进行直播;公司对主播的直播天数、每月累计直播时间、每天直播时间段等工作内容有严格的规定,并对被告进行考勤。以上事实均体现了原、被告具有隶属关系,原告对被告的劳动进行管理。双方存在从属性,故原、被告之间属于劳动关系。
3.〔2021〕湘02 民终1115 号:法院认定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主播独家合作协议》是双方基于互利互惠的合意而签订的合作协议,且在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可见双方之间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从内容上看,原告直播的时间、内容都由原告自主安排,被告不作要求,故双方并不构成劳动关系。
4.〔2021〕苏03 民终6315 号:法院认定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MCN 机构没有对主播进行劳动管理。由双方签订的独家经纪合约可知,仅有主播每天需要直播6小时的约定,但具体的直播时间、直播内容、直播场所并无约定,双方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故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5.〔2020〕京0115 民初12563 号:法院认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MCN 公司与主播签订了《全职主播签约协议》,且公司主要经营的业务为组织主播在第三方网络平台上做网络直播。其间,主播的工作内容为通过在用工方指定的第三方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主播进行网络直播所需的设备由其自己提供,其网络直播地点公司不做干涉。关于薪酬,主播的工资结算周期为自然月,公司在次月向主播发放上个月的工资。除全职主播签约协议之外,MCN 公司未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法院经审理判决: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直播行业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同时,由于配套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许多弊端。在劳动法领域,出现了MCN 机构与主播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种新型劳动关系的认定出现了分歧,新型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模糊。如案例一与案例三,双方同样签订的是名为合作协议的合同,两位裁判人员却给出了不同视角的解读;案例二和案例四,同是主播在直播工作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决定的权利,最终得到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的结果却是相反的。以上案例挖掘出的问题是灵活就业带来的新型用工方式对传统从属性认定标准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梳理直播用工中存在的特点、厘清主播与MCN 机构之间的协议性质,从而准确地对个案中网络主播与MCN 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判断,为直播行业健康发展与主播合法劳动权益保护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三)MCN 机构与主播间新型劳动关系的特征
司法裁判中的分歧,归根结底来源于对法律现状与现行法律的不适应。MCN 机构与主播间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劳动关系的特征。具体表现于:第一,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主播对MCN 机构的从属性趋于弱化。在直播行业中,由于互联网用工的现实因素,往往主播在人格上对用工方的依附弱化,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与内容的输出上保有一定的自主性与自由度,这种自主性会使得其人格从属性表现上较为模糊。第二,MCN 机构对主播之间的管理宽松。网络直播本质属于互联网行业。其工作本身带有了互联网行业的随意性与包容性,在劳资关系、企业管理、组织架构多方面均带有一定的弹性。在直播工作中,相较于传统工厂式劳动,主播可以在用工方规定的一定时间范围内,合理安排直播时间;在直播内容上在用工方规定的大体方向上自主输出直播内容,即在工作时间、工作内容上较为宽松。但是这种宽松,是基于互联网行业的特质,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不能掩盖网络主播在人格、经济、组织方面从属于MCN 机构的本质。第三,MCN 机构与主播的协议具有“去劳动关系化”的特点。资方在资本运营中,总是绞尽脑汁地减少生产成本,这是资本的先天性。互联网行业的松散化运行、直播行业的野蛮生长与配套法律的滞后,更是产生了处于劳动法规制死角的灰色地带,若机械化套用传统的从属性认定标准,则会将该类劳动者排除于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MCN 机构更倾向于签订合作协议而并非劳动合同。虽然名为合作协议,但是在内容上经常存在竞业禁止、工作考核、管理惩戒、请假批准、直播时间限制保底收入、绩效发放等具有劳动合同性质的条款。导致双方签署协议的性质界定模糊,若依据合同抬头名称来断定合同性质,其结果将会与对条款内容逐一分析的判决结果大相径庭。
二、审视传统劳动关系中从属性认定标准的不足
劳动关系是在社会化生产中劳动者与用工方所产生的特殊法律关系。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之所以未纳入民商法的调整范围而纳入了社会保障法来调整,原因在于劳动合同虽是劳动者与用工方劳资双方达成合意的平等合同。但实际上,因为劳资双方的天然不平等,劳动者想要谋生,就必须接受用工方提出的条件,对用工方的管理进行服从,故双方并非民商事合同中的“平等主体”。所以从劳动合同签订之初,由于双方的不平等地位,劳动者天然处于劣势,一定程度受制于用工单位。可见,从属性是劳动关系的天然属性。因此,在判断合同双方是否属于劳动关系时,判断其是否具有从属性是重中之重。虽然我国与德国、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也在市场经济中接受了从属性这一概念,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若劳动者受用工单位的劳动管理、且从事用工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劳动者需遵守用工方制定的管理制度,则可认定为劳动关系,并将从属性细化为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的认定的重要标准。但是,这种传统从属性认定方式是衍生于工业时代工厂与工人的劳动模式下的,此种传统的劳动关系不论是在人格、经济、组织方面,都体现出了强烈的从属性。但在信息时代,劳动关系已经脱离了传统劳动关系中“打卡坐班”模式,劳动者与用工方之间利用网络技术甚至实现了居家办公;生产活动更加具有创造性,劳动方式更加具有灵活性,劳动者对于用工方的从属性往往表现为技术从属性和提供劳动的渠道的从属性。与传统的劳动关系相比,这种新型就业关系的从属性较为模糊、从属强度减弱,如仍用传统的从属性判断标准来套用此种新型劳动关系,可能会因为劳动者表面上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导致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三、完善“直播用工”中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把握从属性的核心实质——劳动管理
有观点认为,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内核是双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者接受用工方管理、指挥、监督并通过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但当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对劳动管理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在实践中综合考量,判断是否存在劳动管理应着眼于以下几个要素。
1.主播是否有最低工作量要求。在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可以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来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约束,劳动者与用工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劳动时间自然要服从用工方的调度。设立最低工作量,可以视为用工单位劳动者劳动的一种管理。在案例五中,涉案《全职主播签约协议》约定,有效主播每月需要完成一定的工作时长,未达到者单个主播无底薪结算。可见,MCN 机构对主播的相应劳动时间具有管理、支配权,事实上存在劳动管理。
2.主播是否受到用工方的指令、监督、管理和惩戒。人格从属性是劳动关系中最能体现劳资从属关系的物质。而人格从属性的体现就是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监督、管理和惩戒行为。在案例五中,MCN 机构曾通过微信通知主播定时开播。可见,MCN 机构对主播存在发送指令的情况。双方协议规定,甲方有权对乙方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在一定情况下,公司有权按照规定处理并取消主播直播资格。可见,主播需要遵守MCN 机构制定的主播管理规定,并接受MCN 机构的监督、管理,甚至惩戒。综上可见,主播对MCN 机构有极强的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
(二)重视直播用工中存在的“技术从属性”
利用电子通讯设备和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远程用工和劳动,已成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的一种用工模式,劳动者在该模式下提供劳动的过程往往发生在用工方的办公场所之外,用工方在该模式下往往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与劳动者进行联络。同时,劳动者在提供劳动方面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上述情况下,劳动者对于用工方的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往往表现为技术从属性和提供劳动的渠道的从属性(如网约车、外卖员只允许在唯一平台注册并进行服务)。在案例五中,主播只能在MCN 机构指定的第三方网络平台上唱歌、聊天,而不得在其他网络平台上做网络直播,即主播的网络直播活动具有排他性。由此可见,主播提供劳动的过程对MCN 机构有极强的技术从属性和提供劳动的渠道的从属性,存在着劳动管理。
(三)厘清“合作协议”的实质,合理认定法律关系
如前文提及,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资本寻求降低开支是必然,显然签订一份劳动合同要比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要更不“划算”,故不能仅通过协议抬头名称来判断双方的法律关系,需综合考察、多要素考察双方是否具有从属性。在直播用工中,直播地点、直播内容、薪酬发放也是判断MCN 机构与网络主播之间是否具有从属性的重要考察因素。若网络主播的直播地点由MCN 机构统一安排集中管理,不允许主播擅自更改的,可认为MCN 机构对网络主播存在劳动管理;直播内容若由MCN 机构进行统一指示、主播仅负责执行演绎,可认为主播是对自己被安排的工作任务的执行,可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人格从属性;若薪酬工资有规律地按自然月发放,对主播按月有规律发放绩效奖金、提成等性质的劳动报酬,具有明显的劳动报酬特征的,也可以作为双方之间存在经济从属性的重要依据。这些要素不会显而易见地体现在合同名称中,需要参照双方协议实际履行情况以及协议细则,判断是否具有从属性,最终确定协议的性质。
结语
随着互联网经济与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MCN 机构+主播”商业模式的兴起既带来了新型用工模式也给传统的从属性认定标准以及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带来了挑战。对于新经济形态下的新型就业模式,现有的从属性标准仍然适用。但是判断是否具有从属性,应根据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劳资管理的实际情况。即便劳动者在提供劳动方面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劳动者对用工方的从属性仍是判断劳动者与用工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为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故对于从属性因素的考察需更加灵活,不能一味强求将新的社会关系套用进传统的判定标准,应更加注重从实质要素考察从属性,从而合理解决新型就业模式带来的劳动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