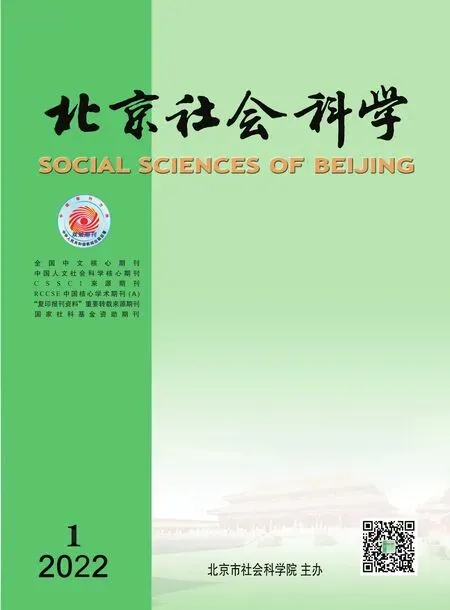论晚明家具的审美“真趣”
2022-11-08仪平策周坤鹏
仪平策 周坤鹏
一、引言
晚明时期的家具一直是中国传统家具研究领域的热点,虽然其形制和工艺在南宋时已基本成熟,但其突出的艺术价值和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却与这一时期特殊的审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心学泰州学派“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等思想的影响下,晚明文士群体开始将自己的热情投注到日常生活领域,他们积极地参与家具等日用器的设计和品鉴,致力于经营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其审美趣味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家具审美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在对晚明家具审美特征与文人趣味之关系的阐释上,学者们大多围绕“素朴”“淡雅”等古典美学趣味展开,如王世襄所提出的“明式家具”艺术价值较高的“十六品”多数都偏于简约素朴、清新自然的风格;朱家溍先生也称明式家具“淳朴厚重”“空灵秀丽”“典雅清新”。然而,从大量晚明时期的话语、文本、图像以及现存家具实物上还可以看到,包括晚明文人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家具审美也在很大程度上流露出崇新尚奇、溺情享乐的一面。那么,为何这一时期的家具会呈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美学风格?到底是哪些文人趣味,又以何种逻辑对当时士民的家具审美产生影响的?这些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的理论空间。我们认为,这种复杂的、多元的家具审美现象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特别是晚明士民拓展了、丰富了的尚“真”趣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尚未得到学界充分的论证,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二、晚明文人承自传统的崇“真”尚“淡”趣味
“真”,是古典美学尤其是道家美学的重要范畴。道家将“自然”视为生成万物、规范万物的最高法则,《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在庄子看来,“真”就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所以他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从现象层面看,道家的尚“真”趣味突出地表现在其对自然、平淡、素朴的审美意象的强调上。《老子》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又云:“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庄子也称:“若夫不刻意而高,……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又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无为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可见,在道家那里,“恬淡”“朴素”是合于天道之“真”和圣人之德的大美所在。道家的这一崇“真”尚“淡”趣味,一方面表现为崇尚“物性自然”的自然主义审美观,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平淡、素朴的审美意象的偏好。魏晋南北朝士人喜谈玄说庄,道家这种崇“真”尚“淡”的观念也随之在文士阶层中扎根。宗白华先生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初发芙蓉”的天真、自然之美在人们眼中开始成为比“错采镂金”的雕饰之美更高的审美境界。
儒家对平淡、素朴的审美意象也多有推重。子思评《诗经》“衣锦尚絅”,由穿衣引申为君子外表暗淡,而美德日益彰显,小人外表鲜明,但美德却日渐消退,认为君子之道在于平淡、质朴而有文采。《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其对君子之道的阐释使平淡、素朴也成为儒家重要的审美意象。
唐宋以后,佛教禅宗思想的流行进一步强化了文士群体崇“真”尚“淡”的审美观念。唐代禅师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马祖道一的俗家弟子、深受袁宏道等晚明文人推崇的庞蕴居士也有偈云:“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禅宗在北宋时达到鼎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平淡”趣味成为文艺领域中极为重要的审美标准。在文学领域,与高僧多有交往的苏轼认为诗文应“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梅尧臣称“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陶渊明的诗亦因其“平淡”“自然”的风格而在宋代被推至高于其他任何时代的地位,如葛立方称赞陶诗:“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所为也。”在绘画领域,米芾称赞董源“不装巧趣”的画作有“平淡天真”之趣。可以说,融会儒、道、释三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本体论色彩的平淡、自然趣味在北宋时已成为古典美学的核心内容。
然而,随着程朱理学与伦理、政治的深度捆绑和对文艺领域的不断渗透,传统的“崇真尚淡”趣味逐渐被“崇道尚理”的风气所淹没。朱熹在阐释周敦颐的“无极之真”时称:“所谓‘真’者,理也。”在朱熹那里,只有体现封建纲常伦理的文艺作品才可称得上“真”。对此明代李梦阳批评道:“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而今之文……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
直到明代中后期,古典美学的崇“真”尚“淡”趣味才重回人们的视野。晚明吴从先直言“趣要澹泊”,陈继儒在为董其昌《容台集》所作的序中赞其诗文:“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矣,姿态横生矣。”绘画领域也是如此,董其昌称赞元代倪瓒之画“古淡天然”,王世贞在谈及万历年间士民对绘画作品喜好的变化时称:“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沈周,价骤增十倍。”在许多晚明文人眼中,倪瓒、沈周等人萧疏淡雅、有“平淡自然”之趣的画作的艺术价值是高于端庄、典雅的宋画的。
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体的古典美学尚“真”趣味之所以在晚明时重新成为文士群体判断文艺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一方面与道家美学、禅宗美学长久以来的文化“积淀”“濡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心学诸子“援禅入儒”的理论路向所导致的“佞禅”世风有关。晚明心学创始人王阳明本人就承认其“心学”与禅学有一定的相似性:“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阳明的弟子王畿也曾言:“深山有宝,无心于宝者得之。”这种不刻意、不造作、顺其自然的学道方法,与唐代禅师临济义玄所谓“随缘消旧业,任运著衣裳……无一念心希求佛果”的修佛路径如出一辙。
泰州学派王艮的思想也跟禅宗多有相似,他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又说:“凡涉人为,皆是作伪。”嵇文甫先生称这种不假人为、纯任自然的观点“全然是一种自然主义”。王艮再传弟子赵大洲也承认自己与禅学的关系:“仆之为禅,自弱冠以来,敢欺人哉!”晚明思潮的中心人物李贽甚至将笃信佛禅的赵大洲誉为泰州学派翘楚,当时的佞禅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阳明后学,尤其王畿和泰州诸子与禅学的这种亲密关系,使晚明文人与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渊源颇深,对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体的古典美学尚“真”趣味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一观念背景对晚明士民的家具审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晚明士民家具审美的古典“真趣”
晚明文人承自传统古典美学的尚“真”趣味对家具审美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们对自然天成、不假人为的家具造型、材料、纹理的喜爱上。顾起元称友人严宾的枣根香几:“天然为之,不烦凿削,最称奇品。”高濂《遵生八笺》记载过一种“以怪树天生屈曲环带之半者为之”的“隐几”,还有其好友吴破瓢藏有的一“几”:“树形皱皮,花细屈曲奇怪,三足天然,摩弄莹滑,宛若黄玉。”文震亨《长物志》也记载过类似造型的“几”,文氏还提到一种自然天成、不事斧凿的“禅椅”:“以天台藤为之,或得古树根,如虬龙诘曲臃肿,槎牙四出……更须莹滑如玉,不露斧斤者为佳。”文氏所言以天然老藤、古树根制成的坐具与陈洪绶画作(《隐居十六观图(之一)》《吟梅图》《祝寿图》)中的坐具亦相仿佛。
在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柴木家具、漆作家具一直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晚明士民却偏爱用天然纹理优美的“文木”制作的家具。文震亨曾直言“天然几”应“以文木如花梨、铁梨、香楠等木为之”。早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便已记载过“花有鬼面者可爱”的“花梨木”、“花细可爱”的桦树“瘿木”和“有山水、人物等花”的“骰柏楠”等“文木”,但当时这几种“文木”主要被用来制作小件工艺品。晚明苏州、松江一带的文人热衷于家具的设计和品鉴,他们的审美趣味使纹理优美的“文木”成为家具设计的新宠。万历年间松江人范濂记载:“细木家伙,……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莫廷韩与友人用“椐木”(即榉木)家具替代民间流行的银杏木金漆家具,与他们对榉木自然纹理之美的喜爱有很大关系。“纨绔豪奢”用花梨、瘿木、相思木来制作家具,其动机虽在竞奢夸富,但也不乏对这些木材优美的自然纹理的欣赏。张岱曾祖张元忭在《绍兴府志》中也记载了几种当地出产的“文木”,如“木纹理缜密,而黄色可爱,堪为器具”的柘木,“理坚,斜斫之有文,可作器”的相思木等。从张氏行文不难看出,木材的自然纹理之美已成为晚明家具审美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文人趣味的引领下,使用“文木”制作家具在晚明逐渐成为时之所尚,目前存世的大量以花梨木、铁力木、紫檀制成的晚明家具正是在这样的审美文化背景下出现的。
此外,还有一些材料也因优美的天然纹理而为晚明士民所喜爱,例如斑竹。斑竹,又称湘妃竹,因竿部生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点而有清雅自然之趣。《绍兴府志》载:“越中有顾家,斑竹用以作床、椅及他器,具甚清雅。”文震亨、屠隆二人都曾提到可用斑竹装饰榻的围屏,高濂称可用斑竹制作“禅椅”。张岱则提到一位因擅长制作斑竹家具而闻名的姜姓匠人:“又有以斑竹为椅桌等物者,以姜姓第一,因有姜竹之称。”仇英画作《人物故事图(之七)》中宾主三人所坐之玫瑰椅、坐墩也是以斑竹制成。晚明士民对用天然树根、古藤制作的隐几、坐具和用纹理美丽的“文木”、斑竹制作的家具的欣赏,与崇尚自然天成、不假人为的古典美学尚“真”趣味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晚明士民家具审美的古典“真”趣还体现在他们“尚古朴不尚雕镂”的偏好上。晚明之前,一般百姓家中多使用价格低廉的柴木家具,而富裕的士商阶层则喜欢装饰性强、富贵华丽的漆作家具。据嘉靖年间巨贪严嵩的抄家录《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家中最珍贵的家具主要是17张未作“变价”直接收入内库的床,如“雕漆大理石床”“黑漆大理石床”“螺钿大理石床”“堆漆螺钿描金床”等。这些床用大理石、螺钿等珍稀材料装饰,用雕漆、堆漆、描金、镶嵌等复杂工艺制作,可谓穷工极巧。此外数百张折卖成白银入库的“变价”之床,如“螺钿雕漆彩漆大八步床”“描金穿藤雕花凉床”等,也都极尽装饰之能事。这种以雕镂为美的家具审美趣味在晚明之前的官绅阶层中非常普遍。
而在晚明,随着文士群体对家具设计和品鉴的参与,他们的审美趣味使原先以雕饰为美的家具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如文风鼎盛的苏州地区孕育出了为今人所激赏的古朴、清雅、不事雕琢的“苏作家具”。晚明王士性曾言:“姑苏人聪慧好古……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苏作家具素朴、淡雅的美学风格与文士群体的“平淡自然”之趣息息相关,这一点从当时的文人话语中也不难看出。文震亨曾明确反对“雕绘文饰,以悦俗眼”的家具风格,他认为亭榭中所设之桌须“旧漆方面粗足,古朴自然”,而卧室所用家具、陈设须“精洁雅素”,倘若“一涉绚丽”,则“如闺阁中,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家学渊源使其深谙传统文人趣味,他在家具及其陈设方面所提倡的“宁古勿时、宁朴勿巧、宁俭勿俗”的审美取向,正是对古典美学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体的尚“真”趣味的一种传承。
四、晚明浪漫美学思潮中“真”范畴的拓展
“真”也是晚明浪漫美学的核心范畴。汤显祖称“不真不足行”,李贽说:“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袁宏道则称赞“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民间戏曲为“真人”所作之“真声”。在袁宏道看来,能够“任性而发”,与审美主体真实的情感、个性、欲望息息相通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难看出,汤显祖、袁宏道等人口中的“真”已不再局限于古典美学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平淡自然”之“真”,而更多是以主体的情感之“真”、个性之“真”,甚至以欲望之“真”为核心。晚明美学“真”范畴的这种拓展一方面源于文士群体对明初文艺领域“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的理学风气,及明中期李梦阳等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所导致的模拟剽窃之风的修正;另一方面更与高扬主体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晚明浪漫美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袁宏道在评价张幼于的诗文时称:“两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所谓“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表面看是对儒家经典话语“率性之谓道”的转述,但其真正意涵已与儒家经典有很大不同。儒家“心性论”所言之“性”,自子思、孟子而二程、朱熹,再而王阳明,都是指纯然至善的先验道德理性,如王阳明称:“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在王阳明看来,《中庸》所言“率性”之“性”即是“至善”的“道”:“‘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而“率性”之“道心”与“人欲”有着清晰的界限:“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可见,阳明所言“率性”尚未脱出儒家经典的框架。
真正将“率性而为”导向自然人性之“真”的是泰州诸子。王艮讲学不似其师阳明般谨严,他认为“良知现成”,提倡顿悟之学。在他看来,一旦悟得良知本体,便可信心而行,甚至不须防检。他说:“道一而已矣。中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识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失,便是庄敬;即此常存,便是持养,真不须防检。”王艮弟子徐樾也说:“圣学惟无欺天性,聪明学者,率其性而行之,是不自欺也。率性者,率此明德而已。”虽然王艮、徐樾等人仍算站在道学立场而言“率性”,但他们这种不加检防的修养方法为颜钧、李贽等人走向自然人性论开了一道口子。王艮弟子颜钧称:“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着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在颜钧看来,欲望只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流露,他称:“贪财好色,皆从性生,天机所发,不可阏之,第勿留滞胸中而已。”颜钧弟子,深受李贽等人推崇的罗汝芳也说:“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理念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核心标准与计划依据,对整个教学过程起关键性作用。然而,传统语文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将教学目光集中在促使学生积累语文专业知识与学习技巧、提高学生语文基础能力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的情感素质人文性教学,这与现代化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学要求不符,也不利于构建学生的自主认知,难以培养学生形成逐步完善独立的学习思考意识。鉴于此,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注重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增加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性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独立意识,增加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李贽明确将“真”的意涵归结于人的自然本性——“童心”,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所言之“真心”是跟王阳明的“良知”类似的本体论概念,在他看来,包含情感、欲望等自然人性的“童心”便是“真心”,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去做事便是合道“真人”。而且“童心”还是文艺创作的根本,文章只有从自己的“童心”流出,才是“真文”、好文。也就是说,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不是达到“礼义”等外在伦理的要求,而是要符合主体情性之“真”的内在要求,艺术家的真情实感、个性甚至欲望才是作品最重要的内容,正如他所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
经由泰州诸子的理论演绎,主体的情性之“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体论色彩,成为“道”、天理的体现。虽然他们口中到达“真”之境界的路径从表面看也似前人所说的“率性”而为,但他们这里的“性”之“所指”显然已不再只是子思、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人那里纯然至善的先验道德理性,而是包含主体的情感、个性和欲望的自然人性了。在晚明浪漫文艺思潮的主要干将中,汤显祖曾师事罗汝芳,袁宏道视李贽为知己,泰州诸子带有自然人性论色彩的思想对其文艺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他们杰出的文艺作品又将这种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新“真趣”传播到晚明社会包括家具审美和设计制作的各个行业领域,对儒家传统的“温柔敦厚”趣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五、晚明士民家具审美的浪漫“真趣”
在晚明浪漫美学思潮的影响下,主体的情感之“真”、个性之“真”,甚至欲望之“真”逐渐成为“真趣”的核心内容。这种对前人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的古典美学“真趣”的拓展,其实质是传统文人的精英趣味与新兴市民阶层趣味的互渗和融合,正如罗筠筠先生所说:“原来彼此毫无共同之处并且相互排斥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向着各自的对立方面的杰出之处重新选择、过渡。”这种拓展了、丰富了的新“真趣”对当时的家具审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表现出许多与众不同的特征。
晚明浪漫美学的新“真趣”首先表现在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对情感之“真”的重视上。如袁宏道称:“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汤显祖则批评在创作中缺乏真情实感、一昧模拟古人的李梦阳等辈只是无缘“真趣”的“三馆画手”“一堂木偶”。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晚明士民的家具审美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情感体验,家具成为人们陶冶性情、寄托情思的重要手段。沈春泽在《长物志》的序文中称:“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明末清初的李渔在家具和室内陈设的设计上更是主张:“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在李渔看来,家具的欣赏和创造与主体的情感体验、情感表达密不可分,是值得付出深深情思的审美对象。清代张廷济的藏品中有晚明书画家周天球的一把紫檀椅子,其上刻有苏轼之诗:“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这种在自己喜爱的家具上刻字的做法在晚明很流行,也是晚明士民在家具上寄托情思的一种表现。
其次,晚明浪漫美学的新“真趣”还体现在对主体个性之“真”的推重上。袁宏道称赞其弟中道的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在袁中郎看来,创作主体独一无二的个性和创造力才是文艺作品的核心要素,即使文章有瑕疵之处,但只要是主体的“本色”流露,便也是美的。晚明士民对个性之“真”的推崇是王艮、李贽等人高扬主体性所启蒙的个性解放思潮的结果,其在现象层面的突出表现是人们对“新”与“奇”的极力追捧。如袁中道评价周伯孔的诗文:“抒自性灵,清新有致。……多出新意,不同世匠。”在他看来,创作主体的性情各有不同,顺应主体个性之“真”的文艺创作就自然能“新”、能“奇”,即所谓:“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张大复也称:“木之有瘿,石之有鸲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也就是说,正是个性之“真”、之“病”、之“奇”才赋予了主体和艺术作品独特的价值。
高濂曾提到当时的一种新式折叠家具:“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这种“叠桌”结构巧妙,是很实用的创新之作。屠隆记载过一种时之所尚的琴台:“用紫檀为边,以锡为池,于台中置水蓄鱼,上以水晶板为面,鱼戏水藻,俨若出听,为世所稀。”这种琴台可以在水晶台面下蓄水养鱼,给人以色彩斑斓、光怪陆离之感,可谓极尽奇巧,与古人所用琴台肃穆、清雅的风格迥异其趣,足见晚明士民对新奇家具的喜爱。文震亨性情简淡好静,品评器物唯尚古雅,因此他将屠隆所言琴台斥为“俗制”。然而,即使像文氏这样标榜“古雅”的文人也难掩自己对一些新奇家具的喜爱,如他每次提及来自日本的倭漆器都大加赞赏,称“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价俱甚贵”的倭台几“俱极古雅精丽”,又说“黑漆嵌金银片”的倭箱“奇巧绝伦”。事实上,常用金银片装饰,喜用描金、剔红等工艺的倭漆器视觉效果富贵华丽,与传统文人的古典雅趣其实并不相符。文震亨身上的这种矛盾之处,一方面或如英国学者柯律格所言是文氏对文士阶层高雅品味的刻意标榜,是一种对新富裕起来的、正日益对文士阶层地位造成威胁的工商阶层所设置的文化壁垒;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晚明家具审美“崇新尚奇”的风潮影响下,倭漆器等新奇的异域之物使文震亨等趣味偏于古典、保守的文人也迷恋其中。高濂、李渔等来自市民阶层的文人对待新奇家具的态度与文震亨相比则开放、圆融许多。高濂在谈到“竹榻”时说:“或以花梨、花楠、柏木、大理石镶,种种俱雅,在主人所好用之。”在高濂看来,家具设计并无一定之规,完全可以根据主人的喜好来选择材料和工艺。高濂的宽容态度实质上是对新兴市民趣味的接纳和认可。
晚明士民还将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投入到了新奇家具的设计上。万历时人戈汕设计出了以13只斜形桌面为基本单元,可自由搭配成130多种形式的新式组合家具。高濂设计了冬暖夏凉的“二宜床”和“式如小厨”可携之山游的“提盒”等家具。“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的李渔设计了夏天在座面下放置冷水给人降温的“凉杌”和冬天在座位下放置炭火来暖身的“暖椅”等极有新意的家具。总而言之,“崇新尚奇”的家具审美观在晚明已成为一种极具普遍性的审美文化现象。但这种追新逐异的风气也使部分家具的设计走上刻意求新、穷工极巧的歧途,李渔曾谈及他在东粤所见:“市廛所列之器,半属花梨、紫檀,制法之佳,可谓穷工极巧;止怪其镶铜裹锡,清浊不伦。”王世襄先生所言明式家具“八病”中的“悖谬”“失位”等几品或也因这一风气所致。
此外,晚明浪漫美学的新“真趣”还有一个充满争议的维度,即士民对欲望之“真”的肯定和追逐。万历中期以后,一种纵情任性、带有浓厚物欲色彩的审美观和人生观在民间蔓延,张瀚对此曾批评道:“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这种特殊的审美文化现象与李贽等人带有自然人性论色彩的思想的风行和市民趣味的流行都有一定关系,部分文人的相与鼓倡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袁宏道在给龚惟长的信中称:“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张岱曾宣称自己:“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袁中郎和张岱的说法充满欲望和享乐色彩,与儒家传统“修齐治平”之道德实践的人生理想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但这种肯定欲望,放任、肆意的人生态度在当时确是许多人的心中所向。这种审美风尚对晚明士民的家具审美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其呈现出一种物欲化的倾向。
张岱曾提到其叔父张联芳在万历三十一年购买一张铁梨木天然几的经历:“有铁犁木天然几,长丈六,阔三尺,滑泽坚润,非常理。淮抚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维遽去。淮抚大恚怒,差兵蹑之,不及而返。”为争夺一张天然几,巡抚竟动用官兵追赶,这一事例折射出晚明文士群体的强烈物欲。晚明宦官群体也对精美的家具趋之若鹜,据太监刘若愚记载:“大抵天启年间,内臣更奢侈争胜。凡生前之桌、椅、床、柜、轿乘、马鞍……皆不惮工费,务求美丽。”晚明世情小说《金瓶梅》的人物、故事虽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因其成书于嘉靖至万历年间,学界普遍认为书中情境与晚明士民的日常生活较为贴合。该书第二十九回提到,潘金莲因妒忌李瓶儿的“螺钿敞厅床”而要求西门庆花六十两银子为其买了一张“有栏杆”、“两边槅扇都是螺钿攒造”,装饰有“楼台殿阁”和“花草翎毛”的螺钿床。潘氏对精美家具的渴望和攀比心理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市民阶层物欲化的家具审美风尚。
六、结语
心学泰州学派所带来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个性解放思潮使晚明士民突破了宋明理学的禁锢,发展出一种意涵丰富的尚“真”趣味。这种尚“真”趣味既有承自传统,以“平淡自然”范式为主的古典美学“真趣”,又有富于时代气息、以追求情性自然之“真”为主的浪漫美学新“真趣”。晚明士民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两种“真趣”的杂糅、冲突甚至撕裂,而就万历以后的普遍风气而论,追求情感之“真”、个性之“真”,甚至欲望之“真”,带有鲜明的市民阶层趣味的浪漫美学“真趣”观似乎更占上风。这一风尚使晚明士民的家具审美在崇尚自然天成、平淡素朴的古典雅趣之外,开始愈发重视家具审美中的情感体验,追求家具审美和设计的个性化与新奇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物欲化。这种融摄古典与浪漫的家具审美“真趣”,是晚明家具的一大文化特征,也是“雅俗互融”的时代风尚在家具审美领域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