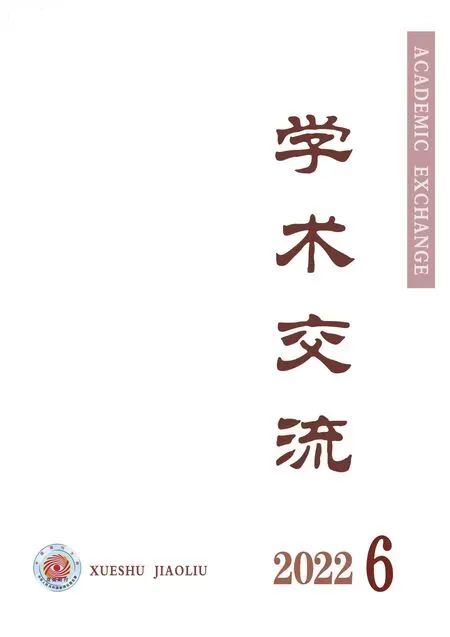“我思故我在”三段论解释的可能性
2022-11-08叶斌
叶 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肥 230026)
引言
“我思故我在”作为笛卡尔哲学的核心论证之一,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长期以来,对于这个论证不是“什么”,似乎已经没有争议。对此普遍的共识是,它肯定不可能是三段论,尽管也有一些解读在不同程度上认为其作为三段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就普遍的观点而言,三段论解释的可信度依然是不高的,因为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答辩中,似乎已经明确地把这个可能性给排除了。
而对于这个论证是“什么”,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比如说在国际研究领域,欣提卡(Jaakko Hintikka)认为这个论证是个践言论证;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则认为应该通过“我存在”这个命题角度来重新理解我思论证;马基(Peter Markie)则试图通过一种改进的直观论证来解释我思论证。而在国内研究领域中,贾克防则认为,以往的研究忽视了笛卡尔的分析方法,而通过这一方法能够使我们重新正确认知我思论证;陈勇则认为,“我思论证”应该从“我存在”和“我思”两个角度去思考,笛卡尔事实上先证明了“我存在”,而后证明了“我思”,由此“我存在”和“我思”构成了第一原理。
由此可见,在我思论证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鉴于此,本文将建议回到我思论证不是“什么”这个共识上来,并且将三段论作为辩护对象。尽管三段论解释将直接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与笛卡尔一些似乎明确拒绝三段论的论述相左;二是在表面上也与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原理形成了矛盾。但是本文将通过系统性的文本分析,揭示出三段论解释的可能性,同时不仅将对这两个难题进行回答,也会处理其他相关理论上的困难之处。
为此,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分析一些既有的非三段论解释,指出其内在的问题,另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能完整展示作为第一原理的我思与《沉思集》中其他论证的关系。第二部分将展开对三段论解释可能性的论证,尽管笛卡尔在《沉思集》的答辩中,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三段论的可能性,但是对其更多相关性的文本进行分析将会发现,三段论是一个极富可能性的、可替代上述非三段论解释的选项。第三部分将回答一些可能的反驳,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三段论解释的可靠性及说服力。最后,在上述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可能的基于三段论的对我思论证的解释,也即将我思纳入观念论框架下,由此揭示隐藏在《沉思集》中的一个论证框架——以观念出发,推论观念所表象的对象的实际存在。
一、诸种非三段论“我思”解释的内在困境
1.欣提卡的践言论证(Performance Argument)
欣提卡引入了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也就是“存在性的矛盾”(existential inconsistency),来解释我思论证。这个存在性的矛盾是由如下进行定义的:p是一个命题,a是一个单项(一个名字,代词或者一个特定的描述);当通过a指涉的这个人说p,p对于这个人是存在性的矛盾的(existential inconsistent),当且仅当“p且a存在”是矛盾的。可以举个例子将这个定义清晰化。有一个句子p(特朗普不存在)和a(特朗普)。当特朗普说,特朗普不存在,就出现了对于特朗普而言的存在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具有一种践言的特征,也就是说,它是基于一个动作或者执行(performance),具体说来就是基于一个命题的表达动作。而当这些存在性的矛盾命题被说出,或者被思考的时候,它们就否定了自身。于是这些矛盾命题的否定命题就得到了自证,并且可以被认为是存在的自证(existentially self-verifying)。举个例子,当特朗普说,特朗普不存在,那么这个命题“特朗普不存在”就否定了自己,而它的否定命题“特朗普存在”就是存在的自证的。
依照欣提卡的观点,在我思论证中也存在着一个存在性的矛盾。据此可以将此论证重新进行如下演绎:
i.我在思考我不存在。这之中存在着对于“我”而言的存在性的矛盾。
ii.因为当这个命题“我不存在”被思考之时,它是存在性的矛盾的,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否定命题“我存在”理解为存在性的自证的。
iii.所以我存在。
因为这个存在性的自证命题“我存在”是通过一个思维动作(执行)表明的,所以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前提与结论的关系,而应当被理解为过程与结果的关系。
尽管这个解释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在其中却依然包含着一个致命的困难。这个困难存在于我思的内容。按照欣提卡的观点,在践言论证中的我思应该被理解为“我在思考我不存在”。这个“我不存在”构成了我思的特殊内容,并且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基于“我不存在”的否定命题,欣提卡才能说“我存在”是自证的。但是在第五答辩中,笛卡尔也写道:
当您认为,我本来可以通过我的其他行为得到同样的推论,您错了。因为我并不能完全确定我任一行为的确定性,除了思考以外。比如说,人们不能推论说:我走路,所以我存在,除非当“我走路”被视作一个思维内容时。
这里笛卡尔认为,从思考“我走路”依然能够推出我存在。这个思维的内容并没有在确定我存在的真理上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就是,任一的思维内容都能推论出我存在。但是欣提卡似乎认为,只有当我思考我不存在时,我存在才为真。他的观点基于一个特定的思维内容,而这与笛卡尔的观点相反。
2.法兰克福的“我存在”论证(Sum Argument)
法兰克福引入了一个概念——逻辑必然的真理(logically necessary truth)来展开他的论证。一个命题是逻辑必然为真的,当它的否定命题是自相矛盾时。但是“我存在”(sum)并不是这样的真理,因为“我存在”的否定命题并不是自相矛盾的。而这个命题,即“我存在,当它被说出(utter)或者被理解(conceive)时”,它是逻辑必然为真的,因为它的否定命题,即“我不存在,当我思考,我存在时”或者“我被欺骗去思考我存在”,包含着一个矛盾。因而笛卡尔在段落(d)中说,“我存在”是必然为真的,当它被说出或者被理解时。
尽管这个解释比较符合第二沉思对“我思”论证的描述,但在其内部还是有一个和欣提卡的解释一样的困境。法兰克福的论证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思维内容,即“我存在”。只有当“我存在”处在上述那个逻辑必然为真的命题中时,才能推出“我存在”为真。在欣提卡的践言论证中也存在一样的问题。践言论证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我在思考我不存在。而法兰克福的论证则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我存在,当我思考我存在时。这两个论证的相同点是,它们都基于一个特定的思维内容,但是正如在反驳欣提卡的论证时所提到的,笛卡尔的论证并不是受限于某个特定的思维内容的,相反,任一的思维内容都可以被用来证明我存在。
3.马基的直观论证(Intuition Argument)
在第二反驳中,笛卡尔写到,我思故我在是通过心灵的一个简单的直观而成真。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直观这个概念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我思论证是直观为真的。然而笛卡尔在《沉思集》中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直观的明确的定义,因而必须在他处寻找解答。在《指导心灵的原则》中,笛卡尔将直观与演绎定义为了两种心灵用以获得知识的能力:通过直观我们可以获得那些不可被怀疑的单项。这个单项具有明见性和确定性。而演绎则通过连续并且不中断的运动将这些单项联结起来,最终推出结论,它不具有明见性。紧接着上述引文,笛卡尔又认为,那些直接从被直观到的单项中推论出来的命题,既可以被认为是通过直观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演绎获得的。
据此可以认为,当我们直接从被直观到的前提中推出结论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种思维的运动,因而也可以将这个结论理解为直观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从前提中推出了结论,因而也可以将这个结论视为是演绎的。在我思论证中,笛卡尔将我思这个前提通过直观进行认知,然后直接将我存在这个结论推论了出来。因而我们也可以将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直观的。
基于此,马基提出了在笛卡尔哲学中存在的两种确定性:第一种是非常合理的(very reasonable),还有一种是确定的(certain)。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前者我们总是还有理由去怀疑,而对于后者则不存在这些怀疑的理由。
马基认为,我思是通过直观而变得非常合理的,而其结论我存在亦是非常合理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两者的确定性由“非常合理的”变为“确定的”。他引用了第二沉思中的一段话来完成这一转变:“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他总是用尽一切伎俩来骗我。因此,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因为此处我思故我在能够躲过这个异常强大的骗子的欺骗,所以可以将我思故我在理解为“确定的”。
尽管这个解释很大程度上与笛卡尔的文本非常契合,但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困难。马基认为通过直观得来的我思是非常合理的,而通过直接演绎而来的结论我存在同样也是非常合理的。另外,他通过对第二沉思的那个段落进行的分析,赋予了我思与我存在更高的确定性。但问题是,为什么我思故我在能够躲过那个骗人的恶魔的欺骗。既然我思与我存在都只是非常合理的,因而按照马基给出的关于非常合理的定义,那么它们依然能够被怀疑。因而它们自身是无法克服骗人的上帝的。
马基给出的答案是:1. 在骗人的上帝的假设中包含了我思故我在;2. 有一条原理,即没有假设能够怀疑包含在它自身之中的东西;3. 因而按照这个原理那么上述的假设并不能证明我思故我在为假。但这样会导致之前他提出的那个区分,即非常合理的与确定的之间的区分,出现如下问题:因为非常合理的意味着,某事物依然能够被怀疑,但是据上述原理,这个非常合理的事物,实际上,是确定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区分上的困难进一步解释:
i. 某个非常合理之物通过某个假设而被怀疑。
ii. 没有假设能够怀疑包含在其自身之中之物。
iii. 因而这个非常合理之物(very reasonable)是确定的(certain)。
那么,如果这个反驳成立,会使得非常合理的与确定的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或许马基会认为,这个原理只适用于确认我思的确定性,并不适用于其他直观。但是这样一来也存在问题。因为他将直观与清楚分明的认识等同起来了,当通过直观得来之物只是非常合理之时,那么其他的清楚分明的认识也只能是非常合理的。这样一来,在第三沉思中关于上帝的那个清楚分明的认识,也只是非常合理的,而非确定的,因而仍然是被怀疑的。那么基于这个认识的上帝存在证明如何具有其可靠性,就出现了问题。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注重如何为我思论证进行辩护,也即如何使其避免一些理论上的困难,但是尽管他们提供了诸多辩护方案,其内部的论证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难处,因而导致其在为我思论证辩护的说服力,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另外,这些辩护很大程度上没完全澄清如何由“我思”论证过渡到上帝存在论证,即第一原理究竟在何意义上成为第一原理。以下我们将对三段论解释进行辩护,在证明其可能性之后,我们也将揭示《沉思集》的一个隐含的论证结构,而正是通过这个结构,笛卡尔实现了从我思论证到上帝存在证明的过渡。
二、为何三段论解释是可能的?
通过对上述我思故我在一些解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困难。但这些解释也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即通过引入一个外部理论,来解释我思论证,也正是由于外部理论的介入,最终导致了它们在解释上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些解决方案也带来一种启示,即我们能否通过回到笛卡尔的文本本身,来找寻一种对我思论证相对可靠的解释。以下我们将着手对笛卡尔相关文本的分析,试图找到本文所主张的三段论解释的可能性。
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写道:
当我说,对于所有按部就班进行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个命题“我思故我在”是第一位的并且是所有一切中最确定的时候,我并没有否认人们必须事先知道“什么是思考,存在和确定性”,还有“思考者是不可能不存在的”(it is impossible that which thinks should not exist),还有其他。但是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概念,或者是一些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提供关于存在之物的知识,我不认为它们需要被列出来。
这里笛卡尔认为要确定“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必须要知道“思考者是不可能不存在的”。尽管这里他没有明确说明我思论证是由三段论进行展开的,但是他也至少给出了一个让我们去认为“我思”论证是一个三段论的契机,据此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展开:“因为思考者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我在思考;所以我在。”或许会有人反驳说,只要笛卡尔没有明确给出三段论的论证,那么这种解释的可能性空间依然是狭窄的。对此我们可以再考察一段文献。
在《与布尔曼的谈话》中,布尔曼又提到了这个三段论的问题,此时笛卡尔给出了一个较为肯定与明确的回答,并对上述引文又进行了一次澄清:
在这个推论“我思故我在”之前,人们要知道这个大前提“任何思考之物都存在”(whatever thinks exists);因为事实上它是先于我的推论的,并且我的推论是依据于它的。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哲学原理》中说这个大前提必须事先要给出的,也就是因为它总是模糊地(implicitly)被预设了,并且是先于那个推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总是清楚地和明确地意识到了它的优先性,或者我知道它是先于我的推论的。这是因为我只注意到在我之内经验到的东西——比如说“我思故我在”。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注意到那个一般的概念“任何思考之物都存在”。正如我之前所解释过的,我们不能将这些一般的命题从个别的例子中区分出来;我们是在个别的例子中来思考他们。
这里笛卡尔明确提到,要推出我思故我在,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大前提(任何思考之物都存在),并且他强调了,我思论证是依据于这个大前提的。换而言之,在这里笛卡尔承认了我思论证确实是一个三段论:因为任何思考之物都存在;我在思考;所以我存在。而他之所以未能在第二沉思中将这个观点明确表达出来,只是因为它是模糊地包含在“我思故我在”之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思论证是不依据于它的。
由上述笛卡尔的两个引文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对“我思故我在”作为一个三段论式的论证进行了肯定。如果我们要反对三段论,就必须对上述两个引文进行反驳或者重新理解,但这样的反驳与理解的空间,通过我们对上述引文的分析,是极为狭小的,或者可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
事实上,除了上述两处,在笛卡尔的重要文本中几乎到处存在着对三段论解释的支持,比如说在《哲学原理》中,他说,“因为这是矛盾的,如果人们认为思考之物不存在,每次当它思考时。因而这项知识——我思故我在——对于所有按部就班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来说,是所有知识中第一位的并且是最确定的”。在《沉思集》中存在好几处对这个解释的支持性文本,比如说,在第三沉思中,他写到,“尽管来骗我,只要他愿意,他愿意骗多少就骗多少,但是他绝不能使我变成无,只要我思考我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在第三答辩中,“这是完全确定的,即思考必须要有思考者,正如任何属性都要有其所附着的实体”;在第七答辩中,笛卡尔说,“在一开始,当我假设我还没有足够地认知心灵的本质时,我将它列入了可怀疑的事物之中;但是之后,当我意识到一个思考之物不能不存在,我就用心灵这个词来指这个思考之物,并且说,心灵存在”。在《谈谈方法》中,他也写到,“我发现,‘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之所以使我确信自己说的是真理,无非是由于我十分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考(in order to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exist)”。
如果对这些相关文本进行一个逻辑性的重构,我们可以发现,笛卡尔认为“思考者不存在”是矛盾的,而基于这个矛盾,我们可以从我思推论出我存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根据笛卡尔,这个矛盾命题导致了“思考者必须存在”这一原理的有效,也正是因为思考者必须存在,他才能从我思推论出我存在。
所有这些文本中,或明确或者暗含地指向了将我思论证作为三段论理解的可能性,尽管它们是分散在笛卡尔论述中的,但是当它们能够被集中起来讨论时,这种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反驳,也就是在第二答辩中,笛卡尔明确表达了,我思论证不是一个三段论,而这个引文也是诸多解读反对三段论解释的重要依据。因而如果要使三段论解释得以可能,那么我们必须对这段引文进行重新理解,或者至少能够得到一种解释,而它能够使得笛卡尔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一致起来。下面,我们将着重考察这段引文: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思考之物,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而不是通过任何三段论的手段推导出来的。当人说“我思故我在”,他并没有通过任何三段论的手段从思考推出存在,但是他通过心灵的一个简单直观将它理解为自明的东西。这一点可以通过这得到阐明,即如果他要通过三段论将它推论出来,他就需要事先知道这个大前提“任何思考之物都存在”;但是事实上他是通过他自己的例子才学到“这是不可能的,即他思考但他不存在”。在心灵的本质中,我们总是通过对个别命题的知识来建立一般的命题。
这里笛卡尔反对三段论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一般性的命题总是通过对具体例子的分析中得到;第二,他认为“我思故我在”是由直观得到的。
对于第一个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对笛卡尔一些文本的分析看到,存在一些文本上的不一致之处。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写道:
但是当我们承认,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既不能将这个命题“无中不能生有”当作以某种方式存在的东西,也不能当作某种东西的属性。它应该被当作一种永恒真理,它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当中,并且以一般的基本概念或者定理存在。属于此类的有:“同一物存在的同时又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 “发生了的事情不可能不发生”; “思考的物,只要它思考,不能不存在”。
这里笛卡尔将之前提到的大前提(任何思考之物都存在)视为一种永恒真理,而对于他而言所有的永恒真理都是先天的(a priori),也就是说,这些真理都不是通过对具体的事例分析得来的。那么这个大前提也不是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得来的。这样一来,在这个大前提与笛卡尔反驳三段论的原因中形成了一种矛盾,即一般命题是由分析具体事例得来的,还是它是先天的,而非从具体事例中得来的。要消除这个矛盾有一个途径:我们可以借用笛卡尔在与布尔曼对话时的解释,即他不是随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大前提的,因而他或许在第二反驳中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大前提,于是就采取了反对三段论的态度,在之后的写作中,他重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后进行了解释,也就是三段论解释。这样一来,这种文本上的不一致就可以被消除,而三段论解释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另外,还有一种途径是,笛卡尔反对的是由具体事例得来的原理进行三段论推论,而不是由普遍真理进行的三段论推论。
第二反驳中还存在的一个原因是,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是由直观(intuition)得来。按照上文中给出的关于直观的概念,我们可以对“我思故我在”进行分析。第一种,“我思故我在”是通过直观得到的简单清楚的概念。这里存在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既然直观具有如此的确定性,也就是说,由它得出的第一确定性能够避免恶魔的欺骗,那么笛卡尔为什么不在上帝存在证明中直接使用直观,而要冒着循环论证的风险采用其他方法。第二,在《指导心灵的原则》中,笛卡尔也提到,他可以直观到他在思考,他在存在。那么为什么他不在《沉思集》中也直接采用这种说法,即我直观到我存在,而要采用我思故我在这个极具风险与争议的说法。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直观理解为一种直接从第一原理中推论出结论时,正如上文所展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思故我在”是一种三段论。因为如果人们能够迅速地从大前提与小前提中推论出“我在”,或者“我思故我在”,那么这种三段论式的推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直观。因而这也并不与笛卡尔的原意相悖。
总体而言,通过对笛卡尔文本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找到一条不同于之前一些解释的道路,即三段论解释。他文本的多处也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对这个解释的支持,尽管存在一些文本上的矛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将这个矛盾消除。因而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思故我在作为一种三段论是可能的,并且是可辩护的。
三、回应一些反对三段论的观点
在给出一种基于三段论的论证框架解释之前,还需要对一些常见的反对三段论解释的观点进行澄清和解答,这不仅将有益于辩护本文的观点,也有利于这种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广泛地接受。
第一,如果在第一确定性“我思故我在”之前,我们必须要确定大前提“所有思考之物”的确定性,那么会否导致这个大前提才是第一确定性。在上文的一段引文中笛卡尔提到,“任何思考之物存在”就其自身而言并没有提供关于存在之物的知识,而第一确定性“我思故我在”则涉及了我的存在。由此可以推断说,对于笛卡尔而言,第一确定性应该具有关于某物的存在的知识。而我们在上帝存在以及一般外物的存在证明中也可以看到,其确定性都指的是它们自身的存在。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大前提是确定的,但是由于它不具有关于某物的存在的知识,也就不能被认为是第一确定性。
第二,关于大前提如何避免恶魔的欺骗。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提到,由自然之光带来的东西我们是无法质疑的,其中包含了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因果律以及“无中不能生有”。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所有思考之物都存在”与“无中不能生有”都同属于永恒真理。既然在第三沉思中“无中不能生有”不能被质疑,那么同理可得“所有思考之物都存在”也不能被质疑。
第三,关于我思的确定性。对此,在第五反驳中,笛卡尔写道:“当您认为,我本来可以通过我的其他行为得到同样的推论,您错了。因为我并不能完全确定我任一行为的确定性,除了思考以外。”这里笛卡尔明确表明了对我思确定性的确信。
第四,我思与我在的问题。欣提卡认为如果要确定我思的确定性,那么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存在性的前提,即我存在,也就是说在证明我存在之前,在其前提中已经包含了我存在,这样会导致一个论证循环。这个困难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回避。对于笛卡尔而言,本质与存在总是要区分对待的,只有当实体的本质或者属性被确认时,我们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即这个实体是否存在:“按照真正逻辑的规则,当我们事先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在关于某个事物时问,它是否存在。”对于笛卡尔而言,是否在我思中隐含了我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是他所关心的,因为按照他的逻辑,我们总是应该确认我这个实体的本质,然后再去追问我是否存在。
第五, 三段论解释还有一个困难在于,它似乎是违背了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所提出的“普遍怀疑”原则的。而一旦那个大前提“所有思考者存在”能够被使用,那么就意味着一般理解意义上的笛卡尔的普遍怀疑面临破产的威胁。因而如果要使得三段论解释能够成立,必须对普遍怀疑进行重新理解,或者说如何正确理解笛卡尔的普遍怀疑。
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提到心灵的两种能力:一种是知性,另一种是意志。通过知性我们可以获得观念,通过意志我们可以将观念与外物联结起来,而由知性与意志的协作我们可以得到真理或者错误。现在就这两种基本能力而言,如果怀疑能够加诸它们身上,那么便意味着真理的不可能性。事实上,笛卡尔在第三沉思中强调了知性能力的不可怀疑性,例如,他说,当观念不被指涉到外部事物时是不可能出错的。错误发生在判断之中,在于人们通过意志的判断作用,将观念指涉到外物时,也就是说,笛卡尔的真理或者错误存在于观念与外部事物的关系之中。除此之外,在第四沉思中,笛卡尔也表明了,意志本身不会出错。那么错误的根源,或者说真理与错误的根源,是存在于观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这样一来,既然知性与意志本身不能被怀疑,那么怀疑的对象只能是观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第七反驳中,笛卡尔证实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他至始至终不将怀疑与确定性理解为我们的思想与对象的关系,相反一直只是将它们理解为在对象中包含的属性。”这段话表明,笛卡尔的怀疑所涉及的对象是观念与外部事物的关系,而非一般理解的普遍怀疑。
在厘清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这个概念之后,作为先天观念的那个大前提“所有思考者存在”,在被理解为知性的属性的意义上,它也是不能被怀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违背了笛卡尔的怀疑原则。
四、观念论框架下的我思论证
以上我们已经证明了我思论证的三段论解释的可能性,并且对一些可能的反驳作出了回应,现在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由三段论展现出来的第一原理如何与上帝存在证明,乃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证明关联起来。为此,我们需要观察这两个证明。
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借助了因果律来证明上帝存在,该论证可如下进行简明的展示:
因为,一个东西里的全部实在性或完满性是形式地或者卓越地存在于它的第一的或总的原因里。
又因为,上帝的观念中包含了我所不具有的完满性。
所以,必然存在一个上帝,是他将他的观念放在我心中的,即上帝存在。
这里的论证包含着一个三段论结构,即我们应该从上帝的观念入手,借助因果律来证明其存在。而在《沉思集》的答辩中,笛卡尔强调了这个第三沉思中上帝存在论证是他最为用心所作。
在第六沉思中,笛卡尔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该论证可如下进行简明的展示:
因为,一个东西里的全部实在性或完满性是形式地或者卓越地存在于它的第一的或总的原因里。
又因为,关于外部事物的观念包含有一定的客观完满性;同时,上帝不可能是个骗子。
所以,外部事物存在。
在这个外部世界存在证明中,笛卡尔依然是借着作为普遍真理的因果律,以及对相关观念的观察,来得出它们的实际存在。从这两个论证的结构来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即证明的基本框架都是从观念出发,借助普遍真理(因果律),来推出观念所表象之物的实际存在。因而,如果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似乎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我思论证是否也采用了这样一个论证模式。
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对“我”这个观念展开了如下论述,即我是一个思考之物(a thinking thing)。而借助于普遍原理“所有思考之物皆存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论证:
因为,所有思考之物皆存在。
又因为,我有一个关于“我”的观念,即我是一个思考之物。
所以,我存在。
这个论证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发现一个隐藏在《沉思集》中的架构,即观念论框架。但问题在于,这里的“我是一个思考之物”和我思论证中的“我在思考”,究竟是否存在不同之处,还是说它们其实指的是一个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借助笛卡尔对区分的定义进行澄清,在《哲学原理》中,笛卡尔提出了三种区分:实质的区分(real distinction),模态的区分(modal distinction),以及概念的区分(conceptual distinction)。第一种指的是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区分;第二种指的是实体的模态与实体,或者实体的模态与模态之间的区分;第三种指的是实体与它的一些属性之间的区分,而缺了这些属性,实体将无法被理解。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我在思考”和“我是一个思考之物”之间的区分属于第二种,即模态和实体之间的区别,而不是一种实质的区分,因为思考是属于思考之物的,并且是它的模态。因而不论我们谈论的是“我在思考”还是“我是一个思考之物”,它们都指向这个“思维之物”,而不是不同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我思考”与“我是一个思考之物”指的是一个东西,因而可以将上述论证中的关于“我的观念”替换为“我在思考”,因而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在其他论证中存在的观念论框架也适用于我思论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我思论证”纳入到观念论框架中来重新理解它。
这样一来,借由我思论证的三段论解释,我们可以将观念论框架视作一个贯穿了《沉思集》始终的隐含结构:笛卡尔借助于他的观念以及永恒真理,论证了观念所表象对象的存在。而我思论证作为第一原理,它的意义在于表明这个框架的有效性,即之后的论证都可以依此模式进行展开并获得其有效性。换句话说,它证明了“从观念出发,我们可以证明观念所表象之物的存在”这种论证方式的有效性。
结语
总体而言,通过对笛卡尔的一些文本的分析,对其中的冲突的解读,以及对一些反驳的回答,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个视角来重新理解我思论证是可能的。
除此之外,尽管我思论证长久以来被视作笛卡尔哲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由此而被忽视的是这个观念论框架结构,而近来的研究却表明,观念论才是笛卡尔哲学的真正核心。长久以来关于我思论证的争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争议,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对观念论的忽视造成的。而将我思论证纳入这个框架下,在诸多层面上能够将笛卡尔《沉思集》的隐含论证逻辑揭示出来,从而增强其整体可理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