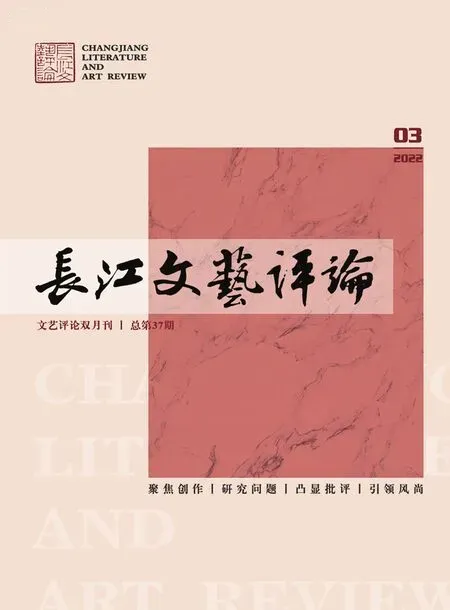《崇山之阳》:地方志乡土散文的艺术探索
2022-11-07陈国和
◆陈国和
李专是一位以乡土散文著称的作家,早年的散文主要以鲜明的鄂南特色为学界关注,如散文集《岁月的痕》。后来,《风雅二十四节气》散文集则逐渐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点。求新求变一直是文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这也表明李专是一位有着远大艺术目标的作家。近年来,李专查阅大量鄂南地方县志、搜寻地方文化典籍、积极创新地方志散文形式,书写咸宁各县市的历史变迁和精神面貌。《崇山之阳》就是经过大量田野调查后进行构思,构建地方知识性的艺术成果。
一、地方志的散文笔法
地方志既不属于纯粹的地理著作,也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实际上属于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性学科。当然,史的性质更为明显。地方志记载某一地的山川、地理、风土、人物、社会经济等内容。地方志最初叫做地记,由地方性的地理与地方性的人物传记汇合发展而成。李专创作的散文集《崇山之阳》书写崇阳的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以及当下扶贫背景下的山乡巨变。《崇山之阳》共有四辑,分别为《奇峰突起的文明》《历史星空的灿烂》《改天换地的巨变》《从前的关注》,通过崇阳的历史变迁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交织,聚焦幕阜山区的古今之变、城乡融合,从自己的角度写出了中国的故事。
如在《从前的关注》这一辑中,主要记录了1990年代李专对崇阳的个体记忆,作者以简单的乡土想象和多情细腻的笔触书写崇阳的自然神话和乡村世界,如《金沙的风》《万山丛中放飞舟》《沧海两粟》《崇敬崇阳》《美食慰乡愁》等。这一系列散文都是一些零碎、散乱的乡村记忆和历史素描,是非常典型的乡土散文笔调,也未能摆脱浓厚、纤弱的文人气质和个人情绪。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论述:“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着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换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在早期的崇阳书写时,李专的地方记忆是“锁闭”的,内心也只是局限于文人墨客的个人感怀、托物言志的艺术追求层面。或者说这种乡村书写还处于上世纪城乡对立时代符号化的乡村想象阶段。但是,当李专树立“想写一本几十年后还有几个人看的书”的艺术志向、为崇阳树碑立传的时候,崇阳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记忆也必然开始进入他的艺术视野,李专的散文因此纵横捭阖、大开大合,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感。
如《历史星空的灿烂》一辑直接从历代崇阳县志中寻找素材,进行点染和艺术虚构。其中的《崇阳知县》主要书写了张乖崖、欧阳晔、任希夷、陈仲微、陈洪烈、金绵祖、李五惇、曹学诗、金云门和冯台异等十位声名显赫的县令,北宋名人张乖崖等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因为“宋以前,朝廷对咸宁这块地方一直不怎么上心,从北宋开始,才‘经营’此地。‘经营’之举,就是派来了张乖崖之后众多的能官。”《崇阳县志·职官志》中记载“至今崇阳成贤君,必曰张乖崖。”他廉洁吏治,“一钱斩吏”,勤于政务,“水滴石穿”,“抚良祛奸,训民以义,岁劝农耕”。在今天崇阳城西白泉港上,接二连三摆开的官堰、板堰、仙人堰三道堰,其中的官堰就是张乖崖主修的,至今还发挥着水利灌溉的作用。仁宗时期,士大夫们将他与宰相赵普、寇准并列,认为他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三位名臣之一。
人物传记是方志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人物,尤其是其中的“乡村奇人”,自然而然在李专的散文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大市村的大事情》中“90后”女大学生程桔就是新时代的乡村奇人。与一般大学生毕业后向往北上广等大城市不同,程桔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回乡创业,2014年当选为大市村支部书记,成为咸宁市最年轻的村支部书记。三年后,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崇阳县首个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最年轻的人大代表之一。多年来,乡村的无望引发了乡村青年精英的逃离,而青年的逃离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的衰落。大市村正是当年发现商代铜鼓之地。此铜鼓是商朝国君武丁率军南征时的遗存物,后来因为河道变迁而被掩埋土中,最终在崇阳大市村中被发现。如果说商代铜鼓是融进崇阳人血液和灵魂的一件国宝,那么程桔就是将铜鼓融进灵魂的那一个。担任村支书以后,程桔制定了“基础设施—产业—旅游”三步走的整体规划。曾经是重点贫困村的大市村成为全县第一批脱贫村之一。程桔是新时代的乡村青年典型,也将成为崇阳地方志书上的“乡村奇人”。李专在当下中国经验中构建或发明了新的传统,“被发明的传统,既包括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李专通过地方志的笔法赋予当下经验以历史感。
地方志散文是乡土散文的特殊形式,是指乡土散文中借鉴地方志的内容和形式元素的形态。李专的地方志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借鉴了地方志书,从而创新了乡土散文的形态。地方志散文主要以地方性知识作为主要内容。
二、地方性知识的审美追求
地方性知识并不是需要通过和其他知识比较而凸显它的特征和气质,而是它自身就是地方的。地方性知识是吉尔兹在研究人类学时经常出现的一个中心概念:“地方性知识”。“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当然,地方性知识并不是和普世性价值对立。有学者进一步阐释,“所谓的地方知识实际上指的是:在焦虑与紊乱、社会损耗与流动、生态不确定性和宇宙易变性等条件下,以及各种亲属、敌人、精灵和夸克等始终存在的离奇事物之中,如何生产和再生产出地方性”。“地方知识事实上是指生产出可靠的地方主体,同时生产出可靠的地方邻里,以使地方主体在其中被辨认出来和组织起来”。李专的地方志散文逐渐放逐了地方色彩的追求而沉浸于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之中,哪怕由此丧失部分散文的文学性。
一直以来,地方色彩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主要特征。风景、风俗、风情成为地方色彩的三个重要维度。乡土小说、乡土散文自然服膺于这一理论的规训。实际上,这一概念属于现代性话语体系,不仅本身意义含混不清,更主要是这种书写策略自然而然地包含着启蒙的立场,成为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宣传个人理论的一种有效途径。在特殊历史时期,这确实有效地书写了中国现代化艰难探索的经验,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中国本土真实的生存风景和生活形态。
地方色彩是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地方色彩作为从域外引入的概念,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在对其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融入了各自的文学观念、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因而,地方色彩这一概念得到了不同阐释,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强调地方色彩对于乡土文学艺术的重要意义,认为地方性与个性是乡土文学的艺术生命。他还准确地指明所谓地方性也就是“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其他的还有茅盾、苏雪林、鲁迅、周作人、朱湘、徐碧晖、张定璜等人都对这一概念进行过有效的阐释,异域情调、乡土色彩、地方色彩、中国的色彩、中国的土气等作为地方色彩的替代词被不同作家、批评家广泛使用。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在阐释乡土文学史时,也基本上是把地方色彩作为乡土文学的一个审美准则。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审美根性,离开了地方色彩,乡土文学的文学性就丧失了灵性,乡土的面相也就变得暧昧不清了。
李专早期的散文集《岁月的痕》就是这种追求,具有鲜明的鄂东南地域色彩,形象地呈现了鄂南的风景、风俗和风情。李专由此进入我省优秀乡土散文家第一方阵。但是,由于作者立德、立功、立言的创作追求,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地方主体性,更谈不上“地方的”情景和环境。如《美目盼兮》就写出了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时的鄂南乡村的风情;《在家乡的土地上》书写了官桥八组新农村风物印象。然而,“地方色彩”毕竟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新时代的文学景观和创作追求。一个地域的风景、风俗和风情,其实就是不同于其它地域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自然而然会凸显出这个地域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语境和特殊意义。文化人类学和知识社会学知识经过创作者的理性思维过滤,进一步虚构,构建成为地方性知识,从而形成了人们关于乡土文学的审美趣味和知识结构。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一种主体性知识的呈现,是一种内部视点的自我呈现。近年来,随着中国作家本土意识的形成,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激荡,地方色彩逐渐被地方性知识所取代。
《崇山之阳》作为地方志散文,就是李专从早期散文的地方色彩追求转向地方性知识追求的转型之作。“崇阳”作为主体成为作者书写的中心和阐释的对象。因此,古今演变的历史知识、叱咤风云的崇阳儿女、改天换地的乡村青年、呕心沥血的党员干部都因为“阳”而聚焦,这里的“阳”就是崇阳的文化精魂和历史血脉。如果我们以纯粹的乡土散文理论来阐释《崇山之阳》未免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因此遮蔽了探索李专散文的积极意义。
三、在地性的文化自觉
客观说,《崇山之阳》创作转型的过渡性痕迹同样也非常明显,知识性常常冲淡了散文的文学性,部分篇什的流畅性不够,甚至影响了阅读的愉悦感。但是,《崇山之阳》作为地方志散文艺术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索。
地方志散文赓续了新时期寻根文学的传统。《崇山之阳》随处可见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文学因子。如文中多处出现关于崇阳发现国宝“铜鼓”的叙述,这种在不同时代关于同一事件的“重复”叙述应是作者有意为之,而同一叙事的细微差别刚好折射了时代的光影。如《崇敬崇阳》中关于铜鼓的叙述是对中国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的由衷敬意;《大市村的大事情》中对铜鼓的叙述意在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忧心忡忡,为当下乡村出现了像程桔这样的新时代青年形象而感到高兴。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日益加剧,青年精英的逃离、基层政治组织的瘫痪,使乡村逐渐空心化。正是像程桔这样的新时代青年重新担当起了振兴乡村的历史重任。这种地方性知识不仅仅是一种资料性的堆积,而且成为当地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和内容,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它不仅仅具有鲜明的民族习俗特征,同时凝结了民族的过往历史、丰富情感和美好的愿望。因此,《崇山之阳》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特点。
《崇山之阳》不同于鲁迅式乡土写实的批判;也不同于沈从文式乡土写意的浪漫。李专的地方志散文虽有承继,但是更多的是赋予传统题材以新质。这种新质背后凝聚的是记忆、知识与想象的地方意识。李专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诸多优秀作品入选全国各地中小学语文教材。同时,李专也是一名优秀的学者,在社会学和文学理论上用心最专。特别是几年来,他骑行在鄂南乡村大地,调查各类文化古迹、搜集各种民间文化典籍,极大地推动了咸宁文化事业的发展。这部《崇山之阳》以他个人的田野调查、实地勘探、文化整理作为切入点,是一部关于当下中国内地县城(主要是乡村)的专题散文集。
《崇山之阳》是李专从地方色彩向地方性知识追求的转型之作,为地方志散文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并提供了相对成熟的艺术范式。通过对现代化冲击下加速蜕变的鄂南乡村世界的敏锐观察,李专这里书写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也有广大基层农民对脱贫艰苦卓绝的积极探索。同时,李专还深入到乡村生活的肌理深处,既观照当下乡村的日常形态,又追索崇阳的历史沿袭,甚至更进一步深入乡村文化心理的褶皱,通过多层面、多维度精细书写崇山之“阳”。这种书写策略的转变不仅仅需要作者具有过人的艺术敏感度和思想穿透力,更需要作者具有高度的智性思辨力。李专通过田野调查,以当代意识探照深邃的历史,赋予历史以新时代的光芒;在当下生活现场的书写中,李专通过地方性知识,构建生活实践的历史感,赋予当下以历史价值。因此,《崇山之阳》既具有理性的深邃,又具有感性的生活质感,是一部闪耀着理想光芒的、具有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学价值的乡村生活观察笔记,是新时代鄂南乡村的活性生活史料。
注释:
[1]【英】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杰:《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3页。
[3]【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1页。
[4]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