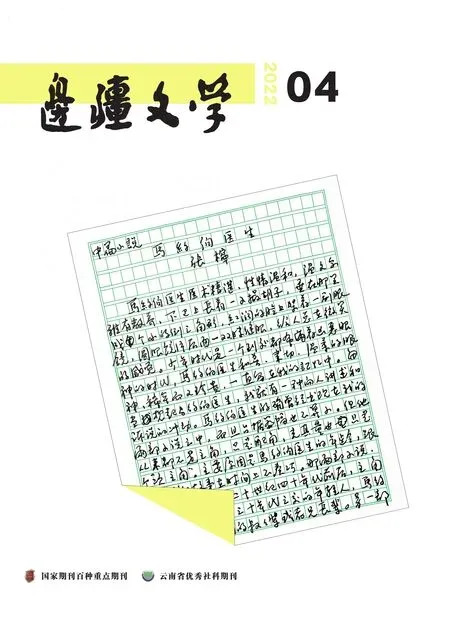青奇叔公
2022-11-05徐春林
徐春林
记得那夜极其寒冷,鸟声刚刚叫出就冻在树杈上,干枯的冬天树杈是挂不住的,咔嚓一声落下来,随即冻在空中,起风的时候,又被大风吹着硬生生地撞在我家对面半山腰上青奇叔公家的矮墙上,撞出了噗噗的声音。
青奇叔公心疼那堵墙,不停地咒骂这该死的天气。仿佛墙上那些坑坑洼洼都是鸟造的孽,都是风设计的阴谋。不过,没几分钟他就消气了。回到屋里,拴上房门。他又担心起树上的鸟来。风太大,鸟窝会不会刮下来。会不会窝里还有小鸟,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想着想着,他又开始叹气了。
外面的风越刮越大,像是要把整个村子翻个底朝天,像是要把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都翻出来。看来鸟也是受害者,只有风才是令人讨厌的。
“哎,真的老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他说的话,只有树上的鸟雀听得见。很多时候,他也就只能和树上的鸟雀说说话。看着鸟雀在树上飞,他倒是挺开心的。
火炉里的火光有些暗了,他拿起铁火钳,想把烧散的柴火堆积到一块。他发现手臂用不上力气。他想再使点劲,可发现火钳根本不听使唤。“真的是老了。”他又说了一遍,不停地用力夹着柴兜朝着中间拖。夜晚越来越冷,他还没有半点睡意。
村子里的老人大多我都见过,也都熟悉,他们都能喊出我的名字。
村子不算小,住着零零星星的几户人家,虽然都隔着山,但大多数都会有往来。青奇叔公家只隔着一条深沟,站在屋门口可以说话,走路大概二十多分钟,算是村子里离我家最近的人家。
在村子里,青奇叔公是我心里最敬重的老人,虽然我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但他却一直留在我的心底。
第一次接触到青奇叔公,大约是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患有扁桃体肺炎,咽喉肿痛,连稀饭都吃不下。村子里的医生只能治感冒病,吃了十来天的药不仅没有消肿,反而越来越厉害,就连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母亲决定带我去一个叫石坳背的地方。说这个地方能治好我的病。母亲开始打算等父亲回来带我去的。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回来,我的病也不见好转。
我得强调的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跟母亲过的。父亲在山外的学校教书,所以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落在她的肩上。
“石坳背”这个地名我算是熟悉的,不止听大人说过。就连小朋友,也常常挂在嘴边。说,谁谁谁又去石坳背了,谁谁谁从石坳背回来了。听到这一去一来的消息,会让孩子们激动一阵子。
去石坳背回来的人,不仅会带回来食物、布匹,还会带回来故事。说是见着了耍猴戏的,还观看了《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电影。猴子我只是在课本中见过,电影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村子里就连电视都没有,谁能够凭空想象出电影来。
大人讲什么,我们都听得好奇。说猴子会钻火球,还会走钢丝。所以,我总想着去石坳背看看,可是一直没有找着机会。石坳背到底是什么地方?其实就是个乡政府的所在地。
那天,天还未亮,母亲就起床准备早饭。天刚刚亮就出发了。
我开始跟母亲走路,走了半天,弯弯曲曲的路盘踞在山间,走了一段还有一段,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陡。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旁的石头上坐了下来。母亲说,才走了五分之一哩。我又站起来,勉强跟着跟母亲走了一小段,就再也走不动了。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母亲又让我歇了一会,再走一段,我就不愿意再走了。石坳背的神奇,此刻变得麻木起来。内心瞬间讨厌起这个地方来。
母亲弓着腰,把我从地上背了起来。我发现,她背着我的时候,比自己一个人走时更快。没一会就爬到了山顶,母亲指着山那边的一个山坳说,你看,那个地方就是石坳背。我远远地看见,那里的房子是白色。房顶是平的,好像还看到有人在上面走动。这是我第一次远望石坳背,第一次看到比村子更新鲜的事物,第一次见着不一样的房子。仿佛我所去的地方是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激动,至今都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是一块固定的画板,清晰地复印着每个高低的角落。
青奇叔公那时大约五十来岁,是乡政府的锅炉工。我和母亲走到乡政府的所在地时,已是下午两点,我趴在母亲的背上睡着了。母亲把我轻轻地放在医院门口的长凳上,但我很快就醒了过来。我听见母亲在和一个男人说话,“你这姑娘,来了这,嫌弃什么麻烦,赶紧把孩子抱到我床上来,别在外面着凉了。”医院就在乡政府的一楼,只有两名医生,门口顶上挂着卫生院的牌子,还没有到上班的时间。
青奇叔公就住在政府的楼梯下,几块砖头上放着一块铺板,这就是他的床。青奇叔公在乡政府做锅炉工少说也有十多年,所以我出生以来一直没有见过他。在迷糊中,我看见一张瘦瘦的脸。“我给你们做饭去。”“不麻烦了,青奇叔,等木牙醒来,带他去店里吃面。”“都几年没见了,还麻烦?我做饭去。”
其实,在这之前,我在村子里没有见过青奇叔公。也不知道,村子里还有这么个人。青奇叔公在乡政府做锅炉工期间,很少回村子去。他干的这个活,一般是走不开的。整个乡政府就他一个锅炉工,就算是放假的时候,乡政府还是有人值班,所以怎么都走不开。
我记得那天中午,青奇叔公是用炒菜的锅煮的饭。我这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煮饭的,饭熟后,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烧巴。不过这样煮熟的饭很好吃。
这大概就是青奇叔公留在我童年里的记忆。在这之后,我记住了他的样子,也记住了这么个人。
后来,我再次见到青奇叔公时,那是我到石坳背读书的时候。我会经常往他那里跑,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我经常会去打开水。他总是笑嘻嘻的,一点都不觉得烦。
他回到村子里的时候,已是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回到村子里好几年,我才知道。他活得悄无声息,像是躲在某个地方。不是有意去找他,很难在某个地方碰上。由于他独立的生活习性,很少有人说起他。我问母亲,青奇叔公活在哪?怎么很少看见。母亲说,他就活在家里,每天都在。“那他依靠什么生活的?”我问。我以为青奇叔公有退休工资,所以长期蜗居在家里,不与村子里的人往来。“他不是不与村里人往来的,在石坳背待了几十年,村子里没有做过人情,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往来。”母亲说。某天母亲指着对面半山腰上说,你看到那个影子没?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老人,弓着腰,背上驮着一捆柴。“他每天都手不停的。”我这才知道青奇叔公干的是“临时”锅炉工,退休后没有工资,就连补贴都没有。本来像他这种帮政府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多少也会有些补贴。退休前乡长找他谈过话,可他说都吃了政府几十年的,不愿意再拿政府的钱了。回到村里,只能依靠自己劳动而生活。
我倒是好奇,青奇叔公是怎么干上锅炉工的?那时乡政府是吃大锅饭的。用锅炉烧火煮饭的,说到底他就是个纯粹烧火的人。饭是在蒸笼里蒸熟的。他只负责烧火,就连柴火也都是乡政府后勤统一购买的。其他的事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他捞不到丁点好处。
我觉得,他真的活得窝囊。在乡政府上班的一点微薄工资,他也基本上自己没有留着。
听母亲说,他不是村里人,是我们徐姓的一户人家带的孩子。我们村子里徐姓的祖先是一户人家,所以延续下来,大家都是当亲戚走动的。青奇叔公来村里的时候念过私塾,后来又去石坳背读了两年。算是村里最早的初中生,当时乡政府进人哪怕是个临时的锅炉工都是要通过考试的。当然,青奇叔公看中的不是这个事业,而是后面附加的条件。意思是干了两年之后,就可以参加事业单位的转正考试。乡政府招聘的一些其他人员,陆续都转了行当。有些直接找上级签字,解决了铁饭碗。青奇叔公没有去找人活动,就连有些政策,他连风都张不到。就这么一拖再拖,拖到后头就变成了纸上谈兵。再后来,他的事就再没有人提起了,上面也取消了这项土政策。青奇叔公没有怨言,他说命中有的自然有,命中无的莫强求。这个事情也就算是告了段落。
刚去石坳背的时候,乡政府的妇联主任找过青奇叔公。有个晚上还特意请他去她家吃饭,说她的外甥女在县城做生意。问他有没有对象?青奇叔公那时才十八岁,村里根本没有合适的姑娘。不,也许在青奇叔公的心里有那么一个,毕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可他还一直没有机会说出来。见着此场景,青奇叔公的心里有些胆怯,想想自己的家庭,村里可都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恐怕是连彩礼钱都付不起。那顿晚饭,他的喉咙里像是掐着鱼刺,怎么也说不上话来。
没几日妇联主任又来找他。说她外甥回女来了,叫她晚上去她家吃饭,顺便见个面,能不能谈成都要看缘分。平日里妇联主任对他格外的照顾,他想不去肯定是不行。黄昏的时候,他看见妇联主任家点着蜡烛,桌子中间还摆着蛋糕,一个穿着牛仔服的女孩坐在左边。妇联主任见青奇叔公来了,高兴地迎了上来,她让青奇叔公坐在女孩的右边。然后一个劲地夸青奇叔公,夸得他满脸红通通的。
那餐饭他的脑子里糊糊的,看不清楚桌子上的菜,筷子在上面划来划去。最后还把自己的筷子和那姑娘的筷子搅在了一起。看到这种情形,妇联主任特别的高兴。说青奇叔公和那姑娘是郎才女貌,天上的一对,地上的一双。说得青奇叔公晕乎乎的。
出门的时候,妇联主任说,你们出去走走吧,年轻人要多接触才好。
外面的月光朦朦胧胧的。这种光亮倒是挺适合谈恋爱的,他和姑娘走了好一段路程。姑娘主动伸手来拉他的手,他感觉就要拉到的时候,把手缩了起来。姑娘说,我妈说过,只要你和我结婚,她就会想法子帮你解决工作问题,以后会把你调到城里去,我是独生女,城里有房。女孩说的这些话他一句都没有听进去,但是“我妈说”这三个字他听得很清楚。“妇联主任是你妈?”“是啊,是我妈。”他这才明白,原来妇联主任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找对象,或者说,她是想为自己谋个未来的女婿。
第二天,妇联主任再找他时,他就没有再见面了。不过,他干活的激情像是高了点儿。他也有意无意地在脑海中盘算着自己未来媳妇的样子。他想得最多的还是简单的生活,理想是找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呢?他还暂时说不上来。
青奇叔公结婚的时候年龄不小了,他错过了最佳的结婚时间。他一个人实在过得憋屈的时候,那就是人们用奇怪的眼神看他时,说他的性格有问题,性别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真有问题,那又会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时候他还能找对象结婚吗?不要说是未婚的大龄女,就连一些年龄小的女人也对他还有兴趣。
可他没有半点想要结婚的想法。有一回,我奶奶去石坳背,回来后她就眼圈红了。那时,我父亲都有了十来岁。可是谁也不会知道,青奇叔公一直暗恋着我奶奶。但是,奶奶早已嫁给了爷爷。而爷爷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名师范毕业生。
情感这东西,绝对是没有答案的。有着特定的因素,不会因为一些事情改变的。青奇叔公后来结了婚,可是婚后没有生育孩子。不知道是女方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那个女人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大约十来年,又改嫁去了别处,改嫁后生了三个孩子。他去看过那几个孩子,但是女人却生活得非常艰难,他又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救济他们。
青奇叔公的主动的确是让人不解。自己本来就是个孤家寡人,留点钱给自己养老有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拿出去做人情呢?何况那个女人和他没有了关系。这只是一些人的看法,也许在他的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甚至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义务。一日夫妻百日恩,他总觉得是自己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那几个孩子倒是嘴甜,见着他就喊干爹。他的心里也是酸溜溜的。想想,自己要是有这么几个孩子该有多好,要真是这样就儿孙满堂了,也不会愧对养育他长大的养父养母。有时候,想着这些事情,他也会黯然泪下。
青奇叔公回到村里的时候,我奶奶已经不在村子里生活,她已经随爷爷去城里陪我叔叔的女儿读书。偶尔回村里,俩人会拉家常,聊一些村子里共同所见的往事,也会聊一些远远近近的生活。比如,如何治疗风湿病,讨论治疗的一些法则。其实,谁都没有学过医,谁都不懂。我奶奶患了几十年的类风湿关节炎,吃遍了全国各地的药。“好在夏老师,要不然你这病……”他下句没说,奶奶也知道他要说什么。“是啊,要不是他我的坟头草都不知道多高了。”然后又举例谁谁谁,患的也这个病,都死了好些年。村子里患这病的人不少,但寿命长的也就是六十来岁。我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算是幸运的了。
奶奶去世很突然,我把她送回村子时,我们全家都已搬迁到了县城。实际上,在此之前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移民到了山外。青奇叔公哪都不愿意去。他说,自己在石坳背待了大半辈子,到了晚年就想留在村子里。说到底,这把岁数的人了,活在哪不是活呢?还是村子里自由。可是,现在村子变成了空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不闷吗?他倒是不在意。我的耳朵聋了,搬到山外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也不想听清楚了。一个人无牵无挂的,活在哪不是活呢!
我奶奶病重的时候,和我们提起过青奇叔公,她说,这老人倔得很,等我不在了,你们要找着空去看看他,他实在是可怜。
奶奶去世时,我们回到村子已是深夜。奶奶还没有入奠,放在里间屋子的床上。在漆黑的夜空中,我老远听见一个老人的哭声,朝着我们这边靠近。我定了定眼一看,是青奇叔公,此刻我感觉他的个头比以前更小了。“中阿走了?”“走了。”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得到的消息,村子里没有了人,奶奶去世的消息还没有散播出去。他跟在后头,喃喃地哭着,一边哭着,一边说着话。他说了些什么,我居然一句都没有听懂。
第三天,我看见他坐在我家老屋的门口。奶奶的棺木停放在堂前的右侧,他的目光注视着奶奶的照片,一刻都没有移开。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让我给青奇叔公,并且送他回家。我把五十块钱放进他的口袋里,他又掏了出来,塞在了我的裤兜里,反复好几回,说他现在还能活得下去,说啥都不愿意收。这大概就是我和青奇叔公的最后一次交往,这之后我没有再和他见面。
青奇叔公去世的时候,依然是夜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听母亲说,青奇叔公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咽喉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中了,像是扁桃体肺炎又复发了,咽喉肿痛,眼泪就滚落了下来。我感觉,像是失去了一位亲人。
听说,他是走后的几天,猎户无意闯进他的屋子,才被发现的。他是怎么走的,谁都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屋子的门是拴着的。他就没打算被人发现,准备就这么长眠下去。可还是有鸟从被风吹破的窗户里飞了进来,在屋子里扑来扑去。他就像是睡着了一样,面部表情镇定且安详。
有时候,我依然会想起和他生活过的那个女人,想知道她后来的消息,可是怎么打捞好似都不存在,有关那几个孩子也不知所向。我想,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照顾下青奇叔公的晚年,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独地离开。不知道是青奇叔公的原因,还是有别的缘由,始终没有见着她们的出现。
后来,我有过猜测,不过没有真凭实据。估计是青奇叔公帮助女人,是瞒着孩子们的。
青奇叔公埋葬在村子的什么地方,我并不知道,母亲告诉过我大致的方向,每次回到村子,打算去看看他的坟墓时,总不能如愿前行。也许,冥冥中这就是他的意思。
我在想,也许此刻他躲在某个地方,活得自在,那种生活只是我们不懂,要不然他怎么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人生?但无论如何?我还欠他一个人情,那天中午的饭,我始终忘记不了那种味道。那种味道,一直伴随着我到现在。
我得感谢那个与青奇叔公相遇的童年。村子里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梦,我似乎看到了那些老屋,似乎听到了那场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