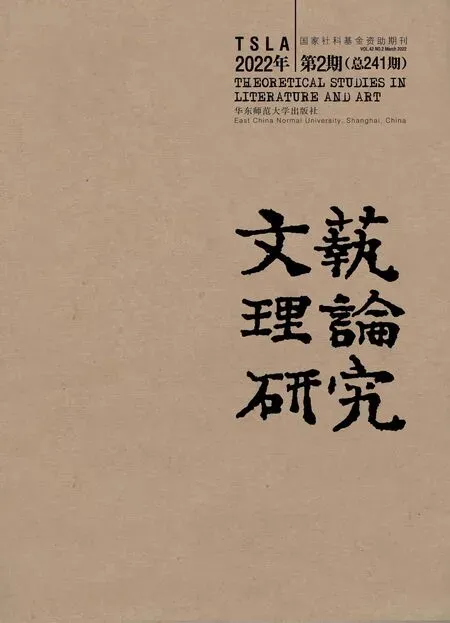试析晚清外交官群体的语言接触及其历史建构
——兼及黄遵宪“言文一致”观再阐释
2022-11-05邓伟
邓 伟
前 言
在晚清的帝国夕照之中,有着一众特殊的士大夫群体,即为晚清外交官群体。他们多具科举功名,但所走的并非当时仕途的“正途”。1866年斌椿由清政府派遣赴泰西“游历”;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虽是由美国人蒲安臣充当使臣;1877年郭嵩焘担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无数的“出洋差”——既有官派的“游历”“公干”,也有愈到后期愈为专业的外交官员——在广泛意义上,造就了晚清社会之中的这一群体。
由于时代的因缘际会,晚清外交官群体的某些地理意识、时空格局、文化观念等,被强行“世界性”地建立与拓展。他们存在的本身,在价值层面,就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此时一般士大夫所标举的“夷夏大防”,带有了儒家正统人士眼中的“异端”色彩。以至于,当时某些排外的士大夫,对于清廷在海外设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使馆,就有了丧权辱国何至如斯的哀叹。
在中西语言接触之中,晚清外交官多不通外语,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不能不重视域外的语言文字,不少人对此深表遗憾。黎庶昌曾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后任驻德使馆参赞、驻法使馆参赞、出使日本大臣,其自道颇具代表性:“庶昌于西洋语言文字素未通知,奉使一年,徒能窥观其大略,而无从细求。耿耿此心,用为憾事,以此益知出洋当以语言文字为先务也”(黎庶昌542)。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说,实际上这也无改于因晚清外交官群体的语言接触,而产生种种“新颖”的语言文字看法,即便是充满了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而首次群体性对中国语言文字直接产生了另外的一种眼光。非常明显,晚清外交官群体的语言接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历史的建构之中,就是直接诞生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的一个重大命题——“言文一致”,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变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 晚清外交官群体的中西语言文字比较
体验到域外的陌生新鲜事物,再与自身既有经验来做比较,是正常人的当然反应。在晚清外交官的日记之中,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中西比较,上至军国大事,下及生活用具。当晚清外交官察觉到与自身固有知识结构完全不同的外语、外文,会不无兴趣地记上那么一笔,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这也说明,他们在异域空间之中,所面对的一种弥散与必然的语言接触氛围。以下是对西方拼音字母文字的一般性看法:
盖外国字母不多,英国只用以上二十六字母;一二字为一话,十数字亦为一话。如A音“阿”,又音“厄埃”,“一”也;“IS”二字音“伊自”,“是”也;“FOR”三字音“佛尔”,“为”也;“STAR”四字音“斯达尔”,“星”也;“NATION”六字连音“内慎”,“邦”也,“国”也;“CHRYSANTHEMUMS”,十四字连音“克力三西墨斯”,义乃“菊花”也;又“INDISTINGISHABLE”十七字连音“因的斯丁圭沙布喇”,义系“乱”也,“难分”也。如是,似与番蒙文同。(张德彝431—432)
今天看来,张德彝——这位同文馆出身的英文译员,后走上职业外交官的道路,也是光绪帝的英文教师——表达的只是一种常识而已,而在此时确是不折不扣的新见。将一个字母认定为一个“字”,“字”直接指向的是语言的“话”,是去拼写语音的,存在不同的音节,就道出了拼音文字的基本特点。所以说,不少晚清外交官在朦胧之中,其实已对西方语言文字“言文一致”有了认识的萌发,具备了看待西方语言与文字判然分离而又合一的意识,看到了语言在其中的超然地位,隐然含有一种西方式的“声音中心主义”逻辑。
顺理成章,晚清外交官群体会调动自身固有的语言文字知识,去解释与应对这一全新的语言文字世界。并且,他们认识西方语言文字的方式颇为引人注目,产生了一种看待世界各国语言文字的新意识,并展现出自己的文明“先见”。例如,有这样的一种看法:
因思四裔结字之形不一,西洋、印度、唐古特、回部皆蔓延缭绕而横行。即满蒙书,自左而右而直行,详绎其义,厥初必有所由昉。乃悟上古结绳而治,与四裔之字形,其蔓延缭绕,总归结绳之象。惟中华自伏羲画卦而后,由奇偶而曲之、直之、方之、圆之、斜之、锐之、聚之、散之,互参迭配,以成书契。而三皇五帝,声教所未及者,尚仍结绳之古式。而后知上古之风,犹有不泯者焉。(志刚275—76)
这一则材料,只是关注到了各国的“文字”,具体为“字形”。这是由中国既有表意文字的视野,对文字形体重视而带来的,从而感兴趣于不同文字书写方式的“横行”“直行”——这一最为直观的外在书写方式。所给出的解释,居然是“伏羲画卦”,似也可聊备一说。并且,此中的“中华”与“四裔”的区分,无疑是以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机制看待“蛮夷”的结果。于是,“西方”在内的“四裔”文字就是结绳的“蔓延缭绕”,属于前“伏羲画卦”的阶段,优劣自不待言。
再如一种看法:
今闻西人言,五洲之内,方言之有文字者,约计八百馀种。我中国则国书蒙古文、唐古忒文、回文、俄文,皆圣朝龙兴以来所习。至英文、法文、拉丁文、日耳曼文,乃近来所习;而和文、西班牙文、印度文,习之者尚无其人。诚以文字或有相同,语言百里各异,通之诚非易事也。(余思诒103)
此中的语言与文字,已在观念上有所分别,扫视世界范围之中有文字的语言,尤其是直谓五洲八百多种有文字的语言为“方言”。内中之意,即是只有汉字书写的汉语才能是“雅言”,才能是“官话”,五洲八百多种有文字的语言不过是异质的存在,与中国国内那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方言”同类,并没什么性质上的分别。这就不同于今天我们认定的外语、普通话、方言的世界性整体语言框架,无疑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观念之下的文化审视,也是令今日我辈汗颜的一种“豪情”。并且,在这一材料之中,如此的“天下”意识席卷全球,“五洲之内”的域外语言使用情形是“方言”的判断,更是符合中国国内“语言百里各异”的看法,可以说晚清士大夫既有的儒家知识体系消化了西方的语言文字的异质性,而语言方面的“雅言”与“方言”的区分视野,迎合了他们的语言知识构成,不会造成任何的内心文化触动与震撼。“文字或有相同”的说法,同样说明了他们的看重之处在于文字,或许在“通之诚非易事”的客观情形之下,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言文不一致”的思路,已经下意识地浮现于他们的脑海之中。这样的观点显然触及了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以下一则材料的观点就更加明显。其言为:
今日习华文者,不知西文为何物;习西文者,不知华文为何物。窃思声成文,谓之音文也者,即因音之所已成之文而缀之也。中外文字虽有异形,制字之初虽有异法,然其缀音成文,则无二致。西文之二字三字拼法,梵文之二合三合,即中国古书中双声叠韵、急读缓读、长言短言之理;而其文之神妙处,只在缀之得法,难以言传,中文然,西文亦然。抑又闻之,古无四声,三百篇文字纯以长言短言调其音节,其一字数音,即长言短言变化处。考之西文,其法亦相似。今之治经者不谙其故,展转附会,不可究诘,而其弊实自四声起,良足叹也!(黄庆澄359)
如此将西文、华文置于同一平台,以“求同”思维来观照中西语言文字,就在“言文关系”方面有了发现——“缀音成文”。众所周知,任何文字都是形、音、意的综合体,文字当然会表现出读音,但对“读音”的理解,中西语言文字系统认识的差别极大。在这一材料之中,西方的拼音文字可由音而成,而中国则需要远溯古书,回到《诗经》的年代,但是中西在创造文字的时候都是“缀音成文”的,都是“言文一致”的,由此还批评基于文字的中国“四声”理论与实践,批评权威的“今之治经者”。这样的观点,已受到其所理解的西方语言文字的言文关系理路的影响,肯定了西方拼音文字式的“缀音成文”,而有了若干书面语的语音方面的在场考虑,进而产生了对自己固有语言文字的反思意识,并直接认为是“弊”,中国“言文一致”观的萌芽已经自然显现了。
由上一系列的中西语言文字比较,折射出晚清外交官群体以其切身经历,面对了一个西方文明的现实存在,而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郭嵩焘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66)。观念保守者如驻英副使、郭嵩焘对头的刘锡鸿,一方面仍是宣称“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子夏曰: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君子不为。非即谓此乎?”(刘锡鸿128),在另一方面也承认,伦敦“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刘锡鸿110)。所以,在他们的面前,西方文明得以实质性地逐渐开展,并在其中获得一个整体返观自身语言文字的机会——在此时,也许他们并不自觉。
二、 薛福成与宋育仁
1890年薛福成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1894年宋育仁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二等参赞,可较为详尽地分析这两位晚清外交官语言接触的观点。因为,他们关于中西语言文字的见解,显得全面而深入,更具有明晰的文化逻辑,乃至于在既有的中国语言文字思维之下,对西方语言文字的“言文一致”思路,已做出了若干的“抵抗”。
薛福成清楚看到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别:“中国之字,以形生义,故有一定之形之义。外国之字,以声传意,故凡字不必以形求,亦不能以义求;往往有以数音拼作一字者,有以数字缩作一音者。中国之字,分喉、舌、唇、齿、牙五音。而西人之音,又往往在喉舌之间、唇牙之间,或且多用鼻音。尽有西人有此音而中国并无此字者,故中西之文不能合一,天实限之,即有翻译好手,只能达其大意,断不能逐字逐句一一吻合”(薛福成290)。所以,薛福成会认为中西文字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一为“以形生义”,一为“以声传意”,其实就是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区分,然后有着若干发音的一般性距离,并由此造成天然而必然的翻译难度。即便在海外的游历之中,作为有心人的薛福成,也会特别注意:“又一室,悬古字横条二十七幅,皆埃及文也,亦自右至左,但横书耳。细审埃及文字,形模已与中国篆书相近,大抵会意象形者为多”(薛福成314)。因为,汉字与埃及文同为表意的文字,所以一样符合中国“六书”之中的若干造字准则,或许这让薛福成感到莫名的亲切。所以,他会认真辨析西方语言文字的源流:“今泰西诸国文字,往往以罗马腊丁文字为宗。一切格致之学,未尝不溯源罗马。盖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昔时英法德奥皆其属地,制度文物滥觞有素,势所必然”(薛福成325)。
薛福成还以中国文字的“六书”造字之法,为中国文字进行辩护。其完整论述为:
西国字体,种类至繁,如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文,各自为体。俄自芬兰以西,即为波兰书矣。法用本国字;而爱勒脱以南,又为哀斯记书矣。考钦天监旧制,有所谓“书拉体”者,即腊丁文,乃希腊文之变体也。希腊字文理较长,而总不外以字母摄音,合音成字;故各国皆二十六字母,惟希腊有三十六字母,而法国只二十四字母,于六书中仅得谐声之义。不知声音之道,年久则变。中国经籍如天、下、华、庆、明、行等字,六朝前犹近秦汉之音,唐以后则纯用今音。以中国之人读中国之字,而高下轻重疾徐,已各自成音,赖有象形、会意等义相维持,故数千年后犹得以考证古训也。外国字母仅知谐音,以口相传,久而易变;况以华言译西语,以今音译古语,以华字译西书,既无一定之音,又无一定之字,而且方言各异,则安如华文之六体兼备而四书不乱哉?(薛福成659—660)
西方的字母文字的实质是“合音成字”,仅使用了“六书”之中“谐音”一种造字方法,而声音是变化的,所以这样的文字靠不住,而超越声音的“中国之字”,使用众多的造字方法,以字形维持字义,故能千年相传。这大概就是薛福成的逻辑推理的过程,让人感觉他是通过论证表意文字胜过表音文字,从而为汉字进行了辩护。无疑,这也是中国既有语言文字体系“书同文”思路的展现。
让我们再来关注宋育仁——这一位在听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利之时,趁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之际,在代理公使的任上,试图在西方招募一只舰队奇袭日本本土的长崎与东京,以求反败为胜,并且已经做出若干具体准备举措的外交官——在中西语言文字方面也多有深思,堪称蔚为大观。
宋育仁明确提出了“语言与文字合一”的命题,并对这一命题做出了缜密的分析:“其文二十六字母,以音相合。如中国之一语而为一字,一字凡数音,孩而学语,其音皆二十六字母之音所合而成,童而习书,知二十六字母之本音,记二十六字母之点画,即知某语。即某之数母音所合而成,依音之次第,画而记之,即为字矣。其市井道路,所通行文字,即是语言,故孩提奚竖乞丐,皆能识字”(宋育仁82)。这样,西方“言文一致”的优点,已被宋育仁表述得淋漓尽致,就是由声音和二十六个字母,构成了一个举国识字,甚至乞丐也能识字的惊人局面。这堪称“言文一致”的典范表达,不管是黄遵宪,还是日后倡导“言文一致”的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者,其赞成的西方式“言文一致”的理由,大抵不过如此。这即是说,宋育仁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晰而自觉的“言文一致”观,并具备某种知识的历史建构的可能。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宋育仁就是中国的“言文一致”命题的提出者,这一发明权也没有人会授予他。因为,宋育仁之后再继续“深入”剖析“言文一致”之时,却没有沿着以上思路继续发展,而是转了一个方向,返回至中国既有语言文字观念,呈现出在今日看来似是某种“倒退”的立场。其分析为:“语言即文字,简易易知,顾其为书,便于直陈器数,难于曲达义理。举国聪明才智,注于器数,故日进富强,无深至之文言,则性情不感,而日趋诈力。其国有善著论、工为诗之士,国人甚重,然不数有。其教惟以永生永罚制人,不讲自然之情义,其害在蔑伦背理而不知,不解中国父子夫妇之伦为何物,反诋中国父权过重,女性见屈,以为承草昧之馀习,势强者擅权,急欲起而革之”(宋育仁62)。尽管西方“语言即文字”的“言文一致”有着种种优点,但在宋育仁的眼里,其实更是有着不可避免的重大缺陷,主要在于其内涵没有“深至之文言”及其蕴涵的中国儒家教化伦理,乃至于宋育仁由此能够否定西方语言文字“言文一致”的优点。至此,我们发现宋育仁尽管已经看清西方“言文一致”的情形,他哪里是要倡导“言文一致”,确切说来,恰恰是反向的行进,即是宋育仁反对西方式的“言文一致”字母文字,而为中国既有的道德文章做出了全面的辩护。
有意思的是,宋育仁不只是消极批判西方语言文字的“言文一致”情形,来维护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机制,而是主动地积极出击,要以儒家的伦理思想在语言文字领域完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主义建构。其策略为:“宜因以广同文之治,命儒臣取六经所有之字,参合大小篆,分部摹成字典,用洋文译古训,引申别义,详为诠释。即用其文,写六经定本,以贻其议院学院、教会学会。彼国太学,有博古一科,重埃及古文。其文主形篆而直行,字形如钟鼎虫鸟篆。今制通行字典,须用篆文,令有形意可见,始能有所悟入。识中文自必读中书,读中书自然知名教,知名教自然贵仁义,服名教。贵仁义,则夷进于夏,可以仁义之道治之矣”(宋育仁64—65)。这反映出一种典型的“以夏变夷”“以文化之”的儒家文化理想,也是一种中国士大夫的积极进取行为。由此,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机制及其从中体现的统治术,似有登上世界性舞台的可能。
从表面看来,宋育仁在中西语言文字的认识之上,似是集“言文一致”与“言文不一致”二者于一身,既对西方“言文一致”的字母文字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又对中国既有语言文字深怀信念。但是,这一切“矛盾”的最终解决之道,还是要回归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回归于其价值认同的儒家观念,回归于既定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世界的逻辑。可以说,此时晚清外交官的语言接触,使得日后“言文一致”命题的视域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显现,折射出既有的中国古代语言文字体系日后变革的大势。同时,处在萌生阶段的中国“言文一致”观,呈现出了一种“混沌”的原生质杂芜状态,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处于逐渐形成而有待于“现代”整合与命名的自然生长过程之中。
三、 黄遵宪: 文化心理的方向转变
在如此的域外语言接触情形之下,晚清外交官群体进而诞生了继往开来的重量级人物——黄遵宪。在其巨著《日本国志》的每一部分的议论之前,都有“外史氏曰”的提示。“外史氏”的称谓,源自《周礼·春官·大宗伯》,而这一称谓的本身,就表明了黄遵宪对自己近二十年外交官生涯的高度认同,由此形成切入语言与文化问题的世界性视野,亦非一般的晚清外交官能够相比。
黄遵宪在语言文字方面卓有建树: 一方面他分享了晚清外交官对中国固有语言文字与文化的自信,也可以说晚清外交官群体的语言文字观念构成了其直接相关的背景,他们确是属于同一时代的群体;另一方面黄遵宪又有着非常重要的推进,乃至是一种方向转变的突破,即是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既有机制,其语言文字见解成为了一种卓异的独立存在。
具有“举人”科举功名的黄遵宪,在外交履历上,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官、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亲身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与西方社会的种种情形。像其他的晚清外交官,乃至于晚清士大夫一般,他必须为自己的海外见闻,做出一个符合自身文化立场的解释——这或许是在中西交汇初期,中国士大夫共同面对的时代性文化难题。
让人出乎意料、也非常精彩的是,黄遵宪沿着晚清“西学中源”之类的流行观点,却得出超越时人的看法,既有别于要继续维持“天朝上国”文化优势的士大夫,又与“西学中源”的文化逻辑融会在一起,显现出一种“奇特”的转变。他说道:“百年以来,西国日益强,学日益盛,若轮舶,若电线,日出奇无穷。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今轮舶往来,目击其精能如此,切实如此,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来,恶其异类而并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黄遵宪1415)这样,西方事物不应视为奇技淫巧,因事关国计民生,更不能轻视,应该重新学习这些中国曾经“固有”的知识,而大有“托古改制”的意味。因为,“古”与“今”似乎同时能显现于当时,“古制”与“新法”就达成了一致与平衡,以此可以批评专务保守之人的狭隘心态。这样,晚清时期的“西学中源”思路,在黄遵宪这里,吊诡地显现出积极的社会意义与开放的文化心态。
再来探究黄遵宪语言文字变革观念的形成,不难发现其另一现实的语言接触背景,即是其亲历的日本“明治维新”社会的语言文字变迁。在黄遵宪来到日本之前,已有前岛密、西周等人,在“脱亚入欧”的背景之下,提出了废除汉文而实现日本“言文一致”的主张,以创造出日本现代书面书写体系,以创造出内化而均质的“忠君爱国”的现代日本国民。黄遵宪在日本的外交官时期,正是日本要求废除汉文的“言文一致”运动的热潮时期,其亲身见闻经历,影响到他“言文一致”观的产生。一个显著的事实即为,黄遵宪关于“言文一致”观的重要论述,都置于其所著的《日本国志》之中。
黄遵宪是将日本语言文字的变化建构,作为一个正面范例的形象,在其中同样持有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其根本观念的“盖文字者,所以代语言之用者也”,(黄遵宪1417)在晚清外交官群体之中,并不能算一个特别新颖的看法。应当说,他们大多都借助于西方语言文字的现实,而了悟到这一情形。黄遵宪的特异之处,在于彻底贯彻了这一观念,并用以观察变动之中的日本书面语,而不再转回到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一般性特征比较。换言之,他不是想再回到中国古代语言文字机制,而是基于现实的情况,坦陈使用汉字作为日本书面语体系所带来的问题,“然语言文字,不相比附,故仅仅行于官府,而民间不便也”(黄遵宪1417),而放弃汉字书写,在日语之中有着自己的缘由,“此皆于汉文不相比附,强袭汉文而用之,名物象数,用其义而不用其音,犹可以通。若语气文字收发转变之间,循用汉文,反有以钩章棘句、诘曲聱牙为病者。故其用假名也,或如译人之变易其辞,或如绍介之通达其意,或如瞽者之相之指示。其所行有假名,而汉文乃适于用,势不得不然也”(黄遵宪1417)。在此,黄遵宪是就事论事,显得开明而通达。
于是,黄遵宪建立起脱离汉字系统的日语书写体系的如下形象:
自草书平假名行世,音不过四十七字,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间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其被之歌曲者,则自朝廷典礼、士官宴会,逮于优人上场、妓女卖艺,一一皆可播之声诗、传之管弦。若稗官小说,如古之《荣华物语》、《源语》、《势语》之类,已传播众口,而小说家簧鼓其说,更设为神仙佛鬼奇诞之辞、狐犬物异怪异之辞、男女思恋媟亵之辞,以耸人耳目,故日本小说家言充溢于世,而士大夫间亦用其体,以述往迹,纪异闻。(黄遵宪1418)
考日本方言不出四十七字中。此四十七字,虽一字一音,又有音有字而无义,然以数字联属而成语,则一切方言统摄于是,而义自在其中。盖语言文字,合而为一,绝无障碍,是以用之便,而行之广也。(黄遵宪1419)
此中的要义,是黄遵宪“言文一致”观的直接表述——“语言文字,合而为一”。这种表音的日本文字,优势为“极易习识,而其用遂”,能胜任书写语言的职责,达到了各个阶层在各个领域的普遍使用,也取得了超越雅俗的社会接受效果。甚至,它还产生了自己的文学——市民阶层的通俗性人情世情小说,而小说文体由此而兴盛。在此,黄遵宪就没有之前晚清外交官所显示出的文化“迷思”与“捍卫”之情,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与真实。当然,这也更为接近我们今天的观念。
四、 《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字·外史氏曰》再阐释
黄遵宪关于日本语言文字变化的描绘,固然是对“明治维新”日本社会的一种知识性介绍,同时更是指向中国自己的语言文字情形,具有强烈主体的“问题意识”。这样,就可以进入《日本国志》有关中国语言文字最为核心的一段论述,具体见于《学术志二·文字》篇的末尾。黄遵宪同样以“外史氏”的称谓,发表了不凡的见解,是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建构之中的重要内容,是本源性的经典文献。这些文字一再被高频引用,将黄遵宪的语言文字观点推向历史前台,被公认为中国“言文一致”诞生的基石。
为了最大限度保持黄遵宪原文的信息,以下可对这一段重点文字,先作逐字逐句的引用,再接着进行较为详尽的阐释: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黄遵宪1420)
黄遵宪在日本的语言文字情形之外,再言及欧洲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的状况,明显是要描绘一种普遍性的“言文一致”的全球图景。这一图景体现为“语音中心主义”,是以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声音”摆脱统一的拉丁文,再形成各国书写方式的文学,或者用以翻译书面的《旧约》《新约》,而在其中“声音”的意义是先导的,是决定性的。这就梗概性地总结出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言文一致”命题,将之作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黄遵宪明显超越晚清外交官群体的中西语言比较思路之处,在于在这一纵深世界性背景的建立之中,关心的不再仅是一个局部性问题,不再仅是一个文明体内部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中西语言文字的特征比较的问题,而是动态地看待世界范围之内的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现代变革问题——这堪称黄遵宪“言文一致”观的根底之所在。在这一宏大意义上,“言文一致”实质性进入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本体,“现代”实质性进入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本体。
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黄遵宪1420)
在黄遵宪“言文一致”命题之中,“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成为一种普遍性知识,在其中超越了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绝大区别,或者说无视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绝大区别。黄遵宪并不关心汉语、汉字的“特殊性”问题,而直接形成了审视一切“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准则,而汉语与汉字问题,无疑应当纳入“言文一致”的普遍性知识体系之中,运行西方式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文字逻辑。正是由于“语言”与“文字”的分离,黄遵宪指向对汉文“通文者少”的批判,如果要做到“通文者多”,自然要实现“言文一致”的“语言与文字合”。于是,日本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做法成为了榜样,具有了“裨于东方文教”的意义。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黄遵宪1420)
黄遵宪在此明确指出中国语言文字“言文不一致”的突出局面,并且是在一种现代意义上认定中国语言文字的“言文不一致”,从而内在形成了巨大的变革需求,或者说形成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言文不一致”与“言文一致”的二元对立。在此二元对立之中,具有明显的优劣的价值判断。于是,从“言文不一致”到“言文一致”的线性发展链条就建立起来,这也是一种鲜明“现代性”进化时间的线性发展链条。进而,从“言文不一致”到“言文一致”,产生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的巨大落差及其变革动力,产生了日后被称为“现代”的若干极大规模与纷繁复杂的语言文字运动与文学革命运动。
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黄遵宪1420)
黄遵宪拟出的中国语言文字变革路径,显得模糊而含混。大致而言,包括了“字体”“文字”与“文体”,追求方向是文字的简便易行、明白晓畅,而不是文字本身的高度艺术性,或者说高度的艺术性恰恰是它需要脱离的。之所以说“模糊而含混”,除了黄遵宪自身的表述的不确定之外,并没有一个现实方案,只是一个指向性的大致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当黄遵宪在坚定表明“语言与文字合”的理念之后,却并不能在其变革路径之中找到“语音”的位置,因为“字体”“文字”与“文体”都是就文字的书面书写系统而言的。这似乎构成一个悖论,或者说黄遵宪至少没有展示出“语音”切实进入书写系统的方式,即文字如何表现出一种在场的类似口语的“汉语”,也没有看到一种去直接描摹“语音”的文字的产生,哪怕仅仅是一种设想。西方式的“语音中心主义”面目,其实在黄遵宪的实践拟想层面是无法分辨与析出的。就中国近现代“言文一致”命题发展而言,这一点同样会是非常重要,是一个“原点”性质的逻辑构成。这即是说,中国近现代“言文一致”的主流,不是要去实现口语与书面语的无差别吻合与重叠,而是指向书面语的建设,更多属于“文”的问题。
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黄遵宪1420)
黄遵宪推崇小说在“言文一致”之中的特殊作用,因为小说语言是使用“方言”,从而达到“言文一致”的效果。“今”与“俗”的定位,清晰表明了黄遵宪期待的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受众,乃是现实之中的一般普通民众。自然,这些普通民众阅读的“小说”,是向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因此这一观点会带来向来鄙俗定位“小说”地位的上升。更长远说来,这也埋下在“现代文学”之中,小说文体占据支配性地位的逻辑。我们可以推测黄遵宪此时的“文学”观念,可能并不再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雅文学的诗文了。由于“小说”的正面标举,至少打开了一丝中国古代文学雅俗界限的裂缝,而“今”与“俗”都值得追求,不再是被鄙夷的对象。
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遵宪1420)
黄遵宪的语言文字观念逐渐溢出与脱离了精英士大夫阶层——他告别了一个世界,也试图开启另一个世界。固然,这一观点还可与儒家“教化”观念联系起来,但已经完全没有常见的儒家“复古”思路。其“言文一致”,面对了使用“简易之法”的“农工商贾、妇女幼稚”,面对了晚清以降世界民族之林的剧烈竞争,具有早期现代启蒙的意蕴。在这一句话之中,甚至还让人觉得梁启超在日后政论文使用的关键词——“国民”——似乎是呼之欲出了。再大而言之,晚清士大夫面对着翻天地覆的变化,已不可能像之前的中国古代时期,自足地栖息于既有语言文字的伟大“光照”之下,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的整体性崩溃,传统社会运行机制势必会渐行渐远,各个社会阶层的界限会被打破、调整与重组,甚至亟需唤醒“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的全体民众,来共同应对时局——这就成为晚清士大夫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不二方案。还需要说明,在晚清时期,由士大夫主导的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所针对的目标人群也是如此。
概括说来,由上黄遵宪的一段重要文字,实质包含了晚清中西语言文字接触而形成的一种基本观念,也清除了其它晚清外交官在语言文字认识方面的杂芜质地与不同理念方向,呈现出单向的“现代”发展情形。这即是说,在世界范围的眼光之下,从现代民族国家出发,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性”初步在“言文一致”之中得以历史建构,“现代”的“装置”边界已然有所打造与建立,而后世就是向此“装置”的容器放置不同的时代内容,直至一种全民性的现代语言文字体系合法性与实践性的全面确立。
毋庸讳言,黄遵宪的“言文一致”观,留有太多的空白之处。即便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文字·外史氏曰》这一段经典表述之中,就“语言”体系而言,有“腊丁语”“语言”“法音”“英音”“方言”;就“文字”体系而言,有“文学”“文辞”“文字”“假名”“孳生之字”“文体”“小说家言”。这一系列的专有名词,各有特定内涵与和适用范畴,并不能在逻辑上相互消化与融通,合起来更是只能建立一个较为混杂的语言文字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为先行者的黄遵宪,在此时就能做出一个明晰而有效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巨型的跨越某个具体时代的重大问题。对它的回答,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时期,知识界都是深深纠葛而陷入其中,并开拓出不同流向的庞杂语言文字实践领域。从这一角度说,黄遵宪最早全局性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的宏大目标,也展现出若干的悖论与症候,犹如打下了一个结,之后就是无数人尝试去解开这个结。还可以说,黄遵宪在“言文一致”方面那些不无含混的表述,反倒是极大弥散与笼罩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变革,形成了在宽泛意义上预言般的昭示存在。
结 语
如果按照当下某些网络小说的桥段,“穿越”的设置必不可少。那么,试想有人从晚清穿越到了今天,或者有人从今天穿越到了晚清,中间就横亘了一百多年的时光。可以作出推测,此人在语言文字方面,料想应当很难与所面临的环境交流。这种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或许正是“现代中国”在语言文字变革领域的展示,呈现出了空前的复杂与高度的紧张。
由本文对晚清外交官群体语言接触的描绘,至少能够看到在这一“古今之变”之中,中国语言文学现代变革的源头性“起点”的历史建构。或更稳妥说,能看到在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之中一种资源性重要思路的历史建构。在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士大夫阅读着刚刚出版的《日本国志》,黄遵宪的“言文一致”观,契合了社会主流“救亡图存”的诉求,自然会不胫而走并广泛流布,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字变革合法性论证的基本思路,成为了一种突出的维新知识构成,尽管它在多年之前就已经构思完成。换言之,基于中国变动社会的现实文化需求,在极为复杂的内外互动之中,中国的“言文一致”逐渐生成了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极大开启了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变革巨大而繁复的实验室。
还可再作延伸观察: 源于晚清外交官群体的中国近现代时期的“言文一致”命题,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天崩地裂般的巨变之中,连续不断与具体时空之中的社会变革内容相结合,由无数的人物、事件、阶层、阶级,无数的因素、线索、资源、机制,汇合成为了跨越中国近现代时期“母题”式的超级统合性的现代语言文字观念与实践。于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之中,“言文一致”激发了晚清以降中国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语言发展的驱动性变革力量,塑造了语言文字这一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最为重要的基座及其制度构成,带来了与现代民族国家创制同构的书写方式、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而“言文一致”造成的中国现代语言文字系统所能达到的疆域,就是“现代中国”所能达到的疆域。
① 日本“言文一致”的情形,与中国“言文一致”情形具有可比性,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中国“言文一致”观念的外来思想资源意义。可参见齐一民: 《日本语言文字脱亚入欧之路: 日本近代言文一致问题初探》(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第二章“必然还是偶然——言文一致的时代背景和原因”、第三章“‘汉字’(‘国字’)的废存和日本言文一致之路”。
郭嵩焘: 《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四)。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Guo, Songtao.()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黄庆澄: 《东游日记》,《走向世界丛书》(三)。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Huang, Qingcheng.()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黄遵宪: 《日本国志》,《黄遵宪全集》。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
[Huang, Zunxian.,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黎庶昌: 《西洋杂志》,《走向世界丛书》(四)。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Li, Shuchang.()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刘锡鸿: 《英轺私记》,《走向世界丛书》(七)。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Liu, Xihong.()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宋育仁: 《泰西各国采风记》。长沙: 岳麓书社,2016年。
[Song, Yuren.Changsha: Yuelu Press, 2016.]
薛福成: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八)。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Xue, Fucheng.,,()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余思诒: 《楼船日记》。长沙: 岳麓书社,2016年。
[Yu, Siyi.Changsha: Yuelu Press, 2016.]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走向世界丛书》(二)。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Zhang, Deyi.()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
志刚: 《初使泰西记》,《走向世界丛书》(一)。长沙: 岳麓书社,2008年。
[Zhi, Gang.()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