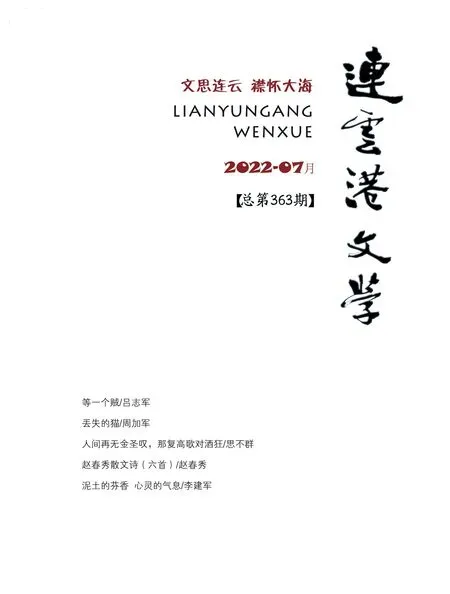泥土的芳香 心灵的气息
——徐东小说集《大雪》读
2022-11-05李建军
李建军
捧读深圳作家徐东的小说集《大雪》,是在初冬的下午。阳光照在书桌上,一杯刚沏的清茶飘着袅袅的热气。心是安静而舒缓的,也是温暖而诚谨的。这部收录了作者十余年呕心沥血之作的集子,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心灵的气息,每一篇都与众不同,每一篇都值得细读、深读。
一
《大雪》收选的文章,从题材上分类,《大雪》《大风》《赶集》《丸子汤》是乡土题材小说,《老于》《老齐》《变化》《丁一烽》《时闻鸟声》等属于城市题材小说。这些中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又以老年人居多,实则是以有限的篇幅和独特的视角,勾勒出人物漫长的生命旅程。如果从篇幅上分类,除了上述中短篇小说外,余者大都是描写城市生活的微篇小说。
以短篇小说《大雪》作为这部小说集的书名,可见作家对其偏爱和自信。徐东在随笔《关于酒关于信任》中写道:“《大雪》是以我父亲为原型的。父亲早年做生意,起早贪黑,冬冷夏热,风里来雨里去,人又黑又瘦,我看在眼里,觉得父亲确实不容易。”既如此,便不难理解他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倾注的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
小说中的父亲为了赚够儿女的学费,即使雪后的路面再难走,也要骑着自行车去赶集卖菜。大年三十的集上,父亲的菜很快卖光了,他又到三十里外的县城批发甘蔗。谁知午饭后,天上下起鹅毛大雪,父亲批发了二百多斤的甘蔗,冒着风雪往家赶。在北京上大学的儿子和大女儿放假回家过春节,加上在家绣花挣钱的小女儿,他们担心和心疼父亲,在夜幕降临后,一起走进雪地,顶着“密密麻麻像是一群发疯的蝗虫”似的雪花,跑出村庄,跑到大路上,迎接他们的父亲。
当我读到孩子们“终于看到那个黑黑的影子——那正是他们艰难地推着车、一步一步挪行的父亲,他们用欢快的、激动的,同时带着哭腔的声音喊他时”,读到“父亲搓搓冻僵的手,从大妹手中接过包子,大口大口呑了两个,又从小妹手中接过水,喝了口水……和孩子们一起扶正自行车,开口说回家”时,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我为在暴风雪中跋涉前行的父亲感动,为在雪地里奔跑迎候父亲的三兄妹感动,也为这一家人深沉而温暖的挚爱亲情所感动。
微小说《大雨》可以作为《大雪》的姐妹篇参照阅读。“我”冒着大雨跑到几里外的大堤上迎接赶集回来的父亲。父亲自行车上的驮筐里装满了三百多斤的土豆,看到“我”来迎他,可以说是“喜出望外”。父亲的脚被玻璃划伤了,流了很多血,却“没有感觉到疼”。二十年后的今天,那场大雨“还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生命里”。
二
《大风》里的李杏斤,《赶集》里的老爷爷,《丸子汤》里的李宝家,《别墅》里的高翠莲,都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除了高翠莲稍年轻些,其余几位都是八十多岁的年迈老人。
李杏斤是在她七十七岁的妹妹上吊寻死后想到风的。“想到了风,她那颗苍老的心竟激动起来。”她用嘴巴制造风声,“发出异常的声音,让她感到快乐,让她的心一下子就好似变成了小姑娘的心。”李杏斤的异常,让她的三个儿子以为她“魔怔了”。实际上,李杏斤在冬天刮大风之前,“就无数次想到了风,想到风中飞扬的一些事物……从能记事的小时候起,到出嫁,到生儿育女……她一生的酸甜苦辣,一生喜怒哀乐的体验和经历。”在一个刮大风的下午,在床上不吃不喝、足足躺了半个多月的李杏斤,居然起了床,走进寒冷的、刮得呼呼的大风里。“她的生命里就像充满了空气似的,让她产生了一种想要飞翔的冲动。”就连身体健壮的三儿媳居然拦也拦不住、拉也拉不住她!
在这里,大风是一种意象,是心灵的呼唤,是大地的召唤。“李杏斤的灵魂被大风吹走了,只留下了身体。”
《赶集》里的老爷爷年轻时“一夜可以砍七亩高粱,一天可以锄八亩地,一顿饭可以吃一桶(十几碗)面条”。现在他老了,连他想到集上走走,儿子们都不给他这个权利了,怕他迷了路或是在路上摔倒了。翻过年他就八十七岁了,他试了试手脚,决定去赶一次集,再到离集市不远的地方去看看这辈子从未见过的火车。老爷爷看到铁道的时候是正午时分,而下午五点才有火车通过,所以等了很久火车也没有来。看看日头,他不能再等了,要回家了。他从铁道上往下坡走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从十多米的斜坡滚了下来。就在这时候,他看到了火车。“火车的到来是通过身下的大地感觉到的……他看到黑黢黢的火车开过来,开近了,在铁道上一闪一闪地通过……”老爷爷的心愿了了,就算生命归于尘土也没有遗憾了。
李宝家回想他过去的几十年时光,“他想得很慢,他的想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虽然在动,可看不到在动。”《丸子汤》这篇小说的叙事缓慢而舒展,平心静气,慢条斯理,一如作者温文尔雅的性格。通过李宝家悠长的回忆,完整地追述了他大半生的生命旅程。李宝家十六岁那年,他的父母饿死了,哥哥也不堪饥寒吊死在庙里。他遇上了卖丸子汤的麻脸,被收留下来烧灶火。麻脸还把侄女——神经不正常的“魔道”女孩介绍给他做老婆。麻脸死后,李宝家接过“丸子汤”生意,一干就是几十年。这些年,魔道妻子每天都站在家门口,看着李宝家出门,又站在门口,等着他回家。他俩虽然没有生养孩子,但相依为命、知冷知热地过了几十年,直到“魔道”妻子去世。一年后,李宝家在清晨去集市的路上捡了个弃婴。他给这个孩子起名李路金,意思是路上拾到的金子。在小路金六岁时,还带他到县医院补好了豁嘴儿,送他上了学,想象他长大了,成了大学生。但是,当小路金的亲生母亲赶来偷看孩子之后,李宝家忍痛做出决定,把孩子送还给他的亲生父母。临送走前,他给孩子做了一锅丸子汤。不久,李宝家就没了。长大成人的孩子没有忘记他,每到过年过节,都会来为他的李宝家爷爷上坟烧纸。
李宝家、李杏斤和《赶集》里的老爷爷,都是“极好极好的老人”。他们善良、宽厚、朴实、坚韧,像广袤原野里的泥土,从来都是默默地奉献,从未想过索取和回报。
《别墅》里的高翠莲有两个儿子,在村里盖了两栋别墅。但是,两个儿子平时都在北京,大儿子夫妻俩在小儿子的公司打工,把七岁的男孩阳阳丢给了奶奶高翠莲。村里人说高翠莲的小儿子是“剥削人的资本家”。受大人的影响,村里的孩子们都不肯跟阳阳玩,高翠莲用糖果和小恩小惠收买,也无济于事。阳阳为了和孩子们玩到一起,只好跟他们一样说爸爸妈妈的坏话,说不想他们,不愿见到他们,还随小伙伴一起喊奶奶的外号“大嘴”。高翠莲感到非常吃惊和愤怒,抡起棍子将领头的小孩李乐乐的额头打破出血。在外打工的李乐乐父母坐高铁赶回家,找高翠莲索赔,双方争吵起来。阳阳见李乐乐一家围着奶奶吵,便冲上去踢打李乐乐的爸爸。李乐乐爸爸拎起阳阳摔到墙上……“阳阳没能救回来,高翠莲也疯了。”
这个悲剧故事描述了乡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大胆揭示了当下农村存在的贫富矛盾,揭示了现实社会复杂的人心和人性,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三
老于(《老于》)和老齐(《老齐》)是生活在都市的老人。老于生活在北京,老齐生活在深圳,一北一南。两个人的性格和境遇也各不相同。
老于是个仓库管理员,五十五岁,没到退休年龄。但他肺部出了大问题,已经是肺癌晚期。老于不想治了,因为儿子大学毕业也在北京发展,刚在通州首付了一套房子,他不想变成儿子的拖累。不过得了绝症的老于打算改变一下自己。他骑着三轮车,到了图书市场大门,与保安小伙子怼上了。“照以前他会下了车,从栏杆底下矮着身子钻过去,然后再伸手拉他的三轮车滑过去。”但这一次,“老于给保安招了招手,笑了一下,示意他开一下栏杆。”保安却根本不理睬他,也不相信他说自己得了绝症,“你就装吧,我看你就得的是神经病!”一来二去,两人撕打起来。老于到附近买了把菜刀,“嚯”的一下把菜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保安一下变得紧张起来,打开对讲机叫来队长……等到保安真的看到老于的化验单,联想到自己家里得了重病的父母,他的眼里才有了泪花,真诚地向老于道歉。接着,保安队长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老于感动了,眼睛也有些湿了,把菜刀“咣啷”一声丢进车筐里。
老于和保安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需要心灵的沟通,唯有爱可以融化人心的坚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在深圳的城中村,上了年纪的老齐靠捡垃圾为生。他租住的是每月租金二百五十元的整栋楼唯一没有窗户的房间。连房东雇来管理和收租的老顾都对他没个好印象,建议过房东让他搬出去。“理由是老齐人太老了,没儿没女,从来没见有亲戚朋友看望过他,如果万一哪天生病死了,谁来管他呢?”
徐东对老齐的日常生活作了细致描写:他挣的钱除了交房租,剩下的只能很节省着用,每天吃馒头就榨菜,偶尔吃碗面就算好的了;他的房子里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电灯,为了省钱并不常开;即使是燠热的夏季,他也不用电风扇。
五十来岁的老顾“平时是个挺冷的人”,有一次,见到老齐被一辆小车擦伤后还一跛一拐地照旧去捡破烂,便动了恻隐之心,把自己做的饭菜留了一份给老齐。老齐也向他敞开了封存已久的心扉。原来,十多年前,老齐和老伴从北方农村来到深圳,是来寻找在此打工、半年没有音讯的唯一养子。就这么一直找呀找,老伴患癌后不堪病痛折磨服安眠药自尽了,他仍在继续找,“找不见就不回老家了。”他把老伴的骨灰盒摆在身边,每天“与他想象中还没有离去的老伴说说话”;每年还给她过生日,许个愿……“那天晚上,他把存下的三千多块钱拿给老顾,拜托了他一件事,他请老顾帮忙在他死后给火化了,带着他与老伴的骨灰回一趟他的老家,请乡亲们把他们给埋了。”老顾郑重地答应了,并完成了老齐最后的托付。
徐东关注城市和乡村的老年群体,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他们的生命晚景,以悲悯关爱的情怀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令人惋叹,令人沉思。
四
《变化》和《丁一烽》是本书篇幅最长、分量很重的两部中篇小说。写的是花秋生(《变化》主人公)和丁一烽这两位年过不惑中年男子的成长史、情爱史和心灵史。在他们身上,能隐约看到作家自身及其身边朋友的影子。
十年前的夏天,花秋生想买两样东西,一条短裤,一台电风扇,却一直难以如愿。他挣的钱太少了,除了寄给老家父母五百元,还有七百元,扣除房租和吃饭钱,所剩无几。他上大学时谈了个女朋友马丽,也因为两人都很穷而分手。马丽回家乡县城开了个鞋店,他来到北京,在一家编辑部做编辑,兼搞文学创作。虽然分开三年了,他还爱着马丽,马丽的心里也一直有他,于是两人又在北京相聚。接着,马丽先到深圳发展,花秋生约了同事李更,也一起辞职来到深圳。两年后,马丽成了开化妆品店的小老板,花秋生在一家企业编内刊,工资涨到每月五千元。他俩在深圳买了房,结了婚。李更则与马丽的好友、化妆品公司老板林蓉结婚,住进了别墅,开上了陆虎。
花秋生结婚后安于现状,缺少激情,写作的想法都淡了。“马丽忙着挣钱,顾不上和他要孩子,让他觉得马丽的心没在自己身上。”“既然她不把自己当回事,自己也应该有些变化了,但最先发生变化的是李更和林蓉。”李更认为“写诗需要新鲜的感情”,常到夜总会等场所找女孩,寻找刺激,被林蓉跟踪发现后,两人离婚。李更觉得自己重获自由,带着女朋友约花秋生钓鱼休闲。花秋生邂逅年轻貌美的毛菲菲,“也想活得精彩一些”。二个月后,两人开房时被马丽捉奸在床。花秋生与马丽离婚后变得一无所有。
在这急骤变化的时代,生活在这熙熙攘攘的人世间,许多人都身不由己地发生了变化。唯独丁一烽还在坚守,还在执着地坚守他内心认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拒绝了唾手可得的一千万。知道这件事的人没有谁不觉得他傻的……”《丁一烽》开头就设置了一个悬念:丁一烽为什么会拒绝这一千万?这一千万与他的前女友和前妻有什么关系?
二十一年前,丁一烽从北方老家来到深圳,这些年他一直在一家玩具厂上班,直到一个月前因工厂搬离深圳而失业。他从最初每月工资三四百块钱,升至每月五千多,成了厂里最老的员工。这在深圳简直就是个奇迹:他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只有他,除了年龄外,别的什么都没变。”
在女工多男工少的工厂,沉默寡言的丁一烽也是有人喜欢的,而且是两个女孩同时喜欢上他。一个是“娇小玲珑”的何笑颜,一个是“要个头有个头、要身材有身材”的马钰琪。这两人还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丁一烽虽然会和两个女孩一起去公园散步,但内心里喜欢的是何笑颜。马钰琪看出来后,主动退出,甘当他俩的红娘。丁一烽对何笑颜的感情在经历“非典”期间的日夜守护后有了突破性发展,两人租房同居。他甚至计划起两人结婚的事。“何笑颜却一直渴望着变化,不想一直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工。”她后来成功地从玩具厂跳槽到一家模具厂,由工人变成销售人员。她不想被丁一烽所牵绊,借口工作的地方远,从两人同居的地方搬了出来。
何笑颜的变心让马钰琪有了机会,她主动走近丁一烽,有一天,他俩借着酒意纵情地合二为一。后来,聪明伶俐的马钰琪成了著名企业家张老板的秘书,经常陪老板去应酬,这让丁一烽难以接受,有些不放心她。不过两人还是买了套婚房,举办了婚礼。婚后,丁一烽仍然怀疑马钰琪与张老板之间不清不白,对婚姻越来越没有信心。两人吵吵闹闹地一起生活了三年多,最终还是离了。离婚时,房子归马钰琪,她写了张四十万元的欠条给丁一烽。马钰琪辞职与何笑颜一起创业,卖了房子,买下机器设备,租了厂房,用了十年时间,一步步获得了成功。丁一烽当初的四十万,被马钰琪折算成投资成本,“现在少说也有一千万了”。这一天,马钰琪和何笑颜一起来见丁一烽,把一张存有一千万元的银行卡交给他:“这些钱可以让你变成一个成功的、体面的男人了。”丁一烽笑着摇了摇头,坚决婉拒了这一千万,他只收下当初那四十万。
当然,作为小说人物,丁一烽面对“一千万”的选择,是作家浪漫主义的理想化虚构。作家在本书中不遗余力地渲染这种理想情怀,呼唤这种“古之义士”道德精神的回归,其拳拳之心和不懈追求令人感佩。
五
微篇小说《陌生人的欠条》在《百花园》杂志发表后,被《小说选刊》等多家选刊转载,获《小说选刊》杂志最受读者欢迎奖。写的是十二年前,一个作家给了一个落魄年轻人五百元钱,年轻人一定要打欠条,十二年后,年轻人知恩图报的故事。这时候的年轻人早已今非昔比,他听说作家至今还没有自己的住房,一定要还他五百万。但是作家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最后只要了他五百元。小说写出了人间的善良和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守。
归于此类的微篇小说还有《读者》《二十年后再见面》《好运到来时》《请让我再想一想》《请帮我拿个主意》等。《读者》里的李更因为读了“我”的一篇充满寓意的小说《毒药》,深受启发,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规划,成为公认的文化名流,从此名利双收。但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否定和批评一切,身上的毒性越来越大。”失眠症也困扰着他,让他生不如死。李更找到“我”,愿意出一百万甚至一千万,求“我”帮他解毒,让他睡个好觉。面对“一千万”的诱惑,“我”并没有做出自欺欺人的承诺,而是写了一篇名叫《良药》的小说送给他。“读完之后,他决定放弃所有的财产去做一个流浪汉。”而“我”再见到“风尘仆仆”从外地回来的李更时,感觉“他心里充满了阳光,像一股春风迎面向我吹来”。
《二十年后再相见》中的苏文举,是“我”大学同学,文学社的积极分子,这些年做生意发了财,“该有的什么都有了”,唯独“作家梦”没有实现。这次到深圳见面,想请“我”帮他写一部小说,出版时署上他的名字,回报“我”的是一百万元。他还打了个比方:“书就像一个孩子,虽然自己亲生的和不是自己新生的不一样,但你收养的孩子,在你名下,也是属于你的啊!只要你不说,别人谁会知道?”面对这样的诱惑,“却又是让我出卖自己”的行为,“我”断然拒绝。
《请让我再想一想》里的小丽,是清贫作家“我”的初恋。她离婚后分得了一大笔财产,“完全自由了”,想与“决心单身过一辈子”的“我”再续前缘,甚至可以不要名分,像二十年前那样做“我”的情人。只要“我”答应,她就飞到深圳,在海边买一套大房子和“我”一起生活,让“我”以后安心写作,不再为钱的事发愁。但是,“我”想起了当年她离开时,“上车后头也没有回”。“我”犹豫了,坚持着说:“让我再想一想。”
变化与坚守,是徐东小说里探寻和揭示的一对永恒的矛盾。评论家谢有顺在《一个城市的青年及其文学记忆》中指出:“徐东的写作温和、执着且不失真诚,他的小说在对芜杂生活的剖析和追问、对精神空间的探寻与守护中,呈现出形面下的荒诞感和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如何在日新月异、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对人生命运做出选择,作家徐东显然以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评判给出了理想化的指向:“即使你混得不是那么如意,将来一事无成,也不要出卖灵魂。”(《请帮我拿个主意》)“因为那种心生喜欢的力量是纯正的、美妙的,可以支撑着我们不断地、与众不同地写下去,也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加舒畅和快乐……”(《时闻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