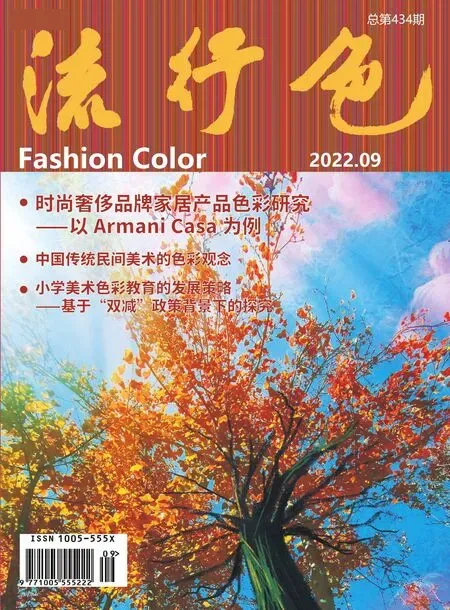宫苑丽人—明代仕女画对仇英绘画图像和色彩的套用
2022-11-04田雪婷
田雪婷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明代有大量仕女画产出,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宫女游园图》的色彩、服饰与内容都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宫春晓图》相似,先将二者对比分析,再将相似图式的其他作品加入对比,尝试回答作品间的借鉴关系,为还原当时书画作伪市场的历史情境提供帮助。
一、《宫女游园图》的笔墨、色彩和款识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宫女游园图》,绢本立轴,设色,高211.1厘米,宽101.3厘米。该图结合了仕女画、山水画和界画的元素,描绘了初春时节在一座藏匿于山水云雾间的宫殿内仕女们起舞奏乐、浇水赏花、弹琴下棋、游园嬉戏的场景。山水为青绿设色,宫殿红墙碧瓦,富丽堂皇,内容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宫春晓图》极为相似。在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展品信息里,这幅图被标记为元代佚名。图中左下方实际上是有盛懋题名的,但这也让人产生一系列的疑问。
首先是画作的笔墨风格问题。观盛懋流传有序的存世作品可知,盛懋画山无论是水墨还是设色作品,山顶多用浓淡不一的墨点作矾头,体现出画面的空间感,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水墨作品《秋山行旅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青绿作品《溪山清夏图》。而《宫女游园图》远景处的山全用极淡的墨色作矾头,现已几乎不可见,且山石的皴法更像是用墨层层晕染而成,也与盛懋其他作品中的山石面貌不同。
其次是色彩问题,盛懋的着色作品如《柳阴书屋图》和《江堤晚景图》的山石色彩更倾向于石绿为主,烘托青山翠绿的氛围;《宫女游园图》中背景处的陡石峭壁则以石青居多,宫殿檐顶和部分仕女服饰着石绿色,用色更为艳丽,与前二图明显不同。且画面中的仕女形象多鹅蛋脸,八字眉,身材削瘦,不似宋元仕女人物画风,更接近明代之后仕女形象瘦弱的特点。
最后是画面中的款识问题。《宫女游园图》左下方落款“盛懋子昭制”,落款下方钤印已不可辨识,但应为盛懋的自钤印章。画心上方正中钤有“康熙御览之宝”,左下角能辨认的还有一款“十洲”印,除此三印外,另有五印不能辨析。这幅图中落款的“盛懋子昭”字形与盛懋其他传世作品差异较大。此外关于仇英的“十洲”印,葫芦形的边框和“洲”字也与仇英被公认为真迹的印章相去甚远。
由上分析,有理由相信这幅《宫女游园图》既不为盛懋所作,也不为仇英所作。那么该作品出自什么时期?是否曾为台北藏《汉宫春晓图》作样本呢?求证这些问题,可对诸多仕女画作品间的临摹关系做出回答。
二、《汉宫春晓图》与《宫女游园图》图式比较
既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宫女游园图》(本节简称为《宫》图)不为元代盛懋所作,那此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宫春晓图》(本节简称为《汉》图)相比,哪一幅更早被创作呢?通过画面局部的细节对比,或许可以为观众揣测一二。
先看景观细节的刻画。将两幅图中的桃木景观作比较,可发现在桃木的枝干和苔点、莲花座石盆上的装饰、盆底足等各处,《汉》图都要比《宫》图精美许多,桃花颜色也更粉嫩,点明季节(图1)。

图 1 景观细节比较
接着就是人物间的呼应关系。从魏晋顾恺之时起就已确立了人物画的标准并千年沿袭。《论画》云:“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1]这段话明确提出了绘画时人物的位置要先确立好,不能轻易改变位置。画人物作揖,其对面必有能对应此动作的人,强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汉》图中有一对镜的组合,镜子后有一仕女望向屋外,院子中正有两人在交谈,人物动态呼应合理。而《宫》图中对镜组合后面的仕女同样望向屋外,在隔了若干台阶和一棵树的距离处有一组人物活动,显然空间是对应不上的,那屋中的仕女向外张望的动作是无意义的,看起来像是在套用图式。台阶处的建筑空间混乱也正好引出下一个不合理之处。
把视角拉远一些,在《宫》图右侧中部可以看到整个宫殿的构图方向为左侧视角构图,而院中的这处盆景,则为右侧视角,从建筑的空间来讲,这不太符合常理。可若把盆景的角度调过来,现处盆景右侧的三位仕女则无处安身,也许画家在此为了顾全情节的完整性,而牺牲了建筑空间的合理性。
顺着这条线索,再看屋内正在捣练和绣花的仕女们。“捣练”组合似乎取材于唐代传为张萱《捣练图》中的熨烫场景,后面绣花的仕女也和传为周昉的《挥扇仕女图》中刺绣一段非常相似。唐代《捣练图》中熨烫的仕女为四个人,《汉》图中也有四人。《宫》图看起来也应该为四人,但有熨烫部分的右侧有一处被建筑所遮挡,第四位持练的仕女没有刻画出来,熨烫的图式与唐代《捣练图》不同,反而与《汉》图一致。
如果以上信息还不足以论断,可以将视线移到《宫》图最下方的女乐组合(图2)。一座殿宇被树木和建筑遮挡后只剩下一块小空间,画家在这里刻画了三个形象:两位仕女各执乐器在一块地毯上配乐演奏,其后方桌前坐一位仕女右臂伏案,低眉垂首,似在出神或是打盹儿。过去的女乐形象组合可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乐图》[2],一般女乐类作品中只有奏乐或起舞的仕女,没有后面倚坐伏案的仕女,倚坐出神的仕女在这个奏乐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汉》图中也可发现一位仕女伏案而坐(图2),与《宫》图女乐组合中的仕女形象几乎一样,而《汉》图中这名仕女是出现在刺绣的组合中的。

图2 两幅图中的倚坐仕女
刺绣的图式可追溯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挥扇仕女图》。在刺绣的场景中,有一女子手执团扇,靠在绣棚上打瞌睡或是想心事,因此有学者将其定名为《倦绣图》。陆游曾云:“白乐天诗云‘倦倚绣床愁不动,缓垂绿带髻类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画为《倦绣图》。”[3]说明在早期刺绣的场景是根据诗歌描绘的,而绘画在最初就已经确立了刺绣场景的图式。
《汉》图中的女子倚靠绣棚打盹儿,团扇都掉落在一旁,与《挥扇仕女图》更为接近,更贴近传统刺绣的图式。《宫》图却将传统刺绣组合中的这名仕女,放置在了女乐组合中。掉落在一旁的团扇也说明,《宫》图可能在临摹时因为将仕女更改了位置,团扇就没有了用途,自然也就舍弃了。
由上推断,《宫》图应是晚于《汉》图的,其在创作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了《汉》图的内容与构图,再结合宋代的山水宫殿绘画,从而形成仿古意的新作品。
三、仿古色彩的其他画作比较分析
除以上二图外,在托名为仇英的作品中,许多画面内容的组成也都非常相似。明代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中有记载宜兴吴氏曾藏有南宋赵伯骕的《桃源图》长卷,“尝请仇实甫摹之,与真无异,其家酬以五十金,由是人间遂多传本,然精工不逮仇作矣。”[4]由是得知,仇英所作某幅作品流入市场后会被人大量仿制。某一画题的诸多伪作虽大体一致,但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一些其他原因,内容和题名可能有所更改。仔细比对多幅画作的内容可发现,这类仕女画中的人物形象或是完全复制,或是动态和人物组别不变,仅在服饰上稍加改动,再或是在原来的动态基础上,改变人物的某一部位,使其看起来像是一个新形象的创造。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托名仇英的伪作当中,仇英追随者的作品中也有如此情况。
除了台北藏《汉宫春晓图》,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幅传为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且内容又与台北藏《百美图》[5]一般无二,红色殿柱与围栏上的水墨装饰画颜色都一样,且多用红色作内衫,只有服饰配色稍有改变。那么,画家故意将服饰作出不同的颜色,目的就不在于制作赝品了,而是在创作之初就将作品更改颜色或者拼凑图式,以定为不同原作的名字。这也是明代仕女画命名混乱的原因之一。
在色彩方面比较,克利夫兰藏《汉宫春晓图》和台北藏《汉宫春晓图》大不相同。克利夫兰藏图中大面积使用朱红,石青等色,画面主体部分的宫殿柱体用红色,人物服饰多用青色,假山也用石青石绿设色,整体颜色颇为艳丽。台北藏图用朱红作人物衣饰,栏杆和帘帐处也用朱红点色,使画面更有唐代人物仕女画之风,颇有古意,假山除青色外,更多用绛色填充,整体更趋于素雅。
以上作品中人物形象相似度颇高。由于台北藏《百美图》和克利夫兰藏《汉宫春晓图》在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的人物组合相似自然不用多说。这两幅图在接近画尾处的院子里都有一组赏花的仕女四人,两站立相谈,两弯腰浇水。这跟台北藏《汉宫春晓图》中第一处宫闱右侧的院子中浇水的四人组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克利夫兰藏《汉宫春晓图》中的人物服饰和发式更具明代特点,而台北藏《汉宫春晓图》的服饰和发式明显与流传下来的唐代仕女画中的形象更为接近。
台北藏《汉宫春晓图》第二个半开放厅与第三个半开放厅之间有一组仕女似在斗草,有四人坐在地上围成一个圈,旁边站立两个仕女,其中一人的胳膊搭在另外一人的肩上;克利夫兰藏《汉宫春晓图》在卷首刚进宫墙处,也有一组正在斗草的人物,有三人坐在地上,旁边有同样站有两个仕女,后面的仕女只是用手扶着前面仕女的肩膀。这两幅画面相同的是旁边都站有两个仕女,总体的布局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人物动态不同,组合人数不同,旁边的仕女站立的角度也不同。从两幅图的这组人物来比较,画家似乎并不是完全的借鉴。克利夫兰藏《汉宫春晓图》左下角的这个仕女腿部姿势怪异,衣纹没有清楚地交代出人物的动态,侧脸的刻画也较为失真,说明了仅凭画家自己创作,刻画人物水平并不高。站立的两仕女角度和动态虽不同,但刻画又比较和谐,动态合理,人物较为生动,实在和坐在地上的仕女有反差,因此画家也许并不是直接借鉴了台北《汉宫春晓图》,或者并不止借鉴了这一幅图。极有可能在这种类型的创作中,有大量类似人物图组的出现,每次临摹复制都可能会改变其中的某个动态或人物搭配,多次之后人物的动态不尽相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传为仇英的《西厢记》册页中的第一幅,左侧的红娘形象腰间别着团扇,背对画面向前走。这与台北藏《汉宫春晓图》第二个半开放厅前抬步上台阶的仕女在形象上也非常相似。不排除当时仕女的一般真实形象为此,但也有更多的可能是这些形象都出自画家们的记忆范式。他们在练习的时候都是用这样的形象来表现,在创作完整画作的时候自然会将其搭配起来。
结语
明末仕女题材的作品众多,想要从中理清作品间的关系,不仅要大量地观看,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不受作品名称的局限。通过上文的对比发现,画家很有可能将某些仕女画中的内容简单归类为若干图式,无论画什么内容,只要是仕女画的题材,都可以从这些图式中去选择、拼凑、重组,或者是略微改动以适应新的画题和场景。不过这种行为,制作者并不是固执地追求对大师作品以假乱真式的作伪,而是作为底层阶级普遍的兴趣交流,那么从研究的角度,或许可以摒弃精英主义的视角,不仅仅围绕真伪来定义作品,更多地关注画工的艺术制作以及这些作品年代和优劣等其它相关问题也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