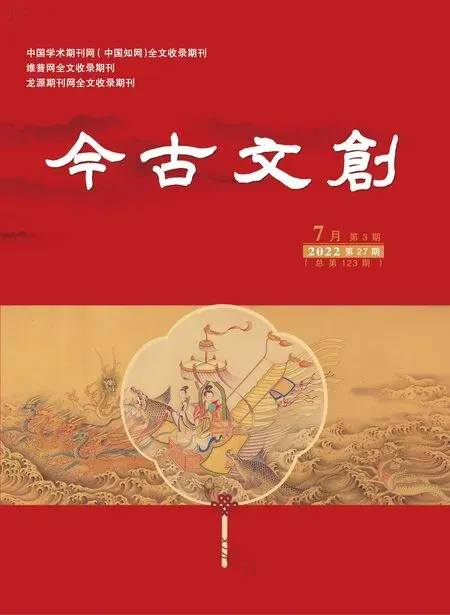浅析《古船》中的家族叙事以及与启蒙叙事的交织
2022-11-01◎杨丹
◎杨 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家族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亲属集团,对于社会而言起到稳定发展的作用,对于个体而言也承载着亲情伦理。在中国,作为大能扩延至国家和社区、小能浓缩到个人家庭的“家族”,它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中介组织。宏观来看,“家庭本位”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家国同构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体的基本构成形式;微观而言,家族观念以血缘为信赖基础延续至今,家族内部的各成员都对其承担管理责任并受其管辖。又因为家族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家族书写在我国文学创作中始终是个永恒的话题。
早期的作品继承了前代作品中家族叙事方式的文化传统,对于家庭生活解读与亲情伦理的诠释又迈上了新的台阶。当代家族小说也在文化启蒙的语境中,在多元文化的探索中达到了丰满。“80年代长篇小说的主题是丰富的,但基本上是启蒙叙事的不同展开。”
《古船》这部小说弥漫着浓厚的家族意识,本文将深度解构作品中的家族叙事,以解读家族叙事的传统性和现代化特点,以及文本中启蒙叙事与家族叙事有机交织的灵魂。
一、家族叙事的传统性
家族延续以血缘为纽带,在宗族制度的深远影响下,传统家族的凝聚力团结性都是现代社会所无法匹敌的,而且这种带有血缘纽带的神秘力量则可以支配着家族的个体。小说《古船》具有中国传统的以“家”隐喻为“国”的家庭叙事特点,它随着家族的历史文化发展与演变,以冷静而切实的口吻书写了一个关于洼狸镇三大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兴衰故事,也重点讲述了这个曾经繁荣辉煌的小城是怎样逐步走向分崩离析的。
故事发生在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小城——洼狸镇上,这里的灵魂从家族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又被宗族精神所灌溉。镇上的人们祖祖辈辈在同一片天空下劳动生长,多年不变的环境古朴而又封闭,传统的家族观念是其延续的滥觞,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封建式族长专制——老赵家的族长四爷爷赵炳。小说中,赵炳凭借自己最高的辈分而非能力或是年龄,成了赵家的实际掌权者,也成了洼狸镇的领袖。作为长者,“赵炳是融革命领导与乡村族长、集体利益与家族意志于一体的专制家长”。小镇上的人对他有种莫名的敬畏与服从。比如小说中地震了,人们惊慌失措,赵炳说地震不会再来了,于是大家不再害怕,当即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待了一夜;他若一生病,全城都为他倒下了。洼狸镇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受到封建宗法家族观念的影响,即使新中国成立,镇子上拥有了新的领导新的指挥者,四爷爷赵炳依然享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与镇长共同议事。
在传统家族叙事视野中,家族的基业与声望是家族绵延不绝的物质与精神基础。所以当家族受损时,每一个家族个体都理应奋不顾身为家族奉献。隋见素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长大的,也造就了他浓厚的传统家族复兴的使命感。曾经的隋家是洼狸镇上首屈一指的大户,家族产业庞大,有最大的粉丝工厂,还在各地开了粉庄钱庄,并且由于家主隋迎之是公认的开明绅士,家族名声显赫。隋见素有过如此富裕的童年,自然在家族衰败后心有不甘。隋见素深受传统家族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对于隋家的家业与声望有着很深的执念,家族复仇的信念支撑着他,使他一次又一次为了光宗耀祖而争夺家业争夺粉丝厂。虽然隋见素的举动有些极端与不妥,但他是为了家族的重新辉煌而奔走,他心中一直怀着家族复兴之梦。立足于传统家族意识与宗法观念,隋见素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理解的。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家族个体为了家族复兴而付出的努力与恒心,符合了传统的家族叙事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统农村社会中家族统治的政治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后来成立的农村生产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构人们内心的宗法家族观念。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家”已内化为人生理想的终极和一种集体无意识,家族中心主义与近两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神话般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所有价值观念的基点。正是基于此基点,族长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统治权能够与家族中心主义融合并延续。而又源于血缘纽带连接支撑的家族内部使得洼狸镇的每一个个体都会产生血缘使命感,以此延续发展家族观念。
二、家族叙事的现代性
作者张炜通过《古船》呈现出小城洼狸镇的盛衰史,以其独有的生命体悟解读家族阐释苦难,其中特有的现代意识更是给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生机。他在《创作随笔三题》中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忠于他的感情、思索,忠于他所熟悉的一切”“清醒地自觉地寻找与这个世界对话的角度和立足点,使自己与面前的这个世界构成某种关系”。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他笔下的家族可能已经跳出了体制意义上的家族,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家族,即不同的家族各有其血缘性与一贯性,在现代性视野下亦可解读出寄托的人文情怀与道理理想。
赵家的命运是与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其在运动中充当了历史的打手从而改变了家族的弱势地位。赵炳从族长到整个镇子上的灵魂人物,赵多多也从无人问津的小混混到备受尊重的团长,身份地位的陡然变化刺激并放大了人性中的残忍与暴虐。赵炳以施恩者的姿态对受害者的零星宽容也被美化,人们因此对他感恩戴德,为其披上了虚伪华丽的外衣。然而这样的感恩并不能满足赵炳心中无尽的欲望,他想要的是人们麻痹思想与情感,变成一味地服从,这其实是人性变相的压抑,正如隋含章与赵炳扭曲的性关系。在经济转型时期,赵家象征为个体意识觉醒的障碍,终究会被历史淘汰。
李家的命运始终离不开科技,李其生和李知常都是洼狸镇为数不多的研究科技相信科技的人。小说中机械化的科技让镇上的人感到惊慌,李知常不知疲惫地为粉丝厂设计“变速轮”,即使并不被身边人理解,但他心中科技的信念支撑着他,他认为自己就是注定做这个事的人。就像小说中李知常念叨的“不能停,都不能停——不能停住机械化”,现代性科技力量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入侵洼狸镇,李家只是被历史选中的使者,历史的车轮始终会向前驶去,那些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的人终究会被历史风尘掩埋,留下的是时代的前沿者与开拓者。小说中,李家几代人相继追随科学的身影是洼狸镇现代化的风景,也成就了其家族开拓创新的家族精神,成为使洼狸镇上的民众摆脱传统重压的希望。
隋家的关键词应该是苦难。作品中父亲的死去和继母茴子的服毒自杀,让隋抱朴、隋含章兄妹陷入了忏悔与赎罪的深渊,他们继承了家族留下的苦难,继而在内心自我压抑忏悔。相较而言,次子隋见素更多是将苦难转化为家族复兴的动力,但动力中承载着难以排解的压力与沉重的负担。隋家三兄妹就在这样的苦难中痛苦挣扎着,展现出那个时代下传统家族中的个体在自我认知与家族意识冲突矛盾时的挣扎与现代意识的觉醒。
作者笔下的隋含章更多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当家族命运的历史责任压在她的肩上时,她选择肩负起这一切,忍受着心理与生理、灵与肉分离的煎熬,毅然投身赵炳怀抱,默默为家族利益献身。她希望通过牺牲自我来保卫隋家,即使自己拥有的只有年轻的肉体,但她依然勇敢地站在了哥哥们的身前,以守卫者的姿态承受着赵炳的凌辱。隋含章虽然到最后都未能打破赵炳的“国度”,但她依旧举起复仇的剪刀公开宣告了自己不屈的抗争和对赵炳的决绝斩断,同时也揭露了赵炳的无耻行径,为洼狸镇的和平安宁贡献了力量。
“苦难在现代以来的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中作为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有关。基督教把人生来就视为有罪,因此把现世生活看成赎罪。”作者将“原罪”的注解体现在隋抱朴的身上,在隋抱朴心中,自己家族曾经垄断财富的行为是罪恶的,这是导致穷困人民痛苦的原因,所以他有意识地将自我置于精神的苦痛深渊中惩罚自己。“赎罪”是隋抱朴生活的全部,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人性的欲望被抑制,故而隋抱朴的苦难主要在于其精神世界中欲望与理性的矛盾冲突。隋抱朴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审判与忏悔,他通过三本书籍找到了自我思想的出口,也开始理解新型国家政权的执政思想。在了解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理论“消灭私有制”后,隋抱朴意识到粉丝厂并不是隋家独有的,也不是属于赵家的,而应该归属于人民大众,属于洼狸镇的每一个劳动个体。所以他每一次都尽心尽力地解决粉丝厂“倒缸”问题,帮助其渡过难关却不求回报,在他看来,隋家的家业与声望都不是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原罪与负担。然而隋抱朴是传统家族的长子,是理应承担起复兴家族的使命的,但他却选择了放手与忏悔。思想与身份立场的矛盾也彰显了文本家族叙事的现代性特征。隋抱朴最终意识到人类应该用人性的“爱”与“善”逐渐消除或减弱人性的“恶”,体现出被苦难打压的人在逆境中重生从而摆脱束缚与桎梏的顽强。
而隋家除了长子隋抱朴的现代性思想与行为,另外叔侄俩的出走也为文本现代性叙事增添了亮色。隋不召在年幼时便与大哥隋迎之不同,他不愿用功读书,而是喜欢在码头上闲逛,表现出其内里反叛与另类的一面。面对父亲隋恒德的管教与约束,隋不召依然不屑一顾,死死盯住父亲。可以说,隋不召的“出走”意识从小就深藏心底。隋不召是作者有意识塑造的现代生命的典范。一方面,他与洼狸镇长期遵循的传统道德相违背,形象放荡不羁;另一方面,他对人类力量和智慧始终保持愿景,对于航海事业的执着便可以看出。
与隋不召从小萌发的叛逆不同,隋见素的反叛主要源于家族的衰败与自己多年心血的付之东流。他年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家道中落后便积极承担家族复兴的使命,倾注毕生心血,一心想从赵家手里夺回原本属于隋家的粉丝厂,并试图破坏赵家的管理与经营,无奈以失败告终,最后选择了出走。隋见素的出走行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同时预示着他在寻找新的生机。隋见素立足于家族与现代的交汇点,他面对家族曾经的辉煌以及现在的衰败,难以与现实和解对话,选择出走漂泊人生,期望走向自己的梦想圣地。“出走”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行动元素,是对个体生命完整性的追求,是对传统家族观念的反叛与离弃,展现了年轻人在追求理想时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启蒙叙事与家族叙事有机交织
总体而言,小说采用的是全知叙事视角即零视角,但叙事者“不但置身事外,且亦置心事外。他仿佛站在一个山冈上,对脚下争斗着的人物一无偏护。他犀利的目光直射历史和人物的内心深处,并客观冷静地讲述着他的发现。”在张炜的笔下,隋家不再是那种剥削人民、道德堕落的典型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有文化有节操的家族。一家之主隋迎之是公认的开明绅士,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子隋抱仆的性格,隋抱仆从父亲那里承袭下忧患意识与原罪意识,以至于隋抱仆前期被强烈的负罪感裹挟,处于压抑与忏悔中,后期在精神世界中获得解放。
对于赵家这个搭上了时代顺风车的家族,叙述者并没有因其农民起家为革命阶级的代表而一味美化其形象,而是揭露出由于地位身份巨变而膨胀的家族内在的狭隘复仇意识。小说并没有把四爷爷赵炳塑造成脸谱化的坏人,他并不是扁平人物,叙述者以旁观者的态度展现出他圣洁外表下的自我放纵以及对正义的扭曲。他作为长辈,却长期以干爹的身份在隋家小姐隋含章身上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反观隋抱仆、隋见素这两个曾经的贵族子弟,失去了曾经的富裕生活,沦落到了压抑人性、自我遏制的地步。随着社会发展历史变革,经济改革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无意间又为隋家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家族个体的命运始终与时代洪流息息相关。
面对当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变革,不可否认的是家族主义对人们根深蒂固的影响,革命者正义的行为背后可能含有一定的家族复仇动机。张炜在《古船》中从人道主义立场与人性关怀的角度重新审视农民革命,他发现,一方面农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合理性与推翻封建政权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他们浓厚的家族观念与家族复仇的强烈欲望则暴露出兽性的泛滥,家族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人们行为产生巨大影响,阶级意识与家族观念交织在一起造成历史与人性的悲剧。即使封建大家庭在历史中瓦解,但人们的家族观念与家族意识依然存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集团对个体、家庭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与感召力,让思想还未解放的人们不自觉遵从。人们难以脱离家族观念,导致几十年都没有走出宗族集团统治以及族长统治的传统。尽管工厂改变了管理制度条例,但家族主义家族观念生长的温床已存在多年,如果没有成功启蒙农民的思想,实现其个体意识觉醒,那么改革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个叙事者用一双悲天悯人的眼睛俯视着人间的苦难,这双眼睛绝不是冷漠的,而是布满血丝的,从眼睛里放射出的目光,有着灼人的热量,这双眼睛里有着忧愁,更有恐惧和震惊……这个叙事者用一双悲天悯人的语调诉说着人间苦难,这种诉说也绝不是冷漠的,而是同时包含着这样的质问:人间为什么会是这样?人间为什么要有这样多的苦难?人对人为什么会如此残忍?”
在《古船》中,叙述者的现代性启蒙立场使文本内涵超脱于家族恩怨情仇,而在传统乡村家族复兴与复仇中开阔视野进行探究。叙述者立足于人道主义,将洼狸镇上家族的苦难上升到民族的苦难,广阔的悲悯情怀增添了文本的现实内蕴。同时,作者的现代化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情怀,充满了人性的同情和怜悯,使小说具有了难得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