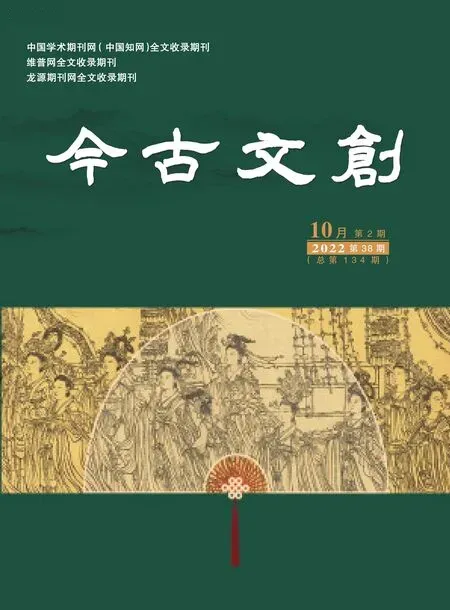论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中的寻找主题
2022-11-01白国芳
◎白国芳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00)
一、追寻身与心的栖居
作为80后新锐作家,孙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文学创作与探索。她的创作实绩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其作品主要包括“痛感三部曲”《疼》《盐》《裂》以及《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以鸟兽之名》等。以《鸟兽之名》是孙频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收录了《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天物墟》三部相互联系、相互指涉的中篇。这是孙频创作的一个进阶,“孙频以《以鸟兽之名》完成了对叙事形态与审美风格的同步建构,有效地充实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诗学。”同时,《以鸟兽之名》这部集子也充盈着丰富的主题意蕴。三部作品都有共同的返乡模式,叙述者因为不同的原因,从现代都市返回山林之中,开启了精神的探索与历险之旅。从表面上看,《以鸟兽之名》中的李建新是在寻找杜迎春凶杀案的凶手,《骑白马者》中的叙述者“我”是在寻找田利生,而《天物墟》中的刘永钧则是返回瓷窑追寻父亲留下的痕迹。但是,文本深层主题则在于作家对于现代性的多元思考,通过叙述者的行走与寻找历程,孙频探讨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实现身心的栖居,如何追忆失落的文明,以及怎样确定个体存在的意义。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之一。因此,本文拟从这三个层面对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中的主题意蕴进行分析,希望能从“寻找”的层面上挖掘这三部中篇的现实指向与艺术魅力,更好地理解这三部作品的深层意义。
首先是对身与心栖居的追寻,这是小说主题的第一个层面。孙频通过描摹山民这一特殊群体的肖像,书写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严肃地提出了身体与心灵的归宿问题。在《以鸟兽之名》中,游小龙及其村民从大足底村整村迁移到了平原的移民小区中,村民们被迫从原来的大山里剥离,他们无法改变原来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身心得不到舒展。虽然居住在楼房中,但他们在周围开垦了菜地,开设了猪圈羊圈,甚至搭建了简易的厕所。大山文化带给他们的习惯依然顽强地留存着,他们未曾真正融进都市里,思想上也无法实现对于平原地区的认同。这是平原文化与山地文化之间的冲击,也是现代化进程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破坏,处于二者夹缝中的山民们无法得到身体和心灵的安居,所以他们一直在用奇异的方式维护自我,比如聚集成小型的带有派对性质的“饭市”等,以期打破空间带给他们的圈禁,一定程度上缓解内心的焦躁不安。
而游小龙虽然通过教育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但在文化涵化过程中属于内在冲突阶段,当他慢慢了解了城市之后,仍然没有办法调和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因此面临着精神的折磨与身份的撕扯。所以一方面,他通过写作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对阳关山进行指认及其命名,书写自己对于阳关山的记忆,同时也在反复地确证阳关山与自我的关联。在游小龙眼中,阳关山是类似于宗教一样的庇护所。另一方面,游小龙的自律、慎独等道德要求与对理想人格的向往也是在不断掩盖自己的过往,他期望从原来的身份中生长出新的灵魂,彻底地融入都市。但最后的结果是,家乡也无法回去,都市又不能真正地接纳他,所以这个人物形象一直处于一种认同焦虑之中,无法对自己做出一个确切的定位。而游小龙的双胞胎弟弟游小虎与游小龙属于一体两面,孙频为我们展现了个体的两种境遇。游小虎下山之后的堕落也是游小龙可能面临的遭遇,更是迁徙到平原的村民随时可能遭受到的处境。
在谈到为什么塑造这类形象时,孙频坦言“我并不是在大山里长大的,之所以关注到这个群体,是因为注意到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山民纷纷迁徙下山,离开世代生活并有着深深情感依赖的大山,来到平原上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当他们迁徙下山之后,我看到的他们与山中已是两样,他们显得迷茫、焦虑,想拥有更丰富的物质,却苦于找不到工作,他们总在言谈之间提到大山,说山里如何好如何好,因为那是他们的故乡和精神家园,但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孙频展现了城市移民化浪潮中个体与世代栖居地的剥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痛苦与无奈。个体失去了处所意识,丧失了归属感与依赖感,他们无法体验到自己和所处环境的关联,无法妥善安放自己的身体与灵魂。或者说,其身体与空间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或许最终会被环境变得同质化。这并不仅仅是山民们的精神忧虑,同时也是现代人的处境。当现代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时,人们不仅失去了栖居的家园,同时也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个体处于无所皈依的浮游状态,心灵是破碎的、虚无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频展现了对于身心栖居的追问与寻找,她看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人的痛苦和牺牲,挣扎与焦虑。作家关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心灵与肉体的停憩,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她锋利地揭露了家园的丧失,这体现出孙频强烈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意识。
二、对失落文明的追寻
在对身心栖居发出问索的同时,孙频也向失落的文明投去了深情的关注。在《文明的微光》中,孙频回忆道:“这些年颠沛流离不断迁徙的生活给我带来的收获之一就是对‘文明’二字的重新认识。”从山西调到江苏的经历使她感受到了流动和迁徙所带来的异质性文化体验,同时也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眼界来看待不同的文化。对文明的多样性理解丰富了作家的认识并折射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因而,在《以鸟兽之名》小说集中,我们特别明显地感受到了作家对失落文明的抚摸与惋惜,也意识到了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冲击与挤压。
在游小龙所写的关于阳关山的文字中,提到了方言中所蕴含的文明。“我们的语言里其实残留着几千年前的远古文明,夹杂着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我们的语言像大山里的那些沉积岩,一层一层累积下来,又经受了几百万年里地壳运动的断裂,低谷变成高山,高山化成海底,它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文明本身。”而这些韵味十足的方言也在被慢慢地改造,甚至走出大山的游小龙都要有意识地纠正自己的说话习惯,减少由此带来的歧视。可想而知,一旦这些方言被彻底同化,就意味着其所蕴含的文明的断层和割裂。
在文本中,《天物墟》中的磁窑及其周边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由于地处偏远,比较封闭,文物古迹得以较完整地保存,甚至“连村里的厕所、猪圈、羊圈都是用各种陶罐砌起来的。路边随处可见各种陶器和瓷器的碎片”。刘永钧协助老元实地考察并对文物的历史进行整理,其实就是在抢救逐渐消失的历史文明。而一辈子没有出过阳关山的老元则是文明守护者的化身,他只注重文物本身的价值,并不以金钱来对其进行衡量。正是因为像老元这类人的坚守,古老村落里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不会被时间吞噬掉,它们得以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或许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这些逐渐废弃的村落并不起眼,有朝一日甚至会变为废墟。但在作家看来,古老大山里的村落隐藏着文明演进的痕迹,走进这些苍茫辽阔的地方,也在一定程度上接通了文化的气脉,感受到了历史的深度与厚度。但是所有的文明都会成为过去,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文明无形之中也在经历着更迭。正如小说中所展示的那样,大足底村和武元诚被淹没在湖水下面,文明正在慢慢走向一种失落。
除此之外,读者还会注意到《骑白马者》中的听泉山庄,建立在木材厂上的听泉山庄是小说中一个核心的意象。尽管听泉山庄已经荒芜,但它的设计构思带有非常明显的现代特征,一如现在所有的游乐园与度假胜地一般。在听泉山庄中,有江南的景致、微缩的世界园、魔幻的史前园以及五颜六色的游乐园。而令读者惊异的是,“就在这游乐园里,竟然还有一块整齐干净的莜麦地,边缘清晰,像一块突然飞过来的绿毯子铺在那里。”这块莜麦地属于杏坛村的老哥俩,它的存在仿佛是一种无言的抵抗,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拒斥。周边的土地当初全都被征走了,仅留下这么一小块耕地,这是现代化进程落在这里的一个投影,也是现代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侵占。
但是对于失落的文明,对于文明与社会的关系,作家并没有在文本中进行深入探讨,孙频只是客观展现了传统文明生态的现状,并把这一问题留待给了读者思考与讨论。因为这并不是某一地存在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问题的一个缩影,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值得所有人深思了。
三、对主体存在意义的追寻
这三部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追问与思索。孙频在文本中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个体存在性焦虑。这三部作品中都有一个返乡者的设置,返乡者同时也是小说的叙述者,通过返乡者的行走与寻找、邂逅与探险,最终其主体存在的意义得到了确证,战栗的灵魂得到了一种庇护与治愈。
《骑白马者》中的叙述者“我”返回老家,骑着一辆摩托车在阳关山里穿梭。文本中多次提到,“我”试图在寻找田利生,这个建造听泉山庄的始作俑者。在寻找的过程中,叙述者邂逅了山水卷的老井,葫芦村的刘天龙,杏坛村的老哥俩,以及花前村的田中柱。这些人物都与田利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最后,“我”重新投资修建废弃已久的听泉山庄,做完了田利生没有完成的工作。可以说,对田利生的寻找指向的是对真正自我的逐渐逼近。因为叙述者“我”和田利生呈现一种镜像关系,这在文本中已有多次暗示。“在那么一两个瞬间里,他从人群中猛地回过头来,我却忽然看到了一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我惊骇地发现,我已经变成了他,或者,是他变成了我。”“我”与田利生都是从都市折返的飘零者,而修建听泉山庄这一共同的象征性行为却意外使得我们获得了心灵的释放。虽然花光了全部积蓄,并且明确知道听泉山庄不久后仍会关业。但现代生活对金钱的异化与对精神的折磨在这里得到了纾解。个体的生存状态得到了平衡,人性实现了自由发展,存在本身的意义因而得以彰显。小说中在都市里骑白马的流浪汉不正是对“我”以及田利生生存处境的一种隐喻吗?骑白马的流浪汉一无所有,自觉游离于都市之外。叙述者“我”最后选择留在山上安然度日,却意外地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天物墟中的刘永钧返回磁窑,发现了父亲存在过的痕迹,并在意外的情况下变成了文物专家老元的助手。在佛罗汉村帮助老元整理文物资料的过程中,刘永钧感到自己被这个辽远的空间所吸纳,他把精神寄托放在了文物身上,同时也重拾了自己的尊严与自信,寻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更为难得的是,他终于理解了父亲坚守在磁窑的原因,与父亲的隔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返乡之旅使刘永钧在多个层面上找到了个体存在的意义与根源。
现代性处境使每个主体都处于一种漂泊无依的状态之中,所以寻找存在的方式和存在的立足点便变得尤为重要。小说中的人物通过重返山林与自然,疏解了现代性焦虑,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与调节。主体最大限度地意识到了自己应该如何调节恢复生命的完满状态。孙频关注时代沉浮中普通人的命运和心理,体察现代个体的生存处境与存在性焦虑,通过对存在的拷问,小说的思想意蕴得到了升华,文本的深度也得到了增强。
四、结语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个体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作家孙频在小说集《以鸟兽之名》中,抱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忧虑,对现代化进程做出深刻反思。小说从寻找的主题出发,最终指向了存在这个话题。孙频在对身心栖居的追寻、失落的文明的追寻及主体存在意义的追寻三个主题层面上,为我们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文本中寄寓了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在对多层次的主题的分析与探讨中,小说的现实启示意义与思想魅力也得以彰显。
注释:
①刘永春:《深入自我与返回远方——评孙频小说集〈以鸟兽之名〉》,《名作欣赏》2021年31期,第100页-102页。
②孙频:《关于山民的前世今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21年6期,第72页-73页。
③孙频:《文明的微光》,《江南》2021年2期,第23页-24页。
④孙频:《以鸟兽之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⑤孙频:《以鸟兽之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0页。
⑥孙频:《以鸟兽之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
⑦孙频:《以鸟兽之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