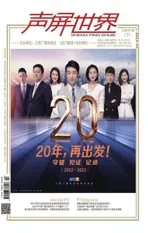2021年中国广播电视研究十个关键词(下)
2022-10-31王哲平殷梦婷
□王哲平 殷梦婷
跨媒介叙事
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中提出的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概念,是指故事系统性地散布于多个平台,各个平台以各自擅长的方式做出独特的贡献。目前,成功的跨媒介叙事案例不胜枚举,如美国漫威公司通过其漫画作品塑造的庞大、独立的世界观体系,国内网易游戏公司以《阴阳师》为核心文本打造了一系列泛生于不同媒介形态的生态产业,等等。
不同性质的媒介具有各自不同的“叙事属性”,它们能够跨越自身的表现性进入到另一种媒介擅长表现的状态,跨媒介叙事是跨越或超出自身作品及构成媒介的本位,去创造出他种文艺作品特质的叙事形式。故事世界是跨媒介叙事的根基,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概念的根本,它通过核心世界观和核心文本构建起整个叙事网络,以保持创作的连贯和秩序。
跨媒体叙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转型,也是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文化转型,不同媒体发挥自身优势互相补充,消费者自由流动,积极地参与其中。有学者认为跨媒介的故事世界建构是基于一种基于互文性的心理模型建构,存在于不同媒介中的不同故事相互关联而互不冲突,并共同创造出新的意义;构建“故事世界”的基础是从属于同一世界的不同故事、不同文本之间的相关性,它强调共同建构。
跨媒介叙事理论契合了IP概念的内涵特征,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深刻演变,网络IP剧蓬勃兴起,国内的网络小说故事世界相对完备,粉丝规模稳定,题材丰富,创作空间大,有条件建立多种媒介叙事体系,包括电视剧、网络社交媒体、游戏等。有学者认为在跨媒介叙事运作下的IP开发,应该立足于本土文化IP,打造内容的合作著述,多媒体协作控制叙事节奏,并加强消费者参与程度,发掘IP再造潜力。
随着媒介平台的扩大,跨媒介叙事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读者在文本创作过程中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者的心境,导致部分作品同质化、低幼化、肤浅浮夸,从而可能导致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版权问题也成为制约跨媒介叙事的发展瓶颈,由于传统的市场模式和企业模式难以和跨媒介叙事的新型创作和传播行为相衔接,版权冲突在所难免,跨媒介叙事因此成为了不同媒介文化的冲突地带。有学者指出,只有创新版权市场制度并辅之以配套的版权法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化解问题。
广播融媒
根据赛立信数据咨询公司发布的行业报告,2019—2021年我国广播接触率继续保持2018年(59%)的水平,历经百年历史的广播媒体已形成了新的市场,广播正以大音频的新生态活跃在新的传播格局中,创造新的听觉价值。
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度开展,广播融媒赛道百花齐放。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持续突破,声音与移动互联的融合也进一步升级,视听传播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传播平台越来越多元化,听众年轻化、终端智能化、传播场景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我国广播媒体融合向全连接、全移动发展,进入了提质提效、存量听众的深耕时代。为适应市场化需要,广播电台的经营手段、盈利方式、营销模式正不断创新,基于城市基因、打造本土生活圈,通过线上线下整合营销提高影响,进行跨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在融媒产品不断涌现的今天,实现广播融媒的可持续发展要时刻警惕形式大于内容,保留主流媒体底色,坚守媒体立场,发挥媒体的舆论引领功能。疫情期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推出的特别节目《爱在春天,守望同行》值得借鉴,节目通过多渠道全媒体呈现,聚焦全国及省内疫情,传播社会正能量,借助智能手段让“乡村大喇叭”通过多媒体渠道实现了“跨屏延伸”,同时提高防控疫情宣传的效率,突出了主流媒体引导力、公信力。
在后广播时代,面对传统媒体信息分发渠道被改变,数据化驱动、智慧化赋能、流媒体运维或可成为广播电台向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未来进路。通过充分挖掘用户资源、节目资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流媒体等技术形成多元产业链,凸显流媒体的强大运维功能,将主播经济、粉丝经济、节目IP等关键要素进行对接,满足用户需求的阅听逻辑,实现媒体商业变现的市场逻辑。近两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动顺应未来媒体环境发展趋势,提前布局“下一代广播”模式——“云听”,借助AI、广播互动等技术,发挥内容优势、平台优势打造了多场景覆盖的“云听出品”,成功为广播转型升级赋能。
社交化广播
社交化广播是广播向新媒体转型发展继网络化、移动化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以广播向社交媒体拓展为主,形成了“广播电台+微信+微博+……”模式。这一阶段的广播融入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之中,以依附于其他应用的音频服务为特征,在用户的社交服务中呈现为社交资讯为主、音频消费为辅的伴随式消费。
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基础是基于社交关系的用户之间的相互关注、频繁互动以及内容生产。从Web1.0时代诞生的银河台、国际在线(CRI Online)、21世纪网络电台等,Web2.0时代焕发活力的豆瓣电台、微电台等,到Web3.0时代的各类音频应用平台,如喜马拉雅、荔枝FM等网络电台,广播媒体正朝着强互动、重社交的方向演进。传统广电媒体在社交化上进行发力,央广视讯2016年初建成的“央广云电台”即是典型案例,它创造性地为每一档栏目打造专属社区,供听众粉丝驻留,同时还建设了包括播放弹幕、互动评论、社交分享等深度互动功能模块,除了在用户运营的端口发力,新时代的广播媒体在内容生产模式上也日益走向了“用户主体”及“社交互动”的新格局。
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越来越多广播媒体开启APP端运营,这一融合发展赋予了广播更多社交化趋势,其音频节目可以轻松地依托社交平台,在更大范围与更短时间内进行分享式传播。用户对自己喜欢的音频节目,可以在第一时间内通过微博、微信等主流社交平台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从而大大拓宽了音频节目的传播渠道,同时,音频节目和广播类APP也可以趁机吸纳更多的听众。此外,节目主播也可以利用社交平台集聚听众,拉近主播与听众的距离,增加听众的忠实度。同时,利用社交平台,用户能够更方便地实现反馈,主播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反馈进行了解并回复,从而大大提高音频节目的质量。
社交媒体的高渗透和扩张方式为广播带来了新的机遇,未来,跨媒介联动带来声音社交的更多可能,如广播与电视台声音节目融合,将有助于广播在内容上创新社交关系。广播在发展过程中积极运用互联网社交思维和新媒介技术显得尤为重要,需要以社交为“切口”,从内容嵌入到渠道嵌入再到日常生活场景嵌入,搭建具有聚合力和强大传播力的社交平台,不断夯实自身媒体地位。
慢直播
慢直播是借助直播设备对实景进行超长时间的实时记录并原生态呈现的一种直播形态,体现出原生态记录、超时长直播、陪伴与参与的传播特点。可以说,“慢直播”的镜头无剪辑、无后期制作与加工,原生态展现事物发展,为受众提供真实的“现场感”。
慢直播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一部名叫《沉睡》的慢电影实时记录了诗人约翰·乔尔诺历时5个多小时的睡眠过程。2013年,央视网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开办IPANDA熊猫频道,对大熊猫的生活进行24小时直播,在国外有一大批收视群体和粉丝。此后,慢直播被广泛运用于自然风光、旅游、文化等非事件性宣传中。青海、云南、广州等地通过慢直播展示当地的自然、人文风光,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诞生了如《青海湖鸟岛》慢直播、《博鳌论坛会场外景》慢直播、《上海这一刻:外滩》慢直播、《花开中国》慢直播、《中欧班列》慢直播等优秀案例,实现了城市宣传营销与媒体影响力提升的双赢。
有学者提出慢直播满足三类受众需求:一是满足了受众休闲审美需求的观光类慢直播,如“云赏花”“云观鸟”;二是满足受众伴随式社交需求的记录类慢直播,如“云养猫”“云种菜”;三是受众参与的关于重大主题事件的信息类慢直播,如“云监工”“云阅兵”。慢直播通过实时的长时间段直播给予人们陪伴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情感需求。
在共同事件前,慢直播能够让相隔千里的观众之间实现虚拟空间的身体聚集,建立起鲜明的关注焦点和情感连带,持续引起集体式的情感体验,构成互动仪式,因此,慢直播也被赋予了社会整合的功能。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视频对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引起了亿万网络监工围观,诞生了一种新的舆论监督模式——“云监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的超级舆论场,彰显出“云监工”的重大作用,慢直播媒介的加入,让最低门槛的公共参与成为可能,集体意识下的监督力度也显得透明有力。
在疫情期间得到的爆发式关注的慢直播也开始走向常态,如2021年“两会”期间,广西新闻频道持续96小时的云观“两会”慢直播。未来慢直播领域,头部效应和平台优势将继续扩大,技术手段与表现手法会更加多样化,在5G视频直播技术加持下,画面更加精细,同时也会加入3D模型、虚拟街景、打榜、弹幕等更吸引受众的元素,并形成稳定网络社区,增加其用户黏性,慢直播画面内容将更具吸引力。
有学者认为直播媒体在开播前应进行用户调研和预测受众喜好,谨慎进行慢直播,避免以量取胜,同时应树立品牌形象,精准定位目标用户。在选题上,应以中国国情和文化为基础,紧扣受众的心理、兴趣与情感,关注垂直化、小众化、差异化内容,同时,应发挥慢直播舆论监督的功用,促进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仪式化传播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他认为,传播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在一起的神圣仪式。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借由仪式传播所蕴含的神圣感和互动性,主流媒体通过举办大量仪式性活动,吸引了无数国人共同参与红色文化传播。
兰德尔·柯林斯认为仪式化传播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互动仪式链”。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会形成高度的情感连带。它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或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同时,它也会给每个参与者带来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从事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活动。通过这种仪式化传播,人们表达了共同的价值观,增强了身份认同,从而增强团体凝聚力。
仪式有着重要的维系社会系统整体的功能属性,同时仪式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增进集体情感、加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它是构建与维护建立人类共同体的纽带,也是确认价值和信仰,巩固自身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嵌入程度上,仪式化传播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模式具有明显的传播优势,因而在表征价值信仰、粘聚社会方面被赋予重要的角色担当。
时下有许多节目都在致力于仪式化传播,如文博类电视节目通过塑造仪式化氛围、唤醒集体记忆和触发情感共鸣等仪式化传播流程,将受众集聚到一个共同的仪式场域之中,围绕着文物意象完成仪式观的奠基与加冕,进而塑造出华夏文明“想象的共同体”。有学者认为可以将观影行为看作是一种仪式化传播行为,电影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模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强有力的思想载体,在推动社会聚合方面担任重要角色。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电影,在国庆档上映,运用仪式化传播方式,传播了家国情怀的仪式性内容,使观众燃起了对家国的归属感。
但是,仪式化传播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话语实践上易于走向“仪式陷阱”,成为“附庸化的形式”,“仪式化”更可能成为价值传播的社会控制形式,对庆典仪式的过度商业开发也会消解其社会公益性。因此,在未来的仪式化传播中,媒体更需深度挖掘文字、诗词、戏曲等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展示文化之美、仪式之美,达到观众乐于收看和参与,并愿意深度沉浸的传播效果,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公众文化仪式,更好的发挥自身凝心聚力的职责和使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