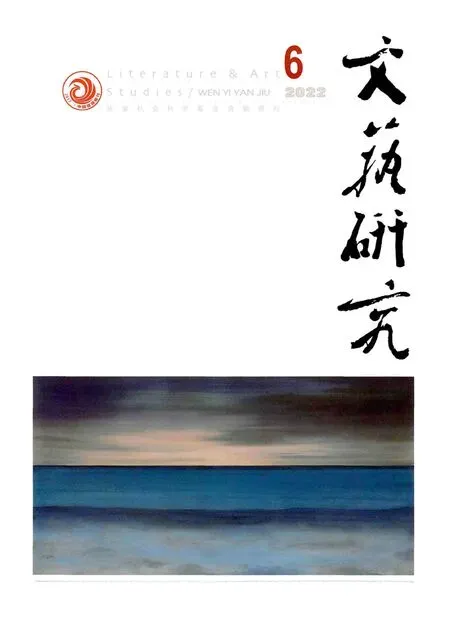明清之际的词统建构及其词学意义
2022-10-31沈松勤
沈松勤
所谓“统”,指事物之间的某种连续关系,维系其关系的,则是具有规范性的纲纪或准则。在古代文献中,“统”通常与“序”或“绪”组合,以示其传承性。也就是说,某种规范性的纲纪或准则自确立后被人们传承下来,就构成了“统序”或“统绪”。荀悦说:“圣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争,一统序也。”朱熹释孟子“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句云:“君子造基业于前,而垂统绪于后,但能不失其正,令后世可继续而行耳。”他们所说的“统序”或“统绪”,指的是政治上的纲纪与传承性,也就是政统。“统绪”观还见诸中华文化的多个方面,如道有道统、学有学统、文有文统、诗有诗统。作为一种新诗体,词的统绪观念生成较晚。最早以“统”命名的词集,是明末卓人月、徐士俊选编的《古今词统》。
任何一种统绪,虽然有人“造基业于前”,但要使之“垂统绪于后”,均需要一个建构过程。其过程需要后人基于当下需求,以追溯的方式来完成。词统的建构就是建构者在追溯中选择过往典范词人的创作为“基业”,为当下词坛开宗立说、继往开来。与政治上不许有二的政统不同,明末清初的半个多世纪是多元词统的共生期。各个词统各自选择的“基业”虽不尽相同,却共同开创了词的中兴局面。这是研究词学思想所不可或缺的一个话题,对认识词的演进历史也具有重要意义,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本文将通过考察这一时期词统的建构及其在词坛产生的具体影响,揭示其意义与价值。
一、重振词坛的词统序列
韩愈鉴于“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至今近千载,莫有言圣人之道者”,率先建构以“尧→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谱系的道统,以重振“圣人之道”。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词始于唐而盛于宋。到了明代,词人唯《草堂》《花间》是从,取径逼仄,“不及古昔”,如朱彝尊所说:“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卓人月与徐士俊通过追溯的方式,以选学与体性范畴为批评形态,建构词统序列,也针对词的衰蔽,目的同样在重振词风。
卓人月、徐士俊编有《古今词统》,此书凡16卷,收录词人486家,其中隋1家,唐33家,五代19家,宋216家,金21家,元91家,明105家,收词共2023首。卷首载有徐士俊、孟称舜二序。据徐士俊序,此书刻于崇祯六年(1633)。关于《古今词统》的编撰缘起,卓人月有具体说明:
昔人论词曲,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乎……余兹选并存委曲、雄肆二种,使之各相救也。太白雄矣,而艳骨具在,其词之圣乎!继是而男有后主,女有易安,其艳词之圣乎!自唐以下,此种不绝。而辛幼安独以一人之悲放,欲与唐以下数百家对峙,安得不圣……余益不得不壮稼轩之色,以与艳词争矣。奈何有一最不合时宜之人为东坡,而东坡又有一最不合腔拍之词为“大江东去”者,上坏太白之宗风,下亵稼轩之体面,而人反不敢非之,必以为铜将军所唱,堪配十七八女子所歌,此余之所大不平者也。故余兹选,选坡词极少,以剔雄放之弊,以谢词家委曲之论;选辛词独多,以救靡靡之音,以升雄词之位置。而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云。
开篇所说“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是入明后十分流行的观念。王世贞还直截了当地说:“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不仅将“宛转”(意同“委曲”或“婉约”)和“纵横豪爽”(意同“雄肆”或“豪放”)对立起来,而且认为后者“不可作”。为了打破这一观念,卓人月通过选人存史,建构“委曲”与“雄肆”两大统绪,从而使“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两径”,再创词坛之盛。
不过,上列引文是卓人月为其《古今诗余选》所作的序。学界一般认为,《古今诗余选》即《古今词统》,又名《诗余广选》。然而,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两者相同,该序为何不载于《古今词统》?卓人月批评苏轼“最不合时宜之人”,并认为“大江东去”“上坏太白之宗风,下亵稼轩之体面”,故“选坡词极少”,但《古今词统》不仅选录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而且选苏词47首,在宋代词人中,入选数量居辛弃疾、蒋捷、吴文英后,名列第四,岂能曰“极少”?
卓回说,《古今词统》由其兄人月编成于崇祯五六年间。今人点校的《古今词统》也署“卓人月汇编,徐士俊参评”。但据孟称舜《古今词统序》,“予友卓珂月,生平持说,多与予合。己巳秋,过会稽,手一编示予,题曰‘古今词统’。予取而读之,则自隋唐宋元,以迄于我明,妙词无不毕具”,则《古今词统》于崇祯己巳(1629)业已编就。徐士俊《古今词统序》说:“兹役也,吾二人渔猎群书,裒其妙好,自谓薄有苦心。”明示《古今词统》的编纂由卓、徐二人共同完成。徐氏还进一步指出:“谓‘铜将军’‘铁绰板’与‘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绝。无乃统之者无其人,遂使倒流三峡,竟分道而驰耶。余与珂月,起而任之……或曰:诗余兴而乐府亡,歌曲兴而诗余亡,夫有统之者,何患其亡也哉!”面对词坛“必以委曲为体,雄肆其下”的局面,他与卓人月“起而任之”,建构彼此关联、互为依存的词统序列,明确表达了词的统绪意识。这表明“词统”的命名,也始于卓、徐二人共操选政。
那么,卓人月、徐士俊何时共操选政?《古今词统》附徐、卓二人唱和集《徐卓晤歌》。徐士俊《祭卓珂月文》说:“与兄定交乙丑之年。”“乙丑之年”即天启五年(1625)。徐、卓二人唱和似亦始于此年。据此可以认定,天启五年,徐、卓定交后,二人在已有《古今诗余选》的基础上,重新“渔猎群书,裒其妙好”,完善原选。卓人月原先所撰写的《古今诗余选序》中的有些观点,与《古今词统》的选况不尽相符,故未被收入其中,但“委曲”与“雄肆”两大体性却在《古今词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昭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词统》卷首“目次”与“氏籍”后,分别收录了何良俊《草堂诗余序》、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陈仁锡《续诗余序》、杨慎《词品序》、王世贞《词评序》、钱允治《国朝诗余序》、沈际飞《诗余四集序》和《诗余别集序》8篇“旧序”;张炎《词源》(误作“《乐府指迷》”)卷下杂论16则,杨缵(误作“杨万里”)《作词五要》,王世贞、张纟延、徐师曾《论诗余》各1则,沈际飞《诗余发凡》等20则“杂说”。每篇“旧序”与部分“杂说”后均有简短点评。选录如此多的“旧序”“杂说”并予以点评,在宋以来的诸多词选中并不多见,但绝非画蛇添足,而是整部《古今词统》的选编纲领。如评王世贞《论诗余》云:
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二安之外,无首席矣。
所选张纟延《论诗余》将词分为“婉约”之“正”与“豪放”之“变”两体,王世贞重提以“宛转绵丽”为“正宗”、“纵横豪爽”为“变体”,也与张纟延一样褒“正”贬“变”。上列点评则将李清照与辛弃疾分别推为“正宗”与“旁宗”的“首席”,为两大体统中承前启后的典范词家;而对于“旁宗”即以“雄肆”为体性的“变体”,予以充分肯定。评沈际飞《诗余四集序》时指出:“苏以诗为词,辛以论为词,正见词中世界不小,昔人奈何讥之。”认为苏、辛词虽为“旁宗”,实则拓宽了词的境界。这既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变体”的偏见,又纠正了卓人月原先对苏词的偏见。又评杨缵《作词五要》云:
人谓览《五要》而词无难事矣,吾正于此见其难。
张炎《词源》说:“近代杨守斋精于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词》……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词五要》。观此,则词欲协音,未易言也。”杨缵属音律家,钟爱周邦彦持律甚严之词,故作《圈法周美成词》,将周邦彦词的声律形诸词法。据王沂孙《踏莎行·题草窗卷》:“白石飞仙,紫霞凄调,断歌人听知音少。”以杨缵与姜夔并称,而南渡以后持律甚严的词家首先是姜夔,故杨缵据周、姜词法,著《作词五要》。“五要”即“择腔”“应律”“按谱”“详韵”“立新意”。这是周邦彦、姜夔、杨缵也是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持律甚严的词人所恪守的规范要素。《古今词统》选录《作词五要》,并与张炎一样强调其难,表明了编者对周、姜一系填词规范的重视,其目的是为了在卓人月原先所辟“委曲”“雄肆”两途外,再辟一径。又评《诗余发凡》云:
词家习熟纵横,故句或无常,而声能协调。且如姜尧章之流,能自度曲,总由精于音律之故,不许效颦也。
沈际飞《诗余发凡》论词谱宫调与词调韵律的生成与规范。该点评据此从词与音乐的关系着眼,将宋代词人及其创作概括为两类:一类如苏轼、辛弃疾,其词虽“声能协调”,却非当行家;一类如周邦彦、姜夔,“能自度曲”,为当行词人。前者填词,“习熟纵横”,不为音律所缚,故纵横排奡,语多无常变化;后者填词,则审音定字,严于运律叶韵,故字正腔圆,语多和平谐美,即评《词源》“词之语句”一则所云:“去其太甚,则音和平。”入明以来,姜夔几乎被人们遗忘。《古今词统》所节录《词源》杂论对“雅正”的代表姜夔及其自度曲、作法、语体等赞评有加,选录这些赞评并在点评中予以张扬,目的在于再辟“和雅”统绪,唤醒人们对姜夔的记忆和重视。
可以说,卷首节录这些“旧序”“杂说”,体现了编选者的词史观与词统观。这些观念也体现在具体的选阵中。据统计,《古今词统》录30首以上的词人有:辛弃疾141首、杨慎57首、蒋捷50首、吴文英49首、苏轼47首、刘克庄46首、陆游45首、周邦彦43首、秦观38首、王世贞36首、高观国34首、黄庭坚33首、史达祖30首。其中杨慎、王世贞为明代人,余皆两宋人。而成书于南宋、盛行于明代的《草堂诗余》收录前几名的词人是:周邦彦56首、秦观25首、苏轼22首、柳永18首、康伯可11首、欧阳修10首、辛弃疾9首、张先和黄庭坚各8首、晏殊6首。姑且不论这两部词选所选范围与数量的差异,仅从其所选宋代前几位词人的排序即可看出两者不同的编选用心。在《古今词统》所选数量居前的几位宋代词人蒋捷、吴文英、刘克庄、高观国、史达祖中,《草堂诗余》仅收史达祖2首、刘克庄和高观国各1首,而未选吴文英、蒋捷。“《草堂诗余》的初编者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坊间无名氏,何士信于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之后增修编订。”蒋捷为宋元间人,未收其词,不足为怪。黄升于理宗淳祐九年所编《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已收吴文英词9首,《草堂诗余》却不选其词,《古今词统》收其词多达49首。同时,《古今词统》还收录了《草堂诗余》未选的姜夔词,共10首。这一选阵昭示了选者所要建构的三大词统系列。
一是“委曲”统绪。在卓人月看来,“委曲”的表现形态为“柔声曼节”,其体格为“艳”,并认为以“艳”为体格的“委曲”统绪始于李白而盛于李煜、李清照:“太白雄矣,而艳骨具在,其词之圣乎!继是而男有后主,女有易安,其艳词之圣乎!自唐以下,此种不绝。”(《古今诗余选序》)自唐以后,文人词中的“委曲”一统确实延绵“不绝”,几乎无人不作,即便是以“雄肆”见长的苏轼、辛弃疾,也不乏“委曲”之作。在体制上,“委曲”一统以小令居多,而小令如《古今词统》节录《词源》所云:“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当以《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在词史上,以温、韦为则的“委曲”小令,以唐五代、北宋及明代为多。因此该书所选唐五代小令数量居前的是:温庭筠17首、孙光宪15首、李煜14首;北宋小令数量居前的是:秦观22首、毛滂18首、李清照13首;明代小令数量居前的是:杨慎52首、王世贞30首。之所以多选杨慎、王世贞,是因为二人是明代词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词家,杨慎生前又被誉为“明词第一人”,而书名既为“古今词统”,以杨、王两家作为“今”的代表,乃应有之义。
二是“雄肆”统绪。“雄肆”是相对于“委曲”的一种体性。该体主要以慢词为体制、以沉雄之气为体格、以纵横排奡的语体为表征,初始于苏轼而鼎盛于辛弃疾。关于“雄肆”的具体表现,选者在评点中多有阐释。如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学士此词,感慨雄壮,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评辛弃疾《贺新郎·自述》:“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评陈亮《贺新郎·再酬辛幼安》:“鹃叫天津,狐升帝座,有此时事,自然有此人文。故漫纸皆恨怨悲愁之音,忽荒诞幻之状。”评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写出脑后风生、鼻端火出之况。”均指基于作者沉雄之气的纵横雄肆之意,说明陈亮与陆游为辛弃疾的生前同调。又评刘克庄《水龙吟》四首:“四词目穷千里,笔挽万钧,识力双高,可与稼轩相尔汝。”评元好问《满江红·对酒》:“遗山极称稼轩,宜其似之。”又评蒋捷《水龙吟·招落红梅》:“尽爱以致祷,迥出纤冶秾华之外。辛之有蒋,犹屈之有宋。”称刘克庄、元好问、蒋捷为辛弃疾的生后同调,同样基于其人沉雄、其词纵横雄肆。从苏轼到辛弃疾,再到辛弃疾的生前、生后同调,选者建构了一脉相承的“雄肆”统绪。
三是“和雅”统绪。《古今词统》卷首节录《词源》杂论云,“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词浑厚和雅……作词多效其体制”,如姜夔、高观国、史达祖、吴文英“像而为之”,却均能“自成一家”,“与美成辈争雄长”。所谓“和雅”,既指“雅词协音,虽一字不放过”,声律与文辞和雅谐协,又指卷首节录《词源》杂论所谓摒弃浮艳后的“雅正”。可见,构成“和雅”体性的体格与语体也就不同于“习熟纵横”的“雄肆”,也有异于“艳骨具在”的“委曲”。在卓人月、徐士俊看来,造此“基业”者为周邦彦,“垂统绪于后”者为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其依据是杨缵根据周邦彦、姜夔两家词总结的作词五要素。《草堂诗余》选词最多的虽为周邦彦,但“与美成辈争雄长”者之作不收或很少收录,《古今词统》却选录了为《草堂诗余》未选的姜夔、吴文英二家,并极大提升高观国、史达祖二家词的入选数量,以示“和雅”统绪的传承性。这从《古今词统》所选诸人慢词及评点可见一斑。如评周邦彦《兰陵王·咏柳》:“不沾题而宣写别怀无抑塞。《草堂选》云:‘“应折柔条过千尺”,自不伤雅。至“斜阳冉冉春无极”,如此咏物,淡宕有情矣。’”评姜夔《疏影·咏梅》:“启母化石,虞姬化草。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化而为梅,不亦宜乎。”评史达祖《双双燕·咏燕》:“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白描妙手。”评高观国《解连环·春水》:“幽藻疑骚赋。”评吴文英《尾犯·赠浪翁重客吴门》:“别调氤氲,自成馨逸。”以上诸家慢词在韵律体格上均审音定字,严于运律叶韵,音律谐美,这些点评则又揭示了诸词所共同具有的“浑厚和雅”的语体与体性。
在三大词统序列中,“和雅”一统尚未涉及“垂统绪于后”的王沂孙、陈允平、周密、张炎诸家,于姜夔词也仅收10首。究其原因,在于他们的词集罕见传本,选者未能寓目。不过《古今词统》通过选学形态和体性范畴所建构的三大词统序列,以及各自由典范词人构成的传承谱系,基本上涵盖了唐以来词的演进状况。而作为词学批评中的体性范畴,“委曲”“雄肆”“和雅”虽已为前人所运用,卓人月、徐士俊却从体制、体格、语体诸方面分别为其赋予了具体内涵,首次建构了以体性为核心的词统理论体系,在词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卓回说:“方今词学大兴,识者奉为金科玉律。”丁澎也说:“《古今词统》之选,海内咸宗其书。”
二、基于“尊体”与“复雅”的词统
如果说卓人月、徐士俊所建构的词统序列具有鲜明的词史意识,那么纳兰性德、顾贞观与朱彝尊分别重构的“今词”与“醇雅”两大统绪,则分别基于“尊体”与“复雅”的词学观及其自身的创作实践。
康熙十六年(1677),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合编《今词初集》,次年刊刻,分上、下二卷。鲁超《今词初集·题辞》说:
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采集近时名流篇什,为《兰畹》《金荃》树帜,期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余得受而读之。余惟诗以苏、李为宗,自曹、刘迄鲍、谢,盛极而衰,至隋时,风格一变,此唐之正始所自开也。词以温、韦为则,自欧、秦迄姜、史,亦盛极而衰,至明末,才情复畅,此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毛际可《今词初集跋》又说:
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艳,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
二人均揭示了该选的目的在于“为《兰畹》《金荃》树帜”,重构“以温、韦为则”的词坛统绪,确立规范性的“填词之准的”。纳兰性德“与梁汾持论极合”。在他看来,“填词滥觞于唐人,极盛于宋,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数,吾为之易工,工而传之易久,而自南渡以后弗论也”。其《虞美人·为梁汾赋》则具体表达了他与顾贞观的词学思想及《今词初集》的选心: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据赵秀亭、冯统一笺:该词作于康熙十六年,“‘凭君’句,指顾贞观回南刊刻《今词初集》及《饮水词》事”。“花间”即“花间草堂”,是纳兰性德与顾贞观、严绳孙、吴雯等同人“剧论文史”之所,“后改葺通志堂”;“共泥犁”指与顾贞观从事“花间课”的具体内容。纳兰性德自称:“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以其言情入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黄庭坚词因以《花间》“致语”书写性情,被法秀禅师斥为“以笔墨劝淫”,“当下犁舌地狱”。“莫负当初我”,甘愿“共泥犁”,意即以“《花间》致语”书写性情,即便像黄庭坚那样遭法秀呵斥,在所不惜,与上文所引王世贞褒“正”贬“变”的言论如出一辙,是对以“委曲”为体性的词之“正宗”的恪守与推尊。下阕表达“花间课”的审美取向。“瘦狂”指基于忧患憔悴的清瘦之态,“痴肥”为外浓中枵的浮艳之状。“判任痴肥笑”就是摒弃浮艳,取法清瘦,其理论依据则是:“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冬郎一生极憔悴,判与三闾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怜春,凤蜡红巾无限泪。”可见纳兰性德、顾贞观甘愿“共泥犁”,合编《今词初集》,虽“以温、韦为则”,为“《兰畹》《金荃》树帜”,但并非完全回归以温、韦为代表的花间老路,而是遵循“《花间》致语”的创作惯例,采纳其规范要素,赋予新的艺术肌体,即通过“美人香草”“凤蜡红巾”的比兴手法,寄托“忧患”,表达性情,从而确立“填词之准的”,保持词“别是一家”的“本色”之“正”,使之“与诗家坛坫并峙古今”。这一主张决定了《今词初集》对就近三十年间典范词人的选择。
《今词初集》凡选184家、617首,平均每家不到4首。然而,选10首以上的词人却有16家之多,分别为:陈子龙29首、龚鼎孳27首、顾贞观24首、吴绮23首、朱彝尊22首、宋征舆21首、丁澎19首、李雯18首、严绳孙和纳兰性德各17首、曹溶16首、吴伟业和王士禛各13首、陈维崧11首、彭孙遹和顾贞立各10首。“云间三子”陈子龙、宋征舆、李雯均在其列,陈子龙词的入选数量且居首位。对以“雄肆”取胜的陈维崧,却仅收11首,皆非“雄肆”之作。纳兰性德、顾贞观以极高的比重选入“云间三子”之作,实出于建构“今词”统绪之需。也就是说,无论词学主张抑或创作实践,他们都想上“以温、韦为则”,下为今词“造基业”。
诚如谢章铤所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宗尚始于晚唐的花间词以及在花间影响下的五代北宋词,是晚明、清初词坛的普遍风气,即便是陈维崧、朱彝尊也不免此习。不过,甲申之变前,这一风习主要是尚俗主情的文学思潮的产物,从中表现的通常是自温庭筠以来花间词作者均拥有的普泛化、共通性的情感。陈子龙便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申明了这一点:
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使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词。
刻于崇祯年间的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唱和集《幽兰草》的主题,正是这种普泛化、共通性的“绸缪婉娈之情”。甲申之变极大地冲击了词人的心灵,给他们的人生划下一道深深的鸿沟。此后,当他们“以温、韦为则”填词时,其体性虽也以“委曲”为特征,却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其间,或如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诸子,率先“于闺襜之际”,“写哀而宣志”,寄寓亡国之痛;或如王士禛词“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其旖旎而秾丽者,则璟、煜、清照之遗也;其芊绵而俊爽者,则淮海、屯田之匹也”;或如丁澎“偏工旖旎愁肠,故《扶荔词》曲尽纤艳之思”;或如顾贞观“《弹指集》,如灵和杨柳,韶倩堪怜,又如卫洗马言愁,令人憔悴”;或如纳兰词“固自哀感顽艳,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纳兰性德与顾贞观所要建构的,正是自陈子龙以来三十余年间这一以“性灵”为创作取向、“委曲”为体性特征的“今词”统绪。
从体性观之,“今词”统绪明显接续了《古今词统》所建构的“委曲”一统。不同的是,《古今词统》建构三大词统序列,目的是为了在“词场之上,遂荡荡乎辟”三径;纳兰性德、顾贞观建构“今词”统绪,旨在推尊以“委曲”为体性的“本色”之“正”,巩固它在当下词坛的地位。当下词坛的情形则是多元统绪相并而行,联镳竞逐,尤其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变早期宗尚“晚唐”为上承“雄肆”统绪,大掀“稼轩风”,并于康熙十年选刊《今词苑》,推尊“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的“东坡、稼轩诸长调”。正在兴起的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又看重以姜夔、张炎等为典范的“醇雅”统绪。这对“委曲”一统带来不小冲击。杜诏为顾贞观词集作序云:
夫《弹指》与竹垞、迦陵埒名。迦陵之词横放杰出,大都出自辛、苏,卒非词家本色。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隽永,本朝作者虽多,莫有过焉者。虽然,缘情绮靡,诗体尚然,何况乎词?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
道出了纳兰性德为何嘱咐顾贞观“莫负当初我”,甘愿“共泥犁”,共建“今词”统绪的背景与目的。
在纳兰性德、顾贞观建构“今词”统绪的同时,朱彝尊的“醇雅”统绪也建构完毕。康熙十七年,朱彝尊经过多年编纂的《词综》问世。而《词综》与次年刊刻的《浙西六家词》被学界视为朱彝尊流派意识与浙西词派确立的重要标志。诚然,朱彝尊将流寓浙地的姜夔、张炎与浙人吴文英、王沂孙等的创作,视为如同江西诗派的派别,是一个“形”虽有异而“味”却相同的“浙词”流派,明显为浙西词派树旗扬帜。朱彝尊说:“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夔之一体。”其由姜夔“造基业于前”、张炎等“垂统绪于后”的词体统绪意识昭然若揭。
朱彝尊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所谓“世人”,即指在陈子龙词学观影响下的纳兰性德、顾贞观等词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指长调慢词,但其所宗并不包括辛弃疾在内的以慢词为体制的“雄肆”之词。宋荦指出:
今人论词,动称辛、柳。不知稼轩词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为最,过此则颓然放矣。耆卿词以“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与“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佳,非是则淫以亵矣。迨白石翁起,南宋玉田、草窗诸公,互相倡和,戛戛乎陈言之务去,所谓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者,此竹垞论词必以南宋为宗也。
由此可知,朱彝尊“论词必以南宋为宗”,是将辛弃疾及其同调之词排斥在外的。换言之,朱彝尊所推崇的既非“以温、韦为则”的“委曲”,又非以苏、辛为典范的“雄肆”,而是以姜夔为宗主的统绪。该统绪的体性特征就是汪森在《词综序》中所总结的“醇雅”。
《词综》凡30卷,选唐五代、两宋、金元词人542家,词1945首,平均每人不到4首,但所选20首以上的词人有20家之多,其中多半属于“浙词”作者,如周邦彦45首、姜夔22首、高观国20首、史达祖26首、吴文英45首、蒋捷21首、王沂孙31首、陈允平22首、张炎39首、周密54首、张翥27首,张辑、卢祖皋虽存词不多,却也分别入选11首与14首,凸显了“浙词”阵营。在此基础上,汪森梳理了词之“醇雅”统绪:“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
张宏生指出:“朱彝尊在从事《词综》之纂时,不仅从《古今词统》选择了相关的材料,而且借鉴了其选词思路。”尽管随着词集的新发现,《词综》选录了《古今词统》未收录的周密、王沂孙、陈允平、张炎诸家之作,但“二者相比,确实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一致性,即突出典雅格律一路风格,而《词综》在这方面的推重更为加强了”。“典雅格律一路风格”源自周邦彦。康熙十四年,严沆在《见山亭词选序》中称周邦彦词在北宋最为“醇雅”,南宋姜夔、史达祖、张炎、王沂孙等人“要其源,皆自美成出”。《词综》选周邦彦词达45首之多,便昭示了这一点。不过,朱彝尊建构“醇雅”统绪,既是为浙西词派树旗扬帜,也是时序与世情影响下创作实践转型后的产物。
据曹尔堪《江湖载酒集序》:“芊绵温丽,为周、柳擅长,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盛年绮笔,造而益深,固宜其无所不有也。”可见朱彝尊前期创作取径多样、众体兼备。然而,随着时序与世情的演变,朱彝尊从先前的取径多样转向了独“爱姜史”和“玉田差近”。这一转型大约始于康熙九年初纂《词综》之时,至康熙十七年全面完成。
从时序与世情观之,康熙听政后,政局逐渐趋向稳定,甲申之变后士人社会与清廷的对立情绪也渐趋平息。换言之,士人对新朝政权的认可日趋明晰,朱彝尊、陈维崧等大量士人赴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试,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不过,尽管如此,赴考者仍怀着复杂而隐密的心绪。这从康熙十七至十八年间由朱彝尊、李良年在京师发起的系列咏物唱和活动可见一斑。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拟《乐府补题》唱和。
《乐府补题》是元初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的咏物唱和集,凡咏龙涎香、白莲、蝉、莼、蟹五题。康熙十七年,朱彝尊携《乐府补题》入京后,分别与陈维崧为之作序,受到在京词人的一致珍视,纷纷拟而唱和。朱序云:“诵其词,可以观意志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认为《乐府补题》继承“骚人《橘颂》”传统,境幽意浓,寄托遥深,咏物体格,出乎醇雅。可以说,这集中体现了姜夔开拓的以咏物为途径的“醇雅”体性。朱彝尊在京师发起这场拟《乐府补题》唱和,是浙西词派承接“醇雅”统绪的一次群体实践,而大量非浙西词人参与唱和的事实,又传达出词坛转型的信息。蒋景祁明确指出,朱彝尊“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究其原因,在于严迪昌所说的:“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这种‘淡化’沉淀心底深处的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心绪,无疑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也符合时代演变的正常秩序。”也就是说,朱彝尊建构由姜夔“造基业于前”的“醇雅”统绪,顺应了时代演变,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词统的词学意义
“词学”一词在古代载籍中指词章之学,在论词的话语中指填词,到了近代,成了包括研究词人及其创作、词乐、词律、词集、词论、词史等诸多方面问题的专门之学。作为词学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词统有辞章之学的成分,也有词论、词史的内涵,具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衍至明代,人们关于词的观念偏执一端。词统却以词选为媒介,以词人词作、词学现象为对象,以词论中最活跃也最普遍的范畴为批评形态,对唐以来的词展开阐释和总结,形成了整体性和引导性的词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体现在对词的体性的阐释和总结。嘉靖年间,张纟延首次将唐以来词的体性总结为“婉约”“豪放”两体,在后世影响甚大,但明人没有对其展开具体的阐释,而且,以“婉约”“豪放”概括唐以来词的体性,也不够全面。卓人月、徐士俊所建构的“委曲”“雄肆”“和雅”三大词统序列,既涵盖了唐以来词的体性类型,又以作家作品为基本出发点,从词的体制、体格、语体等诸多方面予以阐释,揭示了三大统绪各自具有的规范性要素及其有机构成。譬如“雄肆”统绪的建构,就是通过对在词乐上“非当行”的苏轼、辛弃疾、陈亮、元好问、刘克庄等典范词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的阐释,揭示其以慢词为体制、沉雄之气为体格、纵横排奡的语体为表征的“雄肆”体性的运作体系。作为主要以小令为体制的“委曲”统绪的接续,纳兰性德、顾贞观所建构的“今词”统绪,则在“以温、韦为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以“哀艳之深情”或“哀感顽艳”为体格、《花间》“致语”为语体的“委曲”体性的运作体系。朱彝尊则在《古今词统》所总结的“和雅”体性的体制、语体、体格的规范性要素的基础上,完善了其传承谱系。总而言之,词统的建构既使唐以来词的体性范畴的总结趋向完整,又对其内涵的阐释趋向深入和系统化,对后世词学批评起了引导作用。
其次,体现在对词的演变历史的阐释和总结。入明后,词人因唯《草堂诗余》《花间集》是从,故在看待唐以来词的发展历史时,对《草堂诗余》《花间集》所呈现的词史了然于心,此外的词史则并不在意甚至遗忘。“委曲”“雄肆”“和雅”三大词统的建构,阐释和总结了唐以来词的演变历史,对词史的总结趋向完备。特别是“和雅”统绪的建构,使长期湮没不彰的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开始进入词学视野,为词史继“委曲”与“雄肆”二统之后又重新发明一统。另外,词统建构需要典范词人作支撑,某一词人被选为典范而列入其中,其词史地位也就大大提升了。“和雅”或“醇雅”统绪所选择的姜夔、张炎诸家便证明了这一点,“今词”统绪中的陈子龙也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王士禛、邹祗谟看来,陈子龙等云间诸子“论诗拘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在此”。所谓“佳处”,指“丽语复当行”;而“短处”,则指田茂遇所谓“主一不变之说,似严实隘”,取径逼仄,气局狭小。“今词”统绪却首选陈子龙,且所选其词数量位居首位,凸显了他作为“三十年填词之准的”的奠基者地位。后世将陈子龙比作《水浒传》中的晁盖,视之为“词坛头领”,意即“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陈子龙这一词史地位,无疑是“今词”统绪引导建构的。
(二)实践意义
“委曲”“雄肆”“和雅”三大词统建构的出发点虽不尽一致,但都是为了裨益当下词坛创作,故均具有实践意义。
王士禛说:“《古今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此书作用于词坛,一改以往唯《草堂诗余》《花间集》是从之偏,为词人提供了不失其正而又足资借鉴的多元范本,甚至更为多样而经典的词调。邹祗谟评《倚声初集》所载董以宁《暗香》(绿酣红醉):“‘五更风雨葬西施’,无此凄艳,是宜花有叹声矣。”又评董以宁《疏影》(冰玦绿映):“写景处善于言情,须细看其逐次渲染处。”《暗香》《疏影》是姜夔自度曲,为《古今词统》首次选录。当时姜夔词集秘而不宣,朱彝尊编《词综》时也未寓目。董以宁拟《暗香》《疏影》二调,无疑取自《古今词统》。这也证实了自崇祯以来“海内咸宗”《古今词统》而创作的事实。
姜宸英《题蒋君长短句》指出:
记壬戌灯夕,与阳羡陈其年、梁溪严荪友、顾华峰、嘉禾朱锡鬯、松陵吴汉槎数君同饮花间草堂。中席主人指纱灯图绘,请各赋《临江仙》一阕……然数君之于词亦有不同。梁溪圆美清淡,以北宋为宗;陈则滥觞于稼轩,朱则湔洗于白石。譬之韶夏,异奏同归,悦耳一时,词学之盛,度越前古矣。
所谓“以北宋为宗”“滥觞于稼轩”“湔洗于白石”,就是说他们的创作分别接续了“委曲”“雄肆”“和雅”三大统绪。事实上,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延续“委曲”,建构“今词”统绪,不仅是为当时与后世确立“填词之准的”,而且也是以该统绪规范性要素的践行者、继承者自居;朱彝尊在“和雅”基础上拓展“醇雅”统绪,同样如此;陈维崧虽无建构词统之举,但“雄肆”一统的规范性要素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不仅得到了生动的呈现,而且得到了明显的拓展。他们分别接续三大统绪而进行的创作实践,代表了清初整个词坛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姜宸英所说三者“异奏同归”,铸就了“词学之盛”,谱写了继两宋以后词的中兴局面。
① 荀悦:《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7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4页。
③ 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60页。
④㊾ 朱彝尊:《词综·发凡》,朱彝尊、汪森编,李庆甲点校:《词综》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第10页。
⑤ 卓人月:《古今诗余选序》,《蟾台集》卷二,《蕊渊集·蟾台集》,明崇祯间刻本。
⑥ 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
⑦㉗ 卓回:《古今词汇缘起》,《古今词汇二编》卷首,赵尊岳辑:《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2页,第1544页。
⑧ 卓人月汇编,徐士俊参评,谷辉之点校:《古今词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⑨⑩⑫⑬⑭⑰⑱⑳㉓㉕ 卓人月汇编,徐士俊参评,谷辉之点校:《古今词统》卷首,第3页,第1—2页,第36页,第18页,第35页,第37页,第33页,第33页,第31页,第34页。
⑪ 徐士俊:《雁楼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⑮㉔ 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267页,第256页。
⑯ 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65页。
⑲ 陈丽丽:《〈草堂诗余〉成书年代及编者再考辨》,《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㉑ 王廷表:《升庵长短句跋》,王文才辑:《杨慎词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㉒㉖ 卓人月汇编,徐士俊参评,谷辉之点校:《古今词统》,第493、582、585、466、523、448、521页,第598、549、479、545、452页。
㉘ 丁澎:《正续花间集序》,《扶荔堂文集选》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册,第478页。
㉙㉚ 顾贞观、纳兰性德编:《今词初集》卷首,张宏生编:《清词珍本丛刊》第22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615页,第616页。
㉛ 姜宸英:《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腊君墓表》,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附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04页。
㉜ 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统一笺校:《饮水词笺校》,第272页。
㉝ 姜宸英:《跋〈同集书〉后》,《湛园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㉞ 纳兰性德:《与梁药亭书》,《通志堂集》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㉟ 黄庭坚:《小山集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0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㊱ 纳兰性德:《填词》,《通志堂集》卷三,第97页。
㊲ 参见沈松勤:《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216页。
㊳ 谢章铤著,刘荣平校注:《赌棋山庄词话校注》续编卷三,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页。
㊴ 转引自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45页。
㊵ 陈子龙:《陈卧子先生未刊集》卷二,《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陈子龙、宋征璧、宋思玉、宋存标、宋征舆、钱谷于甲申之变后的《唱和诗余》,便寄托了家国之痛(叶嘉莹:《论陈子龙词——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谈令词之潜能与陈子龙词之成就》,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正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1页)。
㊶〔62〕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第660页,第656页。
㊷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卷下,《词话丛编》,第1040页。
㊸ 吴兆骞:《戊午二月二十一日寄顾舍人书》,顾贞观著,张秉戍笺注:《弹指词笺注》附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页。
㊹ 谭莹:《饮水集跋》,《饮水词笺校》卷一,第22页。
㊺ 陈维崧:《陈迦陵散体文集》卷二,陈振鹏标点,李学颖补校:《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
㊻ 杜诏:《弹指词序》,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卷三,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页。
㊼ 朱彝尊:《鱼计庄词序》,《曝书亭集》卷四〇,王利民等点校:《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页。
㊽ 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集》卷四〇,《曝书亭全集》,第453页。
㊿ 宋荦:《咏物词评》,曹贞吉:《珂雪词》卷首,《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356页。
〔51〕 按:朱彝尊编纂《词综》时,与卓人月、徐士俊一样尚未全面寓目姜夔作品。《词综·发凡》云:“《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词综》卷首,第10页)故仅选姜夔词22首。
〔52〕 汪森:《词综序》,《词综》卷首,第1页。
〔53〕 张宏生:《统序观与明清词学的递嬗——从〈古今词统〉到〈词综〉》,《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54〕 陆次云、章昞编:《见山亭古今词选》卷首,清康熙十四年刻本。
〔55〕 朱彝尊:《江湖载酒集》卷首,《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170页。
〔56〕 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江湖载酒集》卷五,《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263页。
〔57〕 朱彝尊:《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江湖载酒集》卷六,《清词珍本丛刊》第5册,第289页。
〔58〕 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曝书亭集》卷三六,《曝书亭全集》,第421页。
〔59〕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瑶华集》卷首,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60〕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61〕〔66〕 王士禛:《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685页,第685页。
〔63〕 田茂遇:《清平初选后叙》,张渊懿、田茂遇辑:《清平初选》后集卷首,清康熙间刻本。
〔64〕 朱祖谋:《清词坛点将录》,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82页。
〔65〕 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陈子龙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67〕 王士禛、邹祗谟:《倚声初集辑评》,《词话丛编补编》,第631、674页。
〔68〕 姜宸英:《题蒋君长短句》,《湛园未定稿》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1册,第7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