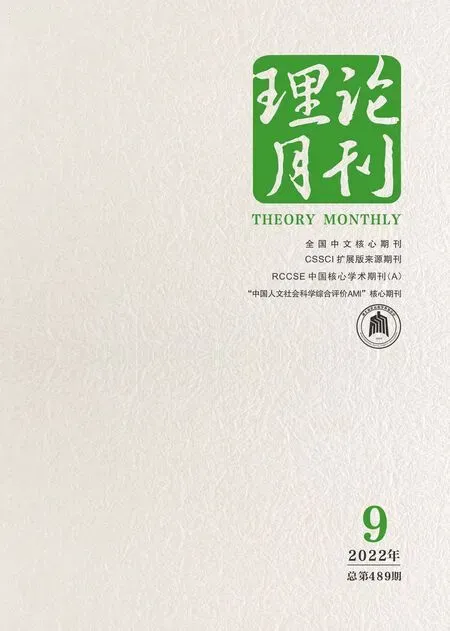纪念空间传承红色记忆的逻辑机理
2022-10-31程慧中
□程慧中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必须保持红色的底色永不褪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红色历史虽已远去,但红色记忆却永远留存,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给予我们前进的力量。红色记忆作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标识着中华民族的 “来路” 与 “去路” ,是全体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财富。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只有铭记刻骨历史,才能更好地前行。然而,倘若记忆的事件没有确定的生发地点,那么记忆就会变成空想。空间是记忆的载体,灵魂深处的红色记忆总是借助于特定的空间得以延续与呈现,纪念空间便是这样的场所。
从社会学角度看,纪念空间可以分为个人纪念空间与社会纪念空间(公共纪念空间)两大类。前者主要涉及与家族和血缘相关的场所,例如祠堂、墓地等;后者则主要指称国家抑或社会统一构筑的公共纪念场所。笔者所论的 “纪念空间” 主要选取其社会性内涵,即公共纪念空间。根据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以纪念意图对纪念物的分类方法,纪念空间也可以笼统划分为 “意图性纪念空间” 与 “非意图性纪念空间”。前者主要指向预设的、意图表达纪念意义的空间,例如纪念碑、博物馆、纪念堂、雕塑等;后者主要指向无原初纪念意图的纪念空间,例如遗址、遗迹、墓地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大量的革命旧址、遗迹等纪念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增强国家认同,以革命旧址、遗迹等纪念地为基地修建了一大批以博物馆、纪念堂、烈士陵园等为主要类型的纪念场所,它们实际上都属于纪念空间的范畴。这些纪念空间以不同形式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储着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是党和国家重要的 “文化基因库” 。
在我国,党和国家留存或修建的纪念空间大多是承载红色革命历史的纪念场域。这些纪念空间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为纪念对象,将革命故事、革命旧址、革命遗存等融合为一体,意在缅怀红色历史、唤醒红色记忆、感召红色精神与传承红色文化。在推动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今天,纪念空间在赓续红色血脉、守好红色江山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纪念空间为何能够传承红色记忆?换言之,纪念空间能够传承红色记忆的逻辑机理是什么?学术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选取逻辑机理这个维度,探讨纪念空间传承红色记忆在理论维度何以可能、在现实维度为何必要、在实践维度如何可能,对于优化纪念空间的现代治理,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价值。
一、纪念空间传承红色记忆的可能性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言,纪念性空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 “回溯功能” :回溯历史,唤起记忆。作为历史的见证、文化的体现,纪念空间是群体记忆物化的表征。当人们走入纪念空间,历史的文化价值、社会的政治表达以及时代的精神愿景都在这一特定场域得以呈现。纪念空间是唤醒集体记忆的意义场域,是塑造情感认同的价值空间,也是实现无声教化的育人场所,这是它能够传承红色记忆的现实条件与实践可能。
(一)唤醒集体记忆的意义空间
纪念空间以其厚重的红色历史为脚本,成为唤醒人们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它承载着遥远的记忆,作为一种中介联系着参观者与特定历史时空,带领人们重返 “历史现场” ,感受历史带来的震撼与唏嘘。那么何为记忆?何为集体记忆?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 “集体记忆”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学概念,最早由莫里斯·哈布瓦赫完整提出。他基于涂尔干的理论将记忆与社会、文化勾连起来,发展出了集体记忆理论。哈布瓦赫把 “(集体)记忆作为上位概念来使用,在这之下再区分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试图串联起记忆、文化和群体三者之间的关联。因而集体记忆不是个人经验的堆砌,而是在社会群体中人们所共享、传承的,是社会环境复杂因素互动的结果。集体记忆对于一个民族至关重要,它不仅形塑着人们的历史认知,而且影响着人们的处事态度。对于英雄的光辉史迹,我们应当肯定并形成正面的集体记忆;而对于耻辱,我们则应吸取教训并形成反面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不仅是联结集体成员的纽带,更是构筑集体认同的基础。丢失集体记忆的群体是无根的群体,遗忘过去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
作为一个特定的空间,纪念空间通过建筑、墓碑、墙、门等元素进行空间设计,并运用隐喻与想象的方式引发观者的思考,从而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纪念空间一般伫立在革命旧址抑或纪念遗存附近,其本身也将时间锚定在某个历史瞬间。空间视觉与空间使命聚合在一起,共同营造出的神圣、肃穆、永恒之感可将历史与当下进行勾连。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作为一个典型的意图性纪念空间,它是党和国家为让国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而建造的。该纪念馆所在地是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和 “万人坑” 丛葬地遗址处,此处也已经成为推动国际和平城市建设的地标。 “遇难者300000” 的石壁墙、 “古城的灾难” 等组合雕塑、祭奠广场、和平公园、赎罪碑等纪念景观,无不象征与再现了大屠杀凄惨的历史瞬间。纪念空间的场馆布局以及景观设置映射着这段惨痛的历史事实,当人们参观纪念空间时,无意识间就受到空间中各种物质元素和景观的感染,从而唤醒遇难同胞被屠杀的苦难回忆。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集体记忆可以是一种物质客体,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纪念空间修建了一批纪念碑、纪念堂以及烈士陵园等建筑景观,将红色历史物态化,使得集体记忆更容易被唤起与传递。加之纪念空间还时常举行爱国主义学习及历史纪念仪式活动,人们身体力行地参与纪念活动后,其情感认同更容易得到激发,从而对这段历史产生持久而深刻的记忆。因此当观者走进这类红色记忆的场域,他们仿佛跨越了时空障碍回到历史现场,集体记忆得以唤醒。
(二)塑造情感认同的价值空间
记忆往往与认同密切相连,二者的关系表现为: “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参观纪念空间,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其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民族的历史认同感,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助力国家政治建构。质言之,当纪念空间成为保存与延续红色记忆的重要场所时,社会成员能够在参观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从而建立起对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历史文化的价值生成常常与其诠释活动相一致。以革命纪念馆为例,馆内的红色遗存为诠释情感认同提供了重要资源。革命纪念馆通过对红色历史事件、历史情节、历史遗存物等赋予意义,帮助参观者融入历史情境从而实现思想的浸润与升华,达致政治情感的激发。更重要的是,红色记忆为情感认同提供了逻辑可能。 “如果没有集体记忆,共同体可能不会持久,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记忆的共同体’,一个不会忘记过去的共同体。”其实,对于认同来说,本质上就是区分他者与我者。红色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套选择并建构起来的具有情感认知的系统,对于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认同与情感指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拥有红色记忆的共同体,对内共享集体的情感联结,形成对集体成员的理解与认同;对外形成对集体外部成员的斥异与区分。这种内生的认同与斥异呈现一种张力,为个体找寻自我的存在之根,明晰与他者的界限,并界定出自身的归属与认同。质言之,从记忆到认同,就是记忆的立场裁决与意识驯化的过程,是塑造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认同和情感指向的过程。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传统社会的 “超稳定性结构” 受到冲击,原本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开始不受控地做起了 “离心运动” ,集体意识开始瓦解。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加剧了公共空间的萎缩,个体的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纪念空间通过收藏大量的历史证据,并借由独特的程序与手段将这些历史遗存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搭建起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桥梁。此外,纪念空间作为承载革命文化的精神场所,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也是社会主流价值与先进文化的传播载体,发挥着传递社会主流价值信仰的重要功能。概言之,人们通过纪念空间回溯革命历史,不仅明确了个体所处的时空坐标,唤醒了有着共同来源的历史记忆,而且能感悟革命精神,受到价值观的浸润与洗礼,从而为个体找寻民族之 “根” ,建立身份与价值认同提供了平台与可能。
(三)实现无声教化的育人空间
空间总是伴随着某种隐喻符号,对人的思想产生无声的熏陶。它常以隐喻的方式表达或投射着某种意义,当人身临其境时,便会感受到一种直叩人心的情感共鸣,于不自觉中受到了感染与教化。以博物馆空间为例,博物馆不仅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而且是一种 “致力于组织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公民的文化性技术”。质言之,博物馆是一种能够帮助公民实现自我约束的文化机构,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其实,自从踏入场馆的那一刻开始,参观者就潜在地进入了一种公共与私密相结合的状态,其思想与行为不自觉地受到博物馆的牵引,以接受馆内文化的熏陶与教化。俞吾金先生曾言,一个人从 “自然存在物要转化为社会存在物,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合格的成员,不得不从小就开始接受教化”。在某种意义上,教化被视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它就是统治者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政治教化的目的在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以及秩序的和谐。这也就决定了教化本身总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导向性。博物馆空间借助于 “知识—权力” 的隐性推力将特定话语传递给公众,其本身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最佳的国家政治话语宣传工具之一。在博物馆空间,馆内的每一处细节陈设都隐含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将深邃的历史外化为可感的事物,使参观者在接受历史洗礼的同时也能够认同既有的管理秩序,从而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念空间在抽象的政治话语与民众理解之间起着 “中转站” 的作用。
事实上,作为 “中转站” 的纪念空间是通过对民众进行审美教育而发挥其教化功能的。具体而言,纪念空间让参观者自觉识别所在场域产生的美学意蕴,在无意识中自觉按照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改造自身,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与行为的转变。博物馆空间的设计与布局便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展示顺序如何安排、空间场景如何布局以及技术装置如何选择等都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参观顺序与信息的接收序次。不一样的陈设,不一样的场景,不一样的技术装置,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此外,在参观过程中,无声的史料引导着参观者对文物的有声解读,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心灵的感染、品格的陶冶与启迪,思想感情发生变化,原有的思想观念得以提升。通过对博物馆的空间美学进行解读,参观者获得了新的审美经验。同时,这种审美经验也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传达出独特的教育理念,让身临其境的参与者感受到一种直逼内心的震撼与共鸣,思想得到净化与升华。博物馆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召唤公众的习性改造,完成意识形态的传递。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场馆内的审美教育完全是在参观者自主认可、内心接受的情况下展开的主动性行为,是审美意义上主体的自我选择与塑造。在参观过程中,馆内的美学意义被公众捕捉与解读,爱国意识、身份认知、政治认同也被激发出来,符合现代化国家与文化审美意义上的合格公民也就潜在地被培育出来了。正如本尼特所说,博物馆提供的艺术智性活动 “能够以一种积极建设性的方式来改善大众的特殊精神活动与行为品质,可以成为培养公民计划的一部分”。毕竟, “博物馆和博物馆化的想象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由此可见,纪念空间能够引导人们接受和认可空间所宣扬的场所精神,以强化民众的思想价值认同,发挥无言的教化功能。
二、纪念空间传承红色记忆的必要性
随着革命年代的远去,红色记忆出现了 “代际递减” ;新的文化语境下,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错误思潮一时间甚嚣尘上,红色记忆呈现式微之势。同时,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交锋也使得价值的冲突与认同问题不断凸显,从而导致社会统一价值标准的 “不在场” 。加之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引起了大众内心的茫然与恐慌。时间流逝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存在,裹挟记忆危机而来的错误思潮导致价值迷惘的现象也在不断产生。面对错误思潮带来的价值整合中断与信仰引领危机,红色记忆的传承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和国家构建的纪念空间是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弘扬革命文化精神、内嵌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场域。应对错误思潮,如何进一步发挥纪念空间的红色教育功能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抵制技术至上主义对红色记忆的碎化
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为红色记忆的存储与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而且为红色资源的共享与传递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然而,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大数据如同毛细血管般侵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人们对网络技术的依赖日益加深,技术至上主义也悄然登场。作为一种技术拜物教,技术至上主义深嵌于人们对技术工具理性无以复加的信任、依赖甚至崇拜之中,导致工具理性不断走向自身的反面。技术至上主义对红色记忆附着的核心表征在于:一切实践活动甚至记忆实践都成为数字符码的从属物,技术先于人本身成为红色记忆的载体。这本身就是一种颠倒。网络信息技术在红色记忆领域的应用,本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填补记忆空白,却在工具理性扩张下颠倒了自身的目的与手段,让人们深陷技术依赖而拒绝依靠自身去记忆。事实上,无论网络信息技术如何进步,它都只是弥补人类记忆能力缺陷的工具,终归不能代替人本身。可以说,技术至上主义直接导致红色记忆主体的缺位。记忆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记忆,需要寓居于人的身体与意识中才能获得生命力,是一种 “属人” 的存在。然而,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与革新,技术逐渐取代人脑成为记忆的外部 “储存器” ,即机器代替人脑去记忆。当把我们记忆的工作交给冷冰冰的机器时,也主动选择了网络媒介附带的遗忘效应。
随着纪念空间向网络领域拓展,个体重温红色历史的活动被互联网的红色历史知识所取代,直观的历史感受活动也被虚拟的线上活动所取代。可问题正在于,网络归根结底是一种非人的存在物。这种网络信息载体仅仅只是记忆持续的物质条件,倘若个体不愿或不能 “自主地” 重温和更新信息,它们就会沦为 “失去灵魂的骷髅” 。红色历史知识终究不能等同于红色历史记忆,前者是例行公事地面对过去,后者则是充满感情地对待过去,强行混同导致的结果就是:这种 “碎片化” 的红色历史知识随时都可能被遗忘。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一面是互联网的高效便捷带来的繁华盛世,一面是互联网 “黑洞” 对红色记忆的撕裂与吞噬,红色基因失去其传承的重要一环。然而,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复活。历史的厚重感往往沉淀于跨越时间框架的纪念空间抑或 “记忆之地” 。作为历史的载体,纪念空间通过空间中的各种物质元素以及附着于上的元素符号,让有关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重要革命历史人物等的记忆得到实体化呈现。回顾历史,先辈们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奋斗史往往依靠亲历者的回忆以及档案馆、博物馆等纪念空间的见证物、藏品等载体保存与展现。纪念空间的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场景都印证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深度唤醒民众对于历史的思考与认知,对于抵制技术至上主义对红色记忆的碎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对红色记忆的侵蚀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红色记忆的传承必须回到其 “本体” ——红色历史中去。然而,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附着给红色记忆的传承带来了严峻挑战:它以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歪曲红色历史,以 “肆意恶搞” 淡化红色历史,以 “主观臆断” 中伤红色历史,使得共同体成员的红色历史记忆不断被消解。 “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如今,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手段与方式更为隐晦,它时常戴着 “学术面具” 、披着 “舆论外衣” ,借助学术活动、文艺作品、网络媒体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传播。这种隐秘的包装不仅遮蔽了自身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拓宽了传播的领域和平台,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性。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不断消解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一方面,它歪曲史实、颠倒是非,意图篡改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它抹黑爱国英雄人物,妄图解构历史记忆。美化反面人物、以 “小善” 粉饰 “大恶” 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惯用伎俩。他们以所谓的 “再评” 历史为幌子恶搞革命英烈,无限放大其缺点而抹杀其历史功绩,并随意捏造史实,企图扭曲真实的历史记忆。他们举着 “反思历史” “还原真相” 的虚假旗帜,混淆视听,试图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洗刷历史的红色属性,以达成其政治阴谋。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袭,红色历史遭到扭曲与亵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原有的红色记忆不断被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红色记忆的教化功能不可避免地遭受侵蚀,民众对于红色历史的领悟和体验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破坏,个人的迷茫感与怀疑感逐渐萌生,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理想信念也可能动摇。纪念空间是 “活的历史” 。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不断奋斗,留下了一大批颇具价值的红色遗存。纪念空间不仅对这些历史遗存进行保护与珍藏,而且借助空间布局、氛围营造、展品陈列、现代技术以及讲解抑或仪式展演等方式进一步还原历史现场,将那段栉风沐雨的红色历史 “活态化” 呈现。质言之,纪念空间能够将参观者带回历史场景,对于激发人们的政治情感,唤起革命的历史记忆,增强历史的正确认知,进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具有重要作用。
(三)抵制价值虚无主义对红色记忆的消解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也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作为一种攻击武器与斗争手段,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带有特定政治目的唯心史观,企图篡史乱今、动摇人心。通过 “虚无” 历史,扰乱历史认知,侵蚀价值观念,鼓噪不满情绪,进而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那么历史虚无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得以滥觞?这其实与它本身契合于社会长期存在的错误价值观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价值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投射与表征,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要想根除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彻底瓦解价值虚无主义。尼采曾言, “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传统社会 “绝对价值” 的失效与当今社会 “相对价值” 的未完成构成了价值虚无主义的出场逻辑,它引发了意义世界的萎缩与价值秩序的颠覆,成为现代社会深刻的精神危机。依照马克思对 “人的发展” 历程的划分,当今中国仍处于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的发展阶段,所以说这一时期依然需要重视物质层面的积累。然而,由于人们对于 “物质” 的过度 “膜拜” 与 “追捧” ,价值虚无主义与拜物教、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相互聚合,进而得以在社会中进一步地滋生与蔓延。人的 “超越性” 价值观逐步退场,缺乏意义支撑的现代人被抛入价值的真空之中。外加消费社会的侵袭,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被困于物质的枷锁中,陷入价值观的荒芜与迷失中,逐渐遗忘了生命本真的价值和意义。
纪念空间印证的是历史的风烟,追忆的是峥嵘的岁月。借助于历史的苦难叙事,它能够唤醒民众的历史记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然而,价值虚无主义的侵袭不仅使共同体成员陷入价值观的荒芜与迷失中,而且让纪念空间的教化功能也大打折扣。例如,如今一些博物馆、纪念馆的观光化与 “走过场” 现象日益严重,使得真正的参观者无法静下心来思考。长此以往,必然会对红色记忆的传承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作为传承与书写红色历史的重要场域,纪念空间传递的是无数中华儿女饱经磨难、奋勇拼搏的红色精神,留存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红色记忆。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意蕴与精神内涵,是纪念空间意义构建的价值基石所在。纪念空间不仅能够传承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而且能够增进政治认同、促进社会团结,具有引领社会价值、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作为红色文物的存储库与红色故事的资源库,纪念空间通过传递精神信仰、传播文化价值进而引领人们产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这正是纪念空间的核心价值所在。人们参观纪念空间的过程,也是对主流价值导向认知、内化和传承的过程。纪念空间能够让人们体悟到革命先辈为国家做出的努力与牺牲,明白生命真谛与肩上的使命担当,进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这对于破除物化逻辑,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抵制价值虚无主义的侵袭具有重要意义。
三、纪念空间传承红色基因的现实性
时空维度留存的记忆并非永恒的。随着红色记忆的 “代际递减” 以及当下错误思潮对社会的影响,红色记忆危机愈演愈烈。这不仅造成了共同体成员身份溯源与定位的模糊,而且也给政治认同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陷入新的彷徨中。基于这种现实,为实现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纪念空间应可以从 “知—情—意” 三维一体展开策略,即打造 “记忆之场” 以激活红色历史认知,推进 “仪式展演” 以增强红色情感认同,塑造空间景观以凝聚红色价值信仰,从而在实践层面上使纪念空间传承红色记忆成为可能。
(一)打造 “记忆之场” ,激活红色历史认知
皮埃尔·诺拉曾说:历史在加速消失。尽管人们不断借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历史介质再现历史事件,但随着时空的迁移,这种当下 “再现” 的象征始终与真实的历史现场存在一定的距离。那么究竟什么需要被记住,什么又需要被遗忘?哪些是可以谈论的,哪些又是需要保持缄默的?在以介质物堆砌的记忆里,历史的真实性如何保证?面对如今 “消费主义” 的整合与 “景观社会” 式的洗礼,曾经 “甘为祖国牺牲” 的民族情感渐渐消弭,碎片化的消费社会中历史又该如何书写,国家认同又该如何获得? “记忆之场” 就是历史留在当下的痕迹,是寻唤过往、建立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当战火纷飞的红色革命年代逐渐远去,在历史的断裂与存续之中沉睡的 “记忆之场” 亟待被唤醒。
纪念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 “记忆之场” 。所谓记忆,它是当下的现象;它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与器物等具象化事物中。既然作为 “经验到的与当下的联系” ,记忆自然能够基于现有的经验进行建构。文物的选择与摆放、场馆的设计与布局、技术的选用以及空间氛围的营造等过程也就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而记忆、历史、情感的勾连只能在特定的 “场所” 中才能发生,纪念空间就是这样的场所。通过特定场所记忆的建构,观者的价值情感与过往的历史记忆得以连接,从而认知得以唤醒、情感得以激发。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空间布局便提供了一个 “记忆之场” 的典型案例。在馆内,参观者需要经过重重暗道才能进入地下的每一个展厅。随着步伐的深入,厅内的灯光由亮变暗,仿佛走入一个 “洞穴” ,参观者的神经也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厅内的设置更加震撼, “万人坑” 遗骨陈列馆以棺椁状的遗骨为大门,让人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曾经的悲惨画面,内心为之一颤。进门后厅内灯箱、泥塑、油画、沙盘以及现代多媒体设备再现大屠杀的历史原貌,让参观者如身临其境,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此外,整个展厅空间狭小、光线昏暗、布局紧凑,都给人压抑与凝重之感,直击参观者的内心。这样的 “记忆之场” 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能够很大程度将历史事件的价值导向渗透进参观者的思维模式中,进而强化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当下的反思。可以说,以公共空间为依托,构建 “记忆之场” 有利于锚定和具化历史价值,对于进一步激活历史认知,促进共同价值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推进 “仪式展演” ,增强红色情感认同
记忆与仪式密切相关。红色记忆在被激活、复现、回忆以及建构的过程中,必然少不了政治权力的参与,而这些政治目标的实现常以仪式呈现出来。保罗·康纳顿曾言,纪念仪式 “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 “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通过仪式的展演不仅能够将曾经的记忆唤醒,而且在重复展演中能让人们产生习惯记忆,从而使记忆得以延续。因此,仪式时常成为共同体用以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方式。通过特定空间的仪式展演,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从而唤醒历史记忆,并在此基础上汇集情感、形成认同,最终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纪念空间就是这样一类仪式性场所,它将历史特定意义事件与过程进行教育赋能,以强化共同情感、形塑历史认知,最终达致个体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的统一。
纪念空间能够赋予历史事件或人物以强而有力的意义符号,并构建出独特的时空观,尽可能还原历史原貌,给予人再次 “体验” 历史的机会。这些是如何做到的?其实,纪念空间本身就是一个 “仪式性空间” 。以博物馆空间为例,馆内藏品以及展示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皆不是当下参与者真实经历,而是通过符号、文本及物件等介质进行重构,再经由受众的移情、想象进而产生了一个虚拟时空。通过营造独特的时空,博物馆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是某种意义上的 “神圣空间” : “一个博物馆或讲台——隔离了神圣与世俗、表演者与听众、超常与平常”。当人们踏入场馆,正逢 “阈限性” 的时空开启,一场红色朝圣之旅由此启程。此外, “任何一种仪式场所都是为某种事情的上演而预备”。作为传承红色历史记忆的场所,博物馆的参观过程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 “文化的展演” 。 “博物馆作为舞台背景,参观者扮演着某种角色。”将博物馆视作 “导演” ,提供一系列包括空间、物品、雕塑等 “场景设置” ;将参观者视为 “演员” ,参与展演。博物馆进行 “编码” ,让参观者自主 “解码” ,沉浸于 “剧情” ,从而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与 “场景” 一同融入意义的 “生产” 中。由此可见,仪式贯穿于人们参观纪念场所的始终。此外,纪念空间本身也是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的重要场所。庄严的纪念活动将特定的历史记忆镌刻进观者的头脑中,将红色的火种播撒进他们的心中,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总之,通过纪念空间的 “仪式展演” ,观者的认知结构得以更新,内心秩序得以重建,共同情感得以激发,这对于凝聚奋进精神、达成社会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塑造文化景观,凝聚红色价值信仰
红色记忆诉说着人们共同的历史由来,也凝聚着人们共同的价值信仰。这种价值信仰正是共同体成员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使命担当的重要力量所在。然而,历史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均具有抽象性。如何让深奥的历史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所 “认知” ,终究需要通过 “入眼” “入心” 的 “景观” 使其具象化。这里所谓的 “景观” , “并非意象的集合;相反,它是由意象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景观都作为现行制度的状况和目标的全部正当理由而存在着”。进一步来说,纪念空间背后的话语是通过其呈现的景观得以表达的,呈现什么景观,如何呈现景观便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涉及引导参观者获取知识的倾向性问题。因此,如何构造符合大众审美和情感共鸣的文化景观便成为纪念空间景观塑造的核心所在。
一方面,景观的塑造必须 “入眼” ,具有审美性。质言之,纪念空间历史文化景观的布置必须符合大众的审美。能否引起参观者的审美感受,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 “观馆” 效果。以博物馆为例,博物馆文化景观的构建可以从场馆的装饰摆设、建筑雕塑的风格选择、配套设施的安排等方面着手,最终构建出具有审美特性和艺术气息的现代性博物馆。例如可以充分运用墙、廊、柱等,形成文化墙、文化廊以及文化广场等人文景观空间,让每一面墙 “活” 起来。这样一来,博物馆的教化功能就能够以审美化的方式传达出来,在更大程度上唤醒参观者的情感共鸣,起到 “润物无声” 的效果。
另一方面,景观的塑造需要 “入心” ,能够增强价值认同。历史文化景观不仅要愉悦眼睛,还要浸润心灵,才能发挥其教化作用。如何让这样厚重的历史 “入心” ,则需要化抽象为具象,化无形为有形。要将纪念空间的历史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话语展现出来,可以通过建构多维的仪式符号言说系统予以实现。具体而言,即通过 “可见” “可听” 与 “可触” 的符号载体,使历史的精神内涵得以具象化地呈现。首先,通过视觉符号传递 “红色影像” 。正如索绪尔所言,符号是由 “能指” 与 “所指” 构成的。 “能指” 指的是符号的形象, “所指” 指的是 “能指” 所负载的意义要素。因此,当人们在观看 “红色影像” 时,不会仅停留在历史遗存本身,而是会不由自主地唤起内心深处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忆。可以说,借助具有历史感的建筑、图片、数字等象征符号进行红色叙事,可以 “复原” 历史本貌,唤醒人们的历史认知。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景观布局为例,馆内矗立着以 “家破人亡” “逃难” “冤魂呐喊” “胜利之墙” 为主题的四组雕塑,让参观者如临巨岩,望而生悲,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悼念广场上 “1937.12.13—1938.1” 的黑色大字触目惊心,即刻将参观者带入当年的时空场景中。此外,馆外还有一处以大片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名为 “墓地广场” ,代表着30万遇害同胞的累累白骨;广场上有三株枯木,隐喻着当年南京城1/3建筑被烧毁的残酷事实。这些视觉景观生动地还原了历史的原貌,瞬间让参观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创伤感同身受。其次,通过听觉符号引发 “红色想象” 。听觉符号可以构建出记忆文本进而嵌入革命精神,有利于 “红色历史氛围” 的营造,激活参观者对于历史情境的想象。在祭奠烈士时,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激越高亢的音乐,将记忆的个体拉回历史现场。再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有一个叩击灵魂的装置—— “12秒” 。 “滴答、滴答……” 每间隔12秒,就会有一滴水从高空落下, “滴答” 一声落入水中;在同一时间,墙上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倏忽亮起又熄灭,如此循环,直击人心,瞬间激活了参观者对于历史的想象。最后,还可以借助触觉符号进行 “红色体验” 。纪念空间可以通过直接的身体触感,给予参观者沉浸式的体验,使其主体性充分被调动起来。当观者亲身融入景观时,自然而然会放低声音、放慢脚步,不由自主地对纪念性空间的场所精神产生认同,记忆将会更加深刻。随着红色历史 “入心” ,参观者的情感流露以及思想感召也会渐次增强,进一步推动他们对纪念空间所传递的价值形成认同和信仰。总之,纪念空间中的景观塑造实际上就是红色精神具象化的过程。它将渺远的历史及其背后抽象的政治话语化为 “可视” “可听” “可触” 的景观,使红色历史精神更容易 “入脑” “入心” ,推进红色基因的 “动情” 传承。
四、结语
知来路方能明去路。纪念空间是守护与传承红色记忆的殿堂,它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参观纪念空间,唤醒红色记忆,其目的不是助长民族仇恨,而是创造美好世界;不是呈现历史面前个人的脆弱渺小,而是唤醒对生命的悲悯与崇敬。纪念空间不仅唤醒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且不断影响与形塑着人们的历史认知与价值信仰。在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发挥纪念空间 “红色基因库” 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 “桥梁” ,有待我们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不断地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