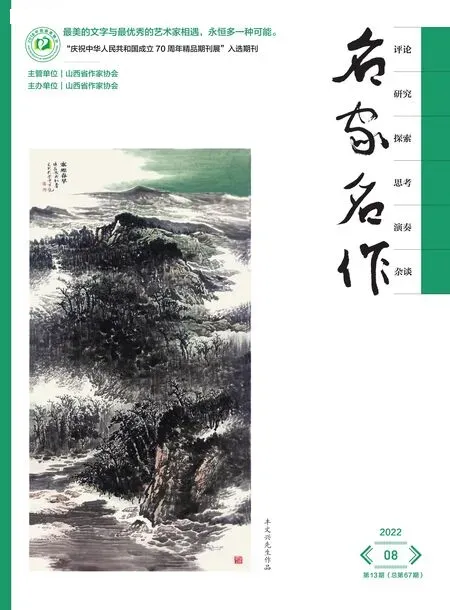浅析滨口龙介电影的改编风格
——以《驾驶我的车》为例
2022-10-30裴艳格李亚星
裴艳格 李亚星
自2015年影片《欢乐时光》入围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金豹奖后,日本导演滨口龙介逐渐受到国际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滨口龙介开始对现代人关系的疏离与脆弱展开深刻的反思和探讨。2018年,他又凭借轻松的小品式电影《夜以继日》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该片以较简单的商业化叙事方式,揭示了当代年轻男女关系的游离和家庭纽带的破碎。时隔三年后的2021年,滨口龙介又推出了两部上乘之作——《偶然与想象》与《驾驶我的车》,前者摘得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后者作为滨口龙介的集大成之作,荣膺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等。滨口龙介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以新锐导演的身份从日本影坛走上国际影坛,引得世界瞩目。
《驾驶我的车》主要讲述了舞台导演兼演员家福和他的编剧妻子音,两者婚姻稳定,非常恩爱,和谐的夫妻活动常常成为音的灵感来源。一次家福出差行程取消,临时返家目睹了妻子与年轻演员偷情。家福悄悄离开,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但痛苦与浓烈的爱只是被压抑下去,直到妻子意外离世,对妻子复杂深刻的爱又掺杂上自我逃避的悔恨与真相不得而知的遗憾,成为家福心中的一份伤痛而无法释怀。这是一部对观众有要求的作品,它需要观众全身心投入以适应多语言的转换,沉浸于缓慢的叙事节奏之中。滨口龙介用他极具特色的导演风格,成功融合改编了难度较大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他是当代最具才华的电影导演之一,并且仍拥有着上升的可能。
一、多义性文本的互动
《驾驶我的车》融合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加之滨口龙介自身的影视语言风格使影片多样化呈现。借助文学、戏剧、电影的三重嵌套,实现多义性文本的互动、多维感官的联通。
(一)村上春树的文学主体
《驾驶我的车》改编自村上春树的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由于村上春树长篇小说的情节枝蔓与主题极具复杂性,影视创作者对其作品的改编一般集中在短篇小说上。而村上春树的短篇在一定程度上一直维持着其主题的模糊性与现代性。在小说《驾驶我的车》的结尾,面对家福有关妻子为何与高槻有染的疑问,渡利的回答仅是“女人就是会做这样的事”,将其与“生活之苦”归结到一起。在作品中,我们透过主人公的视角观察到的是世界的表面,其下纷繁复杂的联系则不得而知,也无法索解。似乎村上春树所把持的核心观念是存在主义式的:事件的存在与发展、消灭有其自在的缘由,主体既无法确知也无法化解,而滨口龙介在此巧妙地化解了这种无法确知。
和电影文本截然不同,小说中所真正经历的时间不过是家福与渡利在车上的闲聊,然而村上春树却通过加福的回忆极大地延长了实际的叙述时间,并在其中引入了妻子与高槻两个有着复杂个性的重要人物。通过主人公们跨时空的“交流”,村上春树实际隐晦地铺展出了一个尚未为文中任何一人所真正洞彻的心理世界,这一点恰好与滨口龙介创作的志趣不谋而合。
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滨口龙介做到了忠于原著,将村上春树的核心文本准确呈现,从意象化的文字里找到最适合影像化的人物和情节碎片,剖析他们的灵魂和感受。例如,音以夫妻活动为灵感写出自己的故事,讲述给自己的丈夫,再由丈夫第二天转述给她,这个片段源自《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第四篇《山鲁佐德》。我们可以发现,电影是在小说《驾驶我的车》的基本人物和故事的框架下,以音之口嵌入了《山鲁佐德》中七鳃鳗和入侵的故事。人生和情感经过发酵,像一坛苦酒被小心拆封,后劲儿和余韵慢慢散开,村上春树文本里的细碎与飘忽不定的情节,与滨口龙介的优雅、敏感、悲伤完美契合在一起。
电影对小说情节的调整,也使部分角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补充。例如,小说的开场是在妻子去世几年后,修理车厂的好友给家福介绍了一个女司机。而在影片的开端是以音模糊的身影及冗长的台词为故事拉开序幕。由此,电影的前半部分将小说中家福的过去还原,让有关亡妻外遇的行径发生在家福的主观猜忌之前,以一般叙事的方式引向更为公平的道德审判。
(二)契诃夫的戏剧思想
电影中应用了两部话剧,一部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另一部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从《等待戈多》到《万尼亚舅舅》,电影的主角家福游走于这两部话剧的角色之中,他本只是一个匠人角色,但却在电影的最后完成了对万尼亚舅舅的极致演绎。
相比之下,滨口龙介对《万尼亚舅舅》文本的征用是全方位的:这部舞台剧占据了影片的较大比重,所涉及的人物也对影片有重要影响。它首先涉及高槻。他是插足于家福与妻子之间的重要人物,也是《万尼亚舅舅》中的演员。家福带着审视和报复的心理给高槻安排了一个“自毁”式角色,这也是这部舞台剧在亦真亦假间来回切换的部分。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家福,家福的成名作是《万尼亚舅舅》,妻子音在去世后和家福“对话”的载体是《万尼亚舅舅》的录音带,家福一度逃避、再度主演并最终成功的戏剧仍然是《万尼亚舅舅》。如果说在电影中音是一直缠绕着家福的不散的幽灵,那我们也可以说《万尼亚舅舅》是缠绕《驾驶我的车》的不散的幽灵。契诃夫的戏剧思想贯穿于滨口龙介的整部影片,且在电影文本中占有核心地位。
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与《万尼亚舅舅》中的人物形象相对照,实现了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双重互文。滨口龙介巧妙借用了《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念白,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化。我们可以从主人公家福的身上看到与万尼亚舅舅同等的迷茫无措、失去生活目标以及自身所反映出的时代的动荡。而戏剧中的索尼娅,也对应了其中的三位女性:和索尼娅共有着悲伤经历的允儿、和索尼娅一样失去母亲的渡利以及无数遍地重复着索尼娅台词的音。
滨口龙介在此使戏剧叙事与电影叙事相呼应:借家福之手,进行了一场多语言戏剧的实验。从戏剧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探索戏剧语言本质与建构新型间离效果的尝试——索尼娅的饰演者是一个使用手语的女孩。在电影叙事层面上,女孩和丈夫的晚餐邀请,让家福和渡利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切与温暖。在戏剧叙事层面上,手语的表达形式契合了契诃夫的内在戏剧性的风格。在原有的文本中,契诃夫通过停滞与沉默构建静态之美,在静态化的场景中隐含着内在的动作。滨口龙介舍弃声音通过手语来演绎,使得文本的内在戏剧性得以放大。
(三)滨口龙介的影视表达
在剧作方面,滨口龙介为了迎合文本而在作品中极大程度地克制了演员对白的表达。巴别塔式的戏剧排演段落阻断角色相互交流与建立外在情感关系的可能性,使得观众更加在意剧作内部情绪的流动。
家福要求演员不带情绪地一遍遍朗读台词,而在实际工作中,滨口龙介一贯偏好的工作坊拍摄模式与“不带感情朗读剧本”的剧本朗读特点和电影中戏剧排演桥段达成现实世界与电影世界的互文。根据滨口龙介的自述,他这套工作方法偷师于让·雷诺阿,而从电影史往前追溯则是布列松。模糊电影边界也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演员自身能动性,调动了演员情绪,保证了演员情感的真实即兴表达。电影结尾,滨口龙介彻底抛弃语言所能带来的直白力量,通过手语动作缓慢凝聚画面情绪,成功完成了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创作。
滨口龙介在《驾驶我的车》中真正贴近了其导师黑泽清“摄影机是记录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无限的他者的视线”的理论。《驾驶我的车》继承了《欢乐时光》中都市空间的选取——城市隧道步入内心,彰显个体精神的迷离,将《亲密》中对舞台表演的机械记录变成了戏剧《万尼亚舅舅》舞台上游离的幽灵,将《夜以继日》中暗流涌动的车内戏变成了情感审判修罗场。《驾驶我的车》中对于前作的继承与创新,实现了导演本身视听语言的一次大胆革新。
二、意象化符号的象征
滨口龙介经常把电影叙事空间设定在都市之中,在谈及都市中男女的生活时常常提到“性”这一概念。他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仍将“道路”隐喻为艰难的人生路,这时“车”便成为主角的情感寄托。他又引入“八目鳗”的意象,同时用“录音机”幻化着妻子的亡灵。
(一)用“八目鳗”消解父权
从内涵上来看,最先引入这个概念的是音,她讲述的故事有关一个前世是八目鳗的女孩。八目鳗通过啃咬的方式进入动物的尸体中进食,如同通过夫妻活动获取灵感的音。这里的八目鳗是音的意象,当他们失去自己的女儿后,夫妻二人一度陷入悲伤的情境,不但更换了工作,连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此时的音正如同女孩,不断地在家福的身上抒发私人情感,得到的回应只是没有感情的表达。此时的家福是小偷,也是山贺:一方面,他是音设想中发现的人,音用笔戳了小偷的左眼,男主也恰好左眼患有眼疾;另一方面,家福在目睹音背叛自己后,如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仍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也恰好对应了故事中的山贺。
从形态上来看,八目鳗像极了吸盘的嘴巴里长满了锋利的牙齿。它的形象十分凶狠,恰恰是对全社会向男权社会崇拜的倒戈一击。正如在几次昏暗的场面里的画面,就如同八目鳗吸附在岩石身上。这个符号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八目鳗具有治疗眼疾的功效,起到了一种男性赖以生存的作用,从而扳倒了父权地位,助长了女性形象。
(二)用“车”寄托情感
小说中“车”的意象并不复杂,它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男人对亡妻的思念。相比之下,电影中“车”所承载的内涵则复杂得多。“车”是家福练习戏剧台词的特定场所,同时象征着家福的内心世界。当家福听到配备司机时,固然产生了被陌生人闯入私密地的不安全感。但在相处中,“侵入者”渡利也一步步通过倾听和旁观走进了家福的内心深处,也在“车”里留下了故事。
车不仅仅是车,狭窄的驾驶空间也是情感的避难所。在规定右舵驾驶的情况下,家福的车的方向盘在左边,一开始就处于错位的岔道上。在错位的空间里,仿佛车才是真正的戏剧舞台。家福在车里的位置也从后排右边转移到后排中间和左边,直至副驾驶。影片的最后,渡利驾驶着和家福同款的车在韩国的街道行驶。这是渡利与生活的和解,她和家福因“车”结缘,又共同从车这个“避难所”里走出,回归到了自己的生活,驾驶着属于自己的车。
(三)用“录音带”掩盖缺席
滨口龙介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个小说中没有的因素——来自妻子音的录音带。正如滨口龙介多次在电影《驾驶我的车》的相关采访中表明的:“女性的不在场”正是男性恐惧的根源,主人公因为女性的出走或缺席进行自我思辨的这一行为,正是其脆弱的表露。妻子死后仍以录音带的形式继续存在,声音即场的真实感与死者的不在场产生巨大的割裂。除了平添了音这个角色的神秘性外,更赋予了车内空间一种跨越时空的超现实感。自此,就算音早已退场,却宛如幽魂般占据了整个影像空间,用不在场的事实倒过来再创造在场。
当然,遭到限制的不只有主角家福,看似自由的音身上也攀附了层层桎梏——是道德的规范,也是愧疚感的鞭挞。就连死后也只能以“录音带”的形式驻留于父权的凝视,承受隐形的拷问。正如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所说的:“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论他们自己。”此时的“录音带”成为一种可视化符号,来掩盖女性在影片中的缺席与不在场。
三、结语
影片《驾驶我的车》通过家福的职业、妻子的变化、渡利母亲的人格分裂等具象化事物,揭示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扮演他者,正如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的“人格面具”。人们为了顺从社会期望的先天倾向,从而表现出某种适应社会的人格。虽是人们生存的必需条件,但过度的压抑终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好在滨口龙介没有如此残忍,家福卸下了自己总是扮演着好丈夫的人格,在渡利的安慰下,直面了自己的痛苦和悔恨。
无论是村上春树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还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滨口龙介都将其通过“车”这个特殊的载体,承载了男主人公的过去、现在以及开放式的未来。家福一场场破碎的人生切片、断断续续的戏中戏,为我们呈现了人物放下过去、重新掌控人生道路的过程。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驾驶自己的车,而是如何在一段车程中愈合自己的痛苦。而真正由我们驾驶的也不只是车,还有我们掌控不了的自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