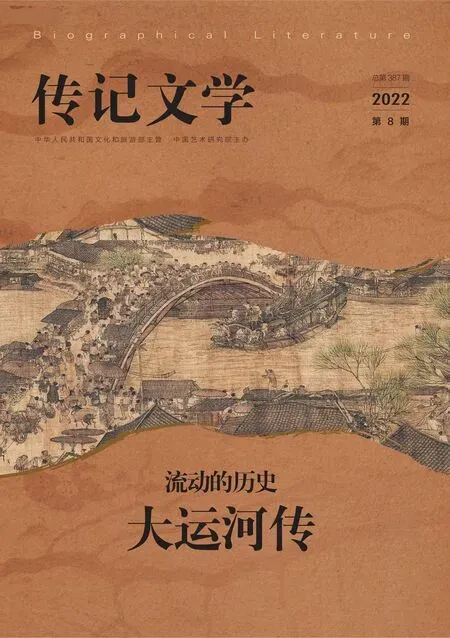中国古代传记观念与作为方法的传记
2022-10-28熊明
熊 明
听了王老师的讲座,关于传记或者传记文学,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我感受比较深:
第一,关于传记中人与事的问题。王老师刚才提到在中西传记史学观念中,对人与事有着不同的理解。相较而言,在西方的传记史学观念中,强调人;而在中国的传记史学观念中,一方面强调人,另一方面也强调事,二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关系。中国史学产生比较早,也比较发达,并形成了非常连贯的民族史。《春秋》和《左传》将人和事逐渐开始结合。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在纪传体中,人与事基本上是结合得非常紧密。围绕着人选取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来表现历史进程。早期像《春秋》《左传》是编年体,《史记》的产生,实际上也与史家对人事关系的认识有关。在早期史学领域,认为仅仅记事是不够的,人是参与历史的,要以人为中心撰写历史,于是有了纪传体的产生。纪传体产生之后,随即出现了《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接下来历朝历代形成了非常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体系,也就是民族历史的体系。
纪传体之后,我们看到编年体史书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在纪传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觉得编年体在记述历史事件、表现历史过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方面有突出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历代纪传体史书(比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外,也出现了相应的编年体史书(比如《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国榷》)。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的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完整、多侧面的中国历史的记录,实际上表现的是人们是以记人为中心,还是以记事为中心的选择。我们先辈们在这种选择中采取了折中策略,即把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当作正史,而把编年体史书当成一种必要的补充。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记史学观念在处理人与事的方面,很显然也认识到人与事不能和谐地在一部史书或者一篇历史记载中表现出来,所以就分而用之,以纪传体侧重表现人,而以编年体侧重表现事,纪传体与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双璧,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世特别有价值的遗产。
刚才王老师提到,西方把记事和写人分开,就是历史和传记。特别提到普鲁塔克的说法,把大事情让给历史学家去写,他只专注对人物的表现。我们祖先的智慧更融通一点,包括司马迁。司马迁在以人为中心,选取人物事件的时候,不仅仅有对人物个性的表现,更有重大事件的书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这实际上影响了传记或者说传记文学。在列传之外,随之大量兴起的杂传,在这个方面更进了一步。在专注重大事件的同时,又专注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小事,就显得更具有文学性。
前四史之后,纪传体史书的文学性是大大减弱了。即使是前四史中,这种文学性也在逐渐减弱。在史学领域,文史分科是必然趋向。同时,在该领域还有另一种倾向,即正史之外的杂传又展现出对文学性的重视——从汉魏六朝开始兴起的杂传,正好与正史、纪传体史书文学性逐渐被剥离的趋向相反,其文学性反而逐渐增强。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学性特色,突出体现在小说化倾向上。另外,随着文人大量参与杂传的写作,文章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倾向到唐宋以后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文人的传记创作成为后来散文写作的一种重要现象,从韩愈、柳宗元,到苏轼、王安石等,他们的传记写作有着文章化的显著特征,由于他们本身的文学素养,使传记创作体现出很强的文学性。这些在文学史中被称为“传记文”的作品,我认为,就是杂传进一步“文章化”的结果。这两种趋向是同时存在的。
第二,关于传记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问题。无论在古代传记,还是在现当代传记的写作中,是突出文学性,还是强调历史性,一直是并存的两大趋向。史学领域的学者传记写作很显然偏向于历史,尤其偏向于对于史料的重视。实际上也有将二者结合得非常好的例子。从中国古代来看,文人写作、文学化倾向显著的传记文,成为散文中的重要一体;同时,文学化和史学化相结合仍然大量存在于史部杂传类或者传记类中,或者称为传记的这一类作品。即使在史部杂传类中,传记体也在不断变化,历代都有新的创造。比如,到了宋代,杂传的新变,出现了专门对人物某一侧面,包括言行的传录,像李昉的儿子写他父亲,就只重视李昉的言行,而这些言行又事关军国大事,因为李昉做了宰相。而李昉的这些言行,由李昉的儿子来写,很显然就必然会带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他的文学性或者凸现出来的李昉的形象,就不只是正史列传中干巴巴的李昉的形象,而是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二者结合实际就体现了对于人在历史中作用的凸显,同时也突出了作为个体人的性格,从而把一个比较鲜活的历史人物呈现了出来。这种处理方式从古代一直到现当代作家,许多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文学性与历史性也并不是一种矛盾,并不是说传记文学的属性是文学,就不要真实。
第三,关于传记作为一种方法的问题。我们回顾传记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阶段是值得重视的,在《史记》中,传记体刚刚成熟不久,或许还无暇顾及或者细致考虑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到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史记》的文学性和史学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到了唐代,我们知道大史学家刘知幾《史通》里面专门有章节讨论传记,讨论列传。其中有一篇叫《杂述》,专门讨论“传记”——这个传记加引号,实际上就是小说。因为在唐代,小说也包含在传记范畴内,所以在这一篇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影响深远的理论,即把原先属于子部的小说也纳入到史部的传记中,提出了“偏记小说”概念。他定义的“偏记小说”,实际就一方面包含所有原先属于史部杂传类或者传记类的所有类别,也把原先属于子部的小说类包含在内。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既促进了后世传奇小说的兴起,也深深地影响着传记的写作。宋初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在收录唐代小说作品时,也把属于人物传记但不带小说性、不是属于传奇的作品大量收入其中。这就形成了传记和小说的互融。一方面,传记给了小说以体例,给了小说以文学体裁的影响;另一方面,小说也对传记,特别是对传记的写作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影响下,传记的文学化实际上也就成为一种潮流。宋代以后,传记文虽然录入了作者的别集或者文集,很显然文学性得到了承认。同时,录入史部的杂传或者传记,它的文学性实际上也体现得很鲜明。包括宋元明以来的学者,还有当代学者对此也都有论述。因此,我认为,无论传记史学观念下,还是文学观念下,文学性和历史性都不应该是一个矛盾或者是对立。
与此相关,我们看到近现代以来,传记(包括体例与技巧)不仅仅是用在了小说中,进入当代,传记已成为一种方法。比如,在西方流行的自传体小说或者传记小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以传记的方法来写作的小说。它们有很强的自传色彩,虚构性又特别强,在此,传记显然是作为一种方法在被运用。
传记成为一种方法,在中国古代其来有自,这种结合是一个历史潮流。实际上,在史学领域,强调传记历史性的观念,特别是从史学角度来强调传记的历史性质,也一直是存在的。比如,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就有很多论述,包括方志中的传记、正史中的传记等史学中的传记,他就提出,当时有很多人还有一个观念,不是史家就不要写史书,就不要写传记,这很显然是史学的观念。可见,传记写作也强调史学性或历史性问题。
我们作为传记研究者或者是创作者,也可以把传记作为一种方法来考察。实际上,结合当今现实和历史的实际,将传记作为一种方法,便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这一新视角,可以让我们避开传记与文学或者传记与小说的矛盾。面对自传体小说或传记小说,有研究者就提出一个“永恒之问”:我们到底如何区分传记?传记还是不是最初的传记?或者说还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传记?在我看来,如果将传记作为一种方法这一角度来理解,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总之,我认为,无论把传记作为文学,还是作为史学,都是一种视域或者视角,由此观照传记,传记应该是史,还是文,传记应该放在史学领域,还是放在文学领域,就没有必要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