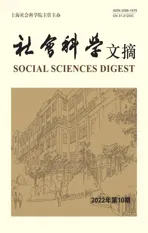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迷思
2022-10-26王义桅
文/王义桅
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创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夙愿,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自信和中国自觉。然而,这些思想均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系。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提法超越了“西方(West)—非西方(Rest)”对立,但忽视了“中国特色”和“天下无外”的中华文化传统。全球国际关系学如何确保不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折射或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扩张?而且其潜在思维逻辑是:西方有的,中国也会有;中国崛起,自然带来理论崛起。却忽视了两大特色:西方特色,理论特色。这是对三大核心概念的误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相对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有与西方对等对话的冲动,更进了一步,但还是有两个陷阱。第一是范式思维的陷阱。既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模式可粗略地概括为“中国特色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核”。不可否认,这种理论建构方式也能够对现实案例进行解释,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称为“中国学派”?第二是线性思维的陷阱。最关键的,忽视了时代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时代来临了吗?是不是批判西方中心又陷入中国中心?再说,理论是格局相对定型后的产物,处于变局下更多的是理念,难以形成理论。
思维陷阱背后是忽视国际关系理论的四个根本问题:来自何处——理论之根?是谁(为了谁)——理论之核?谁的理论——理论之场?去往何处——理论之魂?
理论之根(来自何处):国际关系的起点与发展演变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现代国际关系,由“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新教战胜天主教、确立主权国家体系开创,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国际关系史与世界历史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世界历史研究表明,“一个常见的误解,人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将宗教排除在政治之外,带来了和平。尽管从长远来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推进了世俗化,但它本身并不是完全世俗的和约。神圣罗马帝国只在基督教意义上才仍然是神圣的。宽容只拓展到加尔文宗信徒。其他异议者,以及东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被剥夺了类似的宪法权利”。“三十年战争非但没有使政治世俗化,反而让武力在帝国内部获取教派或政治目标的做法,声名扫地。”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担心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复兴给基督教文明带来威胁。近年,美西方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声称中国是“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国际关系的宗教色彩暴露无遗。
中国不输出也不输入模式,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自己,具有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文化根基,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明渊源。中华文化强调一分为二,中国外交政策强调不称霸,不干涉内政。中国的世俗文化没有产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使得中国人不经意忽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性。
理论之核(你是谁):从探讨中国特色到探究西方特色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试图补充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外交实践的遗憾。用中国的历史传统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或者历史文化去丰富完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道义现实主义、关系主义,引发国际学界高度关注,这是巨大进步。但相比而言,天下体系和共生学派,更具中国本土性、原创性,彰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主体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理论要统领这四大趋势,应该是普遍性的。改革开放,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及至新时代,强调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认知,这里的“中国特色”是外交自信、外交自觉的体现——彰显新型大国风范,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启主场全球化,应该也必然产生国际关系理论。
讲国际关系理论常常与西方画等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后来才提出西方性概念,这是很大的飞跃。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用西方国际关系分析法无法分析中国外交不说,还无法产生中国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主要是讲欧美,因为他们有基督教传统、罗马帝国扩张特性,有西方中心论情结。概括起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性体现在:
其一,强烈的基督教特色、强烈的国家性,主要指美国性。霸权只是美国性表现的结果,根源则是美国的基因:代表性的是“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
其二,西方中心论,维护西方既得利益,维护西方话语霸权,其思维方式是:(1)主体:民族国家,如何适合部落或现代国家没有形成的或一种文明(中国)?(2)客体:主权,如何关注那些没有能力捍卫自身主权的弱国穷国?(3)逻辑:权力,如何关注权利(益)?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里是空场,碳中和时代既是权力也是权利,既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交通运输和思维方式的革命。(4)系统:无政府状态是基督教世界概念,如何涵盖非基督教世界?
其三,无法剔除殖民色彩和种族主义阴影,为强者服务。人类步入工业4.0时代,出现“三非”现象——作为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基督教文明的中国开始领先,而此前的工业革命1.0、2.0、3.0都是西方内部循环,最后全部被收编为美国盟友,触发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神经。这是国际政治的潜规则。
其四,分的逻辑而非整体思维,以所谓的科学面目出现,导致理论乃片面中求深刻,方法论至上。其实,科学乃分科之学。问题本身是具体的,不可能分成哪个学科。
理论之场(谁的):以人的全球化超越资本的全球化
平视世界,首先要平视西方。正如梁鹤年先生所言,讨论“洋为中用”之前,要先知“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滥觞于世,在于其理论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化产物,“谁的全球化”?认清这一点,才能搞清楚,国际关系理论是“谁的理论”。
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倡导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一带一路”“双循环”开启主场全球化,也在开启主场国际关系理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为特征的超级全球化(super-globalization)走向终结,全球化正在进入“人的全球化”阶段。人们所熟知的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人的全球化,是所有人的全球化,追求的是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资本的全球化是有边界、关税等一系列概念的,是世界上部分人群所关注的;而“人的全球化”则表现为地球村的概念,是全世界所有人都需要关注的。疫情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再是“你与我”的关系或者国与国之间博弈的关系,而是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只有共同战胜疫情,人类才能安全,更加凸显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人的全球化”逻辑是:我通过你而成为我,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好,我才好。
面对“人的全球化”,我们需探索建立以人为单元的全球秩序,而这应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人的全球化”正在呼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大历史观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克服资本的全球化或曰庸俗的全球化,迎接真正的世界历史、真正的全球化,改变资本的全球化乃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扩张造成的中心—边缘体系,迎来分布式、网格状互联互通的新体系,迎来各种文明的共同复兴,克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世界悖论,克服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主权、民主、资本不可能兼顾),推动形成各国命运自主—命运与共—命运共同体。
理论之魂(去往何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
去往何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问这个问题,但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不重要。权力掩盖了权益,主权掩盖了谁的主权、如何捍卫主权这些根本性问题;西方的全球治理只问:为何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却不问:为谁治理?国际关系也不问:理论为了谁?掩盖这些本质问题的核心,就是宣称理论是普世的。
中国的“天下大同”观并非认为历史会“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秉承相对主义普世价值观,即“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性,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这表明,中西方观念分歧的核心是关于“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观”的争议。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才能拼出“普世价值”。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正如“文明”的概念一样。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指引。“两个结合”“两个确立”为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厚的理论滋养,也为学术自信奠定了五千年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党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呼唤我们打造通古今中外、融东西南北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可以说,“两个结合”“两个确立”树立新时代的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从崛起到复兴,创造国内、国际模式新形态。国内模式——有为政府加有效市场;国际模式——赋能-铸魂全球化:道德(向善),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1.0:中国式现代化;2.0:中国化全球化,从“被全球化”(globalized)到“主场全球化”(homeglobalization),再到“真正全球化”(genuineglobalization);实现全球化的中国化;中国化的全球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论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国际关系视角,代之以整体世界观,包括安全观: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们的安全;发展观: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合作观:平等合作,开放合作,包容合作;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观:天人合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作为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一分殊),由五大支柱组成:持久和平、共同安全、经济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实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四位一体,并上升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高度。如果说工业革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那么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实践探索,则是中国在自身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基础上吸纳工业文明的优点又超越其负外部性,为人类发展可能做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唤醒各国传统文化初心,共同面对人类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共同身份,是学者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旗帜,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具国际感召力的理念,不仅弘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传统中国外交准则,也为打造融通中外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时代机遇,呼吁构建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构建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
国际关系理论是欧洲经验和美国例外论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工业文明时代西方中心论在国际关系的表达,又带有浓厚的美国霸权情结。纵观人类文明史,你我关系经历了代际转化:游牧-农业文明时代,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工业文明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信息文明时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数字文明时代,我通过你,而成为我;生态文明时代,因为我们,我才为我(类似乌班图思想:I am because we are)。数字/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重要的修正,“双碳”成为100多个国家的共识,更重要的是数字文明正在超越工业文明的逻辑,数据成为新的甚至是主要的生产要素。
数据使用而不占有,越用越值钱,新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劳动力、资本的工业文明时代逻辑,这是美国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重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战略出发点。数字技术、数字规则和数据竞争,塑造中美博弈的基本框架。这个世界是多层化的,不能以一种理论套用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矛盾的国家,更不应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为国际关系理论到底贡献了什么呢?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里,大量强调中国因素,中国自己强调中国力量、中国市场,强调中国的外交实践,提出了很多外交理论,但是国际关系理论普遍不够。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化作为个案,丰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建构主义的关系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道义现实主义,都是“我注六经”。还有,就是以中国的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作为研究主题,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受美西方舆论影响认为这是宣传。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再造国际关系理论,这是时代的重大话题。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但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并没有还原为人类文明的转型,即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结合生态文明的思想,还原真正的世界历史来临的世界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还在人家土地上种庄稼,确立中国乃文明型国家形态,为世界秩序,乃至人类秩序塑造大理论,超越中国崛起思维,真正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开创自主的知识体系,来理解从文明自信到文明自觉,从现代化、现代性到全球性、人类性的主题转化,改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国家忽视人民、关注大国忽视小国、关注外交忽视内政、关注权力忽视权利、关注占有,忽视分享的倾向。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反思的应有道德。
讨论中国学派也好,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也好,要告别崛起的冲动,走出理论的迷失,走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迷思和比较政治学、比较国际关系研究的陷阱。中国经验非对任何一国之启示,启示的是整个天下;中国不是崛起,而是复兴;超越民族性假说、崛起的思维和线性进化的逻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追求自己的复兴,而且还原世界多样性,立己达人,希望各民族都能复兴,开启人类文艺复兴,因而不是探讨中国特色的问题,而是还原西方特色,成就各国特色,从而世界才特色,其逻辑是命运自主—命运与共—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崇人民中心思想,国际关系理论倡导人本主义,超越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告别西方基督教一神论的普世价值,推崇全人类共同价值,告别中心—边缘体系,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结语
汤用彤先生说过:中国接受佛学,第一阶段是求同,第二阶段是别异,第三阶段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似乎正在经历类似过程:首先是求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说的“特色”,实际上首先追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的认同、认可;其次是别异——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试图区别于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最后是合同异以达到更高的同——超越中国特色—西方普世的二元对立,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迷思。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走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三大迷思,说到底是走出西方迷思,树立“四个自信”,迎接真正的世界历史来临,呼唤我们思考理论的原生问题: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谁的,理论为了谁,理论依靠谁,怎么构建理论?探讨国际关系的元理论。
中国共产党倡导“两个结合”,赋予国际关系理论以温度和厚度,推动形成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多数人服务,关注发展中国家,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强者为中心,不是以权力为中心,不是以大国为中心,更不是以霸权为中心,不是简单的呼吁主权平等,而是确实增强这些国家维护主权的能力,参与主权平等的制度建构,强调命运自主—命运与共—命运共同体。
国际关系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形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反对西方理论,也不是去完善西方理论,而是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而是超越现代学科、科学体系本身,回到“以天下观天下”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超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层面,着眼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是人间正道,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的鲜明旗帜,推动从大历史观而非近代国际关系史,以人本主义而非人文主义作为底蕴,以真正的全球化、真正的世界历史作为理论之场,迈入真正的世界政治理论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也推动塑造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从参与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统筹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全球化赋能、铸魂,且正在开创全球化文明新形态,即告别基督教文明扩张式的中心—边缘体系,开创各种文明共同复兴、引领人类文明向数字文明、生态文明转型的新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的全球化核心价值观,主体上将全球上升到人类高度,形态上从相互依存上升到命运与共的层次,法则上从“化”(扩张)上升到共同体境界。中国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的形态,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甚至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的应有之义。
展望未来,在数字/生态文明时代,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超越中国崛起思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切实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观、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未来观,充分发掘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创立人本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华学派,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