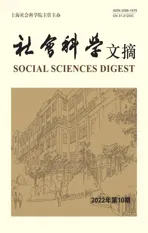“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值得深入反思的“两种自由观”
2022-10-26贺来
文/贺来
众所周知,伯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中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观,这一区分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热议的重大课题。但关于“自由观”的另一种区分,即“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的区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这两种自由观的性质和内涵以及二者的根本分歧进行深入分析和反思,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仅从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的“自由观”与近代哲学的“自由观”之间的比较分析这一视角,提出并切入此问题。
“抽象自由”:马克思和黑格尔对近代自由观的定位与批判
“自由”是近代以来哲学的核心问题,但对于自由的内涵和意义,哲学家们却形成了有重大区别的不同理解原则。这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强调的“具体自由”与其试图超越的自由主义的“抽象自由”的关系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抽象自由”并不是近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对其自由观的命名,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从自己的自由观出发,对前者所做的批判性指称。在黑格尔看来,作为现代性的最核心成果——自由主义哲学家们所极力阐发的“个人自由”,相对于“主观性自由”阙如的前现代社会,无疑必须得到肯定。但由于这种“自由”是脱离伦理实体的、以知性思维逻辑割裂个人“主观性的自由”与伦理共同体辩证关系的自由,是一种脱离具体情境的,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之间的分裂为前提的自由,因而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自由”。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自由观有着多方面的批评,但他同样认为,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所形成的“自由观”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因而所体现的是“有产者”的“自由”,是以掩盖和扭曲真实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形式性的、外在的“自由”,因而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自由”。
哲学史家们普遍承认,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应是黑格尔哲学的深层动机之一。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启蒙的本质归结为“个人自我主体”的绝对化和普遍化,并认为它构成了近代自由观的深层根据。
以这种绝对化和普遍化的“个人自我主体”为根据所理解的“自由”必然是一种无质料的、形式的自由。黑格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把康德作为典型,批判其所代表的自由观的空洞性,指出其把个人的自由意志为根据所形成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和法的原理,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无内容的先验原则。
更严重的是,这种以绝对化的“个人自我主体”为根据的自由必然导致个人与共同体的内在分裂并因此导致社会共同体崩溃,因而是一种知性的、缺失共同体背景的抽象自由。
最重要的是,这种绝对化的以“个人自我主体”为根据的自由因其知性和独断必然走向反面,从自由的追求和捍卫者转变为自由的敌人。以“个人自我主体”为根据的“个人自由”所宣称的“普遍性”是一种充满着暴力的虚假的“普遍性”,“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恐怖”乃是一个铜币的两面,二者是内在相通的。
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对近代自由观的批评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视野。不过,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唯心表达”,其实质是把“资产者变为神圣的自由主义者”,就此而言,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同样把它归结为“抽象自由观”。
概括而言,马克思对这种“抽象自由观”的“抽象性”的批评主要有如下要点。第一,批评这种自由观所自诩的超历史性和绝对性,指出这种自由观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体现因而具有内在的偏狭性。第二,揭穿这种自由观所宣称的和谐的“理性王国”的幻象,反思其所包含的内在分裂和冲突,他认为这种自由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和“自私自利的权力”基础上。
在把近代自由观定性为“抽象”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有着共同的旨趣。他们一致认为,近代自由观所主张的“自由”并不是“本真”的、理想的“自由”,必须超越和扬弃这种“抽象的自由”,寻求和确立与之相对的“具体自由”。
以“具体自由”超越“抽象自由”: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新型“自由观”
在黑格尔看来,“具体自由”之“具体”,最根本的体现在于,它克服了“个人自我意识的自由”这一特殊性原则与“伦理共同体”这一普遍性原则之间的知性分离和对立,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在这种辩证统一中,“个人自我意识的自由”在伦理共同体的中介中克服了彼此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实现了“我即我们”“我们即我”的“相互承认”和“内在和解”,“伦理共同体”也将在既扬弃“个人自我意识的自由”又容纳了“个人自我意识的自由”的基础上成为“自在自为”的伦理实体。
要克服这一分裂和矛盾,就必须超越以市场理性为根据的市民社会,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提出了其著名的国家理论。黑格尔把国家视为克服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和冲突,实现二者内在统一的伦理实体。国家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超越了市民社会以“个人主观性”为核心的形式自由,而达至了“具体的自由”。
以黑格尔对“具体自由”的上述思想为背景,我们就可以深入地理解为何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会聚集于黑格尔的“国家观”。在基本的理论旨趣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均致力于克服“抽象自由”并寻求“具体自由”,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阐释的“具体自由”,并没有真正彻底摆脱自由观问题上的“抽象性”,这在其“国家观”中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因此,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及其所表达的“具体自由观”,是澄清和确立自己“具体自由观”的恰当切入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一开头就直指黑格尔关于“具体自由”的规定,马克思这样概括黑格尔的“具体自由观”:“具体的自由在于私人(家庭和市民社会)利益体系和普遍(国家)利益体系的同一性(应有的二重化的同一性)”,围绕着其“国家观”对此进行深入解剖和批判,构成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枢纽和轴心,同时也成为马克思其后思想探索中不断深化的根本主题。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多个层面展开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具体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被黑格尔视为“具体自由的现实”的“国家”恰恰是“抽象自由”的体现,要实现“具体自由”,不能把“国家”视为“市民社会”的“真理”,而是要深入“市民社会”这一更为深层的社会生活基础,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改造,重建人们一种把每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内在统一的新型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在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它不仅不是“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解决,相反,它是“市民社会”内在分裂的必然产物。当黑格尔把“国家理性”当成“社会理性”时,他实质上是以一种虚构和扭曲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社会本性。政治国家不仅不是市民社会矛盾的克服和解决,相反,它是市民社会矛盾的反映和体现。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国家视为“具体自由的现实”,实质是混淆了“前提”和“结果”,因而是犯了“头足倒置”的错误。
因此,要实现“具体自由”,必须另辟蹊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人民主权”和“真正的民主制”概念,形成了“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民主制即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等重要命题。在马克思看来,“普遍和特殊的统一”的“具体自由”不是在政治国家中,而是通过“人民自我规定”的、“真正民主制”中才能实现。在这里,“民主制”的内涵完全不同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而形成的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制”,因为“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它所意味着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的生成。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和“新唯物主义立脚点”的革命性见解,到《资本论》手稿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描述和论证,马克思不断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这构成了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重大主题。
在马克思看来,“具体自由”与社会关系的性质是内在相关的。每个人的生活状态、生存品性和生存命运受特定社会关系性质的规定,人的自由程度与社会关系的合乎人性的程度内在地关联在一起,因此,“具体自由”要成为可能,就必须改变与人的生存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并创造与“具体自由”相适应的社会关系。
这种与“具体自由”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作为“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体现在对市民社会个人主观性所代表的特殊性原则和抽象共同体所代表的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双重扬弃和超越。马克思在不同阶段的著述中,曾用“人的类存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自由的人联合体”等概念表达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其深层指向是一致的,即“具体自由”不是建立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而是以人与人的结合为前提的,正是在这种“个人”与“共同体”的互为条件和交互关系中,“自由人联合体”取代前现代社会的抽象“共同体”,也取代现代社会抽象的“个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外在联系,并使“具体自由”真正成为“现实”。
对“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两种自由观的前提性反思
反思现当代哲学对自由课题的探讨,不难发现,上述关于“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的分歧,构成自由观问题争论最为深层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源头之一。上述“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两种不同的自由观所蕴含的一系列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的反思。
首先,这两种自由观推动人们反思:“自由”的真实主体和真实载体究竟是什么?或者说,究竟应该是“谁之自由”?这是“抽象自由”与“具体自由”这两种自由观所蕴含的根本性的前提性问题之一,也是当代哲学自由观争论的焦点问题。
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看来,黑格尔批评近代“抽象自由观”把“原子式的个人”作为“自由”的主体,马克思批评它把脱离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虚构的“鲁滨逊式的个人”视为“自由”的主体,其指控并无充分根据。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还是康德,当把个人视为自由的真实主体时,并没有也不会把“个人自由”与“他人”与“共同体”的自由对立起来,相反,正是把个人视为自由的真实主体,才使得社会共同体的自由真正成为可能的基石。
与上述立场不同,以麦金泰尔、泰勒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以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商谈伦理学观点等,均反对把主观性的个体视为自由的主体,认为如此理解自由,其付出的代价是与社会共同体中其他个人之间的“共同感”的丧失,主观主义和情感主义的泛滥以及个人美德和公共美德的消解,从而使“个人自由”陷入“自主性的幻觉”。基于这一判断,他们共同要求超越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观,寻求“真实的”自由主体。虽然他们具体的阐发各有侧重,但都致力于寻求比“个人”更为“具体”的“主体”作为“自由”的承载者。
其次,在上述两种不同理论立场的论争中,所内蕴的一个内在相关的中心问题是:究竟应如何对待和安置“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这是需反思的另一重大课题。
正如黑格尔、马克思和当代“具体自由观”的坚持者所强调的那样,近代自由观把个人视为“自由”的主体,其最根本的困境在于它将个人视之为绝对的、终极的存在者,这使得作为自由主体的个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独断和专制性。但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是,对实体化的个人及以其为主体的自由观的批判是否意味着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由彻底失去其独立意义?如果不持彻底的反现代性的立场和观点,承认和肯定“现代性并未完成”的基本判断,那么,在对待现代自由观的态度上,我们在祛除和解构其实体化弊病的同时,仍需相应承认其不能被完全否弃的存在合法性。
最后,当哲学家们试图扬弃“抽象自由”并以“具体自由”取而代之的时候,需要回答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在“具体自由”的实现中,如何寻求和确立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的普遍自由之间内在统一的真实基础和现实中介?
对此问题,黑格尔是以形而上学的思辨结构为根据寻求解决的。以理念的“具体的普遍性”,超越知性形而上学的“抽象普遍性”,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重大原则,所谓“具体普遍性”,就是包涵个别性和特殊性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黑格尔的“具体自由观”正建立在它对“具体的普遍性”这一形而上学理论原则上。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实质上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在此基础上,所谓“具体自由”所实现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被归结为“逻辑的普遍性”,它对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容纳终究难逃虚幻。
在黑格尔之后,克服这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解决方式,寻求二者统一的真实基础,成为论证“具体自由”最为重大的任务。马克思以对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自觉理解为根据,以“关系”代替“实体”,以“不同个人的社会性结合”代替“思辨概念的普遍性”,为“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的统一确立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形而上学思辨结构的崭新路径,从而为推动和深化这一问题开辟了一个重要的视野。但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也为后来的理论和实践留下了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化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