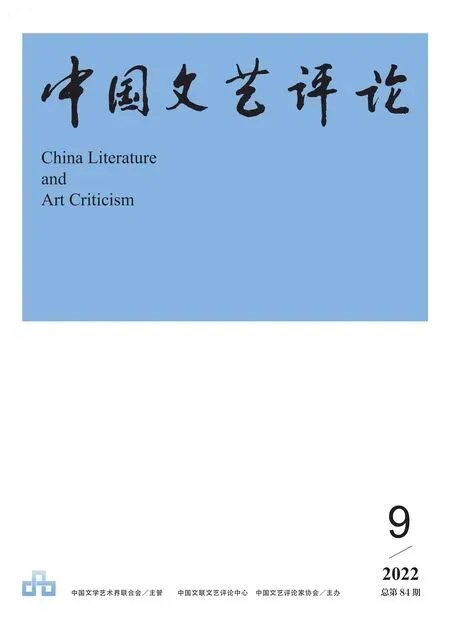以“中国性”建构民族命运共同体
——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新观察
2022-10-25赵卫防
■ 赵卫防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已经成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艺的重要显现,同时也是建构民族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些影片观照到了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当下生态与风貌,并有着对传统的思考与扬弃。在对白形态层面,这些文本中除以普通话对白为主的常规作品外,还有较多的少数民族母语电影以及以混杂的多民族母语为对白的影片;其作者群体中,少数民族作者占据了一定的主导,使其显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叙说。这些均使该类影片创作呈现出多元与丰富的状态。
一、以国家意志的建构书写“中国性”
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中国性”,主要是指其中展现出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制度、中国实力、中国现实、中国策略及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在展现上述中国元素的同时,还将其动态的发展与新时代内涵进行对接,构筑中国价值观和国家意识。这些影片中的“中国性”表达呈现为多个方面,而国家意志的建构和国家意识的书写,是其主体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便成为国家层面建构主体话语、获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面。新生的多民族国家为建立稳固的政权,需要将少数民族纳入民族国家的系统工程建构,而此时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便成为这种建构的主体元素之一。这种建构体现为在影片中直接表达国家意识,即使其中具有少数民族文化、风貌、人物等“主体意识”,亦是围绕国家意识来进行描写的。因而,银幕上不论展现哪个民族,抑或是何种风情,都有国家意识在场,最终指向的都是阶级斗争或新中国建设。《五朵金花》(1959)、《刘三姐》(1960)、《冰山上的来客》(1963)、《农奴》(1963)、《阿诗玛》(1964)等少数民族题材的经典之作,均是以民族特色建构出国家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国家意志的建构和国家意识的书写,使得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构筑起了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充斥着浓郁的“中国性”。在此后的流变中,少数民族的作者逐步增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美学呈现逐渐丰富,还出现了少数民族母语电影等多形态文本,该类题材电影中的少数民族“主体意识”也逐渐增强。然而,这其中的国家意识却依然贯穿,且在国家意识之外,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精神气韵等也蕴含其中,“中国性”表现日渐多元。
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更是呈现出了复杂的生态,但国家意识仍是贯穿主线,其国家意志的建构也在延续以往的基础上显现出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本中开启了多角度的共通性价值表达,并且以新时代的内涵呈现出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使其国家意志传达和国家意识的表现呈现出多样化和深度化的特色。

图1 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剧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年来,在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这种以国家意识统领下的新的“中国性”表达,首先体现在对新时代国家意志的传达上。这些影片将“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中国新时代的国家意志,与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风貌和历史进行对接,赋予了“中国性”以别样的表达。如表现当下苗族生活的《十八洞村》(2017),实际上是在传达精准扶贫的新时代国家意志,片中的苗歌苗鼓、喝“血酒”以及其他的苗族独特性表现,其目的并不在于刻意谱写苗族文化本身,而是在更好地展现出驻村公务员小王和被“帮扶”对象“杨家班”之间逐渐建立起理解与信任的过程。这其中的民族风情展示对影片所呈现的国家意志和时代重大主题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5)、《远去的牧歌》(2019)等影片则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少数民族文化相勾连,将这一新时代的国家意志进行更具体细腻的诠释。如展现哈萨克族牧民由在草原的轮回迁徙到最终定居生活的《远去的牧歌》,表现出了牧民们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的心理变化。影片没有将游牧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定居生活方式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对比判定,而是以新时代的笔触写出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国家意志与哈萨克族游牧生活习惯之间的张力,最终落笔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时代主题。《你是我的一束光》(2022)则更是直接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融进现代的爱情故事之中,演绎新时代的主题。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国家意志的建构和国家意识的书写,其次体现在对“民族团结”“反极端宗教思想”“护边”等国家层面的民族政策表达上。如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塔克拉玛干的鼓声》(2017)直奔民族团结与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时代主题,但影片并未立足于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对维吾尔族的纳格拉鼓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元素的表现,来将上述重大主题更好地落地。影片讲述了政府派驻的工作队一心想驱散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个曾经的“鼓乡”中由极端宗教思想带来的压抑生活氛围,而传统的纳格拉鼓的鼓声能否响起则是其重要的标志。在工作队的努力下,维吾尔族少女实现了舞蹈梦想,村民们也重拾鼓槌,天山脚下响起了久违的鼓声。影片以这一民族的独特性演绎出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另一部新疆题材的影片《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2022)表现的则是大学生选调干部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村庄驻村的故事,影片呈现出的国家意志更为多样,文本中将民族团结、扶贫、乡村振兴、护边等重大的新时代主题融为一体,以塔吉克族的生活现状和民俗文化较好地演绎出了国家意识和时代主题。
总体而言,这些影片均是以少数民族的“主体意识”来体现国家意志,表达中国之于新时代的重大主题和其他时代关切,以此来演绎新时代的“中国性”。影片以这种方式使得观众对国家意志多了一份真切的理解和认识,对时代精神也有了新的解读。而这种新时代的“中国性”表达,更是将少数民族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制度、中国实力、中国现实、中国策略等紧紧勾连在一起,形成新时代的民族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和中国式情感的别样表达
在近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中,国家意识和时代主题的表达,是其“中国性”书写的重要方面。而以少数民族的独特性为视点,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共同性的中国式情感,则是其“中国性”表达的另一重要路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个体之间的人情表现亦是中国式人情的重要方面。近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或对少数民族地区现实问题有着热切观照,或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历史进行独特思考,都逃逸出了纯粹的民族特性的简单表述,寻求各少数民族和整体中华民族之间的最大情感公约数,通过少数民族文化及人情的表现,展现出了具有共同性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式人情,这种“中国性”的展现,也使其获得了建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

图2 电影《红花绿叶》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苗苗执导的《红花绿叶》(2019)讲述了生活在中国宁夏西海固乡村的回族青年古柏和阿西燕之间的情感故事。影片在以少数民族人情展现共同的“中国式”人情方面最具代表性。影片中,古柏自幼患有顽疾,阿西燕也因心爱的男友辞世而走不出心理的阴霾,他们不得已的婚姻在一开始便预示着不幸,但在中国回族的日常和礼节中,这桩看似不幸的婚姻在两人相处、相爱、相离的各种重复中,却培育出了幸福的果实。影片以中国回族青年男女情感表现作为切入点,实则讲述了中国普通年轻夫妻之间经历情感波折而选择的人生态度的故事,表现出在来自中国大地的坚实的文化支撑下,中国式人情推动了美好人性的回归。影片以此试图完成一种中国共通性的情感表达,这里的少数民族元素只是创作者进行中国共通性情感表达的一个独特路径而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中国人共通性的情感,表达对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认知与选择,影片也以此获得了较强的“中国性”。
以《冈仁波齐》(2017)为代表的表现少数民族群裔信仰的影片,亦是以新的角度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表达出了别样的“中国性”。出自汉族导演张杨之手的影片《冈仁波齐》讲述了以尼玛扎堆为代表的11个不同境遇的藏族人历经艰辛结伴前往神山冈仁波齐朝拜的故事,记录了他们在朝圣路上磕长头行走的过程。影片以藏族文化的个性和风致重点展现了藏民族的信仰,而这种虔诚的信仰,彰显了藏族人民真诚善良的品格和纯粹的精神世界。影片以藏民族信仰的光辉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心态中的真善之美,正是有着这样坚定的信仰意识和优美的品性,我们民族才衍生出了澄澈无畏的生命和灵魂。而影片对净化心灵、慰藉灵魂的追求也超越了单个藏民族的信仰,成为当下社会群体共同的诉求。由藏族导演松太加完成的《阿拉姜色》(2018)亦是藏族朝圣题材的影片,该片将关注重点从朝圣本身转向了情感的表达,表现藏族妇女俄玛为了完成前夫的遗愿不顾病体踏上朝圣之路,她一路长跪磕头却在半途中去世,其现任丈夫和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继续替她完成遗愿。在这一追求信仰的过程中,继父与儿子由相互隔膜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影片观察藏族文化下潜藏的人情人性,在信仰这一独特视点下,呈现出的是被普遍的中国观众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亲情,较好地完成了中国式的家庭伦理表达,引发了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亦是对“中国性”的一种深刻诠释。
汉族导演韩万峰推出的一系列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则以汉族创作者的角度诠释少数民族文化,并寻求其与中华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的共通性。他的前期作品如《锹里奏鸣曲》(2011)、《云上的人家》(2011)、《马奈的新娘》(2013)等主要采用更能够体现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叙事方法,力图保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纯粹性。在近期的创作中,韩万峰导演则一改之前的少数民族“原生态”美学呈现,将少数民族个体放置在现代化的城市场域中,以此获得了对中国现代化思考的新角度,体现出了更为浓郁的“中国性”。
当下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以少数民族的独特书写来输出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中国式人情,获取了“中国性”。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这些影片又以“中国性”为主体,寻求各民族之间的最大情感公约数,链接起了各民族之间的生存和情感状态以及未来想象,构筑起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三、“中国性”表达的艺术手段
近期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以国家意志的表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营造出别样的“中国性”主题,呈现出了建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在叙事结构、镜头语言运用等形式层面,这些文本也以丰富、多元而独特的手段,完成了其对“中国性”主题的诠释。
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在叙事上发生较大的转向,充分发挥了类型叙事和民族志叙事的优势,但又未陷入其中,选择了与其他题材影片创作同步的多元叙事。这一时期的该类影片中,类型叙事和民族志叙事等多元叙事手段经过新的配比与融合,在表达民族特性的同时更为深刻地诠释了“中国性”。这样的叙事手段,使得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既没有成为将少数民族特性奇观化的商业类型片,更没有因纯粹的民族志书写沦为无人问津的“情怀”电影,而是成为一种以民族特性来深刻而多元地呈现出“中国性”的新人文电影。这种美学手段,使得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与时代同步,成为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手法。
对视听语言的追求,是近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形式层面呈现出的第二方面的特色。立足于“中国性”的表述,该类影片亦将类型叙事、民族志叙事等多元叙事手段融合起来,在视听语言上呈现出了独特的追求。其一,用多元的视听语言更为确切地表述国家意志和民族心理。如《阳光照耀塔什库尔干》使用大量的移动镜头和变化丰富的镜头调度,向观众展示出了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下的塔吉克民族村落——皮乐村的自然风貌和民俗风情,以及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塔吉克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以摇镜头为主的移动镜头,既将帕米尔高原之下的皮乐村进行了“中国”的地理定位,又让观众可以真正走进塔吉克民族的生活环境,深入了解在中国新时代语境下这一边陲民族小镇中人物的情感状态。影片以这样的镜头语言,较好地完成了对“中国性”的讲述。而《冈仁波齐》则选择了更为平实的镜头语言,影片的影像朴实无华,主创将镜头聚焦于普通藏民,深入到了个体的灵魂中去,并将人物置于西藏壮丽的景色之中。影片因对朝圣者们细腻捕捉而产生的一种心灵的壮美,也深刻阐释了中国人的信仰之力和纯真之美,以简单的影像营造出了神奇。《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则在声画的处理上凸显特色,维吾尔族音乐贯穿于影片的抒情段落,具有民族特色且略感粗犷的民歌和弦声在影片中也时隐时现。这些声音元素在表现民族特色的同时更表达出了维吾尔族同胞的时代情感。该片的声音特色更体现在鼓声上。影片中的鼓声,由弱而强,由散而整,开始时只能听到单个的鼓声,之后的鼓声第次增加;渐渐地,鼓声唤醒了村民们的灵魂,终于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气势。影片结尾整齐而响亮的鼓声,在感恩祖国的同时,更体现了新疆各族儿女追求幸福生活、建设美好家园的真心诉求,也是对“中国性”最完美的表述之一。
其二,近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视听追求,还体现为以风格化的镜语体系来体现少数民族的某种文化肌理以及个体的心灵视像,特别是在藏族作者松太加、万玛才旦等人的作品中,这种风格化更为明显。松太加擅长于将镜头贴近人物,精确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及变化;而万玛才旦则较多以长镜头和隐喻手法诠释深邃的思辨价值。前者如《阿拉姜色》中,妻子在朝拜途中病逝,临终前对丈夫讲出她坚持要去朝拜是因为对前夫曾许下诺言。这时镜头表现现在的丈夫握着妻子的手松开了,镜头先是离他们很近,然后摇上去,对着帐篷,成为一个白色的空镜头,下一个镜头是丈夫的主观视角:摇晃的通道。这组镜头表达出了丈夫的内心:他爱着妻子,为她的去世而伤心,但妻子临终告诉他的秘密又让他感情受挫,他的情感世界摇摇欲坠。贴近人物内心的镜头语言既呈现出了人物的痛苦与迷惘,又表达出了对这种心绪的理解与同情。主创以观众能够读解的电影语言消解了民族、地理与文化的差距,使观众代入其中、产生共情,完成对中国人共通性情感的表达。
与松太加贴近人物、传达心灵视像的镜语风格相比,万玛才旦则更为写意。长镜头是他影像的标配之一,他执导的数部影片中第一个镜头大都是一个长镜头,这种镜语赋予了他的电影一种深切的凝视感和庄严的仪式感,让观众感觉到镜头后面的导演是一个思考者,观众能够沉下来进入他的电影世界,观看他的电影并接收他深刻思辨的过程。如《塔洛》的首个镜头就长达12分钟,在这个长镜头中,开始时是塔洛与派出所所长分别处于画面两边,表达出一种平等的关系;之后画面进行了内部调度,要补办身份证的塔洛站在桌前弯腰询问所长,二人由原来的平等关系转变为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在这个充满仪式感和孤独感的长镜头中,万玛才旦以简单的层面调度完成了中国式的人情书写,也让观众触及到了他深刻的思辨。使用象征、隐喻性的镜语,为万玛才旦的另一重要的影像风格,其遵循了藏族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喜欢运用象征、隐喻、寓言表达一些最基本的善恶、因果等观念。但万玛才旦的镜语力求一种更具思辨价值的隐喻,这在其《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作品中有着更突出的显现。如《气球》中就存在大量的色彩隐喻和动物象征,其白色代表着死亡和不吉,用避孕套吹成的白色气球意味着对生命的阻止;红色代表着吉利和希望,红色气球是玩具,也是希望的代表,而种羊则隐喻着生命的孕育。以这样带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镜语,万玛才旦完成了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以中国视点释出了另一种深刻的“中国性”。
其三,近期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视听追求,还体现为对歌舞等具有少数民族文艺特色的视听表现。对少数民族歌舞的表现,是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传统美学手段,如傣族的孔雀舞、瑶族的花瑶舞、白族的民歌、苗族的笙歌等都因其视听特性和文化内涵而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重要视听元素,也是该类影片进行“中国性”书写的重要呈现。在近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中,如《云上石头城》(2017)、《侗族大歌》(2017)、《你是我的一束光》等也延续着这种手法。其中《云上石头城》较多出现纳西族人身穿民族服装、围着火把堆、手牵手跳着民族舞的场面,影片以简洁的镜语表现出了他们的舞蹈动作既简单又统一,充分体现出民族的群体性,象征着生活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而《侗族大歌》使用了最具代表性和国际传播力的二十多首侗族歌曲将剧情串联,这些歌曲展现出了侗族人的淳朴和侗歌的美妙。其中的婚礼歌舞,从舞蹈到典仪再到民俗,更是透视出了侗族最核心的文化,还避免了民族舞蹈的加入造成的叙事障碍。而歌舞所表达出的情感,跨越地域、民族和文化,成为融通整体中华民族的情感。《你是我的一束光》则以经典影片《五朵金花》作为IP,讲述了五位个性鲜明的少数民族女性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生活和音乐梦想的故事。片中展现出了壮丽的云南大地以及独具特色的白族风俗、服饰文化等,展示了新时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形象。而影片中出现的多段歌曲,既有原IP中的多首经典老歌,又有《你是我的一束光》等当下的音乐创作,如此的新旧组合不仅保留了原IP的经典艺术魅力,更对新时代精神进行了诠释,体现了地域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融合。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歌舞来营造视听,以具有民族特性的影像表达出了新的“中国性”内涵。
近期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以丰富多样的视听,探究了民族性表达的新路径,并以这样的新路径来书写国家意志,输出中国传统文化,演绎出了“中国性”,显现出建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这亦是该类影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至新时代后的美学变迁,其今后将会沿着这一路径不断进行美学和产业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