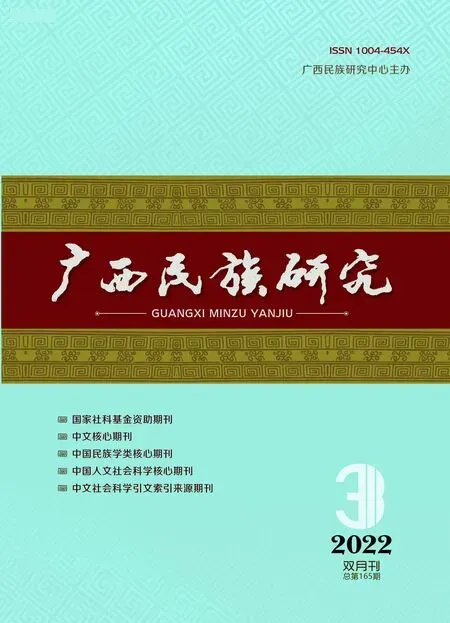从“祖灵崖”到“神龛”
——广西隆林彝族的社会变迁与家屋逻辑研究
2022-10-25王琳淞
王琳淞
彝族是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的民族。大约在宋代以前,彝族所在的大部分区域,其社会是以“则溪”制度为根基建立的“勾”国家体系和以“祖灵信仰”为核心逻辑建构的家支社会。直至明清时期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这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隆林彝族的基本社会结构。一方面,国家力量的强制和汉文化的进入导致彝族社会的破碎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彝族又与汉族保持着较为清晰的族群边界。近几十年的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更侧重于重构彝族的整体历史和“纯粹”的社会文化传统而没有反思彝族的社会文化不断发生变迁的历史事实,历史学则更倾向于用国家的视角去观察地方的开发和经营。无论哪一种视角,都忽视了当地彝族如何因应国家政策和其他文化对其影响的具体过程。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隆林彝族的社会文化逻辑是什么?如何保持其社会文化理想并减少国家强制所带来的压力?如何处理以汉族宗族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所引起的紧张冲突?这些问题都需要回到当地彝人自身的视角进行解答。
一、隆林彝族的基本社会情况
隆林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滇黔桂三省交界地区,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彝族村落主要分布在距离该县县治新州镇南部大约四十公里的石山地区,平均海拔大约一千四百米,从县境西北部延绵至此的金钟山狭长支脉从中穿过,形成由土山自西向东将石山分割于南北的地貌。区内无大河,雨水由土山积聚形成溪水流向南北,石山蓄水能力不足,因此水稻作业只能在狭长的土山地带两侧进行,石山地区只能种植土豆和玉米等高寒作物,基本上可以满足一造喜温作物加一造喜凉作物的热量要求。区域内有彝族、苗族、汉族、仡佬族、壮族等民族以及蔡家人和俫人等群体。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止至2020 年11 月1 日,隆林彝族人口为3780 人,占全县人口的1.08%。基本上分布于德峨镇和阿搞、团石、小德峨、白泥塘、水头、达毛、上洞、弄保、岩头、蛮罗和么基这几个村落。除阿搞和团石外,其他村落均与其他族群杂居。当地彝人被称为“倮倮泼”,用来区别其他族群,族内自称“俄泼”,“泼”即人的意思。
“家支”彝称‘楚加’或‘楚西’,即‘家’‘支’和‘户’的总称。林耀华将家支定义为“由父姓一系流传下来的氏族族属,其族属的结合则以祖先之名号称其支系,一个氏族的人民因有共同的祖先,彼此必以氏族亲属相待”,此后,彝族社会结构的研究基本遵循这一脉络,并逐渐形成当下的家支研究。易谋远认为“所谓‘家支’的‘家’,这个‘家’非指个体家庭,而是由父系大家庭发展下去所形成的一个又一个近亲家族群。每个近亲家族群包括几个父系血缘密切的家族集团,他们在地域、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等方面,都保持一定程度和某种形式的统一性。这个具有统一性的共同体,过去的习惯是称为‘家支’,即某个‘宗族’”。隆林彝族现有王、黄、韦、吴、罗、杨和李七个姓氏,他们分别对应各自的“涅益”,“涅益”一般以职业、地名或是动植物图腾为命名的原则,比如王姓称为“笃撮毕倮西”,是毕摩家族;吴姓称为“扎周涅益西”,是以某种杉木为图腾而命名的称号。同属一个涅益的成员拥有同一位男性祖先,他们被看作是这位祖先繁衍下来的父系继嗣群体,同一个涅益的个体之间禁止通婚,并拥有共同的祖灵崖和家族火葬地。
对于隆林彝族来说,将涅益称之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宗族集团似乎并无不可,但是以上要素并不能完全归纳以血缘与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原则。首先,虽然有非常明显的父系继嗣传统,这主要体现在隆林彝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度”和以父系祖先为主的念祖仪式上;其次,根据两可制的继嗣原则,以涅益为单位的族外婚原则并不能全部囊括彝族的婚姻禁忌,他们遵循交表通婚平表不婚的通婚原则,母亲姐妹的后代之间被视作兄弟姐妹而严禁通婚,以此推知,祖母的姐妹的后代、曾妻子的姐妹的后代,一直追溯到第九代直系女性先祖的姐妹的后代都被视为兄弟姐妹而禁婚;最后,通过女性改嫁或是收养带入不同涅益甚至是不同民族身份的孩子成为某一个家庭的同吃者,他们一样被视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后代同样要遵循九代不婚的原则,例如:A 涅益的某个人“α”成为B 涅益b家庭的同吃者,那么“α”和他的九代之内的后代不允许同B 涅益b家庭的同辈成员及其九代之内的后代通婚;相对的,与“α”同为A 涅益的个体“β”没有成为B 涅益b 家庭的同吃者,无论“α”与“β”的亲属关系是近是远,他和他的后代能够与B涅益b家庭的成员及后代通婚。
无论是“家支研究”还是“宗族研究”的研究脉络,其根源来均自于非洲世系群(Lineage)的研究范式,世系群的研究进路,其概念和分析工具建立在男女二元区分且彼此界限清晰的逻辑基础之上。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面对具体的隆林彝族社区和家庭的研究之中,却常常陷入与经验事实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根据隆林彝族的社会基本原则可知,“涅益”虽然有着明显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结合为社会共同体”的特征,但就具体的继嗣和通婚原则而言,其方式则是以“家庭”为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原则开展的。对此,根据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家屋社会”概念:一个法人,拥有一笔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财产构成的产业。这笔产业通过其世系名号、财富和头衔传承下去。这个世系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幻,被认定是合法的唯一条件是这一连续性必须能够通过亲属关系或者联姻的语言得到表达,而且往往必须两者兼备。
家屋理论旨在超越世系群研究的男女二元对立体系,其包容性是通过世系和婚姻将各种复杂含混的社会关系统合于物质或是象征性的家屋之中。当下的隆林彝族社会,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尽管在谱系上彝族更偏重于自己的父系血缘脉络,但是母系世系群同样是规范继嗣和婚姻的必要条件,同时通过领养的形式将外姓乃至外族纳入到同一个家屋之中成为亲人,并维持这些领养子女原有的世系与姓氏或涅益。单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世系群”为视角无法解答这一复杂情况,家屋理论的提出为理解隆林彝族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要讨论以家屋为中心向外扩展为特征隆林彝族社会,就必须从其祖灵信仰体系以及改土归流后的社会文化制度变迁的视角进行解答。
二、“家支”与祖灵信仰
祖灵信仰是彝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稳定性、共同性的部分,其核心是以“尼木措毕”为主的念祖仪式。彝语中“尼木”意指祖先,也可以指代祖先寄居的竹灵牌,“措毕”则有念经之意,“尼木措毕”即毕摩为亡灵念经。举行送灵仪式,一方面能使亡灵摆脱游离的状态成为祖灵,免遭邪祟侵扰;另一方面,使亡灵找到归宿,永享子孙供奉,造福后代。隆林彝族认为,父母不仅赋予子女肉体,也赋予子女灵魂,子女的灵魂是父母灵魂的一部分。当一个人死去后,灵魂被分为三个部分,一个寄居于竹灵牌,一个寄居于墓地,一个回归祖界。祖界是先祖先祖发祥分支之地,毕摩通过举行念祖仪式,为亡灵指引迁徙之路回归祖界与祖先团聚,新的亡灵才能重新成为祖先的一部分。因此,每个彝族人的灵魂来源于祖灵的分割,个体的死亡意味着灵魂从分割的状态重新回到整体之中,个人与其直系祖先拥有灵魂上的连续性,后人与祖先之间形成了灵魂的连续体。祖灵并非泛指所有的直系祖先,而是具体的某一对夫妇先祖。一对夫妇经历成婚、分家与死亡的生命历程,当这对夫妇去逝之后,由毕摩主持仪式将二人的家魂引入用竹皮或是竹筒做成的一个竹灵牌之中,这个竹灵牌就成了祖灵的寄居之物。由于寄居于祖灵牌的家魂具有不可分割的唯一性,且根据当地彝族人的习惯必须由长子继承,而余下数子在成婚分家之后另起炉灶兴建房屋,要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成为祖灵,新的分家才可以祭祀自家的祖灵。在此之前,分家的兄弟仍然需要供奉自己父母的祖灵。
念祖仪式出现在彝族的日常生活与集体仪式性活动之中,包括节庆、丧礼、婚庆、祭祖和分祖等场合,后人通过念祖将凡间所发生之事告知祖先,同时通过念祖,将食物供奉给祖先,祈求祖先的祝福。根据不同的仪式场合和参与的规模,念祖的规模也不一样。家庭在日常生活和节庆中念祖只需要念到家中居住的祖灵即可,葬礼和祭祖要根据到场族人最近的共同祖先,念祖遵循“从近到到远,从小到大”的父子连名原则,单一家庭念祖需要从家中最老者的父亲祖灵起念到他这个家庭所寄放祖灵牌的祖先,即自家的直系祖先;单一世系念祖则要遵循从小到大的原则从幼支念起,将幼支家庭内的祖灵念完以后并入到它的长房家庭之中,并一直追溯到祭祖仪式的共同祖先。所谓“父子连名”,即是父名在前,子名在后的命名制度,通过“父名—字名”的格式连续下去,形成一个上溯祖先下至子孙的连续谱系。本文仅以黄姓家支的部分父子连名谱系举例。“节月—月则—则俄—俄几—几结—结冲—冲堆……”是黄家大房,相较于二房“节月—月则—则俄—俄几—几波—波墨—墨纳……”可知“几结”和“几波”是亲兄弟,因此,当仪式需要追溯到“节月”,根据“从近到到远,从小到大”的原则,先要从“墨纳”念到“几波”表示二房的的祖先已经全部念到,再将其接入到大房的谱系,从“冲堆”念起一直念到“节月”为止。随着仪式规模的扩大,各家庭通过念祖被组织成为一个扩大的谱系,家庭通过念祖仪式凝聚成世系群。在不同的仪式规模中,可以观察到不同规模的谱系,仪式的规模越大谱系就越完整,世系群的规模也就越大,但是念祖不可能无限往前推进,而是到涅益为止,涅益是世系群的最大规模。那么,涅益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笔者对毕摩王章富的访谈可知其端倪:
彝族的红白喜事都要念祖,念祖就是我们这些后代要孝敬祖宗,给祖宗吃喝他们才会保佑我们,如果哪一家在念祖的时候经常不来,哪怕祖宗只是问一下,他家的人都会有不好的事,要么是生病,要么就是运气不好,容易见血。我的父亲也是毕摩,我会的这些都是他教的,他跟我说过以前彝族人还有一种念祖仪式叫作分祖,就是分祖宗的意思。我不会这个,也没有见过,但是我父亲他见过,他说如果一家人经过九代的发展以后,家族的人开始变多,如果他们想要开亲,就要喊我们去给他们家做仪式,到时候就要一家一家的喊他们全部到场,等每一家都念完以后,要请我们毕摩拿他们家九代以前的竹灵牌放到一个崖洞里面,跟这些祖宗说,“现在这家人已经分祖了,可以开亲了,所以才搬你来这边住,不能住在家里了”。等祖宗放到崖洞以后,这家人就变成两家人,他们就有不同的涅益,以后念祖就念不到这些放在崖洞里面的祖宗啦,后代也不准进,我们毕摩可以进,但是我也不敢进。至于现在我们地方的这几个涅益,他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我也不知道,我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可能他也不知道。我们所有彝族都是阿普笃慕的后代,包括现在贵州云南四川的彝族都是,阿普笃慕有六个儿子,就是这样分下来才分到我们这些后人。
从以上访谈的内容可知,涅益作为世系群的最大规模,因为相同世系群之内禁止通婚,所以在世系群发展壮大之后,需要通过分祖仪式重新规定世系群与族外婚的范围,也由此造成原先世系群分裂和新的世系群诞生。念祖不可能往前无限延伸,否则所有的彝族人都是同一个世系群的成员,联姻就无法开展。念祖仪式所对应的都是在家屋内寄居的具体祖灵,根据仪式规模的大小确定所要念祖的代数和个数,由于“所有彝族的灵魂都是由父母灵魂的分割,并通过送灵仪式重新回到祖先的灵魂之中”的观念,广义上任何一个人的父子连名谱系都可以追溯到阿普笃慕,但是因为分祖的关系,在念祖仪式中,具体的祖先只会念到同一个涅益的共祖,在此之后,则要将先前的祖先泛化为总体的祖先,也就是以“阿普笃慕”指代之。
根据祖灵信仰与家支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祖灵是导致家支生成、发展最终分裂的关键之物,通过分家和祖灵的继承,新的家庭不断生成并发展,最终成为新的涅益。在改土归流之前,彝族围绕着祭祀祖灵的仪式,根据不同的仪式规模形成了从近到远,从小到大,以涅益为基本单位的各级世系群,并通过分祖的仪式实现社会单位的再生产,这是改土归流以前隆林彝族社会结构的基本逻辑。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化,汉族宗族文化的逐渐影响并引起了彝族社会逐渐走向以家屋为中心的社会结群模式。
三、改土归流与宗族文化的深入
隆林在明代置安隆长官司,受桂西岑氏土司统治。长官司域内设十二个甲,分由八姓兵目管制。德峨地区属巴结甲倮倮亭,其统治者为龙氏兵目及其家族子嗣。清康熙五年安隆长官司改土归流置西隆州,但德峨一带仍然受龙氏兵目及其后人统治。嘉庆一年,受南笼府王囊仙起义的影响,巴结甲爆发了以龙氏兵目后裔龙登连为首的苗彝起义。起义于当年即被镇压。失败之后,清政府进一步推进了改土归流的政策,通过向黔西南地区和今天的德峨一带的大规模移民,当地人逐渐开始模仿汉人宗族制度,这是隆林彝族国家化的重要转折点。宗族制度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火葬改成土葬;第二,从使用父子连名改为汉姓班辈名和乳名并用,第三,分祖仪式逐渐消失,新的涅益不再形成。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对德峨社会的影响逐渐显现。从火葬改为土葬反映了宗族意识形态及相关制度在地方社会不断深入的过程。改土归流之前,隆林彝族普遍使用火葬,现今能够看到的火葬坑遗址存在于阿搞、团石和那地三个村。笔者通过对毕摩的访谈得知:
人死了以后,要拿他的遗体到家族的火葬地焚烧,等到剩下骨灰以后,用一个东西包起来,挖好一个坑把它放在最下面,再请我们毕摩给他念祖送饭送酒,等念完祖,祖宗吃好喝好以后,这些装过东西的碗要同骨灰一起放在火葬坑里面,到最后要用一块砌好的石板压在火葬坑上面,不要给骨灰漏风。等这些事情都做完以后,这个火葬坑就不管啦,逢年过节也不需要打理。现在大家都是用土葬,土葬很好,现在清明节大家都要去到祖坟去念祖,以前这些火葬坑都不懂是哪个祖宗的,所以就不懂要怎么念,不念祖的话祖宗要怪罪下来,祖坟打理好的人祖先才保佑。
为此,笔者到阿搞的李家火葬坑遗址一探究竟,现场清晰可辨的火葬坑有数十个,每个火葬坑都用大概50公分见方的石板盖好,有些火葬坑的方石已经破损,周边还散落着一些陶碗碎片。据当地人介绍,每个涅益有自己的火葬地,不同涅益的祖先是不能葬在一起的。
正如缪格勒(Erik Mueggler)所言,“彝族人通过墓碑创造了新的方式来概念化后人与先祖之间的关系,围绕墓碑的仪式重新界定了后人的关系,墓志的书写透露出国家力量的进入”。嘉庆二年改土归流以后彝族人开始改用土葬,迄今为止笔者所见最早的墓碑是“阿搞李阿打夫妻合葬墓”,坟墓位于李氏火葬坑最边缘。墓碑立于道光二十年立,墓碑很小,约100×60公分,碑刻文字极不公整,多处已经损毁,部分文字埋入土内。碑文格式是:中联“父李氏阿打母楊氏二魂並歸之墓”,左联“奉聞父李阿打生於乾隆五年母楊氏□□乾隆七年吉月吉日吉時□□□嘉慶二年故又乾隆五十七年故”,右联记录的是墓主后人姓名,因文字太小雕刻太浅现已磨蚀不清,仍可辨识的只有“道光廿年三月初六立”。墓身仅有120 公分宽,从墓身宽度看,此墓不符合合葬墓的墓身宽度,并且从墓志的叙述无法判断李氏夫妇逝世的先后顺序。为此,笔者通过李氏后人访谈得知李氏先逝于杨氏,可推知李氏逝世于乾隆五十七年,杨氏逝世于嘉庆二年。李氏逝世时用的是火葬,杨氏则是用土葬,因此墓身规模仅容一人,这表示从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二年间,彝族的葬俗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夫妇二人合葬时并没有立碑,四十多年后才由其子李阿泽所立,这与现今当地彝族人在先人入土后三年立碑的风俗不符,并且对照同光年间的的墓志来看也很不相同。例如“团石黄开科夫妇墓”的墓志,该墓立于同治年间,墓志中联为“清仙逝西歸故顯(考妣)黃諱開科韋氏老(大孺)人之墓”,其它清代的彝族人墓也没有“二魂并归之墓”一说,可知“李阿打夫妇合葬墓”在撰写墓志的时候带有“彝族三魂说”的意识,体例上并没有之后的墓志“规范”,从“团石黄开科夫妇墓”可以看到,墓志开始呈现出愈加浓厚的汉文化影响,甲子纪年的方法与对黄道吉日的认可,以及越来越“主流”的墓志,“蓋聞根深自本茂源遠流長而不知混沌初分有定人有存□如□者□木盛衰起予者商也予起祖曰宗曰陰佑後人籍百代之□□□蒙遺接續相傳……父在時為人正直立業忠厚报國……”。相较于李阿打的墓志只简单交代了逝者的生卒年月,可知彝族人开始逐渐对王朝国家产生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原先彝族习惯于葬在集体墓地中,均采用独葬的方式。自从改用土葬以后不再选用集体墓地,而是根据个人的生辰八字和挑选“风水宝地”,且多采用夫妻合葬的形式,并开始在祖坟墓地上举行念祖仪式,由于风水观念导致祖坟的零散分布,以祖坟为中心的念祖仪式也逐渐家庭化,为墓主举行念祖仪式一般只有墓主的子女及其后代才会参与。
改土归流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父子连名制度的改变和使用汉姓班辈名和乳名。乳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父子连名体系,现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是乳名、从子名和从孙名。每个人在出生时都会起一个乳名,这个乳名将会伴随着他的一生,在他死后乳名就会成为毕摩祭祖时念祖的名字。取乳名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例如团石村的黄仕国,他在上学之前乳名叫阿海,在他还没有孩子之前,长辈和同辈都会叫他阿海,晚辈则会叫他叔海或公海。当他有了第一个孩子阿新之后,大家就要叫他新爹,晚辈们要叫他叔新爹或公新爹。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当一个人出生以后父母就会给孩子起班辈名,班辈名和乳名开始慢慢的合二为一,只是在称呼的时候把班辈去掉,只叫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当下所有可追溯的彝族“父子连名”谱系中,原有连环相扣的联名体系在嘉庆年间都突然断裂,取而代之的用乳名续接在原先的父子连名之后,例如“节月—月则—则俄—俄几—几结—结冲—冲堆—阿二—阿意—阿迷……”这类以乳名连续的方式续谱。早期的乳名连续均是彝语称乳名,越往现代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语称乳名。道光年以后,隆林彝族开始制定班辈诗,班辈名主要用于三种场合:需要用文字记录的场合如登记礼簿、碑文、契约等;与外人、官方打交道的时候;上学,彝人在上学之后,就由家长或私塾先生给孩子起一个班辈名,如果此人没有去过私塾或学校念书,那他就没有班辈名。这三种场合都明示班辈名与汉字或外来力量有关。班辈名对于彝族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对外交往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并不高。无疑,班辈名体系和乳名体系均是地方彝族社会在汉文化进入后的产物,它们的出现代表着父子连名体系的终结。父子连名制度之所以被取代,原因是班辈名体系是依照父系血缘原则将个人辈分绝对化和清晰化,父子联名只强调父子之间的线性谱系关系不符合汉族宗族文化父系宗法制度的传统。班辈名代替父子连名给彝族带来了诸多的困扰,原因是原先的并系继嗣制度与班辈名强调的父系继嗣制度的冲突,特别是在联姻中造成了亲属关系和称谓的混乱。在此举例说明:
案例一:文字辈的阿海和国字辈的阿迷是同宗的爷孙关系,两人年纪相仿,但是两人分别娶了黄家的一对亲姐妹之后,他们两人的儿子从爷孙变成了兄弟。从此之后,大家都拿这件事情取笑这两家人,并告诫自己的子女以后结婚要小心,不要变得爷孙不像爷孙兄弟不像兄弟。
案例二:阿林与阿平不同涅益,但是他们是同吃的家屋兄弟,所以阿林与阿平两人是兄弟关系,阿妮和阿林是同涅益的姑侄,对于阿林而言,阿平和阿妮两人是自己同一个家族的人。但是阿妮与阿平既不同涅益,也不是同家屋的兄弟姐妹,所以他们两人可以通婚。阿平跟阿妮结婚给阿林发了请柬,按照当地人的习惯,请柬要写明新郎或是新娘与受邀人的关系,按照惯例应该在阿林的名字后面附上“兄”或“侄”才对,但是无论从新郎这边将关系表述为“兄弟”或是从新娘那边论为“姑侄”都会造成关系的错乱,所以只能用“友”字含糊对付。婚礼结束后当地人有带媳妇回本家探亲的习惯,阿平带着阿妮到阿林家走家门,家里人只能按照彝族的习惯各喊各的。
汉姓班辈名在于明确同姓成员之间的辈分阶序以辈分名的称谓来体现。从表面上看,班辈名似乎造成了“乱伦婚姻”和“辈分混乱”的事例出现,不过这并不代表彝族没有解决之道。两个案例中体现的矛盾均发生于汉语和汉字的情境之中,但在彝语中亲属称谓从来都是根据具体的情景灵活地调整,就如案例二,当离开汉字的书面表达而回到彝语的亲属称谓时,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彝族的并系继嗣传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个体之间的亲属称谓,通常来说父系与母系之间会强调“哪边亲就喊哪边”,这为个体之间的称谓调整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运作空间。究其缘由,彝族虽然在形式上模仿汉姓班辈名,并通过汉姓将父系世系群固定下来,但这不意味着彝族从并系继嗣传统转向单系继嗣,原先并系继嗣制度为基础的亲属制度和婚姻婚姻制度依旧被大家所遵守,彝语中也并未衍生出与汉族亲属称谓相对应的亲属称谓制度,他们仍然采用原先灵活多变的亲属称谓来调整个体间的关系。所以,所谓“乱伦婚姻”与“辈分混乱”的说法是“用汉说彝”的文化误解,从班辈名的推行可以看出隆林彝族对于汉文化的态度:唯以形式为先而已,其实质却不必深究。人们通过形似和求同减轻来自国家和宗族文化带来的压力,是因应“主流文化”影响时主动使用的手段,因此也形成了“汉皮彝骨”、多重混杂的文化景观。
四、隆林彝人的家屋社会及其逻辑
在过去,祖灵崖承载着祖灵信仰和世系群不断繁衍的逻辑内核,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祖灵为核心,象征着祖灵、地方与国家间连结其力量的家屋。随着分祖仪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汉姓将父系继嗣群固定下来,同姓不婚的原则被大家所采纳。基本上每一个涅益都选用一个常见的汉姓,现有王、黄、杨、李、韦、吴、罗七个姓分别对应各个不同的涅益。分祖仪式的消失意味着祖灵不再被送入到祖灵崖,新的涅益和与之相对应的谱系无法形成,但是新的祖灵还是不断的生成,并通过原有的继承方式被安置在各自的家庭之中,祭祖仪式也从以涅益为中心转变为以家庭为中心展开。
根据访谈得知,汉人宗族文化对彝族社会的影响导致了分祖仪式的消失:
从前我们彝族过了九代以后要分祖,分祖以后才有新的涅益,才可以开亲。后来大家改用汉姓,比如原来“扎周”就统一取“吴”姓,“笃撮”取“王”姓,大家就约定好同姓就不能开亲,以后就不做分祖,也就没有新的涅益了。
随着彝族的涅益转化为汉姓,父系继嗣群被固定下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彝族的并系继嗣传统被汉族宗族文化的父系继嗣原则所取代。究其缘由,乃是祖灵信仰仍然被大家所坚持,竹灵牌虽然不再被送入祖灵崖,但是新的祖灵不断产生和继承的过程中传承下来,并通过念祖仪式将祖灵有序地纳入到整个彝族社会的谱系脉络之中。正因如此,隆林彝族虽然部分接纳了汉族宗族文化,在运行的过程中却有些似是而非的意味,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没有发展出祠堂和成体系的家谱可以看出。彝族没有发展出祠堂的另一个文化逻辑源自于“养”,“养”不仅是供养后代,同样也是供养祖先,祖灵信仰的逻辑体现在彝族日常生活和仪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仪式化日常生活的用餐将祖灵和后人联系在一起。如果将祖灵放入祠堂,会被认为割断了后人与祖先的联系,祖灵不再是家里的同吃者,这被人们认为是不孝的行为,正因如此,乔迁最重要的是将家屋内的祖灵带到新的房屋之中,否则会被彝族认为是自己与祖灵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祖灵会失去后人的供养,也就没有办法荫佑后人。
彝族的家屋不单指一个独立的房屋,其概念也由家屋的成员、祖灵以及诸如土地、工具和食物等财产组成。房屋并不能单独成为家屋,只有祖灵栖居之所才能被称之为家屋。因此,家屋不仅指的是具体物质和空间,更是一个象征概念。家屋的命名方式常以从子名相同,即在家的前面加上这个家屋成员中最晚一辈后代的最年长者的名字,比如一个家最晚辈的首生子女叫阿新,那么这个家就被称为阿新家。无论家屋之内有多少家庭成员,它都会被视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社会活动包括政府行政组织以及村落传统的社区组织,比如村民小组,村落或家族内的劳务和费用摊派,红白喜事和村祭等集体仪式活动以及私人的礼物来往,土地也是以家屋来命名。“家”是区分“家人”跟“外人”的标准,“家人”被认为是在同一个家屋里供奉祖灵繁育后代的同吃者,它通常包括一对夫妻及其子女,也包括仍然健在的老人。如果女性带上其他姓氏家族的子女嫁入某个家屋,这些子女也被视作这个家屋的成员;相对的,同姓的家族成员没有成为某一家屋中供奉祖灵的同吃者,则不被视作这个家屋的一份子。共同供奉祖灵的同吃者是判断个人是否归属某个家屋的标准,雇工或者其他临时居住者不被视为家屋的成员。个人不一定只属于一个家屋,因为母亲改嫁或是寄养等原因,子女长大以后回到本家供养自己的祖灵,就会同时成为多个家屋的成员。
卡斯滕(Janet Carsten)认为,同吃行为根据同源食物造成同吃者的身体连结,因此在一个家屋之内通过制造同源食物的同吃者可以被视为家人。在此基础上,何翠萍提出“家屋具有孕育的力量,家的声望以及人的声望与人观的理想所建立的价值密不可分,这些声望被理解为道德、伦理或宗教的实践”。家屋是一个生命体,它与人一样,要经历出生、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历程。人是家屋的生命之源,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供养家屋,人死后会成为祖灵纳入到神龛之中,一个家屋的成长需要人的付出,人丁衰落意味着家屋的衰亡;以祖灵为核心的神龛建构出一个神圣空间,是家屋内部的力量之源;土地是供养家屋的物质来源,它为家屋的成长提供物质材料。而将家屋、祖灵、后代和土地连成一体的逻辑是“养”,通过后人与祖先同吃的“养”的逻辑,彝族实现了自我生命意义的建构。
生育在隆林彝族的家屋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只有生育了后代(首生子),夫妻才能够成为家屋的祖灵被后人供奉,如果一对夫妇没有孩子,那在他们去世以后家屋也会随之衰亡,人的延续意味着家屋生命的延续,家屋与人是共同生长的生命共同体。因此,首生子的诞生成为家屋延续历程上的标志性事件,为庆祝首生子满月而举办的满月酒是最重要的生命礼仪筵席之一。满月酒一般由新生子的父母举办,这意味着这一对夫妇完全成年,等到他们去世后能够成为祖灵被后代奉养,新生儿的父母亲从此也就承担起了供养后代的责任。筵席当天,村子里每家每户都会被邀请赴宴,外婆会给新生儿送背带,舅舅和阿姨给他送去衣物被子等用品。父母亲会向参与筵席的亲朋好友告知新生儿的乳名,乳名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能与其他人重名,因为这个名字在当地人群的指称与分类中非常重要,被用来标识这个家屋的其他人。满月酒之后,大家都要根据新生儿的乳名调整对这个家屋和成员的名字。父母获得了从子名,祖父母获得了从孙名,家屋也有了新的名字,并被用来标识家屋所拥有的一切天地与其它财产。
家屋的核心是围绕着祖灵信仰与象征国家力量的神灵结合而成的神龛体系。每一个家屋的神龛上,除了供奉自家的祖灵之外,一般会供奉“九天九厨灶王府君”“桂花院内七曲文昌”“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大都至富财帛星君”等汉文化神灵。神龛的布局显然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其中以“天地君亲师”最为明显,它是汉文化关于生命本源和人伦纲常的集中表达。“天地君亲师”之上一般写着“祖德流芳”,近十几年随着彝族人对本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之故,很多家庭将“祖德流芳”改为自己的涅益,比如“笃撮毕倮西”或者“扎周涅益西”等,还有一些家屋会模仿汉族人的堂号,比如王姓的有些家屋使用“太原堂”,黄姓是“江夏堂”等等,使用堂号并不意味着彝族将自己的祖源追溯到这些地方,彝族还是通过念祖仪式将自己的祖源追溯回阿普笃慕和祖界,这也说明了这两套追溯祖源的系统并行不悖,汉字的书写更多代表着彝族对国家在场的认识和感受。从神龛文字和供奉神灵的多样性可以看出,隆林彝族对国家力量的存在和社会文化变迁给其命运带来变化的深切感受,并以符号化的方式表达国家力量在家屋中的在场,将代表国家认同的汉字书写与祖灵信仰为核心的个人、家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结合起来。神龛上的神灵除了“天地君亲师”外,对土地公的认同也带有明显的汉文化色彩。土地被放置在神龛的最底部,它不仅寓意着家屋的根基牢固,同时也表达出人们通过虔诚奉养以祈求土地公保佑大地丰产、六畜兴旺之意。神龛被视为家屋内在力量的源头,与家屋有关的仪式,例如祈福除秽,以及节日庆典都需要在神龛前举行。要定期对神龛焚香祭祀,家里有好酒好菜也要先摆放在神龛上供祭一会才给人吃,乃至逢年过节或是平日有客来访,都要将客人引到神龛前,礼物亦要摆放在神龛附近,这被认为是为家屋增添荣誉与财富。
神龛的最顶端是祖灵,祖灵在上代表着祖灵信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神龛体系最重要的核心。当地人认为,没有祖灵的神龛是没有用的,祖灵是唯一从家屋中诞生的神灵,也是家屋的本质所在,所有对神灵的供奉和祈求必须要通过祖灵向其他神灵传达。因为个人的灵魂与汉文化的神灵并非一体,所以并不能在精神上产生联系,只有同一个家屋的祖灵和家庭成员才能达到灵魂的沟通与契合。因此,除了祖灵之外的任何神灵和文字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调整和改变,唯有祖灵是不可变的。祖灵是个体生命的根源,祖灵与家屋成员在灵魂的层面上是一体的,后人是祖灵在灵魂上的连续,是肉体和精神上的连结。它既是产生于家屋本身,同时也是家屋的本质所在。祖灵栖居之所被当地人视为家,没有祖灵的房子只被认为是暂居之所。后人的幸福被看作是祖灵的恩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必须要通过对祖灵的祈求,愿望的达成要告知祖灵表示感谢。特别是婚姻与生育,彝族人都要烧香以敬谢祖灵,这意味着祖先的灵魂得到了延续,新婚夫妇在逝去以后才能够化作祖灵,与他们共赴祖界,永远在这片乐土上快乐地生活。
人们通过在土地上劳作养育着家屋,土地是家屋成长的物质之源。一个家屋的成员可以看作是工作上的伙伴,通过家屋结合成最基本的劳动手段和成果占有的劳动单位,夫妻与孩子在劳动方面形成了一些习惯性的分工。丈夫主要负责田地里的工作,包括挖田、耕田、耙田、插田、打谷等。女性负责家屋内部的工作,包括种麻、收麻、织麻、制作衣物、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没有劳动能力的孩子,讨猪菜喂养牲畜等等。已经具备劳动能力的孩子主要负责放羊放牛,如果家里的孩子都太小,放羊和放牛的工作就要由夫妻共同承担。虽说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形成了上述的劳动分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分工之上建构出一套劳动的文化逻辑,并将其归纳为男人该干什么活女人该干什么活。对于当地人而言,一般男人的劳动女人也可以参与,反之亦然。正如郭立新认为的那样,“劳动的分工并不意味着男女之间的差异为异,而是强调男女之间的统合而不是分辨其间的差异”,男女之间差异的统合是建立在家屋之内的。
除了劳动合作以外,“养”的逻辑也体现在夫妻共同劳作成果供养家,通过同吃同住成为一家人,夫妻与子女通过“养”与“被养”成为一家人。“养”的逻辑冲淡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世系逻辑,由于改嫁或收养等各种原因,其他涅益甚至是其他民族的孩子均可以通过父母对他们的抚养来确定亲子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养子要并入到养父母的世系群,他的母亲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姓氏或者涅益,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可以回到自己原先的家中继承财产,也可以选择留在养父母家中分得一份财产,无论他们如何选择,养子与父母兄弟之间的家人身份都被当地社会所承认,他们的后代同样视彼此为一家人。父母与小孩通过养与被养成为一家人,火塘就成为了家屋中另一件重要的神圣之物,它是兼具神圣和世俗生活的象征,家中的灶君也寄居于此。因此,围绕着火塘也有诸多禁忌,例如不可跨过火塘,火塘的火不能熄灭,火塘不能煮猪食等等。火塘是“养”的转化之物,工作或生产是“养”的重要环节,彝族通过在土地上劳作,将获得的谷物、蔬菜和肉类在火塘上转化为食物供奉祖灵,养育家人,是从世俗转化为神圣的关键之物。正是因为火塘有将世俗事物转化为神圣事物的功能,所以世俗生活与仪式生活被连接成了一体。家人同吃的每一顿饭都必须要在堂屋中,饭桌要正对于神龛,背靠祖灵的主位一定要是家屋和祖灵的继承人,他们可以是家中的男性或女性老者,也可以是长子或是长孙,如果没有祖灵继承着参与用餐,那么背靠祖灵的主位就要空置,用餐代表着祖灵与后人同吃,家屋和祖灵的继承者被看作是未来的祖灵,要将他们放在和祖灵相同的位置,日常生活的同吃也就成了祖先与后人同吃,同吃也因此被当作是仪式而神圣化了。通过火塘的神圣性转化,彝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着祖灵与家人同吃的理想,并以此完成自我生命意义的建构。
五、结语
本文以“从祖灵崖到神龛”为题,通过对祖灵崖和家屋这两个文化和信仰载体的观察,发现从祖灵崖转向家屋的背后,承载着自改土归流以来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宗族文化深入到隆林彝族社会,彝族对国家力量的接纳和对自我文化的维系与坚持,并将代表国家认同的宗族文化与祖灵信仰为核心的个人、家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对于当地彝族来说,似乎能够用“家支”或是“宗族”来一概而论的理解其文化和社会,但深入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却又表现出明显的家屋社会特征。究其缘由,其形塑力量不仅包括彝族先民原有的社会文化逻辑,更包括它与中央王朝互动和与汉文化交流的具体过程对具体社区的社会文化传统的遮蔽与扭曲,当地彝族运用这两种力量孕育出了以家屋为中心向外扩展的社会形态。祖灵崖和它的仪式逐渐被彝族人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家屋的神圣建构,汉族宗族文化观念导致分祖仪式的没落,代表着隆林彝族涅益的生命逻辑被中止,涅益不再经历诞生、成长和衰落的生命历程。不过这并代表彝族社会内在生命力的消亡,因为彝族的祖灵信仰没有受到国家力量的强制而发生改变,象征着祖灵信仰的竹灵牌仍然被有序的传承,念祖仪式也能基本维持下来。彝族主动将社会的生命力转化到家屋之中,通过对家屋的养育,家屋成为了社会生命的核心,祖灵信仰的逻辑仍在,并以此规范了彝族社会交往的具体原则。也正因如此,彝族继续以祖灵信仰文化实践着自我生命意义的建构,并以此形成了以家屋和核心向外扩展的社会文化格局,将个人、家屋与地方社会、国家合为一体,呈现出斑驳且多样的地方社会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