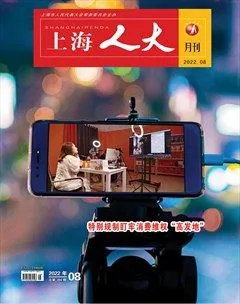谨防地方性法规的“政策化”倾向(下)
2022-10-25孙述洲
文/孙述洲
(续前期)
(二)口号式、标语化
地方性法规中常常出现“鼓励、支持、提倡”等宣传性用语,如某市全民健身条例规定: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利用单位闲置场地配置全民健身设施。法律关心的是行为,“鼓励”的具体手段是什么?是精神鼓励还是物质鼓励?出台什么具体政策予以“鼓励”?该法规对此均无具体规定。“鼓励”仅仅表明了立法者的某种意愿和方向,行为主体在法律上的义务并不明确,这种“鼓励”式条款使法律混同于政策宣传和标语口号。由于缺乏“鼓励”的具体措施,相关主体尤其是企业出于利益考量并无积极性,是否配置全民健身设施,完全依赖行为主体的思想自觉。尽管从一般理解上,“鼓励”一词表意是清晰的,但在法律规则中,其所表示的行为模式却模糊不清,使法律规则与宣传性标语无异。因此,站在立法的角度,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鼓励”,而是如何“鼓励”。因为法律是行为规范,对行为的规定必须具体,只有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规则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或许有人说,该条款旨在倡导全民健身的价值观。的确,“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的确有倡导社会价值观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作为行为规范,“法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申言之,法律是以“行为”为“中介”,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指引,间接达到形塑社会价值观的目的,而不是直接表达价值诉求,否则法律与道德规范、政策宣传就没有区别了。
口号式、标语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降低了地方性法规的可诉性。可诉性意味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否可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保障自身权利,是检验法律质量的重要指标。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直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以上述法规为例,设想一下,公民以某国家机关未利用单位闲置场地配置全民健身设施为由起诉该国家机关未遵守该法规,法院是否该受理?如果国家机关以场地并非闲置而是另有他用,或者法规规定的是“鼓励”而不是“应该”为由予以抗辩,法院是否该支持公民诉请?由于对相关主体的行为即义务规定不明确,法规对当事人和法院的裁判失去指导意义,丧失了可诉性。
法律天然与司法相联系,当权利被侵犯、义务被违反时,如果当事人不能依据地方性法规诉诸法院,保障自己合法权利,司法机关不能以地方性法规作为裁判依据,追究违法责任,则地方性法规作为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人们对地方性法规的信心和信任度难免会降低。在依法治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当下,这显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三)日常用语与法律用语不分
地方性法规中常常运用在日常一般性文件或文章中使用的语言,如某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主动接受家庭教育培训,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以健康的思想和良好的品行教育影响未成年人。上述法规中“主动”“健康的”“科学的”“良好的”等词语,如果运用在一般性文件或文章中,意思是明确的,也易于理解,但出现在法律条文中时,就会引发歧义。何谓“主动”?被通知要求学习算违法吗?什么是“健康的”“科学的”“良好的”?界定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理解该条款时很自然会产生的疑问。产生这些疑问的原因在于,上述法规将日常语言混同于法律语言,使用较为主观的、难以量化的形容词等,导致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不清晰,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不明确。
法律语言是一种有别于日常语言的技术语言。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对行为的表述必须规范,含义明确。如果将日常语言与法律语言混同,法律条款就会出现表意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的情况,行为主体不能据此准确判断行为的边界而莫衷一是,法律也就难以发挥其指引、评价、预测等规范作用。法律一般很少使用形容词或表示程度的副词,原因在于其主观性太强、标准难以把握,使用时易产生歧义。在必须使用形容词的场合,通常有一套限制性的、可评价的配套标准。如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是否“严重”,司法实践中会根据犯罪嫌疑人违法次数、动机、行为特点、是否初犯、日常表现等情况来综合判断。
实际上,上述法规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合格的家庭培训,为实现该立法目的,需要对行为主体的行为予以明确,明确相关义务,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接受培训的时长(课时)、场所(如政府指定的培训机构)、合格要求(如拿到培训合格证书等)等作出规定即可。
(四)“规划先行”
地方性法规常常在对政府相关工作作出规定前,对政府制定相关规划提出明确要求。如某省中医药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中医药发展专项规划。规划是较为典型的政策性文件,如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种“规划先行”的工作思路在政府日常行政工作中十分普遍,对推进行政工作也确实有效。规划是政府推进某项工作时所做的预先设想和计划,本质上是政府开展行政工作的一种方式。地方性法规“深入”政府工作内部,规定政府工作方式,存在疑问。因为地方性法规不仅仅是为政府制定的,而是明确相关行为主体的权利义务,即确定行为规范,并“通过规范人们行为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因此,立法要关注的不应是政府制定规划过程本身,仅仅关注是否“有”规划而不问规划的内容和质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立法目的不明确。
或许有人会说,规定政府制定相关规划是为了促进政府相关工作。如果目的在于此,地方人大更应该通过监督而不是立法的方式。如果说确有必要立法,其目的也在于通过明确政府相关义务,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社会监督,促进政府提高规划质量和更好实施规划,从而提升社会参与地方治理水平。而要达到此目的,就需要围绕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从交互的角度,规定规划何时、以何种方式向社会公布和更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从何种渠道、以什么形式获取规划,以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立法只有从这个角度切入,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才是明确的,行为模式才是清晰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落实。
综上所述,地方性法规的“政策化”,混淆了法律与政策间的区别,偏离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基本属性,降低了立法质量。一方面导致法律规则行为模式不清,权利、义务、责任不明,可诉性差,法律难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也使地方立法介入了本不该介入、也难以处理好的地方,浪费了立法资源。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立法质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立法领域中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201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各领域法律已经基本具备,立法已经不再是国家治理的短板和瓶颈。当前,地方立法不应仅仅关注“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为此,地方立法者需要特别重视和提高立法技术,尤其是立法表达技术,如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概念和语言表达等,回归法律作为行为规范的基本属性。让法律的归法律,政策的归政策,切实提高地方性法规的质量,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