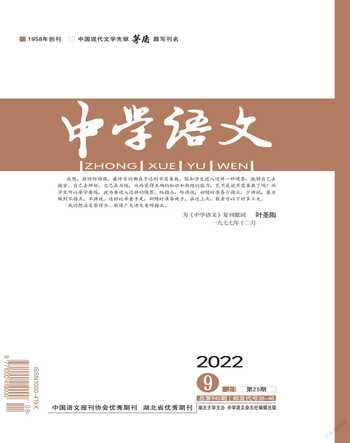跳跃的文字深沉的旨趣
2022-10-22曾芳艳
曾芳艳
摘要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王羲之用跳跃式的、似断实连的文字表达了深沉的“乐”“痛”“悲”,文中描述了两重境界的大小之乐,并行不悖的痛惜与痛爱,生命情绪的永恒悲叹。由乐而生痛,言痛而感悲,写尽了当时文人因苦痛而慷慨、因放诞而洒脱、因反叛而自由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乐而不淫善待死生悲而不哀生命觉醒
东晋时期统治严酷,国势日衰,互相倾轧、残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士大夫们大多不求进取,往往崇尚老庄,认为生即死,死即生,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玄学盛行,文学创作内容消沉,出世入道和逃避现实的情调很浓。但王羲之一反“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的风气,提出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中心思想,高呼“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在其“放浪形骸”的外表下,注重个性与精神的自由,珍视人格与生命的完美,表现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关注。
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感悟到人生悲剧的终极处境时,更应用行动去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善待生命,活出生命的价值。千古同心,千古同慨!
王羲之与他的《兰亭集序》早已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福祉。本文尝试研读文本的“不合逻辑”之处,深度挖掘,深入体会文段似断实连的言外之意,认识作者深沉“悲”叹中所蕴涵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一、“一分为二”的“乐”——乐而不淫
新旧教材的段落切分,扩大了主语的范畴,也呈现了两重境界的“乐”,“一觞一咏”之宴会小乐,“极视听之娱”之精神大乐。
1.小我、有我之乐到大我、无我之乐
以前的教材一、二段是合在一起的,现在在“亦足以畅叙幽情”后面把它分成了两段。照理说,文章三段,由乐而生痛,言痛而感悲,层次鲜明,逻辑清楚,既符合行文原理,又贴近学生的写作现实,兼顾了作者和读者,可谓两全其美。可为何在此断开呢?
细读之下发现,一分为二后的两段都“足以”“乐”,只是“乐”的内涵是有区别的。第一段写宾客以诗会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人杰,“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映带左右”之美景,“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之事趣,实属盛宴,足以让人快乐;第二段写感官在天地间延伸,值此“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良辰,尽享“仰观宇宙,俯察品类,游目骋怀,视听之娱”的兴雅,人与天地宇宙融合,意念在心灵的旷野上奔驰。这种超脱物外的境界足以令人快乐。
一个是眼前人物、景物、活动,体现的是“一觞一咏”之宴会之乐、小我之乐、有我之乐;一个是纵深到自然万物、融入到天地宇宙中的精神旨趣,“极视听之娱”,这是一种忘怀物我之乐。“一分为二”,更能体现由人到自然,由小我到大我,由有我到无我的升华。
2.酣畅之乐到恬淡之乐
暮春之初的江南,应是草长莺飞,柳绿花红。可《兰亭集序》里的画面却简单几句“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描述景物只在山、水、林、竹,而舍鲜花吐芳。写林写竹,也只言“茂”“修”,而弃绿、碧、翠,极力营造素淡雅致的格调。明明良辰美景、贤主嘉宾四美兼得,与会者无不畅怀痛饮,可文中却不喜形于色,只一“幽情”概括。不禁思考,这是否符合作者本意?
结合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这正是一部分文人学士追求的雅素恬适之乐,作者内心的喜悦之情并不过分显露,同时也是王羲之从容淡雅人格性情的体现。在当时文风非常浮华的年代,如此清新优美的文章难能可贵。这种乐,超脱世俗,由心而生,清新明快,乐而不淫,体现着作者从容恬淡的气度。
二、“并行不悖”的“痛”——痛惜更痛爱
“俯仰一世,老之将至”之人生短暂,“所之既倦,情随事迁”之世事无常,“向之所欣,已为陈迹”之往事不再,“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生死难测。尽管生命如此渺小脆弱,但这种痛的背后正是对生命的深爱。痛惜生命,痛爱生命,并行不悖。
1.乐极生痛的人之常痛
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实在是快乐的事。当大家对此感到欣喜、自得,沉浸于高兴、满足之时,却不知老年将要到来……按语法,第一段小结句“信可乐也”后紧接“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自然顺畅,那这中间插入一段“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用意何在?
细读发现,“其”字所指的对象范围发生了变化。若是紧接,“其”乃第一人称,代指前文参会的24人,甚至仅王羲之自己,流露的是当时宴会上乐极生悲的特定、特殊情境中的感受。显然,作者的用意在于人的共通点。插入之后,范围由兰亭集会的24员,扩大至所有的人与人相处,无论是晤谈或放浪、爱好和取舍、静或躁,都有这种由乐及痛的体验。“其”所指的不再仅仅是宴会之人,而是纵深到古人、今人、后人。乐极而生痛,乃人之常情,人之常痛。
2.不可触摸的生命之痛
痛人生短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宇宙浩渺无垠,自然万物繁盛不息。然而,“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对比之下,人的个体生命显得渺小短暂,无可规避。人和人相处,有的把自己的胸怀抱负,面对面在室内畅谈;有的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自己的情怀,不受约束、自由放纵地生活。虽然各有各的爱好和取舍,虽然性格静躁不同,虽然都会对所乐之事感到欣喜、自得、满足,但是猝不及防的年老,让短暂之痛油然而生。
痛世事无常。“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等到所喜爱或得到的已经厌倦,感情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感慨随着这种变化而有所不同。这里有个逻辑起点:“事迁”。并不一定是个人主观上的厌倦、抛弃,而是环境发生了变化,自身不得已而跟着变化。曾经苦苦追求的那份喜悦与执着,眨眼间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无助,只叹世事多变、人生无常!
痛往事不再。“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以前感到欢乐的事,顷刻之间,已经变为旧迹,仍然不能不因它而引起心中的感触。虽然面对着曾经的心仪之物,或许依然万般留恋、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但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也只能睹物遐思。时不待人,往事不再,又多一层伤痛!
痛生死难测。“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更何况寿命长短,听凭造化,终究归结于消灭。生命的渺小、短暂,是自然规律。就像史铁生的感慨: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但真正站在生命面前而束手无策的时候,那种复杂微妙的伤痛是非常强烈的。
3.时代使然的“死生亦大”之痛
人生短暂,世事无常,往事不再,生死难测!这是让人极痛的一件事。“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岂不痛哉”!如此连贯自然的衔接中,为什么要加一句“古人云:死生亦大矣”?
结合时代,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在作者这里,自然规律使然的生命之痛,是可以坦然面对的。但其中夹杂着的社会因素,是作者不能释怀的痛根。当时东晋统治严酷,国势日衰,互相倾轧、残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放浪形骸”的外表下,王羲之高呼“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展现的是个性与精神的自由,是对人格与生命的完美的珍视,是生命意识的觉醒。
宗白华评论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社会黑暗,生灵涂炭;
生命富贵,顷刻丧落;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朝代政权更迭频仍,门族党派互相倾轧。当时的文人,要么从老庄中寻求哲学的庇护;要么转向艺术,追求崇美;要么沉迷放诞的生活,饮酒、服药、游历、清谈……以此来逃避现实,保全自身。朝不保夕的混乱现实、有限生命,一方面刺痛了人们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也刺激着有志之士积极寻求生命价值。生命短暂,世道黑暗,这也是特定的时代中、特定的文人由乐而痛的必然的心路历程,饱含着深深的无奈之情。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到:“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感悟到人生悲剧的终极处境时,更应用行动去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善待生命,活出生命的价值。
因苦痛而慷慨,因放诞而洒脱,因反叛而自由!爱的愈深,痛的愈深。痛源自于对死和生的看重。“死生亦大”,暗含着对生命深沉的眷恋和热爱。千古同心,千古同慨!
到底应该怎样度过这一生?人生短暂,留恋生命,活在当下!
三、千古“不能喻之于怀”的“悲”——悲而不哀
一个“不喻”,三处悲。昔人之悲,似有矛盾,不可捉摸;今人之悲,内心无奈,冲突尖锐;后人之悲,莫名悲慨,难以言表。
1.不喻古人之悲
“每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虽世殊事易,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每当看到古人对死生发生感慨的原因,就像符契那样相合,纵使时代变了,世事不同了,但是激起心中感慨的原因和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既然大家思想情致都一样,那就应该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可是作者又说“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这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不妨先探究下这里的“昔人”所指,广义上肯定是指古人,但细读文本,应是侧重儒道孔庄。联系前段结尾“死生亦大矣”,其实,庄子两次提到过,一次是在《庄子·田子方》中:“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一次是在《庄子·德充符》中:“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既然庄子借孔子之口提出“死生亦大矣”,那么对死生是一件大事的看法,孔庄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有了前文“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的表述。那不能喻之于怀又是为何呢?
死生亦大,既是庄子的看法,又是孔子的看法,这是若合一契的。但是具体表述中又有不同,道家认为死生只是事物存在的两种不同方式,死生应顺应天道。而儒家认为,虽然生命有限,但精神可以永垂不朽。儒道两家对死生看法的似同又不同,庄子的两次转述亦有内心矛盾之处,所以每次看到古人对死生发生感慨的文章,就为此悲伤感叹,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总不能明白于心,消解释怀。
唉,古人自己对此也是矛盾无解的,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不能喻之于怀。
2.不喻今人之悲
“昔人”对死生看法的不同,孰是孰非,何去何从,作为今人的王羲之内心是否能喻之于怀呢?他到底倾向于谁呢?站在王羲之的年代,看看王羲之的内心有什么冲突。
《兰亭集序》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本来知道把死和生等同起来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虚妄之谈。一死生、齐彭殇,都是《庄子·齐物论》中的看法,王羲之的“固知”“虚诞”“妄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不认可的,甚至是贬斥的。《兰亭诗》中说“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宇宙悠悠运行的法则,永无停歇,人并不能主宰自身,来非吾因,去非吾制,乃自然陶化耳。这是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困境。人所珍宝的宗统在哪儿呢?只有顺应事理,才能获得安泰。这是采取了老庄的态度,即持哲学反思态度,超越日常狭小的功利世界。一贬斥,一遵从,这是否两相矛盾呢?
不矛盾,但是内心是矛盾的。《古文观止》如此评《兰亭集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一时,士族文人多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口实,鄙夷事功,好尚玄想,故作放旷而不屑事功。王羲之与一般谈玄文人不同,他曾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旗帜鲜明地指斥晋朝文人士子清谈无为之世风。然,尽管如此,尽管本来明知其虚妄荒诞,王羲之仍不能不借重于老庄来散忧,以玄对山水,回到自然,享受大乐,体玄悟道,体会有无之际的玄理。孙绰在《兰亭后序》中说:“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借自然山水消释、化解俗居生活失却本心的苦恼,从而寄寓人之回归大自然而感悟的无待、本然的愉悦。玄言春日诗,建构了某种审美超逸的空间,满足了人的感性慰藉需要。
有悲哀,需要排遣;有快乐,应当体会。又倏忽之间乐往悲来,又扬眉瞬目挥去哀愁。悲欣交间,内心亦是冲突尖锐,王羲之本人也不能喻之于怀,不能消解、释然,只能以一“无奈”作结!
3.不喻后人之悲
“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纵使时代变了,世事不同了,但是激起心中感慨的原因和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兰亭雅集已成为一个审美符号。它承传着上巳之游的古老精神,启发了流连山水的审美情趣,同舞雩歌咏一样,成为后人思慕的对象。直到今天,春回大地的时候,当我们登山临水,触目茂林修竹的美景,回想曲水流觞的韵事,“亦将有感于斯文”。真可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啊。
然,兴怀之由相同,兴怀目的确有不同,所以仍避免不了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王勃《滕王阁序》说到:“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渴盼伯乐识才、渴望建功立业。同样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环境的不屈让王勃发出“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宣言,这种强烈的情感直接表达出来的是唐代文人的风格,表现了初唐时期,除旧布新,思想自由开放的时代特点,青年才俊虽步履艰难,但仍积极进取的雄心。如何让生命发挥出最大的光彩是他们关心的。而身处这个时代中的王羲之,内心无比的沉痛无奈,只能做立言之事。
古人,今人,后人,面对死生,种种感慨,然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这种热爱,实现生命的价值,却各有各的选择。问世间死生为何物,竟让人不能喻之于怀,谁又能把它想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静观万物,“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乐往哀来,良会不再。越是用新的目光发现了境界的神奇,就越是为它的“信宿同尘滓”而感到悲慨。这种生命的悲慨,作为禀天地之性灵而生的人,谁又能躲避得开呢?真乃千古之悲!
从狭小的功利世界超脱后,大美的自然呈现,心情无往而不畅于三春。散怀山水,萧然忘羁,不知不觉间,由乐而生痛。“痛”是个体对“人生苦短 , 生命不居”的痛惜,而“悲”是对个体之“痛”的理性思考:生命情绪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因此“死生”之“痛”必将是人类永恒的悲叹。
[作者通联:广东深圳市横岗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