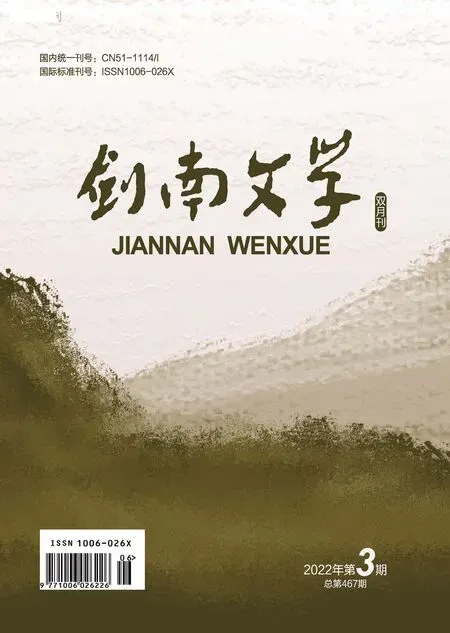鉴宝(外一题)
2022-10-22王平中
□ 王平中
张先生是乐至县城一个古玩鉴赏家,很有名气,在古玩市场一隅开了一家古玩店,除了自己收藏古玩外,更多时间是帮一些玩家鉴宝。
张先生面目清瘦,两只小眼睛时常半眯着,似睡非睡,一旦那里面射出的两束光灼停在某个玩物上,那个物件肯定价值不菲了。然后,张先生就会告诉那个玩家,他淘到的玩物是哪个时代的、有何特色、价值多少。
刚开始时,一些玩家对张先生的话半信半疑。张先生说,你若不信,可另请高明。我若走眼,百倍赔偿。张先生鉴宝是要收费的,鉴一次宝,收十两银子。百倍赔偿,岂是闹着玩的?那些对张先生鉴赏的古玩还半信半疑的玩家,悄悄到省城甚至京城找鉴宝大师核对,结果结论不差分毫。于是,张先生名声大振。
淘到宝的玩家,找张先生鉴宝时,大气不敢出,紧张地盯着张先生那两只半眯着的小眼睛。如果里面半天没有闪出亮光,顿时就会脸色苍白,浑身发软;如果看到里面亮光灼在玩物上,便是满脸喜色,欢呼雀跃。因为淘宝的玩家,一旦买到假货,往往是半生财产付之东流。
闲暇时,张先生也常到小城古玩市场走走,看能否“捡漏”。每走到一个摊位时,摊主都满脸堆笑,向他打招呼:张先生,来了?张先生用手捻了捻下颌的山羊胡须,微微点头一笑,算是回答。如摊位上正有玩家在淘宝时,张先生总是半眯着眼睛,看着摊主眉飞色舞地给玩家推荐宝贝,自己从不掺言掺语。如有玩家问他选的宝贝如何时,他只是笑一笑:物归识主,物归识主!
张先生给自己定了规矩,只有玩家在他的古玩店鉴宝时,他才发表意见,以免坏了别人生意。大多时候张先生只在古玩市场随意走走,偶尔停留在某个摊位旁,如果那两只半眯着的小眼里射出亮光,他便与摊主讨价还价了,十有八九,那玩物会落入他的手中。不过,张先生在古玩市场看得多,买得少。
这天,张先生在古玩市场看到一位年轻人,手中捧着一只九龙杯。年轻人穿得不新但很整洁,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张先生认识他,他是小城里一位落魄书生。
张先生从书生手中接过九龙杯,有人就跟着凑了上去。只见整个杯体由九条龙装饰,一条龙头部伸到杯底,尾部伸出杯口并弯曲为杯柄,另外八条龙组成四对,每对一条头朝上,一条头朝下,头朝上的四条龙头伸到杯口内呈喝水状。张先生两束眼光在九龙杯上来回移动良久,却没有半点亮色。
书生见状,有些急了:这是我父亲遗留给我的,说是祖传之宝。我进京赶考缺少盘缠,实在没有办法,才拿到市场来卖。
张先生闻言,那两只半眯着的小眼睛又仔细盯在九龙杯上,慢慢地射出了亮光。他一手托着九龙杯,一手指着说:这九龙杯乃宋朝御用杯,只可惜杯柄有损,才流落民间,但价格大大打折,我出银百两,你看如何?
书生连忙点头:行,足够我进京赶考的盘缠了!
等书生走后,有围观的玩家对张先生说:听说御用九龙杯是纯银制作,这个却是陶瓷的,做得虽然精巧,但仿造假冒的可能性太大,价值还不到十两银子,只怕你这次看走眼了哦!
张先生依旧笑笑说:物归识主,物归识主!我看中的宝贝岂止是这个九龙杯啊!
玩家被张先生的话弄得云里雾里,想要再问,张先生已托着九龙杯回自己店里去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小城突然流传着一个消息,那位书生在京城高中状元。玩家们这才悟出张先生话中含意,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咳,真不愧是鉴宝高手!
两年后,那位在京城做官的状元回到了小城,找着张先生要用万两白银赎回他那只九龙杯。
一万两白银呀!小城玩家们睁大了眼睛。
你任翰林院修撰才两年,就发财了啊!只见张先生捧着九龙杯,那两只半眯着的小眼睛在上面东瞅瞅、西瞅瞅,又在状元身上东瞅瞅、西瞅瞅,脸上似笑非笑,突然手一松,九龙杯啪地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这个九龙杯就是个赝品,值不了多少钱,我原来看走眼了,碎了也罢!张先生说完,返回屋中。
从此以后,张先生不再鉴宝。
表叔
很小的时候,我感到张大山同母亲关系不正常。当我心里第一次出现这个念头时,突然天昏地暗,一条刺眼的闪电龙似的在头上前方张牙舞爪地乱窜,然后就是一声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炸响。是的,我这个想法是大不孝的,是该挨雷劈的。我忙用双掌紧紧地捂着头,但雷并没有劈在我头上。雷声渐渐远去,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大山是我的表叔,同我们一家关系很好。母亲煮点什么好吃的,总是叫我去请表叔到家中一起吃。那时我家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叫我去请表叔吃饭,一年也就三五次。母亲叫我去请表叔,我是很乐意去的。
表叔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的医药点距离我家不到一公里路。我屁颠屁颠地跑到表叔的医药点,他见了我,满脸笑容地说,家里又煮什么好吃的了?我说,爸爸在田里捉了鱼哩。我又有口福了。表叔一边说一边从身前木桌抽屉里摸出三五颗水果糖给我。我剥去糖纸,将糖放在口边,用舌头添一下,嘴里顿时甜滋滋的。
后来,表叔就经常到我家来了。不是因为母亲煮了什么好吃的,是因为爸爸病了。爸爸腰椎骨上长了一个恶性肿瘤,而且已经扩散,只有回家保守治疗。爸爸经常疼得用手紧紧按住腰椎,额上大汗淋漓。这时,表叔就背着药箱到我家,给爸爸打一针,爸爸的疼痛就减轻了。表叔对母亲说,给表哥打的是吗啡,只能缓解疼痛,治标不治本呀。
表叔给爸爸打吗啡,开始两三天打一次,后来每天都要来打一针,爸爸还是疼痛难忍,整夜整夜不停地呻吟。爸爸日见消瘦,脸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
这天晚上,表叔又来给爸爸打针,我想跟进爸爸的卧室,母亲却叫我到外面去玩。我在门缝中看到母亲向表叔说什么,表叔连声摇头。母亲忽地跪在表叔面前,表叔叹口气,将母亲扶了起来。这晚,表叔很久才从爸爸的卧室出来。
母亲送表叔返回爸爸的卧室,突然传来呼天号地的哭声。我忙跑进去,看到爸爸永远停止了呻吟。
爸爸去世不久,表叔突然把医药点关了。母亲找着表叔说,表弟,你开的医药点是方便乡亲看病,怎么能把医药点关了呢。表叔惨然一笑,医药点是救死扶伤,可我……母亲说,孩子他爹的死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力了。
我经常看到表叔伫立在爸爸的坟前,久久不愿离去。有时,母亲前去劝他:表弟,你不要自责了,真的不怪你。表叔叹口气,什么也不说,然后蹒跚着走了。我突然发现,表叔背有些佝偻,苍老了许多。
表叔的医药点虽然关了,但他看到我还是会给我糖吃。他看着我剥去糖纸,将糖放在嘴里,脸上堆着笑,似乎在讨好我。甜不?甜。我点点头。甜就好。表叔摇了摇头,然后蹒跚着离去。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农活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凡是挖红苕、点麦子、栽秧、打谷等农活,母亲都要叫我去请表叔帮忙。表叔再忙也要放下家中的活儿,到我家帮忙。有时,母亲同表叔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我向他们那儿望,神色便有些不自然。
村里渐渐传来闲话,说母亲和表叔关系不正常。邻居狗娃对我说,你妈偷人。我回道,你妈才偷人。狗娃说,你妈偷张大山。我冲上去就给了狗娃一拳,打得他鼻血直流。
母亲问我为什么打人,我抽抽答答说了缘由,然后问,狗娃说的是真的吗?我话音未落,母亲挥手狠狠地掴了我一巴掌,然后怔怔地望着目瞪口呆的我,泪水哗哗地流了出来。
表叔似乎听到了什么,农忙时,虽然还是随叫随到给我家帮忙,但是不再在我家吃饭,晚上也不赶着做活,早早地就收工回家了。
这天,表叔和母亲又在窃窃私语。我看到表叔双手扯着乱蓬蓬的长发,满脸痛苦状。后来,他和母亲声音越来越大了。表叔说,我快要疯了。母亲肯求说,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呀。
表叔还是说出去了。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竟然给我的爸爸注射了一种毒药,结束了爸爸的生命。
表叔被警察带走时,他面带微笑,对母亲说,我这下解脱了。
想不到表叔这样坏,我冲着远去的警车“呸”了一声。
孩子,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母亲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素芬,我实在痛得受不了了,请你一定说服表弟给我打一针,让我去吧,求你了。
这是你爸爸留下的。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