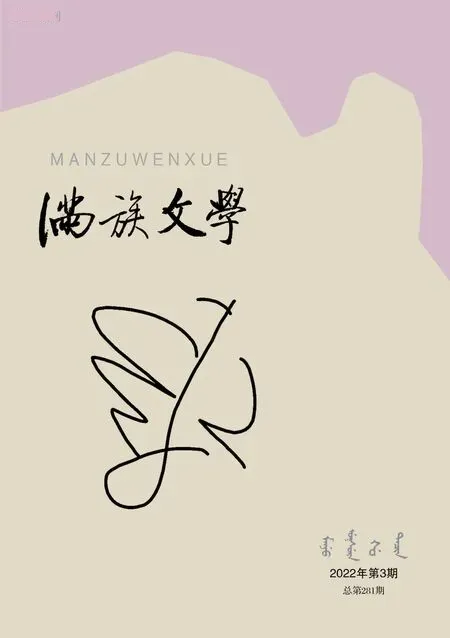满族书面文学流变(八)
2022-10-21满族关纪新
[满族] 关纪新
满族的书面文学,满打满算,也仅只有大约四个世纪的历史。可是,富有内在张力的流变,却每每震荡与充斥其间。满人用汉文写作品,从民族文学的常规说来,似乎不如他们选用母语创作更有价值,甚至很容易被人看作这只是少数民族在被动无奈场景之下,对大民族文化的一种随波附丽。——此种看法有无道理,或许有待于其持有者在全面了解满族文学总貌之后再来商议。
清代从始到终,满族基本还是艰辛地维持着自己在文坛上双语创作的态势,所谓艰辛,是指其双语创作中母语创作的一翼。社会的大环境,使他们日见蓬勃的汉文书写,比愈益萎缩的母语书写,要醒目得多。不管是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上讲,满族一旦开启了运用汉文写作书面文学这只“魔瓶”,便势所必然地,要走上文化与文学大幅度转轨的方向,这一方向所昭示的,恰是一条漫长修远的“不归”之程。倘若单从汉族旧有的文化观念出发,便会轻易地把满人的汉文创作统统扫进“汉化”的箩筐,以为它那特别的民族文化价值到此已告了结,而倘若单凭从满族的文化站位去思想问题,率先跨进汉文写作这道门槛的鄂貌图,则因其舍母语写作而改操他民族文字写作,便非但不是“功臣”,反倒像是一个“罪人”了。
历史现象的价值判定,或许并不那么直截了当。当代学人,业已超越了历代先人的偏狭文化思维,可以用更加科学的民族文化观来指导自己的文学考察。是耶非耶鄂貌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历史上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大文化背景下,重新找寻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即便是现在就亮明到这儿,也未必能为刚刚阅读此文的读者接受。笔者以为,假使可以大致读完本文中的内容,鄂貌图——满族文学史上第一个在语言文字上面铤而“越界”的书写者,其价值内涵,就会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
在满族文学的历史演进当中,鄂貌图可说是一个醒目的转捩点。
重视到鄂貌图个人的坐标性质,却不是说离开了他,满族文学的整体发展就会是另一番气候。诚如前文所介绍,满族既然横下一条心倾巢进了关,就必得学会在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振臂遨游,转而运用汉文写作,那不过是迟一天早一天的事情。
只比鄂貌图稍晚了不多时日,满族当中以汉文书写作品的第一个创作梯队,便及时跟进上来。
其中需要着重介绍的是高塞。高塞(1637—1670),是清开国时期的宗室(即皇族。清代制度规定,只有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始得称为宗室。)显贵,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六子,顺治皇帝的庶兄。此人在那么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委实是爱新觉罗家族当中的特例。打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多尔衮拥戴着冲龄幼主福临进入北京紫禁城,建起清皇朝的一统江山,满洲民族尤其是当时的爱新觉罗们,绝大多数人都极度兴奋地成长在英雄主义的炽烈氛围里。孔武尚勋、建功立业的迫切诉求,是他们压倒一切的人生追求。多少勇猛的将士战死沙场,也有那炙手可热的宗室近支,无悔无憾地倒在了皇权争夺之下。而唯有这位高塞,是一个不为时势所动且完全置身局外的人。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不多,我们知道的,仅是他常年索居于辽东医巫闾山的峰峦之间,过着喜禅慕道、诗书琴曲的闲在日子。当时的爱新觉罗·高塞,必能精通满语满文,但没有留下母语作品,而汉文创作上,却有自己的作品《恭寿堂诗集》(又作《寿祺堂集》)。
高塞的汉文诗,题材面比较窄,基本上是反映个人于山中闲居的现实见闻及精神生活,其中也有不少兴致盎然地游冶名山秀水的作品。
终朝成兀坐,何处可招寻?极目辽天阔,幽怀秋水深。浮云窥往事,皎月对闲心。兴到一樽酒,沈酣据玉琴。
——《秋怀》
平生爱丘壑,历胜恣登眺。医闾夙所期,兹焉惬怀抱。鸟道薄层云,盘纡陵树杪。系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颜发皎皎。问渠何来时,云在此山老。修岭逸惊麏,斜阳急归鸟。古洞驾长虹,细泉屡回绕。亭亭阶下松,百尺参青昊。托根护斯地,籽落无人扫。逶迤度几峰,下瞰群山小。旷然豁心目,顿觉离纷扰。再上白云关,万象咸可了。石门破苍蔼,返景堕空杳。烟霞情所钟,登陟险亦好。大海面岩岫,波光动林表。自古递相传,其中有蓬岛。安期与羡门,往事终绵邈。滉漾失端倪,气色变昏晓。岂识天地心,物理费探讨。冷然此游豫,何用心悄悄。
——《登医巫闾山观音阁》
高塞远离凡尘纷扰,将自己全身心融入山水云林,先前可能会有点儿造成这一个人行为的社会原因,但从他的作品来看,那主要还是缘于他的个性。亲近大自然,向往着自身生命如“百尺参青昊”般的松柏托根于山川大地,是跟满洲民族古远的自然崇拜观念相通相系着的。不论有什么原因教他与身边的军事政治狂潮彼此隔膜,高塞的心毕竟不再属于尘世。在《立秋》诗题下面,他吟道:“萧萧夜雨暑初收,清浅银河淡欲流。怀抱不堪闻落叶,相思何处是南楼?边尘朔气催征雁,塞草西风劲紫骝。回首云山忘岁月,一声蝉噪已清秋。”这是今人能读到的他唯一涉及战争事项的诗,诗人一意坚持的,仍然是“回首云山忘岁月”的心绪指向。
王士祯对高塞的看法是:“性淡泊,如枯禅老衲。好读书,善弹琴,精曲理。常见仿云林小幅,笔墨淡远,摆脱畦径,虽士大夫无以逾也。”足见其心灵倚傍及艺术修养之端倪。
他很有一些高僧宿道的知交,常常与他们赠答唱和,哪怕其中有的人出家前后有所谓政事涉嫌,他也并不在乎。他不想作政治人物,心里就不会存有相应的芥蒂。朋友韩宗騋,本是前明礼部尚书的儿子,削发为僧后,法名剩人,因为有反清倾向,被流放关外,高塞和剩人和尚结成了要好的诗友,后者圆寂,高塞还写诗悼念他:“一叶流东土,花飞辽左山。同尘多自得,玩世去人间。古塔烟霞在,禅关水月闲。空悲留偈处,今日共跻攀。”(《悼剩和尚》)
对照鄂貌图等汉文诗歌的第一批写手,高塞的诗,从内容到风格,更显恬淡洁净。他是最早写汉文作品的满人之一,是颇得唐代“诗佛”王维余韵的一位少数民族诗客。没有“皇兄”的身份,高塞不可能那么早便得到良好的中原文化习养,没有跳出“圈儿”外的人生抉择,他的诗作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走出一条满人诗歌创作的特定轨迹。
鄂貌图的创作调式,与高塞是有区别的。如果把鄂貌图的创作道路,认作是满人写汉诗源头的一道主流,那么,高塞的创作,则可以说是它的一道支流。主流、支流的会通,恰是满族书面文学刚刚启用汉文书写时的本来图景。
既然我们把鄂貌图那端比作主流,就让我们再来看看主流发端过程的另外几位作者情况。
图尔宸、禅岱、顾八代、费扬古,都是顺治朝代略晚于鄂貌图和高塞而开始写汉文诗歌的满人。顺康时期,图尔宸做过工部侍郎,禅岱当过吏部侍郎,顾八代是个立有军功的礼部尚书,费扬古则是在大败噶尔丹战争中勋绩卓著的抚远大将军。下面各选他们的一首诗作:
野色初开宿雾清,晚清天气嫩凉生。半陂新水鹭鸶立,一架落红鶗鴂鸣。霁后烟痕连树碧,雨后虹影接霞明。蒋生三径无人到,怊怅行吟句未成。
——图尔宸:《晚步》
衡阳南头少塞鸿,故园只有梦魂通。三秋旧病千山里,一路新诗百感中。瘦马总肥云梦草,破帆还受洞庭风。归家可耐亲朋老,白发文章未送穷。
——禅岱:《大军次衡阳西山,是夕余先之武昌》
弱冠读经史,胡为事远征。挥戈追定国,从帅靖滇城。崇荫非投笔,髫年未请缨。妖氛围上将,参赞委书生。一自单车去,相将万里行。机宜因合算,攻伐偶然成。以此堪归隐,谁知更作卿。余年叨禄养,报国寸衷萦。
——顾八代:《述旧》
秋日出都门,言寻西山道。试登最高峰,放眼观浩浩。天风飘塞鸿,荒原衰白草。日暮起层阴,落叶随风扫。烟云荡长空,野水枯行潦。蓟邱古战场,杀气飞霜早。草昧窃英雄,妄意窥大宝。千秋几斗争,士卒涂肝脑。白骨幽黄沙,扑面伤怀抱。依杖独徘徊,漫忆渭滨老。百世树奇功,长往终难保。何似赤松游,飘然归绝峤。
——费扬古:《杂诗(四首选一)》
以上四人,都与鄂貌图近似,是明清之际“积极入世型”的满族官吏将领。几位写的诗,功力虽有参差,欲以中原传统诗歌形式来表述的思想,却跟鄂貌图很近似。作为当时置身军旅的满人,他们无不豪气充满胸臆,以功名事业为人生鹄的,可是作为汉文诗歌的作者,又跟鄂貌图一样,总得顾及中原的文体及文化传统对自己的约制,得让作品带有些个“中和”色彩。即便分明是奋不顾身的征人战将,却还是要在创作上添加几笔“愁”呀“归”呀的文辞,似乎不这么着,就不像是在写汉文诗歌,也得不到中原诗坛的认可。他们作为汉族“先生”的首批满族艺徒,希望自己的写作“中规中矩”,希望获得“先生”的满意和夸奖,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殊不知,这在无形中却又束缚了这批异民族作者真性情的崭露。
从鄂貌图到高塞,再到图尔宸、禅岱、顾八代、费扬古……清朝开国不久,满族就及时地从一个母语写作民族,转变为在文坛上两面出击的双语写作民族。而且,一旦汉文写作这扇门被訇然推开,满族人的汉文写作就仿佛领受了八面来风的激励,迅速超过了母语写作的规模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