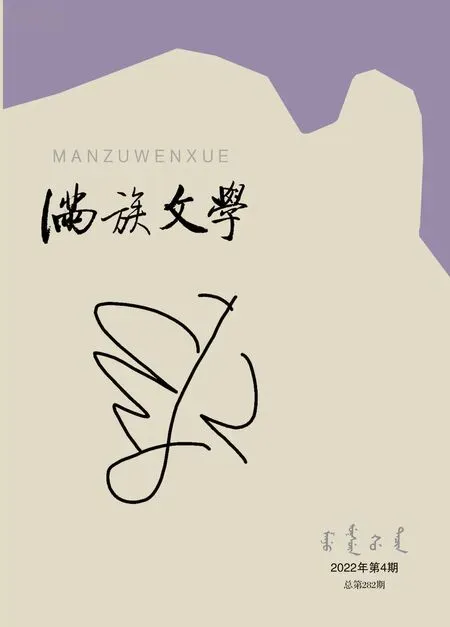树·石头·河流
2022-10-21李广智
李广智
树敲敲就碎了
树敲敲就碎了,像一个人老掉的牙齿,活动活动就掉了,从此再无瓜葛。我挥动着护林员(兼职导游)赵大哥帮我新斩断的一截木棍,努力向大青山峰顶攀爬时,不小心碰了一下那节灰色的树枝,咔嚓一声,仿佛寂静的时空一声爆裂的响雷,枯枝断裂,掉落在地上,时间刹那间在一节树枝上掉落、凝固。树枝闲置在老枝上,老死在树上。树再也用不着它长枝叶,再不用它结果子。可树跟人不一样,它从不把一件闲置的事情随意丢弃给生活,枯枝只好留下,举在空中。不知疲倦。
树枝在树上老死,一截一截地老死在树上。先是叶子枯萎,掉落,然后是树枝干枯,水分从树枝内部一点点抽离。生命不会突然消失,它一点点地消耗自己。在一棵树的身体里,在一棵草的身体里,也在我们的身体里,直到所有的活力消耗殆尽。我们说剪掉就剪掉一截树枝,从不吝啬,可在大青山上,所有的树都是自由生长的,它们想往上伸出一枝就伸出一枝,想往下伸出一枝就伸出一枝,从无顾虑,不像生长在我们身边的树,长错了方向,就被无情地剪掉。大青山上的树不怕浪费营养和姿势,它们覆盖了一整座山,以山为王。在高高的山上,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村人。
很多老去的枯枝横亘在山上每个角落,没人搭理,像个孤独的人。我看见一棵山梨树,它没有一片叶子,灰色的枝丫伸向空中,安静、孤单,我看不出它是一棵什么树种,安梨,白梨亦或花梨?仅一个照面,我判断不出一棵树的种类。有些树和地上的蚂蚁或者毛驴一样,模样差不多。我和老家院子内外的果树打了二十年交道,可我还是分辨不出没长出成熟果子的梨树。
我喜欢一个人孤独地写作。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安静地倾听大地的声音。抚摸一棵草、一棵树,对视一只蚂蚁。我一直试图找到与它们对话的方式,尽管总是徒劳,可我不想放弃。我渴望了解一棵树的孤独,然而,我没能分辨出一棵孤独的树。
在快要登顶大青山时,在盘根错节的树林里,爬山略急的我呼吸急促。我已经很多年不做这样剧烈的运动了,我居住过的村子没有这样的高山,爬上山顶也费不了多少力气。许多年前,我只在长跑快结束时才会如此呼吸急促,我心里清楚,这是心肌缺氧的表现。我只好停下来,止住脚步,眼前是几棵梨树,树皮开裂着,有几处甚至已卷起。那是好久没有水滋润的表现。树缺水了和人缺水了一样。我不清楚整座山里到底有多少棵果树,这也是我难得遇见的几棵梨树。我用木棍轻轻敲击满树的枯枝,满耳响起了咔咔嚓嚓断裂的声音,满眼便是树枝掉落的景象。一截截曾经的生命砸落地上,发出一声声脆响。我的骨节疼痛,仿佛听见一棵树的生命渐渐离我而去。
丛林里有着很多老去的树,树龄不大。它们还保留着死亡前的尊严,或躺或卧在大地上,或依靠在同伴身上。我不知道这些树在整片山林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在远处看见了整片山林的光鲜,没有谁会为一棵树的死亡心怀愧疚。就像某个人的猝然身故,我们不会心怀愧疚一样。在屯子里,记不清多少次,某棵树会突然咔嚓一声,我不清楚是某处断裂还是别的缘故。我一直认为自己已经是屯子里的一棵树了,可我站不到一棵树的高度,这让我不能更深刻地了解一棵树。在寂静的空间,我有时会听见身体里的骨头嘎嘣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体里剥离出去。也许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东西从我的身体里丢失。离我最近最亲的爷爷奶奶,被父亲和叔叔埋在了屯子的土地里,他们也会和这些掉落的枯枝一样,经过数年,最终和大地融为一体,成为泥土,无法分辨。只是我们这些晚辈还会怀念起他们。这些枯掉的枝杈不知会被谁怀念。我们和树是两个世界不同的生物,谁被谁怀念也无法断定。我们不知道一片叶子或者一根树枝的掉落是不是一棵树的忧伤?一棵树肯定也不懂我的忧伤。我隐没在丛林中,轻轻抚摸一棵树断落后的伤口。我是第一次登上山顶,第一次看见这片远离人家的成片树木。平日里,肯定没人愿意费时费力爬到这片山林。导游赵大哥说,好天气,站在山顶可以看见百里外的海上日出。临近大青山的学校曾无数次在天未亮时就组织学生到山顶看日出。确切些应该是看渤海的海上日出。只是我没有一双火眼金睛,穿不透远处的一片雾霭,看不见大海的影子。居住在屯子里的人,白日里,把力气洒在田地里,晚上也许把力气洒在炕上,没有闲力气穿越树林,爬到山顶,看一看海上日出。都说站得高望得远,大青山在县城地界是最高的山峰,但肯定有很多屯人没上过山顶。
这个世界没有谁比谁更接近死亡。我并不想费上些力气非得敲掉些树枝。它们只是我行进路上碰见的一些逝者,树们无能为力。在坚守岁月的时光里,也总会有些人丢失在路上,我们甚至无法用手拉住他们。作为人类,同样无能为力。在时间的路上我们与万物一样,弱小而无助,这更让我对一根枯枝,对一棵老树,对沉默的大地,对所有的生命,充满敬畏。
我知道,我敲掉再多干枯的树枝,它们也只是岁月里的细枝末节,我敲不断时间的任何一段枝节。那些咔嚓咔嚓的声音有一天也会在我的身上响起。
石头河
石头也会淌成河。在大青山上淌成石河,流一坡石迹。
在山的中上部,一块又一块巨大的岩石禁受不住大自然的考验,更古老的岩石在某个时候轰然坍塌。那个时候,天空也许滂沱大雨。雨水进入到岩石的内部,沿着开裂的缝隙,到处流窜,潜伏下来。严冬很快到来,那些深入到岩石内部的水开始凝结成冰,巨大的膨胀力,进一步撑裂岩石的每一条缝隙。一些尘土也被带进缝隙,也许还有种子,它们也可以在缝隙内安家生长,根系像一根根深入岩石的尖撬,一步一步撬开每一块岩石的裂缝。所有深入岩石的力量,在悠长的岁月里,在寒冻风化的作用下,一步步分解着山上裸露的岩石。然后那些巨大的岩石在炎热的阳光下,也许是在连绵的雨天里再次轰然坍塌碎裂,顺着山坡向下滚去。这样碎裂的石块越来越多,碎石汇集到斜坡下的沟槽内,像一条河流一样,沿着沟槽向山脚下延伸。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块在重力的作用下,像翻滚的水浪,在山上起伏动荡。
石头河到处都是棱角分明的凸起。在我踩向一块大石块时,它晃动了一下,石头与石头轻微地碰撞了一下,发出几声嘭嘭的响声,显然底部不稳,它随时会发生翻动,人也会掉进石头河。我不想沦陷在一群石头中,稳了稳身子,让身体尽量保持平衡,不至于摔倒。在石头河里,让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与身体发生碰撞,身体肯定会一片青紫,也许皮肤会被割开,流出鲜血。在大山里,这种流血也许是致命的。石头河离村子很近,却需要走很久。那是一条河的距离,我只好尽可能地踩向那些平稳的石头。然后用手里仅存的那根临时拐棍,探向前方的石头,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小心,才能继续向前探索一条石头河。
如果石头河的底部是松软的泥土,一场持续连绵的透雨,肯定会让这些石头像一条河流一样继续向下方淌去。那些坚硬的石头,流淌起来,一定是世界上最坚硬的河流、最恐怖的河流。山下,村民抬头看见山上万千石头如万马奔腾般,声音如雷翻滚而下。所有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景象,可是石头河在历史的河流中,肯定不止一次向下流淌过。
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河,远离村庄,据守山腰之上,像悬挂在大青山上的一条条天河,被“冰封”成各种形状,无人可撼动。只是大青山有点高,石头河的位置也有点高,更有些分散,它们终究不会像河水那样汇聚成一条大河,奔腾于山野之间。远远望去,它们更像绘制在大山上的一幅幅灰色巨画,牢牢镶嵌在山林之上。
我多想趟过几条石头河,那是一条条承载着大青山历史的河流。有些河流中的某个地段,石头已被护林员或者先前的某个探路者摆正,平滑的一面露在外面,石与石之间互相挤压,牢固而平稳,人走在上面,像走在一条石砌的路上,让人心里有了“安全感”。
我累坐在空旷石头河的一块石头上,一阵又一阵风掠过山腰。它们在树林中嘶喊着,有石头在风中轻轻抖动身子,石头的撞击声响起,那声音在石头河中回响,仿佛要引动一条河流的咆哮。我内心陡然一惊,我听见那条河流开始奔腾,它们正快速向下涌动,一块块石头开始翻滚,巨大的轰鸣也正从石头底部向上传来。这样的河流经过的地方将被石头覆盖,青草、树木的生命将被翻滚的石头迅速收割。我惊悸地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眼睛游离于每块石头之上,内心被恐惧掩埋了一遍又一遍。
据资料查证,石河的运动速度其实很小,可在重力作用下,它们会一直流到山麓堆积下来。在高高的大青山上,抵达山麓的距离几乎可以耗尽我全部的体能。我不清楚石头河会在何时咆哮起来,但我确信这条河流会继续向下涌动,这是一条流速缓慢却危险的河流。
沿着一条河流向上
我确信每一条河流都是生命的开始。有水的地方才会有烟火的村庄,草木才会在河流的臂弯里丰盈。
我是沿着一条河流向上,最终攀爬上海拔1223.8 米、素有“辽西屋脊”之称的大青山峰顶的。上山没有路,山太高,林太密,无路可寻。水会绕开石头、树木以及一切障碍,自上而下奔淌,为自己冲刷出一条道路。人们沿着一条河流向下的道路逆行而上,一条河流就是一条道路。
我曾不止一次地沿着河流向上,想看看每一条河流上游亦或源头的样子。有一次,我身处一条河道的下游,模糊地知道,我寻找的村庄就在那片地域,索性不打听,一直顺着河道向上行走。我笃定那个村庄一定在河道的上游。我沿着一曲白水向上。那条河流时而安静,时而活泼,水流不似大河那般粗壮,涓涓细流,像个不谐世事的村妞。朴素、干净、干练。穿行过数个村庄,遇见来接我的人,果不其然,那个村庄就在那条河流的上游。
小时候,我几乎寻遍了村里每条河流的上游,那时差不多每一条沟的尽头都有一泓清泉。它们有的从岩石或泥沙里悄无声息地渗出,有的自地下涌出,像一池沸腾的水。这水不烫人,清凉甘甜直入肺腑。看见的人不遮不掩,径直俯下身,大方地将头探入水中狂饮。亦或用手掬一捧泉水,温文尔雅,轻咂细饮。我在外地学习时,就遇见一个相熟的人喝过我老家甘甜的泉水,说那水好喝,一定要找机会回去再喝上一回。我一直以为山泉水是大地的乳汁,滋养着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大青山的水也一定养育着大青山的草木和村人,这让我对沿着河流向上的大青山充满了期待。
我们从大青山脚下一个村子开始,沿着一条河流向上,这是我们攀登大青山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在大青山上,只有山上水向下流淌过的地方,树木、石头才略显稀少,行走也才不会太难。
山太陡,只能抓住一棵又一棵树的枝干。我已经看不出水流漫过一棵树向上部分的模样。所有的树已经在河道两侧亦或中间扎根生长,根部深抓大地不知多少岁月。它们远比我高大,我在一棵树上再加上一些力气,也无法让一棵树倒下,更无法撼动一棵树的生长。稍不留意,脚下一块松动的石头失去了平衡,哗啦一下,像一头脱缰的野马,砰砰地撞击着树干亦或同样坚硬的石头,横冲直撞地向下快速滚去,消失在视线里。它们是一条河流向下隐秘的雷声。很多年前,我家门前那条河流在大雨过后,时常会有这样滚动的雷声,等到暴涨的河水退去,我看到满河套落满大大小小的石头。它们都来源于一条河流的上头,这让我不断萌生出沿着一条河流向上的念头。
我们怀着这样的念头,一路攀爬到大青山顶,再寻不得一泓清水。山太高,一条条水迹清晰的干涸水道悬挂在山坡,只有山峰常接云端。我们在山巅俯视沟壑纵横的沟底,一条条向上的河流潜伏于沟壑底部。它们隐去湍急的声音,隐去纤细或粗壮的身体。河流已成为一位隐士。隐没山林,隐没大地。在河水干枯的季节,听晓一条大河美名,在沟壑纵横的大地上,却寻不到那河流。向当地的村人打听,果然有一条大河隐匿于这方土地,却只在夏季时突然咆哮于河谷之中。
我听闻,沿大青山左近的一条河流向上,可以寻见拥有瓷釉般质地、古玉般光亮的蓝花石,那石头里同样藏匿着一方奇世界。我不知道那些遗落在河流中的蓝花石是如何冲刷而下的,那石头也许不在大青山的腹地。我手里没有一块可以让我看透一条河流的蓝花石,可我知道它在一条河流的上游。
沿着一条河流向上,我们会看见鲜花,看见树木,看见水从云上来,看见一条河流清澈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