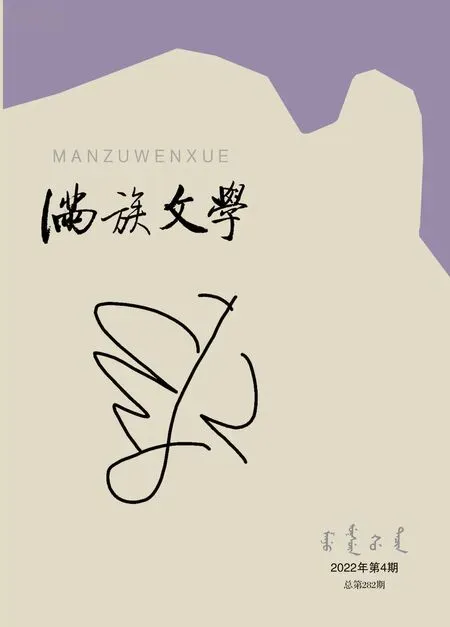动物三章
2022-10-21罗张琴
罗张琴
虫儿飞
小暑之后,南昌实实在在就是“火炉”了。苦夏难捱,心绪烦躁,每天一下班,哪也不想去,只愿待在空调屋里,读闲书,吃西瓜。只是,冰箱再大,西瓜品相再好,也再难吃出儿时用仙人井井水沁出来的那般好滋味了。
前段读清少纳言的《枕草子》(林文月译本),这本书,早年周作人先生也曾译过,两相对照着看,我总要忍不住感叹,这世间,再有才气的男人,实在不如女人更懂女人的玲珑奇巧。
首篇《春曙为最》,一看难忘:春,曙为最。逐渐转白的山顶,开始稍露光明,泛紫的细云轻飘其上。夏则夜。有月的时候自不待言,无月的暗夜,也有群萤交飞……读到“群萤交飞”时,眼前仿佛突然悄立一扇柴门,我只伸手轻轻那么一推,便站回了三十多年前家乡的那条水渠边上。
生平第一次下田,原是为母舅家“搬禾”去的。七岁多的我,赤脚在母舅家金灿灿的稻田里奔跑。稻子很香,阳光饱满的味道。稻子成熟,真是会弯腰。稻子弯腰的弧度,与大人们收割稻子时的弧度,一模一样。
我将大人们用镰刀割下的一茬茬稻禾搂抱胸前、腋下,搬运给在打禾机劳作的两个表兄。表兄们的小腿可真结实有劲呀,我们几个更小的孩子用再快的速度也赶不上他们踩动打禾机的速度。成长既喜悦又残酷,结局既丰满又虚空。“轰启,轰启”,谷子被打禾机剥离的声响,简直就是要人命的号角。太阳下山,待母舅在大板车上堆好粮包,我的双腿已经腾云驾雾,接不到一点儿力气了。我最后漂在大表兄的黑脖子上。
我在巨高的黑脖子上看见八子。亭亭玉立的八子头枕双臂,仰躺在水渠边的草地上,仿佛一个做着甜蜜好梦的仙女。我让“黑脖子”蹲下并赶他们都走。我要一个人独闯我向往的、她的仙境。
“嘘!”八子没有睁开眼睛,她捏了捏我的手,示意我与她保持同样姿势。一川山水。放空身心的我们,将迎来什么惊喜?我不敢动,仿佛身边遍地是岁月之钟。
流水淙淙,流云蹁跹,都是迎接月光的队伍。“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是一种美;夜色辽阔,月光洒进广袤田野,是另一种美。此时的月光,再不是稀疏残雪,而是大地之上最为轻柔绵长的丝绸,它让暗夜不再恐怖,让黑色不再沉重。一切朦胧可亲,我们仿佛躺在老祖母的怀抱里。
有不一样的光在眼皮上动了一下,两双眸子瞬间亮晶晶地对视、环顾。一点光摇曳着从草丛中升起,又一点光活泼地从草尖上弹起,追向它。一点两点三四点,光呼唤着光;一片两片三四片,影重叠着影。水渠幻化成天河,我们是潜入天河的会动的小小石头,而那些发着光的萤火虫就是在天河里游来游去的尾尾小鱼。单纯、古典、美好的气息纷至沓来,将我们席卷。这样的夜晚多么使人沉醉呀。
我们在月色溶溶里向姑婆兜售萤火虫的轻巧、萤火虫的飞翔以及萤火虫的束束流光,天知道,那个老太太为什么那样固执她的己见:“萤火虫,是孤苦无依的灵魂,它的光,与坟茔旁的磷火一模一样;萤火虫是不祥之物,但凡沾上,好好的黄瓜秧苗全没了根,胖胖的蜗牛全化成水,它有看不见的毒针,永远别让它近你们的身……”用来盛装萤火虫的小小玻璃瓶,在姑婆的呵斥中碎了一地。萤火之光,如沉凝的流水,四散而去,不言不语。同样不能言语的还有童年的委屈。
我们用孩子的方式执拗着对萤火虫的喜爱。
比如,在夜晚的溪边徘徊,以身为饵、展开双臂等待萤火虫的到来,我们端详它们,就像打量倔强的自己。别说它不是从坟茔中长出来的,即便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旧坟处,不断生长出新坟,一代一代人老去,而萤火虫一直都在。
不发光时的萤火虫,普通甲虫的样子。身形扁平细长,大部分都只一厘米左右;两扇纹着一圈金边的黑色翅膀,遮掩着腹部发达的腹足以及腹足上整齐排列着的许多小钩;小小的淡金色头部,长着一对细长触角,中心有一点红;最与众不同,尾部一节向外凸出。那是它的发光器,只在夜晚以或快或慢的频率,闪耀淡金色的光芒。这不灼伤自己的冷光,为人类照明提供了灵感,人类依此而制造了安全照明。我们也曾在数枚鸡蛋上完成了对萤火虫的“发明”:蛋顶上敲开一个小口,清空蛋清蛋黄,将萤火虫放进去,再用白纱线捆住伸进蛋壳的细小棍子,数盏“移动飞灯”很快在村子里蜿蜒。
比如,被大人强行禁足的夜晚,我们一遍遍反复高唱同一首歌谣:萤火虫,点灯笼,飞到西,飞到东。飞到河边上,小鱼在做梦。飞到树林里,小鸟睡正浓。飞过张家墙,张家姐忙裁缝。飞过李家墙,李家哥哥做夜工。萤火虫,萤火虫,何不飞上天,做个星星挂天空。在未经世事的孩子眼里,从萤火虫那里看到的,从来都是生趣,都是希望。
待长大,读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时,我突然被一种哀愁的叹息击中。宫女居住的庭院竟然有流萤飞动,无事可做的宫女,只能以扑流萤来消遣无边寂寞与孤独岁月。宫门一入深似海,那一扇“轻罗小扇”上承载了多少被遗弃的命运?那些美丽的流光背后,是多少曾经渴望绚烂绽放的花样年华?我几乎是在那一刻,读懂了姑婆的执拗。命运多舛的姑婆,终生未育的姑婆,在她久经沧桑的心里,一切美好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云烟易散,陪姑婆长久的,是漫漫长夜与无边寂寞。
八子常说我是一个活在旧时光里的老派人,我觉得这是赞美。为了匹配她的赞美,这些天的夜晚,我是陪奥特曼一起读《我的二十四节气》度过的。书中所写“大暑。一候腐草为萤”,当是古人对萤火虫最美丽的误会了。萤火虫当然不是经腐草变生,而是由雌雄成虫通过发光器闪光频率相互确定爱恋关系后交配繁衍生息的。
萤火虫寿命长不过两年,它们短暂一生,经过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种形态。一颗颗自带荧光密码的圆形卵,形如迷你夜明珠,被雌萤产在杂草丛生的潮湿处。顺利孵化后,进入幼虫期,幼虫长有非常发达的上颚,像一柄弯镰刀,刺入蜗牛、蛞蝓、蚯蚓等猎物体内,同时,通过上颚中的管道,向猎物注入消化道内具有毒性的液体,使之变成肉靡状的液体吸食。在半年到一年左右的幼虫期,要经三到五次蜕皮才能进入蛹期。化蛹时,幼虫用泥沙做成茧,两周后羽化成虫……这些知识并非来自我的观察,而是我从纪录片里总结提炼再转述给孩子的。我还给奥特曼罗列了萤火虫各种绰号:流萤、夜光、耀夜、宵烛、复景天……给他讲了车胤囊萤照读的典故与查慎行“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的诗词。可奥特曼始终无感,他说,妈妈讲那么多,实在比不上带他去看一只真正的萤火虫。
这真令人沮丧。一方面,萤火虫是对环境非常敏感的生灵,轻微的污染足以让它们选择逃离。另一方面,萤火虫成虫期不过一两周时间,这一两周,它们的全部使命就是通过发光器的“光之语”,找到同频共振的爱侣,完成交配,产出虫卵,然后了无遗憾地死去。灯火通明的城市,早已完全覆盖了萤火虫的光亮,无法循光而至的雌雄成虫们,在孤独中,慢慢悄然绝迹。多么害怕,那些精灵,从此只在童谣的高山之巅、流水之畔,发出光芒。
看着孩子的眼睛,比月夜更璀璨晶亮的眼睛,我实在必须掩藏我的悲伤。这些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出空调屋子,去往江边湿地公园。在萤火虫可能发光的戌时,我陪着奥特曼在草丛边蹲守。我如此渴望,那些曾在暗夜背景上闪着诗意的点点萤光,能将孩子的眸子照亮。
与鼠为邻
亲近自然是孩子的天性,即便远离洋溢湿润气息的泥土,孩子们也能变着法地用从商场买来的各色彩泥,揉捏出许多鲜活于心的生灵形象。
灰色、滑泻的身躯,暗红、漠然的眼神,银色、层叠的鳞片……当奥特曼把他手工课作品递到我跟前的时候,我分明感到了一种扭动的凉意。看上去温顺、沉默的蛇,永远潜藏着巨大危险,多像那个蜷曲、漫延在我们躯体里的灵魂啊。
“快拿开!”我心慌一吼。“对不起,妈妈。我本来是要捏一只可爱的小老鼠送给你的,可是,太难了,想到昨天学了成语‘蛇鼠一窝’,就捏了它的好朋友蛇来代替。”蛇,老鼠的好朋友?又一个被人类强行捆绑并胡乱摊派的危险误会。亲爱的奥特曼,相对于猫,老鼠真正害怕的天敌其实是蛇。
擅长打洞的老鼠,一双豆眼儿虽近乎弱视,听觉、嗅觉及味觉却很灵敏。它时刻将大耳朵竖得挺括,那严阵以待的劲儿,仿佛连尖嘴上的胡须都成了钢丝。一有声响,老鼠屁股一绷,尾巴一翘,以百米飞人般的速度变成一束灰光逃回洞中。那些洞口大不过婴儿的小拳头,小的只五分钱硬币大小,再厉害的猫,料也钻不进,只能干瞪眼;只有蛇,“哧溜”几下,就用那滑泻的身体将老鼠堵了个正着,一饱口腹之欲。
老鼠,可爱吗?也许是有的。“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儿歌里的小老鼠顽皮淘气,天真烂漫。“鼠咬天开”。在天和地混沌未开、乌黑一片时,第一个站出来、将天咬开一个大洞、让太阳光漏进来的老鼠多么勇敢,于是中国人将它排在了十二生肖榜首,每入民俗画,喻义大体指向灵巧聪慧、家族繁盛;古埃及人认为老鼠象征大地的富饶资源与盎然生机,将它与月亮联系一起,计算着人间的岁月;古罗马人以看见白鼠为吉,以鼠咬破衣物为厄运将至;还有米奇老鼠,机智杰瑞……
奥特曼尚小时,我教他画的第一个简笔画动物形象不正是一只卷曲着小尾巴的可爱老鼠吗?可是,天知道,小时候的我,有多讨厌、害怕老鼠。
我讨厌它们不劳而获。谷子、红薯、南瓜、花生……几乎所有庄稼收获,人类的即是老鼠的。老鼠个虽小,食量却惊人,每天至少要吃掉自身体重的百分之十以上才会摸一摸肚子,呼一声“满足”,然后,第二天,接着吃。吃就吃吧,还那么嚣张,白天黑夜,一点不怕人。谷壳遍地,老鼠屎横行,噬咬声几乎成了每个夜晚我们必须过关的神经考验。
老鼠的门牙极发达,没有齿根,可以终生不停生长,所以它必须不停寻找物品噬咬以磨短门牙。木柜被咬坏,水泥被咬烂,就连钢管都难以逃脱碎裂的命运,更别说我们心爱的小衣衫、小白球鞋了,最恨的是它居然连我珍贵的小人书都要咬,简直天理难容!
每回狭路相逢,我都故意咳嗽,或大声吞咽,或使劲跺脚,老鼠不畏不惧,只躲在暗处发出“窸窸窣窣”的动静。偶尔,它还张狂一窜,吓得人魂飞魄散。胆小如我,能奈之何。我最期待的日子,从来不是除夕,不是春节,而是立春那天。立春那天,姑婆在房前屋后插上无数根跳动红色火焰的蜡烛,领着全家人一人持一根大棒子在墙壁门板敲敲打打,叫醒蛰虫,迎春接福。我对迎春接福不很在意,我只觉得老鼠或许会被这喜庆的动静震晕,被这满屋子的红火所惊吓,从而抱头逃窜,再不来犯。
宁静是短暂的。在旧日乡村,孩子与老鼠的战争就像一块翘翘板,按下这头,弹起那头。不对,应该说更像是小熊推秋千,用多大力推出去,秋千很快就会用更大的力反扑回来,一个孩子的好胜心常常因此被伤得体无完肤。大人也毫无办法,他们不断更换鼠夹、粘鼠贴甚至买来老鼠药,可狡黠的老鼠,似乎永远都占着上风。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幼时,我每读《诗经》此首,总将“无”“逝”两字读得既忿恨又决绝,仿佛字中藏有千钧万力,能将一干贪婪鼠辈撵赶得一干二净。
与老鼠嫌隙渐小,我以为是在一座山巅。山巅是我与八子同窗好友云的家。高二还没放暑假呢,云就不见了,问过与云同村的同学才知,她因家生变故,不得已辍学返乡。
县城坐大巴到乡里,乡里搭运粮的手扶拖拉机进村道,暑假一放,我们便急急跟着人去往云家。人烟稀少处,村道也没了,前后踩了几溜田埂来到一座山脚下,手脚并用攀过这段陡峻山梁,才望见目的地。
一个村子,六户人家,各占一个山头。六幢大小不一的土坯房在山峦间遥相呼应。太阳下山,鸟凛然一收翅膀的声响,让人身上的汗水瞬间蒸发。云背对着我们,先用木耙将晒天里的谷子收拢成堆,再半曲着一条腿抵住偌大的撮箕,两手奋力挥帚,将谷子往撮箕里扫。家鸡们,捣蛋鬼一群,扒散谷堆、偷食谷粒不说,还一个劲在云身边磨来蹭去,仿佛嘲笑她独木难支的狼狈,任凭云怎么“嗬曲”都赶不走。磨到光亮的泥地,仿佛包了一层暗沉的浆。
饭是赶在最后一抹云霞落幕前,云自己做的。几个月前,她家一根横梁松动了,她父亲上山寻料,运回家里,从半山腰一脚踏空,滚落山底,骨折并被尖石穿破了一颗肾脏,母亲及弟弟在医院陪护,云在家抢收抢种,料理仿佛是救命薪火的家禽牲畜。四顾群山,路远水寒,瓜果蔬粮都是自产自销,权作口粮,唯这家禽牲畜一年能卖几茬,换些票子应急。
天黑沉了,不见云亮灯。一屋子,三个女孩子,说话还好,话语一停,夜仿佛一头似梦似醒的哑巴怪兽,让人心下惶惶。
村子太偏,电线没架进来;这段时间没出山,蜡烛也用光了。原不是云节省。只是,一个人守一座山,该有多害怕呀!我与八子同时摸索着,将云的手紧紧捏住。云的手上,新磨出的水泡,硌得牙齿,生疼生疼。
“没关系,多好的月光星子呀!”云的眼睛晶亮晶亮的。
“那没有月光星子的夜,要怎么办?”
“还有许多老鼠邻居呀。听,它们正‘吱吱吱’叫呢!”
月光之下,许多只老鼠从容啃着不设防的红薯、南瓜,它们的暗影相互重叠,数根卷曲的尾巴就像数只互相攀扯着的小手。鼻头莫名一酸。人生之中,恐惧是短暂的,悲哀是永恒的。我们又何苦跟老鼠过不去呢。
蛙声十里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一场雨过后,天渐转凉,南昌城里,秋的脚步,已然“沙沙”作响。
秋日闲暇,适合看画,尤其适合看中国水墨画。是的,于画,我所学甚薄,天资也钝,只能说“看”,断难有言“赏”或“品”的功力。
远山映衬,山间堆满乱石,青苔覆着石上,石间泻出一道清涧,随清涧而下的,还有数只摇着小尾巴的蝌蚪,蝌蚪们贪玩,不知不觉离开了妈妈的视线……《蛙声十里出山泉》当是齐白石先生被世人所公认的最优秀代表作之一了,不仅被收入各级美学专业课本,还被印成邮票,名扬五湖四海。
画是绝品,其来历也颇浪漫。作家老舍爱画,曾在家中专辟一墙以挂藏画,每更换一批,必邀人赏鉴,日久,这墙得一雅号“老舍画廊”,在坊间颇负盛名。老舍尤喜齐白石先生画作,素爱藏之,齐老九十一岁那年,他又上门求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年求出了新意,即他以诗句为题,由齐老“依题”完成。
“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几树寒梅映雪红”,第一次,老舍给出曼殊禅师的四句诗,齐老一看,点头微笑,不难嘛,诗中暗含春夏秋冬,合在一起正好是一年四季的花卉配诗画。
到了夏天,老舍再次以四句诗求画,其中,最难一句当属查慎行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如何表现“山泉十里”有“起伏蛙声”,齐老可是足足思考了三天,才寻得灵感。灰色蝌蚪是绿色青蛙的孩子,黑色蝌蚪长大会变成蛤蟆,试问,哪个贪玩孩子身后少得了来自父母的千叮万嘱?“蛙声十里出山泉,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题在画上的这段话,不仅道出了天才画家加生活家的奇妙构想,更向世人描绘出了一朵经两个艺术家思想碰撞后产生的瑰丽火花。
作为两栖动物,青蛙是最早离水上岸的生物,其上岸时间大概可追溯到三亿年前,大体是生存环境面临极大挑战的石炭纪,气候变得干燥,沼泽地大大减少,为了适应陆地生活,青蛙不断进行自我进化。又长又健的后肢,使青蛙独具跳跃本领,有些高度可达身长的五十多倍。我在网上浏览到一则青蛙捕食的视频,那跳跃真使人着迷,捕食之后,它顺荷梗而下的样子,冷静又酷炫,多像是一个风姿卓越、气质出众的铜管舞演员呀。
青蛙以虫为主食。冬天,虫子太少,青蛙饱餐一顿后,开始了漫长又无欲无求的冬眠生涯。我不只一次,在水草丰茂的湿地,撞见过青蛙提前走进冬天的场景:尾部向下,头朝上,懒散而又机警地,由屁股发力,将身体一锉一锉地往沙里坠。不是加速度的“坠”,是一点多一点地往下挪。我无法确定青蛙是否提前挖好了沙洞,也不知道它是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挖洞的,我只知道,它就这么一点接一点地将自己慢慢没入了沙土里。
惊蛰一过,天,暖和起来。“咕呱”“咕咕呱”“咕呱咕呱”“咕咕咕呱”,频率不一的蛙声随溪水涨起,渐渐,漫过童年的整个原野山乡。潮湿而又充满生机的蛙声,让山峦更显静默雄浑,让溪流更添欢欣清澈,田园收获的希望在乡人的心里变得无比丰厚起来。说蛙声是农耕文明的一个别致鼓点,一点也不过分。不过,在雌蛙的耳朵里,“咕呱”之音哪里是什么鼓点呀,从来都是雄蛙向她们发出的求爱宣言。爱的宣言,庄重绵延,宛如漆黑长夜望之心安的灯塔之光。雌蛙循“光”而动,从冬眠的洞穴里一跃而出。
家乡老屋的后边是水塘,东边是南山岭,南山岭再往东,是大片大片的水稻田。稻田之间,有座山,山里有个桃树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桃红李白。一条不知名的十里长溪绕山脚而过,浇灌稻田绿油油的成色,也滋养了我整个童年。水塘边、稻田间、杂树丛、烂泥坑,年幼的我,常陷入蛙声的海洋。
印象最深,是溪水暴涨时,青蛙们总是两两“套”在一块,长久不分开。熊孩子看不惯,觉得生腻,便常常恶作剧地找来棍子将它们拨开。只是,才拨开这一对,那一对又粘一起了,转身去拨开那一对,这一对又瞬间粘上了,简直就是做无用功嘛。气恼得不行,便使出吃奶的劲儿去拍打水面。
经年后,才知有一种罪过叫“棒打鸳鸯散”。“抱对”本是青蛙繁殖的一种手段,雄蛙趴在雌蛙上,相当于丈夫给妻子陪产,刺激妻子又快又不那么难受地完成分娩。然而,雌蛙分娩的痛苦,与哺乳动物没什么不同,甚至更锥心,因为雄蛙在看到雌蛙完成一次产卵任务后,会快速离开,去寻找另一只雌蛙。这行为,要是放在人类世界,简直就是罪无可赦嘛。
结束分娩的雌蛙,全身肌肉僵硬,瘫痪般一动不动趴在原地,足足有五六分钟之久。在雌蛙张开的后肢夹角顶点处,一团黑乎乎的蛙卵,有成百上千个,这些蛙卵在水流的作用下渐渐施展为一排长线。可怜的雌蛙甚至没有力气回望她的孩子们一眼。第二天早上,元气大伤的雌蛙,咽下最后一口气。多少是个安慰,她的孩子正在水下迅速成长。蛙卵孵化对水质要求高,对水温很敏感,十五摄氏度左右的水温是最适合的了,只需七到十天,小蝌蚪就能“破茧而出”。蝌蚪出生时,桃树坑的十里长溪,黑压压一片,那小小而又密集的攒动,足以叫一帮孩子兴奋尖叫好一阵子。
岸边的尖叫,蝌蚪不以为意,真正危机四伏的,是水下。水下,到处都是捕食者。那些成功避开敌人的蝌蚪,像得了胜仗的士兵,在水里游得那叫一个神气活现。两个月后,蝌蚪长大,用后腿使劲撕裂皮肤的伤疤。生长的蛮劲,使人热泪盈眶。之后,前肢发育,尾巴融化并缩短,最终消失,化作加速游动的能量。是时候从水中上岸了,小青蛙们从水中一跃而起,蹿上岸边,在草丛石棱间窸窸窣窣,它们将用两年时间,以成蛙率不到百分之一的悲壮迈向成年。
夏天,于青蛙,是生与死相交的季节。青蛙瞄准蜻蜓、蚂蚱,而麻雀鹰、野猫等则朝青蛙迅猛扑了过去,甚至小小的甲虫,都在一前一后伺机对青蛙发动袭击。青蛙用弧度优美的跳跃抛物线,演绎着动物界的生死博杀。从来没有绝对强者,也不存在绝对弱者。
少年的我,也曾垂钓过青蛙。大白天,躲在水边草丛中的青蛙实在是太没有城府了,它怎么就能那么轻易总上一个熊孩子的当呢。看看,熊孩子只是让姑婆挖了几条蚯蚓,砍了一根翠竹,备了一根白棉线,姑婆只是将白棉线的一头缠在竹竿上,一头绑上了一条断蚯蚓,并嘱咐熊孩子握紧钓杆底部,把绑有蚯蚓的钓杆尖部伸向草丛,不停升落起降,仅此而已。青蛙怎么就能前仆后继乖乖就擒呢,真是太傻了。
我和弟弟们陆续长大,慢慢,家乡老屋就只剩姑婆一人守着了。日渐衰老的姑婆,日渐残破的老屋,日渐荒废的南山岭,是家乡的大写意。突然,就有一天,世上再也没有姑婆了。青蛙呢,它们都去哪儿啦?
万物分别,形迹杳杳,时光是回不去的。合上画本时,《蛙声十里出山泉》湿了一角,水墨泅散,望之感伤。
秋深如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