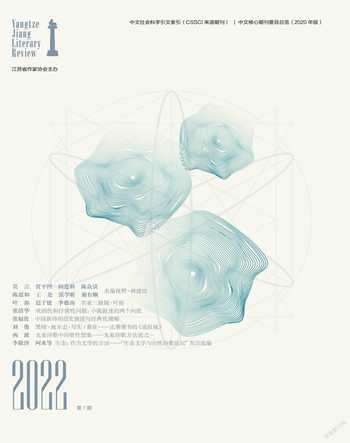戈麦诗歌中的智性想象
——戈麦诗歌方法论之一
2022-10-20西渡
西 渡
1997年的时候有人问我:“随着时光的流逝,你还坚持对戈麦的高度评价吗?”我当时回答说:“我现在对他的诗歌品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比过去更热爱他的诗歌。”时间又过去二十多年,下个月戈麦去世就满三十年了,现在我可以更坚定地重复一遍我二十多年前的回答:我比过去更热爱戈麦的诗歌。实际上,戈麦去世以后的三十年,诗人、批评家、读者一直在进行戈麦作品的辨认工作,我自己也是如此。今年编辑《戈麦全集》,让我对戈麦在诗歌上的贡献有了更新的认识。虽然三十年并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水落石出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戈麦绝对是新诗史上才华、成就最突出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
戈麦的写作生涯从1987年夏天尝试诗歌写作开始,终于1991年秋天。在短短四年的写作生涯里,他写下了诗歌300多首,小说3篇,散文3篇,文论十多篇。戈麦的写作呈现了一种令人目眩的加速的天才现象。他的诗歌写作几乎每半年就完成一次蜕变,四年中完成了其他诗人几十年的成熟过程。当然,这种加速成熟的现象也是19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当代诗歌迅速成熟的过程在一个天才诗人身上的体现,同时也密切关联于戈麦的母校——北京大学新时期以来辉煌的诗歌小传统。骆一禾、海子、西川、臧棣这些身边学长、友人的创作在不同时期起到过鼓励、激发、推动、催化其创作演变的作用。但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戈麦自身突出的创新能力。而在戈麦身上,这种创新的能力始终与一种自觉的方法的发明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刚开始写作的第一年,戈麦在几个主要的写作阶段都有方法上的重要创新,《厌世者》时期是“智性想象”,《铁与砂》时期是“词的繁育术”,最后阶段是“幻象工程学”。本文拟就戈麦早期诗歌的特征,特别是《厌世者》时期的智性想象展开分析,由此考察这一方法的创新对戈麦的“自我成立”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当代诗歌的启示。
一、戈麦早期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戈麦1989年以前的作品主要受朦胧诗影响,但已显出个人特色,尤其是一种混合着严肃、深思、自嘲和反讽的声音,在1980年代的当代诗歌中相当罕见。这个时期戈麦用过白宫、松夏两个笔名,也代表了他早期写作的两个阶段。白宫时期练笔、习作性质更显,但其想象已显出深曲、含蓄的特色,如“那美人鱼的传说/使你把夜晚想象成一堆渔火/凭栏相望/而烟对面的脸孔/给你的陌生/如河”(《歌手》)“梦把两片拥抱的影子/埋于绿影婆娑的长河/百年后的勘探者/挖出一幅湘西漆画”(《假日》)。前例中,夜晚与渔火之间的联想,因美人鱼的传说而建立,曲折有致,也显示其感受力的敏锐;后例中,梦、影子、湘西漆画之间的转换,显示了想象在虚实之间穿梭的功夫。出色的想象力也表现在以下诗句中:“叶子像无数肥硕的星星”“波涛的皮癣滋养了他的一生”“雨夜栖于树冠的影子/醒来纷纷死于树下”(《梦游》)“赶车的老人/赶着五十年冬天血红的饥饿”“五十多个直立的梦想/被寒冷封堵在一间雪屋里”“雪夜的天空如一件崭新的羊皮大衣”“北方是一条紧紧关闭的白色睡袋”(《隆重的时刻》)“想象是一只空背的野牛”(《已故诗人》)“数以万计的囚徒/如亿万棵颓老的病树”(《刑场》)。敏锐的观察力体现在对细节的准确刻画:“正午的杆影如黄豆”(《乐章第333号》)“母亲苍凉的白发/在红柿子地里飘扬”“路灯如一群灰黄的向日葵/低垂着脑袋”(《十七岁》)。在“护城河的浓荫不可上涨”(《经历》)这样的句子中,语言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准咒语使用,其暗藏的力量已经被一位初试身手的年轻诗人悄悄把握到。下列诗句则相当准确地捕捉到了情调、语调和节奏的关系:“童年/是一幅冰冷的中国画/寒风旖旎的江上/河流凝动了/载着孤零的乌帆//我们坐在船里/想着航行的事/雪狸们默默地立在河上/凿开一个又一个春天/免于幻想。”“寒风旖旎”“河流凝动”是诗人创造性运用语言意识的表现。
这些诗在主题上也显出与一般少作很不相同的特征。一种与少年意气不相称的迟暮沧桑之感可见于《青楼》 《流年》 《假日》等诗中。一种深深的失败感也时有流露:“我们刷洗一尽的铅华/星星点点/盛在这只失败的瓶子底下”(《杯子》)“多少个春天了/我还是不能相信失败/雨就这样打在路上/雪流成了河”(《遗址》)“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有这么多的星宿/这么多的失败者”(《流亡者的十七首》)“人,是靶子,是无数次失败”(《叫喊》)“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誓言》)。此一主题也为后来的诗所延续。在《通往神明的路》里,他说:“那些目光为存在所折断的行者……守住失败的灰土。”诗人不但自认为失败者,而且认同失败,把失败当作自我和人的属性,甚至认为失败是一种挽救的行为,文明的弱者才“匍匐在成功的旗下”,而胜利是耻辱(《新生》“我品尝过胜利的耻辱”)。这些看法可与海子的想法相映证。海子认为,诗的胜利以生活的失败为前提,在诗歌上胜利的民族将付出整个民族惨灭的代价。正是这种失败信仰把戈麦导向对生命底里、生存深渊的追问,继而向幻象-原型诗歌快速推进。衰老、死亡的主题在这些早年诗作中也有透露。“晚一个季节/也走向秋天/焕发从未有过的/令我敬慕的衰老”(《乐章第333号》)“等待我成年的人/在我成年之后/等待着我的衰老”(《哥哥》)。《七月》里写到“停尸场白花花的尸体灿烂着”,《金色》写到“我长眠的遗像”,《门》写到“尸体们悻悻走了出去”。《衷曲》 《悼师》 《刑场》 《已故诗人》都以死亡为主题。《衷曲》描绘了一种奇幻诡异而令人脊背发凉的死:“为最后的祝愿/在酒器中浸泡了你的青春/如无数个他人死去/你的愿望散发剧烈的香醇//趁今夜星光/我们拥入海底/海蛇尾随着我的背影/我的喜悦你细细地凝视。”酒器中浸泡青春的尸体,在死亡中散发剧烈的香醇,尸体相拥而入海底,彼此相视而嬉,背后海蛇尾随。这是波德莱尔式的“恶之花”,而比波德莱尔更诡魅。1988年《在春天的怀抱里去世的人》,题材上与海子《春天的自杀者之歌》类似,但海子把自杀写得美丽无比,戈麦却沉迷于对腐尸可怕情状的细致描绘。一个青春的诗人却沉醉于这类死亡的想象,确实令人骇然。实际上,厌世的情绪、死亡的书写一直贯穿于戈麦的写作。1988年的《我的告别》已流露自戕倾向:“谁走路谁就得再活一生……我愿从此杳无音讯。”在1989年的《打麦场》中,他高喊:“生命太长。”1990年的《远景》描绘了海上、草原、雪山三个远景,但戈麦在其中看到的都是毁灭:海上折断的帆布和桅杆,草原上死去的鸟儿垂直落入戈壁,雪山上死者留下的滑雪板在阳光下静静呼吸。生活对于他,似乎只是“死神来临以前的前提”,甚至“诗也是一种死亡”(《海子》)。在诗与死亡之间画上等号,可能与他重视行动的信念有关。他说:“我不是一个嗜好语言的人”(《岁末十四行(二)》)“没有人会崇拜椅子/在房子里静坐一生”(《逃亡者的十七首》)“写作对我们并不适合”(《写作》)。这应该是他1987年之前抗拒诗歌的原因。到最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是“误入文字生涯”(《想法》),认为“我的一生被诗歌蒙蔽”(《当我老了》)。可见,戈麦对文字生涯始终有一种不甘心。1989年以后,他写下了一系列死亡主题的名作,集中而猛烈地表现了其想象力中阴暗的一面:《游泳》 《家》 《死亡诗章》 《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 《金缕玉衣》 《深渊》。在绝命之作《关于死亡的札记》中,他说“死亡就是陪伴我们行走/以及睡在我们床上的那个影子”。他接着写“死亡在最终的形象上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只曲颈瓶上的开口,它的深度无限”。戈麦一直试图探测死亡的深度,而经验无法企及这一深度,梦看起来是一个入口,但携回的信息仍不能满足诗人探测的渴望,这促使他直接采取自杀的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弥合我们与死亡的间隔,进入死亡这只曲颈瓶的内部,进入它的无限深度。
到松夏时期,戈麦写出了《七点钟的火焰》 《克莱的叙述——给塞林格》 《太阳雨》 《秋天的呼唤》 《坏天气》《徊想》等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作品。《秋天的呼唤》连续使用通感将“呼喊”不断强化,写出了诗人对生活、对绝对之物的强烈渴望,是戈麦的第一首杰作。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些诗中独特的语调,它们不仅是个性化的,而且是创造性的。与这种语调配合的一种意味丰富的冷幽默,成为这个阶段戈麦风格上最显著的标志:“这不曾预期的降临/像一瓶药酒让我怀疑/歌子太长静得有声/以至于消失”(《七点钟的火焰》)“纽约的黄昏是一位老人/那里佛塔小得像一只甲虫/瑜伽少女喷吐花白的头发//她,吹来过春天/这寒冷的灰尘/维也纳也有人吃过”(《克莱的叙述》)“没有雨的节日/他人去园林植树/我怀念雨季//西方的诗人说话/食物打湿而腐烂/我从不相信”(《太阳雨》)“我走入往日的壁橱/搜寻随嫁衣裳/玻璃的缝隙草一样生长/牙齿落地生辉//道路如同目光/我被熟知/历史青春期的扉页/一页煎炒过后的鱼/书写死亡”“几只长脖子野鹤/在沼泽地里高声叫卖/惊走狼的孤独//猎人们忘记举枪/皮货占有了市场”(《星期日》)。这类诗句颇多自嘲,表面少见激愤,也可以说,它用一种冷静的疏离感化解了少年的激愤,转化为一种自我解嘲的、怀疑的笑。但如果你懂得这笑的内涵,你也许会明白激愤正是它的底里。
这个阶段的诗作还表现出一种对罪的敏感和探测:“唇被封堵/品尝是一种罪过”(《星期日》)“谁若去衔接心灵和心灵的秘密/谁就会成为自己的罪人”(《设身处地》)“我的心盛满了罪恶/像毛玻璃里的酒/模糊成罪恶的一滩”(《杯子》)。第一例表现了对欲望的压抑和回避;第二例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的失望;第三例是对自我的失望乃至嫌恶(自我不洁感),这种情绪直接引向《厌世者》时期的《脊背上的污点》。1989年9月,戈麦写了一首题为《罪》的诗。此诗一共三节,三节结束的诗句分别是:“砸碎的鸡骨没有罪”“呆立的柱子没有罪”“空白的废纸没有罪”。三个“没有罪”,与标题的“罪”构成对抗。此诗的主题是罪与罚的不对等:鸡骨无罪被砸碎;柱子无罪遭火焚;孩子无罪而不免忍饥。在人间的法庭上,无罪被罚,小罪大罚,大罪逍遥,是常态。无罪而罚,使人绝望于人间公义,而天上的法庭也不可靠:“一切罪恶横陈于天堂”(《骑马在乡村的道上》)。这种对罪的敏感和思虑,使戈麦的诗一开始就拥有一种伦理的关怀和深度,但也在对心灵的不断拷问中陷入自我折磨。他说:“仿佛长久的怀疑 我的眼睛/染上了一层鳞质的病痛”(《逃亡者的十七首》);他说:“在风中 我回想着/并且歌颂/我的邪恶/我的苍白”(《风》),并将自己的一个自选集命名为“我的邪恶,我的苍白”;他自称为“不愿生活的人”(《深夜》)。戈麦的弃世多少与这种过分严厉的对自我、对身体的自疑、自责、自罪倾向有关。
这些诗作的缺点是声音、意义、形象的配合尚未臻于完美,它们的整体性仅依赖上述个性化语调的凝聚。因而戈麦这一时期(也包括短暂的“白宫”时期)的作品多难于索解,甚至不可解。这种不可解也是诗人对自我、世界的认知尚处于混沌之中的一个标志。1989年10月,他在《自学》杂志发表散文《北方冬夜》,首次采用“戈麦”做笔名,写作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打麦场》 《渡口》 《夜晚,栅栏》 《白天》 《疯狂》 《我知道,我会……》《开始或结局》 《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 《游泳》 《家》《二十二》 《誓言》 《岁末十四行》 (一、二、三) 《死亡诗章》等一批诗作为标志,戈麦进入了第一个“完成”的阶段。这一“完成”,从诗的内部看,就是声音、意义、形象的一致,一首诗是三者统一的一个整体。这个阶段,他的诗一下子好懂了。当然,好懂并不意味着这些诗可以被概念的语言清楚地解释,而是说它们具有一个可以被清楚感知的稳定的内核——它在形象、声音、意义之内,就像灵魂在身体之内,果核在果肉之内。从功夫在诗外的角度看,它是诗人的美学和他的认识论、人格、生活的统一。在此之前,诗人身上的这几个部分经历了各自发展的阶段,彼此并不完全和谐,有时候甚至是冲突的。在这个阶段,戈麦在个人生命体验基础上完成了对世界、对自我的个体认知,并影响及作用于其诗歌美学、生活实践。这个统一的过程,既显示了时代的特殊症候,也与个人症候密切相关。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戈麦的前《厌世者》时期。
二、智性想象:《厌世者》时期戈麦诗歌方法论的发明
始于1990年4月、止于6月中旬的《厌世者》时期,是戈麦在精神和诗艺上实现飞跃并开始独立飞翔的阶段。这个时期从时间上说,为期不足三个月,但在这段时间内,戈麦写了48首短诗(47首刊于《厌世者》,《新一代》收入《铁与砂》)、28首2-4行的超短诗(全部刊于《厌世者》),数量占到戈麦存世作品近四分之一,质量也迥出前期,几乎篇篇都是精粹之作。这是戈麦的诗歌天才开始进入燃烧的时期,堪比郭沫若的《女神》时期、海子1987年前后的《太阳》时期。事实上,戈麦对当代诗歌的若干重要贡献都始于这个阶段。在《厌世者》第三期的《短诗一束》中有一首题为《诗歌》的三行短诗:“朋友们渐渐离我远去/我逃避抒情/终将会被时代抛弃。”“逃避抒情”正是戈麦诗歌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抒情是1980年代诗歌的显著特征之一,尤其是北大诗歌传统中的主流,也是海子、骆一禾的重要诗歌遗产。戈麦这时候说“我逃避抒情”,意味着要跟这个传统告别,前一行说“朋友们渐渐离我远去”是和朋友分手,后一行说“终将会被时代抛弃”是和时代分道扬镳。
戈麦所说的“逃避抒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逃避抒情”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告别主观主义。逃避主观、反对沉迷自我和自我暴露是戈麦个人品性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方面,它体现在诗歌品质上就是对抒情、对自我表现的警惕。对于戈麦来说,“逃避个性”恰是其天性的体现,而无待于艾略特的教诲。戈麦说“我逃避抒情”,其实他逃避的是那种私人的情绪和情感,尤其是对这种情绪和情感的自我迷恋、自我膜拜,但他并不回避表现人类情感的状态,或者这种普遍的情感状态正是他追求的目标。第二层是对日常、已知和常识的超越,而抒情恰恰停留于日常和已知的范畴,因而难以让戈麦这样对诗有更高期待的诗人满足。他在自述中说:“他反对抒情诗歌的创作,他认为那东西可以用歌曲和日记代替。”《厌世者》第2期刊出了一首标题也叫“厌世者”的诗,在这首诗中戈麦把“发现奇迹”当作诗的根本目标。在更早的一首诗里,他说:“贫困的日子里/石头也向往奇迹。”(《总统轶事》)而抒情作为一种自我表现的手段,显然无法满足“发现奇迹”的需要。1989年11月24日,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这些期待奇迹的人包括海子,也包括戈麦自己。“现实的漫长”,现实因为庸常和已知而显得漫长。超越的办法就是去探索、发现、揭示未知,展示人所未见、未闻、未知。
戈麦参与创办的《发现》创刊号的发刊词说:“发现。对,就是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它总结了我们劳作的本质。”这个发刊词出自臧棣的手笔,但也是包括戈麦在内的北大诗歌同仁共同的诗歌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戈麦导向了一种可能的诗歌。臧棣说戈麦“始终运用一种可能性意味浓郁的汉语来写作”,“炫人眼目地纠缠语言的可能性”。可能的诗歌,从根本上讲,就是致力于语言可能的探索:“发现是人类和语言唯一的汇合点。作为一个持续的精神动作,发现最终统一了人类和语言的分歧:使人成为语言的一部分,也使语言有可能传达人类的呼声。”这一探索对戈麦来说首先是从朦胧诗优美、崇高乃至凝练的意象化语言中解放出来,从它已经模式化的象征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个目标与第三代诗人有相当的一致性,但戈麦断然拒绝了第三代诗歌对日常语言的迷信。戈麦这个时期所使用的词语冷静、准确、克制、渲染、铺陈、密集以至堆积,而最大限度地剔除了多余的情感和现成的意义,与古典象征主义、朦胧诗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就像印象派与古典绘画在设色,罗丹与米开朗琪罗在手法上的距离一样昭然。对这样的描述,读者或许会产生疑问,冷静、克制、准确可以与渲染、铺陈、堆积并存吗?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冷静”“克制”,是就戈麦的语言与情感的关系而言,戈麦这个时期的语言决然剔除了那种自我表演化、戏剧化的情感,显示了其冷静、克制、内敛的品质;“准确”则是就感觉的传达而言,而不是外部世界客观呈现的程度,不厌其烦地铺陈、堆积是为了同样的目标——富有强度的感觉的传达。也就是说,这个“准确”是印象派意义上的,而不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印象派正是善于通过色彩的堆积来传达准确的主观印象。这个时期的戈麦,或可以称为“语言的印象主义者”。戈麦说“我逃避抒情”,也应该在上述意义上理解。实际上,戈麦的抒情性、其激情的强度并不亚于任何以抒情著称的当代诗人,譬如海子、骆一禾。诗人晓归(吴浩)把戈麦的这种抒情性称之为“浓质抒情”,而陈均认为戈麦是骆一禾和海子合而为一。但戈麦这种“浓质”的激情在表现上是克制而内敛的。他极少使用感叹号(现存全部诗作中仅用到10次感叹号),极力抵制伤感和自我怜悯。就像我们在《梵·高自画像》这样的诗中看到的,汪洋恣肆的激情被动作化、细节化,流动的被转为凝固的。而在后期的《北风》 《浮云》 《天象》等诗中,情感的运动被转化为意象的运动。较此更重要的是,戈麦在他的抒情中有意识地置换了当代诗歌抒情的内核,清洗了当代诗歌的抒情主题——爱情、友谊、幸福、日常生活、文化与反文化、崇高与反崇高,而代之以个人化的存在主题:青春、时间、死亡、孤寂、绝望、罪与拯救、语言与存在……
戈麦在语言上的抱负之一是尽可能地激发一种新的、丰盈的现代感性,为此他把一种惹人注目的分析性带进了当代诗歌。这是戈麦向语言的可能性掘进的技术途径。这种分析性曾经在高峰期的艾青、穆旦身上短暂地现身,随后告于沉寂。戈麦重新激发了它,而且在强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此,臧棣曾对戈麦的《梵·高自画像》 《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做过精细的分析。同类的典型之作还有《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 《孩子身后的阴影》 《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 《雨幕后的声响》 《黄昏时刻的播种者》 《查理二世》 《我们背上的污点》等。艾青的分析性结合于视觉形象,穆旦的分析性结合于经验,两人各自完成了其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或文化批判性的诗歌,戈麦的分析性则结合于想象,其诗歌理想是一种自律的、体验型的诗歌。戈麦的诗当然也有其批判性,甚至更加尖锐而急迫,但其矛头所指,并不是具体的社会事实、文化事实,也不是历史处境中的人类经验,而是生命的、精神的、灵魂的、存在的事实,并在准宗教意义的拯救主题中得到升华。由此,戈麦也刷新了新诗想象力的品质。
分析性和想象力的胶合,是戈麦激发语言可能性的方法论,也可以说是戈麦的语言战略。这种特殊的方法论,臧棣称之为“想象的理性”(见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就想象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称为“智性想象”或“分析性想象”。其典范之作如《如果种子不死》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眺望时间消逝》 《妄想时光倒流》等。在这些诗作中,无羁的、自由的想象为严格的理性所操控,其运作井然有序、层次分明、一丝不苟,具有严格的秩序和结构感。理性与感性、神秘与逻辑、分析与想象、理智与激情在这些诗中扭结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说激情是这些文本的外部驱力,想象是它们的内部驱力,而一种基于语言良知的敏锐的现实感则是其动力总枢纽。这种悖论式的结合,其效果令人耳目一新。想象在早期的新诗中是一种罕见的品质,稍后郭沫若贡献了一种情感的想象,李金发、卞之琳发挥了一种感觉的想象,新诗才有了诗意的发现。以后,艾青把视觉艺术的观察力引入新诗的想象;穆旦的想象结合智力和分析,但其分析性和想象有时发生内讧;冯至在新诗中引入了某种智性,但其想象和感性都嫌单薄。所以,这种智性的想象几乎是戈麦的独门利器。另外,艾青观察性的想象,在戈麦的《梵·高自画像》 《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 《孩子身后的阴影》 《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 《雨幕后的声响》《黄昏时刻的播种者》 《南极的马》 《查理二世》等作中也有出色的表现。这与戈麦早年的绘画训练不无关系。
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正是戈麦独立飞翔的起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戈麦作为一个个性鲜明、风格独特、富于创造力的诗人形象得到了确立,他不再是朦胧诗的摹仿者,也不再是其北大学长们谨慎的追随者。戈麦这个阶段写作的加速也与这一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它为诗人写作的推进提供了额外的动力。这一方法在随后的《铁与砂》时期及最后阶段的写作中还有更让人振奋的发挥,以至让诗和工程学发生联系。从戈麦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智性想象不但是戈麦独创性的诗歌方法论,也是其独特的诗歌品质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智性想象的诗学启示
这样一种智性的想象,其美学的、诗学的意义何在?对此,臧棣曾指出,戈麦这种方法的提出源于“他对汉语所迫切需要的某些元素的敏感”“只有对汉语的良知、汉语的道德、汉语的洞察力、汉语的表现力怀有卓异的抱负的人,才会像他那样写作”。也就是说,戈麦是要借此刷新新诗乃至汉语的品质,赋予它所匮乏的良知、道德、洞察力和表现力。因此,这一方法的意义不止是美学的、诗学的,它同时也是伦理学的。对伦理的关心,在戈麦的诗歌中是隐含的,它并非戈麦写作关注的焦点,也非他工作的首要目标,但戈麦天性中对伦理的异常敏感——这种敏感给熟悉戈麦的亲友无不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往往成为他们回忆的中心——时时在一种加速的写作中被携入或卷入到原本以美学自律为目标的文本中,由此产生了戈麦诗歌与时代的悖论关系。
臧棣在《犀利的汉语之光》中曾说:“从戈麦和海子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理想的因素进入了汉语的躯体;其中最惹眼的是汉语诗歌首次集中显露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欲望”“戈麦和海子这两位诗人短暂一生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是避免诗歌和所谓的‘时代的悲剧’产生密切的联系”。就两位诗人的诗歌主题和题材而言,臧棣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海子尤其是戈麦的诗歌都最大限度地专注于普遍的主题,在诗歌的题材和素材上也对所谓时代的经验漠然置之。但是,当时过境迁,我们回头来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转型期诗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戈麦的诗恰恰成了这个转型时代最出色的文学表现,也最恰切地表现了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生命状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富于张力的时刻。这一时代的张力既体现在《献给黄昏的星》 《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所呈现的客体性意象体系中,也体现在《梵·高自画像》 《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自画像》 《空望人间》 《我们背上的污点》这类诗作所呈现的心理性意象体系中,还体现在《北风》 《浮云》 《沧海》 《大风》 《佛光》《眺望时光消逝》等诗作所呈现的幻象世界中。在最后的那些诗作中,借胡戈·弗里德里希评价波德莱尔的话说,戈麦“‘灼热的精神性’燃烧得最为激烈,这种精神性要挣脱一切现实”。它实现了这样一种最高意义上的自由:“我们钢铁一样的思想/在笼子一样的禁锢里/扶摇直上九霄。”(《通往神明的路》)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一心挣脱现实的精神在与现实的对抗中,却与现实彼此深深嵌入,最终让诗人成了现实的肉身。在戈麦最无羁、最自由的想象和最高的虚构中,正有着这个时代最高的现实。是戈麦,而不是别的诗人、作家,成了这个时代的肉身。这个事实确实令人惊异。在我与张桃洲、姜涛、冷霜的对谈中,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戈麦的诗不是纯诗,它和世界、和现实有非常深刻的纠缠。戈麦的诗有批判性,有见证性,但你很难说它是见证的诗。因为它在见证和批判的同时,却仍然保持了一种奇怪的而充分的自足。或者说,它不是从外部见证时代和现实,而是让时代和现实在诗的内部发生,而诗人自己则成了时代的肉身,成为时代的痛苦本身。”
戈麦诗歌与时代关系的这一悖论,颠覆了批评界一直以来甚嚣尘上的一种偏见:诗人应该去拥抱时代,努力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显然,时代的意志并不像某些自作多情的批评家设想的那么单纯,相反,拥抱时代的念头多数时候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更可悲的是,你拼命讨好、追求的女神很可能并非时代本尊,而不过是她用来检验追求者智商、情商和品质的无数幻影中的一个。时代选择它的诗人,正如明智的恋人选择她的追求者,并非以他们脸上表演的热情,或者舌头上吐露的巧语花言,而是以其内在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戈麦正是被时代选中的诗人。这一选中的意义,在时过三十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得较为清楚,但若要看得更加清楚,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一事实给予诗人和批评家的教训是,一个诗人首先需要忠于他自己,其次是他的缪斯。无论如何,忠于自己的艺术个性、艺术良知,保全自己的人格、尊严,比追求时代的青睐更重要。
帕斯曾经说:“现实是最遥远的,它是一个需要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抵达的东西。”有不同的现实,也有不同的现实感。利益的现实用鼻子就可以闻到,但精神的现实却需要最敏锐而深沉的心灵才能发现。后者依赖于一种穿透性的心灵领悟能力,它不仅能够看到现在的现在性,也能看到现在的过去性,最重要的,它能看到现在的未来性。归根结底,真正的现实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感。当然,对未来的预感也需要基于过去和现在,尤其需要一种超越势利的敏锐良知。也就是说,它首先需要克服利益的鼻子无所不在的干扰。在这点上,戈麦充分显示了其心灵、人格、修养和诗才的优势。时至今日,戈麦的诗业已向读者充分证明了它的预见性和未来性。三十年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们锐意探索的那些主题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心灵难题。而那些自以为可以驱遣现实的批评家,时间证明,其所谓现实不过是用鼻子闻到的利益的气息,与真正的现实有“最遥远的距离”,其执迷的主题在今天也日益显出空洞、陈腐的面目。
这是两种不同的现实感,它们朝向不同的现实,也朝向不同的时间。寄身于利益的现实感朝向短暂的现在时间,它最害怕过气,却随时过气,所以它总是倾向于即时兑换;投身于精神的时间,朝向未来,同时朝向永恒的时间,在自身之内培育着永恒。这个永恒,即使已经被现代性侵蚀了其神学的内核,也仍然保留了准宗教的性质,它是始于人类学而终于宇宙学的时间。戈麦的时代感、现实感,按照臧棣的说法,它并非来自他与时代接触的经验,而是来自他对时代语言和写作的体悟:“虽然他感到艺术上的孤独,但他仍然有着十分强烈而又独特的时代感。他多少认识到,我们时代语言的堕落在本质上表现为语言的贫乏,甚至连精神生活异常丰富的人都难以完全摆脱语言的贫乏的侵害。在他最受非议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意识到我们时代的语言的弱点并竭力创造新的语言元素来加以矫正的诗人”“他既对我们时代的诗歌所缺少的品质敏感,又对我们时代的汉语所匮乏的元素敏感;更主要的,他还对我们时代的写作本身非常敏感”。这种从写作本身,尤其是写作的材料——语言——中升华的时代感正是一种朝向人类学时间和永恒的时代感,它倾心并投身于未来和宇宙学的时间,而让戈麦的诗艺具有昭然的永恒性。
【注释】
①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04页。
②与死亡主题相邻,戈麦在当代诗歌中发明了一个关于“少”的主题。在《九月诗章》(1989)中,他说:“少一些,再少一些”“我不是祖辈/是多年的梦里减掉的光”。《金缕玉衣》(1990)中说:“不会在地狱的王位上怀抱上千的儿女”。这些诗表现了一种中断生命、让生命之流不再延续的决心。
③戈麦:《戈麦自述》,《彗星——戈麦诗集》,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④⑥《主持人如是说》,《发现》第1期(1990年12月)。
⑤⑧⑨⑪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发现》第3期(1992年12月),第20页,25页,21页,20页、25页。
⑦西渡等:《“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戈麦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诗探索》2013年第7辑。
⑩[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