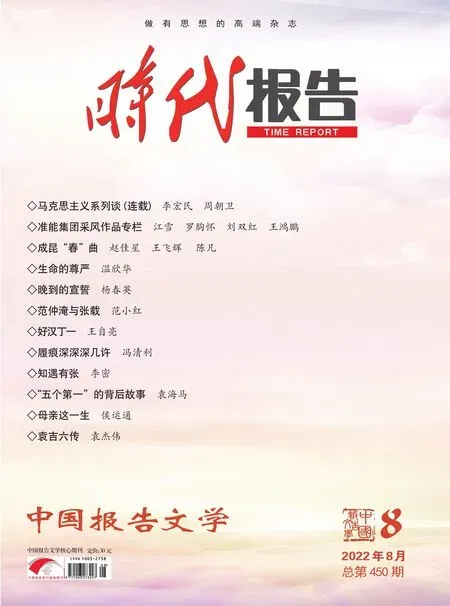拉祜山寨的春天
2022-10-20杨杨
■ 杨杨
我最先是从云南艺术学院老教授陈饶光先生那里听到了拉祜族苦聪人的故事。陈教授曾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陪同上海的一位大画家去金平访问和写生。现在,陈教授听说我要到金平采访,就叮嘱我一定要去拉祜族苦聪人居住的地方看看。在那里抚今追昔,定然会有许多感慨和收获。
陈教授说,当年,他们是从个旧市到金平的。国家刚刚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公路。不过,那样的公路太简易了,是从羊肠小道拓展起来的,弯弯曲曲,穿过高山密林,如同探险一般。他们坐在汽车上,只见白如牛奶的浓雾在填满了山谷之后,又一阵一阵向山腰曼延。他们的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如同穿云破雾,让人惊恐万状。他们整整“熬”了一天,终于到了金平县城。那根本就不像一座县城,只有唯一的一条街道,从街头走到街尾,夸张一点地说,几乎只需要燃一根火柴的时间就走完了。街上只有一幢较好的“四合院”,那就是县人民政府。
那时,陈教授和大画家全靠步行和骑马,来到了金水河和勐拉乡。在那里又经过几天的折腾,才在乡政府一位民族工作队员的带领下,走进了原始密林。当时,那些苦聪人就隐藏在这样的密林深处,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他们每年砍倒一片森林,然后放火燃烧,茂盛的草木因此被烧成了一层灰烬,覆盖在山坡上。他们就用加工过的木杈,在地上戳一个洞,放一两粒玉米在里面,然后等着它们发芽、开花、成熟。这样种出来的玉米,山林里的鸟兽至少要来分享一大半,剩下来的只够拉祜人吃两三个月。其余的时间,就要靠采集野果和打猎为生。他们采集来的野果有的是有毒的,因而常常有人误食而死。打猎不一定每天都有收获,有时也会空手而归,所以很多人常常挨饿。
苦聪人不会种棉花,不会种麻,不会纺织,不会打铁,又不敢走出大森林。他们只好把仅有的一些猎物,拿到路边放下,然后躲藏在树林里。等到汉族、哈尼人或傣族人路过时交换一些东西。过路的人开始时听不懂他们的话,也不明白他们的意图,待慢慢懂得了这是苦聪人试图与外界人以物易物的方式后,就脱下身上的旧衣裳,或者把盐巴、砍刀放在路边,然后带走路边的那些猎物,大多是飞狐、松鼠、野鸡或动物的干巴,也有一些野兽的皮毛。
大多数苦聪人是不穿衣服的,他们用树皮或芭蕉叶做成的衣服,其实根本不能抵御寒冷,仅仅是用来“遮羞”而已。苦聪人都是以“家”为单位,各守一方,难以形成固定的寨子。在这样的家中,既没有床,也没有被子,长辈、父母与子女们都是围在火塘边睡觉。有的人一辈子没走出过森林,从不知米饭和油盐的味道。
苦聪人的妇女生下孩子之后,因为没有衣服和棉布,往往用芭蕉叶把孩子包裹起来,用树皮当布袋,背着孩子就到森林里挖野菜,采野果。有很多孩子就在母亲的背上,被冻死或饿死。
正如一首云南古谣所唱的那样:
树叶做衣裳,
兽肉野草当食粮,
芭蕉叶是苦聪人的屋顶,
麂子的脚印是苦聪人的大路……
遥想千百年前,苦聪人的祖先作为古时氐羌的一支,从大西北迁徙到哀牢山区,遁迹山林,害怕与外界接触,成了一支神秘的“野人”。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形态之后,直到1953年,他们苦难的生活状况才被党中央发现。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干部与解放军一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金平县哀牢山中的原始密林里,从茫茫林海中把苦聪人找出来,在原始森林的边缘,教他们建房子,开梯田,养牛喂马,种稻谷,还送给他们稻种、大米、盐巴、药品、衣服和农具。当他们把家搬到半山腰后,却发现这里没有了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森林,没有了山涧和小溪,没有以前的自由自在,面对着一切全新的事物和生活,苦聪人极不习惯,在他们把稻种全吃了,把耕牛放成了野牛之后,又返回了原始森林里。
后来,党和政府成立了“寻找苦聪人工作领导小组”,再次派人前往原始森林去寻找他们。一次又一次寻找,一次又一次劝说,总是坚持着,不放弃,最终苦聪人被工作队的诚意所感动,鼓起勇气,搬出了山林。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找寻一个被旧时代遗忘了的少数民族兄弟,先后花了5年时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最终让这支苦聪人一步跨进了社会主义社会。
那一天,陈教授其实是为我讲述了一部最生动的社会发展简史,让我完全相信了这个如同传说一样的苦聪人的跨越故事。事实上,拉祜族的这个支系,在被发现之前的确处于原始社会形态,长期与世隔绝,无论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保留着诸多原始生活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原始的一个族群。
今天,我几乎是追寻着陈教授60多年前的足迹,来到了金平县城。一眼望去,它已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更是一座边陲幻城,各种崭新的建筑和事物出现了,有最现代的学校、医院、商店、街道和公园,有最纯洁的云雾,有最绿的树木,有最清的山泉,有最吸引我的那些头上顶着“红帆船”的瑶族同胞,有穿着蓝色短褂的哈尼人,还有一身白色素装的傣族姑娘,他们在层层叠叠、高高低低的街巷里,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简直就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民族万花筒。因此,我立时就被这座县城的魅力、故事、个性、表情所打动,恍然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似乎身体在真实中行走,而心灵已在梦幻中浮想。
我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我要继续向南去寻访苦聪人的现实世界。我先后到了金水河镇、者米乡,深入到了南科村、地棚村等地,一路都是故事,一路都是感动,一路都是无限春光。在者米乡顶青村委会地棚村,69岁的庙正昌拿出他珍藏着的父亲的一组照片,那是1950年10月他的父亲刚刚从“野人”变身国家“主人”之后,曾作为拉祜族的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之后又去北京、东北等地参观学习时所拍的纪念照。庙正昌说:“父亲当年从首都北京回来以后,兴奋了很长时间。他召集族人开会,激动地说,我们也要社会主义!”
然而,走出大森林的苦聪人,事实上并没能走出贫困。幸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激活了全中国人民,为此后国家脱贫攻坚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在哀牢山深处打响,苦聪人因而又迎来了命运的第二次历史性改变。
李云是苦聪人“猫公”(神职人员)的后代,是从大山里走出的拉祜族大学生,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巨变。他认为,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前的几十年里,苦聪人贫困落后的面貌依旧没有多大改变,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没有自己的产业,生活依然过着原来的生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吃不饱饭,一个近百户人家的村落没有一幢钢筋水泥房,人均收入不足800元。
李云所说的这个村子,应该就是南科村。这个边陲山村是金水河镇的一个行政村,地处中越边境。海拔940米,距金平县城百余公里。追溯南科村的历史,可发现这个拉祜族村寨村至少已搬了3次家。每一次都很传奇,发生了很多难以想象的故事。这一切深深吸引着我。
据李云回忆,在1956年夏天,解放军工作队在他们称之为“草果坪”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以他的曾祖父为代表的苦聪人。他的曾祖父的名字叫李大,是解放军工作队给取的。拉祜族的姓氏是以动物、植物或地名等来命名的,比如李云的姓氏是“泛蓝拓”,在拉祜语中的意思是“松鼠”,说明李云的祖先最擅长打松鼠。拉祜族中的“王”姓也一样,用的是“犀鸟”作为姓氏,所以“王”姓的祖先最擅长打犀鸟。
李云的曾祖父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一个人就能拉开三四个小伙子都无法拉开的弓弩,一个人就可以把高大的树藤弄歪拉到地上。1957年前后,曾祖父配合政府的工作,带着近2000名拉祜族人走出大山,到河谷落户定居。
河谷瘴气肆虐,让很多老人小孩生了怪病,白天黑夜都在发抖,直至病死。奇怪的是,他们回到大山后,发抖的怪病就莫名消失了,大人小孩慢慢恢复了健康。
苦聪人重新跑回了大山,这事急坏了当时的民族工作队长,他把这件事上报到金平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寻找苦聪人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前往原始森林去寻找苦聪人。工作队三番五次地找到李云的曾祖父,动员他带领族人搬迁到原来的地方。在工作队的软磨之下,曾祖父同意了,但他要求重新选一个村址。工作队同意了,在旧房那里,建盖了新的瓦房,让苦聪人定居下来。
后来,苦聪人又第二、第三次返回大山。同时,政府的民族工作队又三番五次地到大深山里把他们找回来,千方百计让他们过上新生活。李云说,由于苦聪人长时间处于原始社会形态,他们的财富积累几乎为零,很难适应现代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只有南科村的苦聪人,似乎从大山里搬到这里之后,就慢慢爱上了这里,慢慢适应了河边生活。几十年来,虽然生活依然贫困,但再也没有返回森林里。当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后,这里也成了一个小小的战场。当地政府为了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安居乐业,很快在美丽的南科河畔为他们建盖了一幢幢漂亮的安居房。
可是,这么一个在脱贫攻坚战中变得越来越美的拉祜族村寨,却在2019年6月24日遭遇了一次意外的劫难。那一天,在南科村一带,突降特大暴雨。仅仅两个小时,降雨量高达170余毫米。一天下来,竟然达到了300余毫米。时任金水河镇党委书记向萍告诉我,那天凌晨两点多钟,她已进入梦乡,突然手机响起,一看是南科村委会一位村民小组长打来的,报告那里的险情。这位村民小组长名叫黄秀珍,她在电话里声音很急促,如同马上就要发生天崩地裂的大事一样。她说,雨太大了,太大了,从南科河传来的巨大洪水声,已把村民们全震醒了。但大家都躲在家里,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是好。
黄秀珍打完电话后,来不及穿外衣,摸黑来到河边,打开手机手电筒一看,天啊!洪水滚滚而来,已冲垮了河上的吊桥。她只感到大地正在震动,洪水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垮两岸,冲进村子。可以说,村子已岌岌可危,随时有被淹没的可能。向萍惊出一身冷汗,从床上蹦起来,已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当即指示黄秀珍,让村民尽快转移,什么东西也别带。
黄秀珍急忙转身往广播室跑去。可没想到,她刚拿起广播的话筒,准备通知村民尽快避险时,一道闪电划过黑夜,紧接着灯黑了,电停了。她只好冲进雨中,跑步去敲开一家又一家的大门,大声疾呼:“快醒醒,快醒醒,山洪暴发了,大家赶快转移到山上,千万别忙着带东西!”
短短10多分钟,整个村民小组135户人家,共547人,再加上南科小学的289名师生,都在黄秀珍的呼叫声中,相互照应着,急速从村中撤离。她当时只穿着睡衣,拼命在雨中来回奔跑,完全变成了一个狼狈不堪的“水鬼”。在轰隆隆的巨响中,她家的整幢房子已滑入大河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小时之后,向萍带着抢险队和急救物资赶到南科村时,看到的是河水改道,山川变形,一个美丽的拉祜族村寨已基本消失。向萍说:“如果当时没有黄秀珍的呼叫,那么这个小村子的人将遭受灭顶之灾,第二天的河谷里将出现什么惨状不可想象。”
村子被冲走之后,100多户人家失去了家园。金平县举全县之力,上下同心,攻坚克难,在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的同时,把恢复重建工作摆在首要的位置。
重建家园的工程于2020年2月份正式开工建设,半年之后,一个美丽的拉祜族新村重现在南科河畔。一座座美丽的家园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一条条崭新的道路连接着家家户户,一盏盏亮丽的灯光辉映着整个村庄。一个直过民族村,在党委政府及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正从灾难中走出来,直奔幸福的新生活。
告别南科村之后,我来到了金平县地棚村,开始探访其他拉祜族村寨。只见地棚村坐落在树林茂密的山坡上,村中有小广场和篮球场。居住在这里的56户拉祜族人家,都是从其他村寨搬到这里的,住的是国家盖的安居房,家家户户有电视机、电冰箱等电器,有的还买了小轿车。村民李发财是从苦聪大寨搬来的。近几年,李发财真是发了财,夫妻俩不但种了几十亩橡胶,还一起外出务工。政府又投入了近7万元,帮助他家建起了安居房。李发财又在安居房的基础上,加盖了第二层。夫妻二人美滋滋地入住了小洋楼,用的是智能手机,骑的是摩托车。李发财虽已49岁,但还特意把头发染成淡棕色,为的是追求一次时髦。
拉祜族苦聪人目前有3万多人,主要居住在金平县、绿春县与镇沅县之间的广大哀牢山区。早在1985年,这个族群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划归到拉祜族之中,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中最特殊的一员。除这些地区之外,在西双版纳、普洱澜沧、临沧和玉溪新平等地,还有拉祜族的许多支系族群。在脱贫攻坚战役中,政府为他们新建了安居房,并配发家具、家电,还把自来水引进各家各户。
面对这些从原始部落走出来的拉祜族群众,驻村工作队以思想之变促其行为之变,以观念之变推动发展之变。从改变他们原先的生活习惯开始,耐心教他们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洗澡,怎么做饭、炒菜,怎么洗衣,怎么叠被……一切从头开始,让每一个拉祜族群众像成长中的儿童一样,学会新的生活。驻村工作队还及时引进龙头企业,帮助拉祜族群众发展黑木耳种植。目前,全村已种植10余亩黑木耳,发展“雪芽100号”生态茶165亩,还发展了板蓝根等中药材种植产业。去年,黑木耳被上海老板收购一空,每户增加收入约1000元。村民王夫沙对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心怀感激,他说:“感谢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厚爱,帮我们把房子盖好了,让我们有了好的生活条件。”现在,王夫沙除了种植橡胶、草果、胡椒,开小卖部之外,空闲时,还到山里采割野蜂蜜,并在扶贫挂钩联系人的指导帮助下,学会开网店,把野生蜂蜜卖到了全国各地。
2020年初,云南省正式宣告拉祜族等9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的民族实现整族脱贫,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贫困。我所走过的刚刚摆脱贫困的拉祜山寨,都在发生着梦幻般的变化,村村寨寨繁花似锦,处处是春天。那一切似乎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想象之外。当初最原始的拉祜族彻底抛弃了原来的山林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创造了新的历史。那些新的村寨已是云南高原上最神奇的风景,是云南历史大跨越的最好佐证。透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云南最深处的民族记忆、传奇故事和时代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