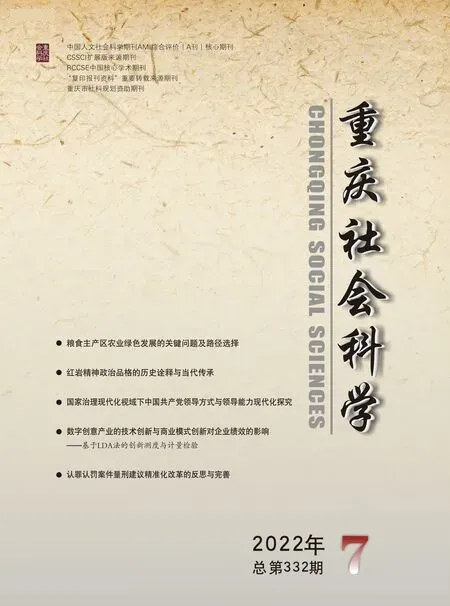大历史视野下超越文本的叙事:从观念到形态
2022-10-14钱践
罗兰·巴特在一段广被引用的经典表述中谈到“叙事”:“它像生活本身,就在那儿(It is simply there, like life itself)。 ……任何质料(any material)和不同实体(different substances)都适于故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社会,‘叙事’无所不在。 ”
值得注意的是,巴特这段话谈到叙事像“个人”的生活,但他列举的主要范例,如神话、传奇、寓言、小说、历史、戏剧、电影、漫画、新闻、对话等,大多数并非“个人层面”的叙事形式。 也就是说,这段话既在说单个“个人”,也在说整个“人类”:“叙事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出现;任何地方都没有也从未有过没有叙事的一个人……叙事跨越民族,超越历史,超越文化……”
这种“超越”视角是理论家探讨“叙事”的原点,但叙事学理论几十年来的发展却偏离了这个原点。 首先罗兰·巴特即是“只说不做”的典型,他论及各种叙事形式,但自己的研究对象很少涉及小说之外
。 另一些理论家雄心勃勃试图“把握叙事的本质”
,事实上仅仅是指“西方叙事传统”,而且主要是“西方文学叙事传统”这一特定叙述形式。 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叙事理论发展的初衷,也不能满足当今全球文化发展现状的要求,是时候将叙事研究从“西方文本叙事”的虚幻藩篱中解脱出来了。
一、 “叙事”清源
“叙事”的常用定义是“一个事件或事件序列的表征(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or a series of events)”
。 在文学批判或“诗学”中,“表征”常常自动等同于“文学表征”或“文本化的表征”,“叙事”的定义也“滑”入了这一“经典”探究轨道:“叙”(叙述)和“事”(事件,无论真实或虚构)两者相联系的理论表述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渊薮——柏拉图对故事讲述中的“叙述”(diegesis)和“模仿”(mimesis)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是对现实世界中人物行为的模仿,通过“叙述”(“逻各斯”logos)建立理念,从而构成“情节/故事”(muthos)的单位,即“事件的组合”
。 茨维坦·托多罗夫于1969 年最早使用“叙事学(narratology)”一词,有学者认为实际应译为“叙述学”。 随后涌现的理论家们开拓这一领域
,理解“叙事”的范式一直在西方文艺理论内部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框架内展开,主要研究的是“文学/诗学”的问题。 “叙事”由“故事层面”和“表达层面”两部分结合而成,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的“本事(fabula)”和“情节(sjuzhet)”,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的“故事(recit)”和“话语(discours)”的基本概念区分中。 “故事”是“一个事件或事件序列”,是事件(行动、事故)的链条,外加所谓实存(人物、背景的各组件);“话语”是指这些事件的“表征”之一,是内容表达的方式
。 由此,对故事的分析主要成为文艺学探讨的主题,急需回答的是“话语何以能成为艺术作品?”这一根本问题。循此路径,“文本叙事”被置换等同于“文学叙述”。 在探索叙事现象的特性的过程中,文艺理论做出过极大贡献,但文学叙事理论受“非认识论”的影响太大,“文学”有一种“天启式”的起源,其产生是不可理解的天才迸发的结果。 “文学性”一词亦造成了困扰,其中熔铸了启蒙时代以来浪漫主义的文艺传统,惯于凌驾于通俗文化之上而形成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这些都对“叙事学”成长为“术语之兽”(指叙事理论的术语特别繁复)
负有重要责任。因此,纠缠于此的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的主要是“文本叙事”,而狭义的“文本(text)”是“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话语”
,与书写媒介的存在为前提,其局限性日渐显露,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口述叙事的传统被遮蔽
文学叙事先天有遮蔽和抹杀前辈口语叙事的倾向,但一切书写都是基于某些先前的口语叙述,后者才是文化的源头。在文字和书写载体漫长和艰难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早期人类艰难地在泥版、莎草纸、甲骨、青铜器或岩石上留下文字,口述是更优越的讲故事方式。虽然文明的起源隐没于史前的迷雾之中,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故事讲述传承机制,即神话叙事传统;关于世界起源的叙述,即“创世神话”,是大多数叙事的开端。在发明了文字以后,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的《梨俱吠陀》、古波斯的《阿维斯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等文集以文本方式固化下来,后人从文字形式上读到它们,最初都是从口述故事开讲。西方文明在三四千年前故事讲述者的技艺就在社会各阶层培养起来,伊尼斯认为,“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
,具有一个强大的口语传统。 早期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三者混在一起,形成“史诗综合体”,是关于具有超人和神的特点的民族人物的长诗,采用“英雄体诗歌叙事形式”,例如荷马史诗就是“口述叙事”传统的骄子:分为24 个章节,全部一种格律,即扬抑抑格六音步写成;《伊利亚特》只是其中一部分,至少是六部分组成,其中大部分都已经遗失了;整部诗全长1.57 万行,根本无法一次讲完,是为几天的节目准备的,像后来的电视连续剧一样,一段一点地讲,一边弹奏里拉琴,一边讲述;几个世纪后到公元前9 世纪到7 世纪,这部史诗才以文字形式出现。古希腊对叙事的理论化首先针对的是史诗向戏剧的转变,其中合唱抒情诗是桥梁。 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具有“纯粹宗教根源”
:大约从公元前7 世纪开始,古希腊每年都在“酒神节”中以歌队形式向酒神献祭,“……从悲剧歌队中产生,一开始仅仅是歌队,除了歌队什么也不是”。 口语传统的力量在悲剧中达到高峰
,很多戏剧未能流传下来,亦因为口头叙述和文字叙述的本质差异所致,后者对前者的遮蔽已然发生。 在我国难以考证上古时代的故事讲述活动,能够记述的上限时间大约在2500 年之前,主要是巫师祭师反复宣讲传承的故事。 中华文明的奠基文本是“六经”,其中如《论语》这样的典籍首先即是口述的经典,而不是书写的经典。因为表意文字书写系统尤其发达,对口述传统的遮蔽尤其严重,这也许是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创世神话故事不完整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还有一个和“正统”的书写系统并行的时隐时现的“民间”口述传统。中华文化中的口语叙事传统亦非常强大,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非常繁荣,但仅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山海经》中以零碎的方式保存下来,或者有一部分会在《庄子》《列子》等子集和《搜神记》等杂录中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
。 我国宋代以降的“话本”形成“文学文本”的流行,其根源仍与官方正统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书写系统有所差异,在勾栏瓦舍中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口语化故事讲述机制。
(二)历史叙事的地位被矮化
历史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却长期被文本叙事理论贬低于“文学”之下。 古希腊哲学以一种形而上理论的抽象方式“规定”了“文学(诗)”的地位高于“历史”,被认为是“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其根据“普遍性/可然或必然原则”是“可能发生的事”
。“(传统)叙事学的基础是文学研究,根植于虚构叙事理论,其精细的模型与术语难以用于非虚构分析”
,“历史叙事”作为一种“有关事实”的“纪实性叙述”
,无疑不应因为记载或试图记载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因其“非虚构性”而被置于此一较低位置。 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和虚构两种叙事类型之间具有结构统一性,“在含义或结构层次上存在着一种家族相似关系”
。“历史”与“文学”是同一的叙事,“不是因为历史是故事,才需要采取叙事的方式,而是因为历史学的时间维度,决定了它总是叙事方式的”
。 我国是一个“历史叙事”高度发达的文明体:在商朝已经在政治机构中设置了史官;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被称为“五帝三代之书”,实为夏商周建立国家治理国家的叙事;钱穆说“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而言,应该是《西周书》。 ……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第一部“正史”,确立“史官”的正统书写传统;《二十五史》四千七百万字,建构了一个纵贯四千年不断绝的“故事世界”,而且几乎不可翻译成其他语言。 可以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由巫而史”
后告别神话叙事,《尚书·禹贡》开辟了历史叙事的“中华空间”——“九州”,并以开放的姿态在以后的叙事中不断拓展,“共和元年”开启了二千多年不间断的叙事“时间”。 “历史叙事”的核心不在“文本表征”与“事件”的关系,而是“故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以“事实性”为基础,即根据考古证据推测实际发生的“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假设性的关系。 虽然历史学家们普遍认可历史叙事中充满了“文饰”和“谎言”,但“历史”是建立在“实际发生”思维基础之上的“关于事实”的叙事。 作为奠基性的“非虚构”并非缺陷,而是在另一个思维领域制造叙事可能性。
当前许多无线收发系统的射频前端电路,如3G与4G手机、蓝牙及WLAN等,已经逐渐采用系统级封装方式,以实现功率放大器模组与天线切换开关模组等的微型化。在电子系统中,片外组装的无源元件占据了可观的面积,成为系统尺寸进一步减小的瓶颈。缩小无源元件的尺寸以减小元件所占据的空间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1]。基于多层薄膜技术的集成无源元件IPD(Integrated Passive Device)由于其相较于分立无源元件具有尺寸小、高频特性好、可靠性高、设计灵活、成本低的优点[2],正在军事、航空、医药、照明、消费电子等应用中不断地取代传统的分立无源元件。
(三)电子媒介中的视听叙事难以适配
“一座火山爆发了”不是叙事事件,将地球上所有火山爆发的地质记录汇集在一起只是纪实清单而不构成“叙事”,而“维苏威火山爆发了,几万庞贝居民(作为智能主体,即使被动参与)在瞬间被杀死”就是“事件”,其中有“智能主体”才能成为故事的“素材”。 不仅仅因为“人物”是“叙述文本的底线定义”
,故事中的“智能主体”是认知建构的结果。 例如,“神话”是“神或近似于神的存在的故事”,以“神格”为中枢,通常是神的人格化或祭司和祭祀机构的神格化;童话和寓言中的动物角色是“模拟智能主体”,这产生于人类历史发展早期的“万物有灵”或者“灵魂轮回”的设定,如印度文化“灵魂不灭”“轮回”等观念即促进了寓言和童话的发展
。 “心智假说”(Theory of Mind)认为人类具有假定我们交流的对象是和我们一样有意识和智能的主体的心理功能;根植于“主体性拓展”的诉求,故事中智能主体的外延拓展到动物、非生物、机械等,在寓言和童话中,兽可以说人的话、做人的事、具有人的情感,甚至在动画片
中一条线和一个点也会相爱。 “人格化”的基本要求包括跟人类同构的人格、情感、智能、意志等,从而成为叙事中的人物角色(character in narrative)。 “故事中智能主体”的水准和能力有高有低,以现象学式的“意向性”和能够驱动行为的“意志”为最低条件,即具备目标指向自主行动(action)的能力,从而成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制造者,但却不必然以现代意义上的“人”为模板。 福柯曾指出,“在18 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 ……人是完全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其双手把他制造出来还不足200 年”
。 如果执意按西方的“现代性”的标准来评判,古老的或其他文明系统讲述的故事中的“智能主体”都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灵魂”。 事实上,“人格化智能主体”可以看作使事件序列获得整体相关性的一种基本认知建构手段,在各种形式中产生,如历史或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国家和民族被“人格化”为主体。 此外,从类比角度亦可将“宇宙”或“自然”人格化和智能化,如整个宇宙起源发展所有的“事实”归宿汇集在一起的“大爆炸理论”,或“为天地立心”的儒家学者心中的“天下”,从这个意义上(并联系其他要素)讲,“宇宙演变和进化的故事”和“天下苍生的延续”亦是“叙事”。 康德曾说灵魂、宇宙、神不是知性认识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来,叙事思维从逻辑性范式思维的领域出发并超越了它。
(四)网络媒介中的互动叙事高速成长
叙事是一种在不同实体间建立联系,构建整体的综合性思维。 这种“实体”间,包括事件间和主客体间多样化的相互联系,可以在康德的“纯粹悟(知)性概念范畴表”的“关系”和“形相(模态)”中找到思维方式的根源
。 “关系范畴”包括实体性、因果性和相互(协同)性,其中“因果性”在故事讲述中独占特别的地位。 以古希腊戏剧为滥觞的西方叙事传统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情节论”上
:情节是“悲剧的灵魂”,为“张力之弧”,是叙事的核心特征,是“对行动的模仿”“事件的组合”及“故事各构成部分及其功能与关系”“统一的因果链并导向封闭结尾”即成为“故事”的最重要的部件。 “情节这个词的所有意义都在于表明叙事框架”
,但“情节”只是建构事件序列的诸多框架之一,破除叙事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首先需要消除这种“情节观”。 中华文化最早的神话体系《山海经》中,故事情节完整的神话,不过七八段
,但并不能以此来评判中国神话体系缺乏叙事性。 《山海经》是最伟大最精彩的古代神话叙事,宏大而奇崛的时间和空间想象展现了中华古代先民对宇宙、周遭世界诸种关系的理解,其中的意义创造非常丰富,不因情节的缺少而减色,而且中华文化的叙事体系并不以“因果链”作为思维标杆。 “模态范畴”的思维方式在叙事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尤其关键,建立起可能的(可能性)、现实的(事实性)和必然的(必然性)的“思维之公准”
。 “叙事模态”规定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多样化的故事建构中做出本质性区别,内在地规定了“虚拟叙事”和“历史叙事”的差异。 17 世纪前三十年,作为“虚拟叙事”代表的新型叙事综合体“小说”兴起,其特点包括:虚构性、散文体裁、用足够篇幅通过细节来发展人物
。 “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根本任务是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是“个人对现实领悟的信念”
。小说的“虚构性”是“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即仅在故事世界中为真:读者知道鲁滨孙这样的小说人物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而是在虚构的“可能世界”中存在。 “可能世界”
概念源于莱布尼茨,是一个不包含逻辑矛盾的虚构世界,而“历史叙事”却恰恰相反,即使有一定的虚构故事存在,但必将“事实世界”作为思维活动的基础。 例如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正史中的很多记载作为历史事实都不一定真实发生过或者不可证明其真实性,但一定以相关的人和事的“事实性”(factuality,确实存在过的)作为认知建构的基础,否认这一点“历史叙事”的表征基础就将分崩离析。 “神话”对于古代先人来说具有“事实性”,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口口相传的“实存”,对于今人来说神话具有某种高于虚构的“必然性”的思维定位。 童话、寓言等故事形式,或是“架空”的幻想(fantasy)故事,如网络小说中的玄幻、魔幻、修仙等内容,既不发生在“可能世界”中,也不是事实性的“实存”,但揭示万物轮回的“必然性真理”,或是作为世界的“隐喻”,这是此类叙事活动得以继续的基本思维模态
。
“叙事文本”只是以文字书写媒介中固定下来的人类故事讲述活动,“叙事文学”作为精英化的故事话语表达,出现的时间相对更短。 从“文本”,特别是“文学文本”的自我设限中解放出来,回归“叙事”的本源,超越已有的术语系统来探究“叙事性”,才能将多样化的叙事现象纳入考察。
二、“叙事性”辨析
“叙事性”是“叙事”区别于“非叙事”的典型特征,是对“叙事”的质性规定,涉及“程度”的度量(a matter of degree)
,或“怎样讲一个更好的故事”
。 后经典主义的叙事学,如认知叙事学和跨媒介叙事学,受到越来越广泛关注,原因之一即其对“叙事”的界定超越了“文本”框架,将“叙事”与普通文本形式,即编码在符号和话语中的表征,区别开来。 故事乃一心理意象、一个认知建构、关涉到特定类型的实体,以及这些实体之间的联系
。 瑞安将“叙事性”视为一个分级属性,总结了八个条件
:第一,空间——世界中栖居着个性化的存在物;第二,于时间中历经显著改变;第三,改变是由非习惯性物理事件所引起;第四,事件参与者是智能行动者(有心理活动和情感反应);第五,行动者有目的地行动(有自由意志并目标驱使);第六,事件序列形成统一因果链并导向封闭;第七,事件的发生为故事世界的事实;第八,故事向接受者表达某种意义(有主旨,point)。 瑞安“提供了一个工具箱,供自制定义”
,但没有明确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条款,而且其中尚有较明显的受传统文学叙事理论束缚的痕迹,如五、六、七条就完全继承了普林斯所界定的事件描述、完整性、叙述定向的“叙事性”
,而我们看到许多叙事现象并不完全呈现为这样的形态。
从“语言学转向”的立场,现代哲学普遍认为语言塑造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维特根斯坦即认为“叙事”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游戏”
。但作为“语言游戏”就有本质差别,不同源的语言会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如印欧语系的表音系统规则运用于汉语系将是失效的,索绪尔即认为作为符号学基础的语言学理论只适用于“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
”。 如果将“语言将决定思维方式的差别”纳入考虑,无疑对我们理解植根于文化体系的叙事现象带来巨大挑战。 从人类的心理认知建构的基础上来分析,“叙事”更应该说是一种“思维游戏”,是跨文化而同一的,甚至更进一步,“叙事”是在“语言”之前就存在的生命活动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范式(逻辑)”和“叙事”(paradigmatic vs. narrative cognition)是个体两种最基本的认知模式。 这一区分具有启发性,但也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误导,即将两者对立起来,似乎“叙事”认知是与“逻辑”或“范型”认知模式并不相容的。 在叙事活动中,个体调动全面的思维能力来建构“事件序列的表征”,遵循认知过程的基本规律。 从这一基础出发,可将“叙事性”条件进一步梳理,合并相容项,规定必要界定,然后在必要条件中判断“程度”区别:
1.事件必须在“空间”中发生。 (前述第一条)
“叙事”(narrative)从希腊语词源上(词根narratio,原意为“陈述”,意思是“探究”)指对已知或可知事物的描述,或者说曾经知道又被遗忘的,因此可以通过适当的话语手段召回的事物,它预设有一个“知者”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导致“叙事要点”
(或“主旨”,point of narrative)出现和传达。在叙事话语产生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一个有交流意愿的“知者”(“自然智能主体”)作为叙述者
,所创造出来的“表征”能够为另一个“自然智能主体”(即接受者)所理解。 叙述和接受双方“智能主体”,无论在时间上间隔千年,或是空间上相距万里,都具有人类“普遍的心理结构”
(univeral mental formulation),进入以叙事性所规定的意义交流框架或“契约”中:叙述者知道后来的接受者会接收到这个故事,接受者通过现象学式地共情叙述者的意识状态从而获得意义。 例如,在考古中我们发现史前时代人类用绘画在岩壁上描述他们狩猎的故事,我们“辨认”出这个叙事者是和我们智力能力和意识结构方面同构的个体;玩家在电脑游戏中能够产生一段叙事形式,这个具体的“故事”是游戏程序和玩家合谋生成的,但在程序背后仍然是人类设计者;“人工智能”写稿机器人能够模仿人类智能生成一个叙事(新闻故事或影视故事),AI 为人造机械物,但AI 制造者具有意识结构,这为主体之间交流提供了基础;甚至“梦”和“幻觉”作为一种“心像叙述”也是一种叙事形式,“自我”既是“叙述者”也是“接受者”,必须接受自己传输的“叙事要点”才使得这种叙述具备“叙事性”。事实上每个人在理解叙事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性的“主体间性交流框架”(framework of intersubjectivity)之上。 我们可以认为,第一次电影放映“火车进站”时人群惊恐奔逃,部分原因即是因为观众未能建立这个“叙事理解的交流框架”。 叙事所构造出来的“主旨”指向这个文本外的表意叙述者,不管他/她是“太史公曰”式的显性表达还是用各种质材掩盖的隐性叙述, 作为叙事接受者知道叙述者有意志、 观念、情感、判断、价值观。虽然很多故事都包含道德主旨,但这不是僵化的训诫,而是主体间关于生命体验的交流;叙事认知模式展现了人类思维的复杂性,恰恰与逻辑认知的清楚明晰相对;叙事通常不是一目了然、直来直去的,它再现、图解和阐释一些不寻常的、问题丛生的东西,对接受者有价值和有关系的东西。 “没有对接受者一方的欲求和这一欲求的满足,就没有叙事的要点(正如没有发送者一方“生产出叙事”的欲求就没有叙事一样)……一旦欲求得以满足,叙事必须停止”,这种“欲求”可称为“叙事期待”
,是个体进行叙事认知建构的心理基础。虽然在所有的人际交流活动中“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都是必然存在的,但在叙事叙述者和接受者之间,通过事件序列表征进行的复杂意义阐释必须在“叙事期待”的基础之上才能发生。
3.实体间(事件间及主客体间)建立联系。 (前述第六、七条)
“那我下的牛女,可是我并不喜欢那个狠心的织女啊,自己飞升成仙,不要牛郎也还罢了,那两个孩子却是无辜的!”上官星雨说。
不管是采购、安装、折旧的哪个阶段,固定资产的管理都存在松懈和不规范的地方。其提高的重要手段就是在部门内部建立固定资产管理小组,分管固定资产的财务管理问题。并对固定资产采用全生命周期的问责制,每个单位、每个部门购进的固定资产必须有确定的工作人员对这项资产负责到底,使得资产管理落到实处。
5.“(故事外)表意叙述者”必定存在。 (前述第八条)
(一)在叙事中进行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性运用(关于1 和2)
“冲突”源于古希腊语agon,意为“对抗”
,是西方文化中典型的叙事观念之一。古希腊戏剧起源于史诗和歌队,总是两三个演员,通常发生在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一天)内,用歌队咏唱来转场。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傻瓜史诗”《马耳吉忒斯》分别是悲剧和喜剧的先声
。 “悲剧起源于狄苏朗勃斯领队的即兴口诵,喜剧则来自生殖崇拜活动中歌队领队的即兴口占。 ”
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总结,“冲突”成为其叙事的核心特质。 经过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后的文艺复兴,意大利学者们接续了古希腊戏剧传统,琴提奥于1545 年根据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整一化”提出“三一律”,正式条文是卡斯特尔维特洛在此后提出
。 欧洲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将情节行动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布洛瓦要求从“一天、一地、一人一事”的方式进行叙事,虽然僵化的时空关系、刻板的类型化人物饱受诟病,但时间、空间和情节的集中非常适合展示故事中人物之间及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冲突”。 近代大众媒介发展以来,戏剧和小说两种通俗文化的故事讲述方式开始繁荣,“冲突即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加悬念设置”是吸引大规模观众和读者以创造利润的利器
。 电子媒体时代好莱坞商业电影将“冲突”作为叙事的动力来源,给主人公的自由意志行动设置障碍以形成与环境的冲突是吸引观众提升票房的灵药。 “冲突”观念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突出外化表现,但只是人类文明演化中形成的诸多叙事观念的其中一种。 从上古无数的神话到今天的网络时代叙事的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角色结构”“时空关系” 和 “世界架构”在叙事认知建构中的作用往往大于“冲突”,“故事”的目的从来不是不断对抗对手而达至封闭“结局”。
(二)在叙事中进行关系和模态的自由运用(关于3)
在网络媒介中,一场“叙事革命”正在到来。 瑞安曾谈到调和叙事性与互动性的艰难,“互动性”乃数字环境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线性叙事的时间、逻辑、因果的单向性相悖。 在网络的互动性、社交性、移动性等核心特征的直接作用下,多样化新型叙事现象不断涌现,如超文本文学、多媒体文本、赛博文本、数字叙事、粉丝参与式叙事、互动叙事、沉浸叙事等等
,传统文学叙事学理论已无力解释旧媒体、新媒体、新新媒体中的这些创新的叙事形式。 网络小说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互联网生态所培育的超长篇商业类型小说,网络小说的兴起和发展高度依靠商业模式的成功,充分展现了“新文化工业”
的生产特征,如“巨量化”(海量内容生成)和“用户自发产生”(平台生产、数字劳工、用户生成内容、智识无产者、非成熟劳动)等;建立在“互动性”上,其中反复出现的“欲望叙事”,如爽文、YY 文,是通过网络达到的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思维同构,如果没有打赏的预期,一切创作都不会发生;高效地借用数字时代的文化质料,如从网络游戏中借鉴的世界观设定(换地图)、装备和升级设定等;建构在“亚文化圈”(如御宅、耽美等)基础上的意义再生产;符码意义的自我循环,迷因(meme)、哏(梗,neta)等新型语料,已然脱离传统文化资源再生产的规定。 在全新的媒介传播模式中去寻找与旧的媒介叙事形式的对应之处,例如在网络小说中去苦苦搜寻“文学性”,辨认类似于印刷和报刊通俗小说的叙述模式,极力挖掘“经典文本”,诸多努力往往是徒劳的。 如果不墨守“文学文本”的框架,“互动性”并不天然地对叙事有破坏作用,例如网络电子游戏和VR 等创造的虚拟时空中设定了玩家共同创造意义的方式,在新的维度上开创了极大的叙事自由度。
(三)故事中的智能主体为必要(关于4)
电子媒体的发展给叙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特别在电影、电视等电子视听媒介中,通俗文化方式的故事讲述获得了解放。 电影自发明以来从商业通俗小说中吸取很多养料,对印刷和报刊连载小说类型有一定的继承,但形成了独特的类型影视形态,创造了很多“造梦”式的故事架构。 抛开任何传统文学批评的标准,运用镜头语言进行的故事讲述都可称为别开新路,开拓了人类叙述经验的视野。 最早开播的广播肥皂剧《指路明灯(The Guiding Light)》(1937)在1952 年6 月转变为最早的电视肥皂剧,到今天仍然在以每年52 周、每周5 天、每集60 分钟的标准方式延续着故事,创造了人类叙事史上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奇迹
。 电视媒体的内容表达很大部分采用传统戏剧的形式,由演员通过模仿表现,并且利用情节、对话、人物、手势、服装等全副的戏剧表现手段,成年电视观众平均每周观看相当于五到六出完整的舞台剧
。电视节目中不仅仅剧集(肥皂剧、情景喜剧、系列剧等)在“叙事”,新闻报道、纪录片、综艺节目、谈话节目、体育赛事等电视节目中都有“叙事”,高度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形成了电视节目的程式化、配方式,也形成连续式、嵌套式的故事模式。 例如新闻节目中,长历时的密集报道使每个小故事拼接串联成大的故事;综艺节目会通过塑造参加节目嘉宾的人物形象来获得戏剧效果;体育赛事现场直播中增加情节元素从而使实时记录具有叙事结构
等等。 电视媒体所创造的电子视听版的故事,其数量之大、形式之多、影响之巨是人类叙事经验从未有过的大爆炸。 视听形式叙事与书写文本叙事的本质区别,是展现在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直接的逼真模仿,如从情节剧发展而来的通过音乐和画面共存、音乐和对白交替所营造的“情感伴随”状态在影视剧视听叙事中成为常规
,和日常生活体验(包括梦境)具有同构之处;每一个视角镜头和无缝剪辑都是模拟个人经验中的视觉认知过程,替代主体视角以传递意义;媒介呈现的视觉形象依靠“镜像阶段”的心理机制让观众从屏幕上认出“自我”以建立共情和认同;“奇观叙事”的电影和虚拟现实等最新的视听媒介技术通过“呈现于眼前”的沉浸感建构叙事时空;等等。 电子视听形式的叙事已经挣脱文字的束缚,如果以文学叙事为模型对其展开阐释,是非常不适配的。 必须对影视进行符号化的文本转换后,强塞入符号学的概念系统中才能开展意义研究,如杰出的电影叙事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艰难地用多重理论“建构电影的意义”
,很多情况下只是在理解电影的“文本意义”。
(四)故事外的表意叙述者为必须(关于5)
2.事件必须在“时间”中发生。 (前述第二条)
三、跨文化和跨媒介的叙事观念和形态
叙事是个体组织和理解“经验”的基本方式。 每个人在每日的人际交流中,每夜的梦境中,都在进行组织自己的人生经历的“生活(自然)叙事”,这是一种普遍地通过给予“事件、意识和关于人类的一切事物”以“内在连贯性”从而获得生命或意义的思维活动
。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将个体的“生活叙事”与人类大规模进行的“普遍叙事”区分开来,虽然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 在文化场域中,某些普遍性的“叙事观念”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形成了“惯例”“程式”和“模型”(convention, fomula, pattern),与“模式”“模态”或“形式”(model, mode, form)等概念相区别,即是具体的“叙事形态”。 “叙事形态”或是在政治权威、文化精英或社会机构的支撑下完成“经典化”,或是因商业成功而在大规模人群中形成了“流行”,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大众媒介实现显著的指涉意义,同时反过来对个体性的“日常生活叙事”有所影响。 “叙事形态”从个体心理认知建构的角度实现了前文所述的“叙事性”,在具体呈现中超越个体层次:既在内容方面,也在形式方面;既指叙事话语表达的部分,也指故事叙述所用的质料(叙事作为form、material、content、expression 的区分)
。 因此,“叙事形态”这一综合性概念将跨文化、跨历史、跨媒介的方方面面叙事性元素涵盖进来,通常在话语表达中与媒介条件密切结合,亦常常表现为一种历时性的模型建构。
为实现对深度、航向角等数据的存储管理,需要增加数据库功能。文献[17]在Qt基础上移植了MySQL数据库。由于只需要简单的数据库操作,用户操作软件选择轻型的SQlite数据库。
在康德哲学中,“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之纯粹方式”
,是人类基本的思维能力,作为先验形式在叙事中灵活而自由地运用。 即使如印度文化中没有时间和空间观念
,但古代印度人仍在“故事讲述”中建构时空中的“可能世界”。 人类通过创造故事自由地构建或改变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从而拥有掌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魔力。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神话讲述的故事“没有日期,也无法确定日期,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将其放置在编年史上”
。这是与世俗领域泾渭分明的神圣时空, 是人类思维构造出来的实在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的神话是“想象的历史”,神话人物与人类共享一个时空,如“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后乃有三皇”
,神话似乎就发生在有史记录的“三皇五帝时代”不久以前。 中国的神话和仙话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成为独立的系统,但连绵不绝,如《搜神记》《八仙传奇》《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神和仙一直在人类身边共享时空,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华文化的叙事时空往往特别宏大和浪漫,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有几千里大,动不动“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因此庄子如果遇到年长十五岁的亚里士多德,肯定不会同意他“动物个体……太大了也不美”
的论断。 延续到今天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中以千年为单位的太空计划,或《吞食者》中能将地球套住的外星舰船等
,这些宏大的时空想象所具有的叙事魅力亦来自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滋养。 在电子视听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时代, 从无到有创造出虚拟时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科幻神魔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界面等,都能成为展开叙事的时空场所。
总结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可先由各组进行自我小结及评价,然后由教师归类、讲评,指出操作中的优点和不足,提出建议。通过这一教学环节,既能使导生及其他学生产生成就感,提高学习积极性,又有利于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便于今后改进和完善。
中华文化中的叙事观念是完全另一番风貌,其他文明中没有人像古代中国人那样就“万物相生相成”和“历史复杂性”进行过那么多深入认真的思考,并呈现在多样化的叙事形态之中。中华文明的“神话语料库”散见于各种经典古籍,虽不系统,仍非常丰富。 与西方文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期仅仅在教士的《圣经》宣讲中和教堂的彩窗玻璃上所讲述的故事相比,同时代的中国的志怪、传奇等叙事形态高度发达。 虽然长篇叙事的创作力似乎都汇聚于“正统官修历史”中,但与此同时根植于口语传统的民间故事也在顽强地生长。 例如,起源于宋代的“说话”:“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为‘说话人’。”
根据《东京梦华录》,宋代涌现的大众娱乐中心和戏曲表演场所——瓦舍勾栏,在东京有五十多所,临安也有二三十所,所讲内容以“说三分”历史故事、“八仙”等神话和仙话故事较多。 说书人可以不断地对故事进行叠加式的创作,这一“集体创作”过程可能持续了几百年,经过转化为书写形式继续进行传播,故事才以文本方式固化下来。 “拟话本”是说书人口述故事的书面转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出现于宋元之间,形成了最初的章回小说,并在后来提炼为具备高度文学性的“才子奇书”。作为长篇章回小说集大成之作的《三国演义》,以“历史+口述”故事形式成型,“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 “章回小说”动辄几十上百的人物出场,多线索叙事层层推进,与西方随印刷媒介兴起的长篇小说“novel”大异其趣,时间上亦大大早于《堂吉诃德》《帕梅拉》或《鲁滨孙漂流记》等小说;其后明清以来与印刷技术同步发展的小说形成神魔、人情、讽刺、狭邪、侠义及公案、谴责等潮流呈现出类型化的特征
。 现代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作家的武侠小说受章回小说的影响极大,依靠报刊媒介而风行于世。电视普及后,我国的电视连续剧并不完全复制欧美的肥皂剧和系列剧形式,形成独有的电视剧风格样式。 一直到今天繁荣于中文互联网生态中的网络小说,其中亦有“中国古典式叙事”的特征,如想象性叙事时空建构、历史背景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情节线索的“辫结结构”等等独有的故事特性,体现中华文化特质的叙事形态一脉相承。
4.“(故事内)智能主体”必须参与。 (前述第三、四、五条)
“叙事形态”不等同于文化体系内部的文学叙事传统,而是将各种外部文化因素纳入考虑,从而将“叙事研究”从针对单一文字书写文本模式中解救出来。 “叙事性”存在于许多“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之中,是跨“文本类别(type of text)”,与“类型(genre)”或“文体(literary form)”相区别的质性规定。 包含“故事讲述”的体裁或类别包括:神话、传奇、传说、民间故事、寓言、史诗、宗教故事(圣经、石刻、教堂和寺庙装饰绘画)、历史、戏剧(戏曲、歌剧等)、游记、说书(话本)、童话、小说(志怪、传奇、章回小说、骑士小说、现代主义印刷小说、报刊连载小说等)、电影、广播/电视(电视剧、电视节目、新闻、直播等)、动漫(动画和漫画等)、电子游戏(单机游戏、社交游戏、多人多角色游戏等)、超文本小说、同人小说、互动剧、实景游戏(密室逃脱等)、剧本杀、网络小说等等。蔚为大观,难以尽举。很多情况下,跳出文本类别特性更能清楚地看到叙事作为心理认知建构的样态。 通常意义上,媒介内容皆可归类为从属于特定媒介的广义的“文本”(与前文所述的“书写文本”相区别),但“叙事形态”是跨媒介文本的,在各种媒介传播中固化下来成为程式化“认知惯例”,单独于特定媒介都不能完整描述。 “媒介性”一方面指各种不同媒介自身具备的叙事能力,另一方面指媒介特性对叙事性具有显著影响力
。 媒介可界定为口语、书写、印刷、电子、数字、网络、社交等等多种类别
,并非连续相继产生,如口语媒介的叙事传统就一直延续,在戏剧和戏曲、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中都有展现。 媒介的技术特性与“叙事性”相结合,形成既受媒介影响、同时也超越媒介的“叙事形态”。
2.3 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BMI、空腹血糖、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为自变量,而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空腹血糖、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影响纤维蛋白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见表3。
在某些情况下,“叙事性”在某种文化形式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或构成核心特质,如宗教通常会借用故事讲述的方式传播;许多叙事诗歌中也有或长或短的故事;中国戏曲和西方歌剧中的故事并不喧宾夺主;电子游戏的世界观设置具有故事的外壳;等等。 但叙事性的诸要素通过形成富有活力的“叙事形态”而得到保留。 此外,聚焦“叙事形态”可以避免去注意那些并未被大众广泛接受的“认知惯例”,或并未形成“文化结晶体”的叙事现象。 各种媒介中不间断地进行着数不尽的叙事实验,例如各种实验派小说,先锋文学,或是网络媒体中的互动文本、多媒体艺术等,但是其中只有一部分“叙事形态”存留下来并被固化,受到大众“叙事接受者”的普遍认可。
四、大历史视野下叙事体系的差异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建构
考察“叙事”超越文本的视角同时也是跨文化的大历史视角。 以此着手对“叙事”的本源性进行理论探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其一,叙事形态在历史中形成和演化的普遍规律为何? 其二,在各文化体系内部的叙事传统如何独立发展又怎样在各文化体系之间互相融通? 其三,媒介深度融合时代的未来叙事形态将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及显著变化?
季羡林认为世界文化有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四大“体系”
: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阿拉伯,再没有第五个
。 不同文化体系在历史中不断演变,孕育出多姿多彩但不绝如缕的叙事传统。 印度很可能是世界上大部分寓言、童话和小故事的老家,如梵文《五卷书》中的故事在全世界被翻译与传播,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亦受其影响
。 伊斯兰阿拉伯为世界贡献了《一千零一夜》民间故事集,它起源于口述故事,从八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经过数百年锤炼,具有“嵌套结构”的“框架故事”,被称为拥有一个故事应该拥有的一切要素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是关于“讲故事的故事”
。雅斯贝尔斯谈道:“(使用印欧语的)印度-日耳曼民族创作了英雄传奇和史诗,发现、形成并思考了悲剧精神。 ”
“悲剧精神”中蕴含了希腊文化的独特叙事观念,如主体的觉醒、对“人之存在”本质的意识、对高于自身的力量,通常是决定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神”的反抗和超越等,其中有“正/邪”“人/神”二元对立冲突的结构
。 各种文化体系中孕育和发展的叙事话语体系无高下优劣之分,没有可自认为高于其他文化体系的理由。 尼采认为普罗米修斯盗火传说反映出雅利安族的民族性格,如同原罪传说反映了闪米特人的性格
。在其后的叙事话语体系中,《新约》中的“耶稣”被改造升级而创造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形象,从而与犹太教的《旧约》叙事有所区分和对立。 神话叙事的差别被扭曲、夸大并推至荒谬的极端,最后走向针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的浩劫。 雅斯贝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进行的反思,提出“轴心文明”概念,试图重新梳理文化差异的起源,亦是为历史的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的一种尝试。
平衡条件:55 ℃,30 min;萃取头解吸条件:250 ℃,3 min;萃取头吸附条件:55 ℃,40 min;气相色谱条件:进样口温度:230 ℃,质谱条件为四极杆温度:150 ℃,离子源温度:230 ℃,电离电压:70 eV,方式为:EI,质量扫描范围:20~500 u[13,14]。
中华文化的叙事观念和形态无法削足适履地适应西方叙事理论的“精巧”标准,呈现出一派举世独有的恢宏气象:深厚的历史叙事机制,万古一系的历史观,从更长的连续时间视角来观察事件;中华上古时代的神话体系被发达的以官方权威背书的历史书写系统掩盖了,但通过顽强生长、连绵不绝的民间口语叙事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 中国叙事从来强调以人为中心,“仁者,人也”,“中国古人则从头下来重在人”
。 《史记》作为我国的第一部正史,叙述了近三千年的国之大事,“家族史”《太史公自序》也侧身其后:“……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中国叙事扎根于个体的情感体验,思考历史的意义和目的,展现出中华文化独特的人文精神。中华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了异常恢宏而同一的世界空间想象,在叙事体系中深刻地思考了“天地人”,即人与命运、与苍生(社会)、与宇宙(自然)的复杂关系,在故事讲述中展现出“口述/书写”“庙堂/江湖”相生相成的状态。中国故事的叙述者“为天地立心”,将无意志的自然(天地万物)构造为有情感、有道德判断的主体。 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将整个人类共同生存经验组织为“叙事”,以此承载“人之命运”的终极价值,创造出不同于其他文化体系的叙事观念,同时具有极强的普世意义。
我国绵长的历史和超稳定的结构并非意味着封闭守旧。中华文化极善于融通外来文化,如近两千年来吸收融合佛教思想的精华,近两百年来兼容并蓄西方优秀文化的养分,都是极好的例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将视野放到广阔的大历史格局中,会发现人类在漫长的时间中创造了多样化的叙事观念、叙事形态和叙事体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
以来,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新闻宣传实务,对“中国叙事”相关问题的理论化和学术化一直未形成风潮,基础理论未能深入开掘以提供学理支撑,经典叙事学对文本的过度关注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形成此领域沿用“西式范式”作为主导。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破除叙事学领域中“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是在此道路上探索的开始。
[1] H.伯特·阿波特.剑桥叙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2]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3.
[3]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M].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0.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6.
[5]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97-200,206-213.
[6] 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叙事研究论文选[M].侯应花,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7] 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5-6,18.
[8] 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关于语言、行为与解释的论文集[M].J.B.汤普森,编译,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116.
[9] 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6-60.
[10]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三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6.
[11] 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5.
[12]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3.
[13] 袁珂.中国神话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2,171.
[14] 张新军.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6.
[15] 张耕华.历史学的真相[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173,198.
[1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13.
[17]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38.
[18] 苗棣.美国电视剧[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9] 阿瑟·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
[20] 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M].张新军,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74-90,95.
[21] 詹姆斯·L.史密斯.情节剧[M].武文,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22] 大卫·波德维尔.建构电影的意义:对电影解读方式的反思[M].陈旭光,苏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3] 亨利·詹金斯.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M].郑熙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4] 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5] 王曦.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来——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J].探索与争鸣,2019(7):147-156+160.
[26] 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43.
[27] 张江.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J].探索与争鸣,2022(1):36-42+177.
[2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4,97.
[29] 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0]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薛克翘,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144-151.
[31] 汉斯·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M].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67.
[3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
[33] 刘慈欣.科幻小说自选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34]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6-7.
[35] 张瑜.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19.
[36]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312.
[37] 海登·怀特,罗伯特·多兰.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M].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70-171.
[38] 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M].李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7.
[39] 杰罗姆·布鲁纳.有意义的行为[M].魏志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39.
[40] 刘一兵.电影剧作观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16.
[41] 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M].甘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8-81.
[42] 珍妮斯·A.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M].胡淑陈,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43] 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
[44] 玛丽-劳尔·瑞安.跨媒介叙事[M].张新军,林文娟,等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15-16.
[45] 赵勇.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大众文化[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21-27.
[46] 季羡林.东西文化比较[M].张光璘,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25.
[47] 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M].黄少婷,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6:230.
[48]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李雪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68.
[49] 卡尔·雅斯贝尔斯.论悲剧[M].梁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16-17.
[5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761.
[51]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01).
[52] 求是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EB/OL].[2021-06-02].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1-06/02/c_112752238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