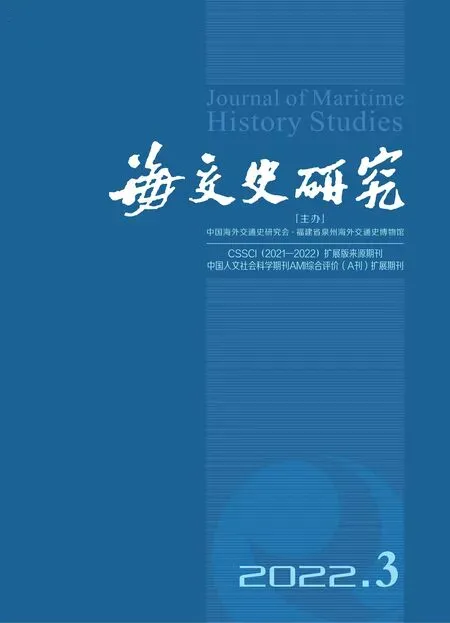1759年洪任辉事件所见清中期治理的制度困局:以6%加征和1950两规礼为中心*
2022-10-08冯佳
冯佳
一、前言
1757年,乾隆帝颁发谕旨:限番商于广州一口交易,不得再赴宁波。(1)[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3页。试图突破广州贸易不自由的束缚,175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派洪任辉(James Flint)不顾清廷禁令再度北上,祈望将公司的诉求越过粤海关监督和行商而直达乾隆帝。(2)《清史稿》卷129,《邦交》2,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515页。尽管清廷依照洪任辉呈词所控诉的粤海关勒索外商惩办了时任粤海关监督的李永标及其家人、吏役,然而不仅洪任辉呈词的四项主要诉求无一兑现,而且在随后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发的《防范外夷规条》中,广州一口通商的制度进一步法律化,为《南京条约》签署前中西贸易架构之滥觞。(3)有关 1759年洪任辉呈递给乾隆帝的四点诉求,参见: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0, p.67.洪任辉事件对广州体制的形成之影响,参见: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Vol.5, p.93; 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第138页。
洪任辉事件及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因其作为鸦片战争前中西方冲突的标志性事件,而成为历来史家讨论的热点。通过爬梳记载该事件的各类档案文献,既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呈现了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出台的多重面相。第一个观点认为,广州体制的形成是广州不可比拟的对外贸易优势所决定的。(4)[美]范岱克著:《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页。这一点不仅体现了粤海关在清廷各海关中的特殊地位,而且还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即17世纪后半叶英商甫在厦门设立商馆,广州便已成为英国商人梦寐以求的通商口岸。(5)粤海关设立之早及地位之特殊,参见:李金明:《清代粤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征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8页。有关17世纪后半叶英属东印度公司开辟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努力,参见: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6, pp.45-46, 78.第二个观点是,清廷出于防范“奸民”和“夷商”的媾和,担心宁波变成第二个澳门。(6)王华锋:《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出台原委析论》,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77页。中国人历来有将西洋人视为生事之徒的偏见。(7)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第112页。对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港口限定政策的实施实则是避免重蹈澳门问题之覆辙。(8)陈尚胜:《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与澳门问题》,载耿昇、吴志良编:《“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1—137页。第三个观点结合其时西北边疆正在进行的准噶尔战争,指出江南作为清廷巨额军费的主要供应地,维持江南海疆的稳定、不使宁波成为第二个澳门,对清廷西北边疆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9)曹雯:《清代广东体制再研究》,载《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94—95页。最后,着眼于广州在对外贸易方面长期以来的特殊地位,有学者指出,禁止番商赴浙虽然对浙人生计有影响,但影响范围远不及广州大。番商弃广州而赴宁波还威胁到了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的收入,威胁到了广州外贸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10)顾卫民:《广州通商制度与鸦片战争》,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66页。史学家们都试图证明自己所强调的单方面原因是18世纪的清廷决定推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主因,并试图声称自己所秉持的单一原因实为解释鸦片战争前清廷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唯一钥匙。(11)陈尚胜教授指出无论“闭关”还是“开放”,均体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农业文明国家的话语霸权。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载《文史哲》2002年第6期。
然而,这种仅从清廷方面的材料出发分析中西交流、冲突问题的原因的做法不仅忽视了作为互动另一方的英商,而且既有研究所表现出的为复杂历史问题寻找单一原因的研究方法,不免有陷入历史还原论之嫌。更具体地说,只是揣摩清廷方面颁布一口通商政策的动机和意图何在,不免倒果为因,误将制度的表象当成了制度本身。其结果则是或者结论与史实不符,或者难以就清廷18世纪一口通商政策的出台及延续这一“长时段”问题形成一以贯之的解释。
首先,以广州的天然贸易优势的观点虽然可以解释17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英商对赴粤进行贸易的觊觎,却不能解释为何东印度公司早在18世纪20年代开始便考虑重回厦门,至洪任辉事件前数年更是继续向北,回到了多年未至的宁波。(12)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176, 296.其次,防范外夷、国家安全的考虑一说虽然颇有说服力且为史料所直接证实,却不免有混淆“虚构”(myth)与“现实”(reality)的嫌疑。(13)Lien-sheng Yang, “Historical Notes o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in John K.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2.研究历史上制度变迁的学者已经深刻地指出,新制度往往诞生于旧制度不可调和的危机之中,因为旧制度存在很大的惯性。制度中的人厌恶风险,而在旧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往往意味着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风险。(14)Wenkai 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England, Japan,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4-50.以这一观点视之,清廷以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有的对于番人的偏见来解释其针对西欧商人的贸易限制政策,更像是其大事化小的托辞。史家止步于当事人避重就轻的解释,不免停于表象而失于实质。再次,从同时期西北军事行动的角度虽然解释了1759年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然而,这一观点却无法解释长时段视野下一口通商政策何以在清廷西北边疆平定后又延续了近一个世纪。最后,也是与本文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点是,尽管有关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和粤海关两个问题的研究都非常丰富,然而,不仅这两个原本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问题被人为地分成两截,而且既有研究没有将对于粤海关既得利益集团的理解放在粤海关设置、税收的特殊性等背景下进行分析,更没有充分讨论这些充满制度韧性的特殊性在作为中西制度冲突的洪任辉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将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文献为基础,围绕促使18世纪中叶英商弃广州、向北开辟新通商口岸的粤海关的两项加征,即6%的进口货物加征和每船1950两规礼,重审洪任辉事件及此后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出台之由来。至18世纪中叶,粤海关新涌现出的这两项加征集中反映了清统治制度层面的两种困局。一方面,尽管雍正时期的火耗归公改革旨在将地方私征税收收归中央,然而在地方经费短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地方税负有增无减。洪任辉诉状中所集中控诉的每船1950两规礼即为火耗之外新的火耗之例证。另一方面,洪任辉事件还反映了粤海关与皇权的特殊联系,集中反映了中国帝制时期皇权根植并超越于官僚体系的特点;这种与皇权的特殊纽带关系使粤海关成为18世纪中叶清皇室财政扩张之有力推手。因此,与既往从清廷文献出发揣摩18世纪中叶清廷颁布一口通商政策的考量不同,本文将以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两项关税诉求为着眼点,即6%附征与1950两规费,指出清廷处理洪任辉事件的结果和随后一口通商政策的出台实为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之手段,反映的恰是18世纪以来清政权“高专制权力”和“低基层渗透”、世袭君主制和官僚制悖论的结合等根本制度层面的危机,一个清廷难以解决的制度困局。(15)“高专制权力”与“低基层渗透”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对于中央集权帝国政治结构特征的概念性总结。迈克尔·曼指出,受限于财力,起初依靠军事征服建立帝国的统治者终无法以直接控制的方式统治辽阔的疆域和远超于征服者的被征服人口,而不得不与被征服的地方精英建立一种“强制性的合作”关系(compulsory cooperation)。因此,帝国的中央集权和中央对地方社会的低程度渗透并非自相矛盾,而恰恰是历史上帝国中央集权制度一体之两面。世袭君主制和官僚制则出自马克斯·韦伯,前者指的是政府按照家长与家仆的关系进行组织,官员依附并效忠于皇帝,后者则指的是政府由领薪、专门化、职业化的官僚构成,一切有章可循,国家事务不以专制的君主意志为转移。不过,韦伯基于西方经验的概念总结并不能准确概括帝制时期中国的历史实际。正如黄宗智教授所说:“既不是简单的世袭君主制,也不是官僚制,而是两者的矛盾结合决定了帝制后期中国的国家特征”。参见: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5;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上述两对矛盾关系可作为阐释清廷在处理洪任辉事件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两个问题的概念框架。更具体地说,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清中央财政理性化改革后地方税关存在的火耗之外另有新的火耗的问题,以及粤海关与皇室超越官僚制的特殊利益纽带关系在英商税负日增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对应上述两对矛盾关系,而清廷对这一事件避重就轻的处置,则恰恰揭示出洪任辉事件实则触及了中华帝制晚期集权与分权、世袭制与官僚制之间悖论结合的根本矛盾,是为制度当权者所无法解决的制度困局。
二、6%附征与1950两规费之由来
清方档案中,洪任辉呈词中所述粤海关关口勒索的各项陋规总计每船“三千三、四百两不等”。然而,这些英商眼中的“勒索”(exaction),除时任粤海关监督的李永标家人、吏役勒索的二三百两“工食”外,其余3100余两均为“则例开载应征之项,并非李永标额外加征”。而应征的每船3100余两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进口、出口各项归公规礼银两,即每船番银1950两和樑期正银每船“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不等”。(16)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53—255页。清廷的回复不仅回避了洪任辉所要求免除的各项规礼的加和1950两,而且对洪任辉免除6%进口加征的请求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对策,可见清廷处理此事时避重就轻的态度。(17)洪任辉诉中有关免除加征的两点请求,参见: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p.67.以下,笔者将依次梳理洪任辉要求免除的6%进口货物加征和1950两的来龙去脉,以期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角度,揭示粤海关各项勒索背后清廷不可言说的秘密。
英属东印度公司于厦门建立在华通商的第一个据点(1676年)不久,英商便已经认识到,尽管名义上清廷官方税率不高(官方税率为6%,这个税率远低于同时期的英国),但由于官员薪俸微薄,“报酬、特权收益、规礼、勒索和贿赂”种类、数量异常繁多,实际税负远高于刊布税率。(18)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45、70、81.据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材料,1687年在厦门的英商首次被要求缴纳樑头银(Measurement Dues),官方关税之外的负担包括“规礼、小费、报酬和贿赂”,且存在重复征收的现象:除华商代缴的部分之外,还有外国商船自己支付的樑头银。(19)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80-81.
1700年,为了吸引英商到广州贸易,清廷免除了华商代缴的部分。然而,在那之后,英商便发现各类附征逐年加增,种类之繁多,令人应接不暇。(20)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00.初有“百分三”之税。(21)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89.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页。1704年9月25日,时任粤海关监督安泰离任前,又有所谓“百分四”之税附加于正税外。据东印度公司文献,这项新的附征是作为中间人的华商以非正式的方式支付给通事(Linguister)并由通事转送给监督的1%酬谢费,以及向华商索取的3%办事酬金的加和。(22)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40.粤海关监督名录,参见:梁廷枏辑:《粤海关志》(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72页。1718年,英商大班抵达广州后便向粤海关监督提出了免除4%进口加征、所有税款在缴纳樑头银时一并完纳的请求。尽管答应了其它条件,4%加征的请求还是被否决了。(23)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58.此后,来华的英商大班屡屡抗争,然而至1723年,4%的进口货物加征径直涨到了6%。英商大班坚持此项加征不在官方税则里,为前任监督之苛捐。而时任粤海关监督的那山则以此项加征“存在已久”为由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24)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75.
初至广州时,虽然1708年清廷新增6%附征,英商仍觉税负远低于其时之欧洲各国。(25)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06.然而,1723年免除6%进口货物加征的努力未果后,英商竟萌生了弃广州、重回厦门的打算,实则暗示此时英商在广州的实际税负尚不止6%一项。(26)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76.显然,像这样将家人属吏、通事私征的部分收归官有,对于英商来说,并非仅仅是税款易手的问题。事实上,在地方管理经费不足未有改观的情况下,陋规收为官有,而家人属吏、通事之私征依旧,英商的实际税负无异于名义附征额的两倍。1748年,据两广总督策楞奏报,长久以来,“规例条款碎繁”“有减免在前,仍行造入册内者;有续经奉文宽免,而未及删除者”,普遍存在“重复科征”的问题。(27)《粤海关志》(二),第560—561页。
1724年清廷推行火耗归公改革。该项改革虽意在限制地方私自摊派,然则仅从粤海关的情况来看,改革后英商的实际税负不降反升。据载,粤海关“向征外洋商船税正课之外,另有船规、分头担头耗羡等项银两”,从前系官吏“私收入己”。1726—1729年间,耗羡银两归公奏报解京。(28)《粤海关志》(二),第561页。然而,刊刻奏报的税则不仅仍出自书吏之手,不免“格外需索”,而且若干已经奏明刊入例册的规银,家人、巡役、水手等仍照收不误,实为“归公”之外又有“火耗”,“致累商民”之例证。(29)《粤海关志》(二),第563—564页。
1727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文献中首次提到了1950两规礼银。这一年六月到达广州的英商发现除了原征收的樑头银(Measurage)之外,每船在樑头银项下又多出了1950两的规礼银。(30)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85.到1730年,每船征收1950两规礼银已经成为惯例。(31)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99.按照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说法,1950两早在1704年便以规礼的形式零星存在。而从1727年开始,1950两作为规礼银的加和而成为正税,无论船只的大小、货物的重量,统一征收。(32)法国每船的规礼银数额为2050两,来自印度的港脚船每船缴纳1850两。 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68.洪任辉事件中免除此项加征的努力失败后,粤海关1950两规礼银的征收一直到1843年方被取缔。(33)[美]范岱克著:《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第6页。1743—1774年东印度公司船只在华贸易缴纳关税的项目和数额,参见: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5, Appendix AL.
对比东印度公司和清廷方面有关1950两的记载,进而可以看出粤海关规礼银合并归公后胥吏二次征收为己用的“重复科征”性质。1739年东印度公司的日志中记录下了1950两的明细。其中,外国船只入口和出口征缴收入皇帝金库的数额分别为1089.64两和516.561两,另有度量单位而产生的差异银9.359两;其余11项陋规,总计334.44两。(34)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68.而1759年,新柱等审明李永标各款的奏折中,洪任辉诉状所罗列的关口勒索的各项陋规,共计355.7两。(35)《史料旬刊》(一),第253页。洪任辉所控诉的粤海关私征陋规比此前“归公”规礼还略多出一些。
随后,新柱调查后所做出的结论也指向了粤海关“归公”规礼之外另有“私征”规礼的事实。新柱、李侍尧的奏折中罗列了外洋番船进口规礼共计30条,出口规礼共计38条,“头绪棼如,实属冗杂”。(36)《史料旬刊》(一),第337页。奏折中还揭示了与直省各关相比,粤海关陋规的特殊性:“直省各关从无规礼名色载入则例,独粤海关存有此名者,因从前此等陋规皆系官吏私收入己。自雍正四年起,管关巡抚及监督等节年奏报归公,遂同正税刊入例册,循行已久,自当仍旧征收。但存此规礼名色,在口人役难免无藉端需索情弊”。(37)《史料旬刊》(一),第337—338页。
清廷调查出的粤海关胥吏私收陋规的问题虽然客观上加重了东印度公司的税负,却非后者抗争的主要议题。18世纪前半叶,粤海关对外国商船的附征巧立名目,数额逐年加增。1728年8月,粤海关以“入于皇帝金库”(Emperor’s Treasury)为名,对刚入口的两艘英船进口或出口货物加征了10%的“缴送费”。(38)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89.这项附征引起了英商的强烈反对。(39)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92.在粤海关的苛政面前,英商一筹莫展,这也助长了粤海关监督无度加征的嚣张气焰。英商认为,这些原本出于“自愿”的规礼(Voluntary Gifts)如今变成了强制性的税款(Arbitrary and Annual Taxations),而且税无定法,监督可以对英商船上携带的任何物品征税,而不仅仅局限于商货。(40)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95.
附征名目之繁杂、头绪之纷乱实为其时包括英商在内的所有欧洲商人之观感。1732年,英、荷、法、比利时、瑞典的商人一道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其条款如下:1.请求粤海关官员澄清究竟哪些是正税;2.免除他们缴纳已久的6%附征;3.免除近3—4年附加的10%进出口货物税;4.免除买办通关所支付的部票金(Chop);5.免除每船1950两的规礼银。外商认为以上6%、10%和1950两均有悖于皇帝自己的意愿,不在官方税则之内,是为粤海关之私征。清廷官员避实就虚,欧洲商人的抗税斗争无果而终。(41)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11.
此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抗税此起彼伏,终于在1736年乾隆改元之始迫使清廷裁革了10%的“缴送费”。英商逐渐意识到免除全部附征的难度,于是在1733年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免除10%“缴送费”的努力上来。英方以当季的两艘英国商船并非来自印度的港脚船只(Country Ships)为由,要求免除10%“缴送费”。(42)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16.然而,10%的“缴送费”在随后的1734年征收依旧。173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再度提出免除10%“缴送费”的要求,监督百般刁难后,英商以北上厦门相威胁。(43)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33.英商的努力终于在1736年乾隆登基时有了转机。这一年的上谕里,乾隆帝承认10%“缴送费”与历来樑头银加船钞的旧例不符。至于加增“缴送”税银,尤非其“加惠远人之意”,下令“查照旧例按数裁减”。(44)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91页;据英属东印度公司编年史1734年的记载,10%的缴送费实则为16%。参见: 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23.然而,据英商所述,尽管乾隆谕旨,监督仍然执意收取1736年的“缴送”银,裁减该项附征从下一年开始执行。此外,办理该项裁减时,官商以办事费为名,向英商索要6000两礼金。(45)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250-252.
然而,尽管英商奋力抗争,6%附征和1950两却保留了下来,是为1759年洪任辉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如前所述,6%附征实源自1704年的4%附征,于1722年增至6%;1950两自1727年首次出现在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文献中,尤其是1730年成为惯例,此后与6%加征一道,成为历次英商抗税斗争中的主要议题。
173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将抗争的焦点放在了1950两规费的免除上,并以船只推迟不进港、去别处贸易相威胁。粤海关监督则声称免除1950两规礼银非其权力所能掌控,最终以免除其时入口的英商等额税负作为权宜之计。(46)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23.1736年8月,英、法、荷商人在广州再度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抗议10%“缴送费”和1950两规礼。11月,乾隆帝谕令抵达广州,同意免除10%“缴送费”和1950两规礼。然而,英商大班很快意识到,减免远非一纸谕令那么简单。(47)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49.粤海关监督先是将实施谕令里的减免推迟到第二年。而监督已经心领神会谕令的意图不过是一种怀柔远人的姿态,并不在意粤海关关税的细节。(48)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50.1737年,当英商试图借着乾隆帝撤销10%“缴送费”的契机,进而免缴6%附征和1950两规礼时,粤海关监督却以前一年已为其免除10%“缴送费”为藉口而拒绝了。(49)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60.鉴于广州税负的沉重,1744年,在英属东印度公司自厦门迁至广州进行贸易的40年后,英商首次再度造访厦门。(50)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4.由于1950两是按船征收,这对于货物少、吨位低的船只尤其不利。由于英商的贿赂利诱,1750年10月,粤海关监督同意免除True Briton号1950两的规礼银,条件是豁免的英商必须保守这一秘密,以防其它欧洲商船提出同样的诉求。(51)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5, pp.7-8.
1750年减免1950两规礼仅为特例。175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其在广州入口的商船依旧缴纳,1950两已成为惯例。(52)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5, pp.22、46.1755年,英商已经开始考虑北上宁波贸易:一方面广州苛捐杂税日益繁重,另一方面,宁波更靠近英商所需的茶叶和丝绸货品产地。(53)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5, p.25.这与清廷文献所记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有往宁波贸易之红毛番船一只”“六月又到有一只”“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屡有红毛夷船来浙”,恰相吻合。(54)《史料旬刊》(二),第129页;《史料旬刊》(一),第241、750页。据广东巡抚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奏报,“乾隆十九年共到洋船二十七只,乾隆二十年共到洋船二十二只,乾隆二十一年共到洋船一十五只,乾隆二十二年共到洋船七只”。由于粤海关“每年所收税银,惟视洋船之多寡以定盈绌”,洋船递年减少,以致粤海关盈余税银减收严重。(55)《史料旬刊》(一),第206页。1757年,清廷照粤海关则例,将浙海关税提高一倍,企图以浙江高税额、“不禁之禁”的手段逼迫英商重回广州。(56)《粤海关志》(二),第567页;[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103页。不久,又向英商申明:“浙海已奉禁开港不准贸易”。(57)《史料旬刊》(一),第193页。一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免掉的6%附征和1950两,而另一边则是“以不禁为禁”的浙海关,最终逼迫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委派洪任辉绕过粤海关和浙海关,向北探寻新的通商口岸。(58)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68.
作为洪任辉事件的直接诱因,6%附征和1950两规费之难以免除实则与这两项加征的特殊性质有关,而对这一点,清廷文献始终讳莫如深。借助英属东印度公司文献,我们得以了解6%附征和1950两背后不可言说的秘密。早在1728年,英商便从行商处得知,6%附征与1950两之不可免除,是由于这些税款“入于皇帝之金库”。(59)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189.1734年,英商又从粤海关监督处得知,免除1950两非其职权范围之内。(60)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223.1735年,粤海关监督声称,1950两的免除,他甚至“不敢启口”,因为这些加征最终归于皇帝金库,故而免除这些加征的努力都将是徒劳。(61)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232-233.1757年,英商已经意识到,无论他们如何抗争,1950两都无法免除,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都入于皇帝的金库。(62)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57.1759年,监督特别强调了1950两的特殊性,这是英商所有诉求中唯一不能向皇帝禀告的部分。(63)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81.洪任辉事件后的1762年,粤海关给英商的回复中再度重申,1950两规礼和6%的出口加征均为皇室金库(Royal Treasury)收入,不能做任何更改。(64)H.B.Mors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105.
英商数十年间屡次抗争6%附征与1950两的免除而未果,实为洪任辉事件最为直接的诱因。这两项加征不仅反映了火耗归公改革后地方经费仍然短少、税负加倍的问题,而且还折射出粤海关与皇权的特殊关系,反映的恰是清统治“高度中央集权”和“低度渗透基层”之根本制度困境。
无怪乎清廷对洪任辉事件的处理采取的是避重就轻、息事宁人的态度。1759年,新任粤海关监督新柱与两广总督李侍尧,向英商声明了清廷官方对于洪任辉所控诉的粤海关加征税款的处理决定:既往陋规是由于前任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吏役收取陋规,故免去“一切陋规”,尽管洪任辉的实际诉求是免去6%附征和1950两,尤其是与陋规相关的1950两,而后者实为清廷已载入则例的正税。(65)《史料旬刊》(一),第251、343页。
三、乾隆时期皇室财政的扩张和粤海关
根源于满族早期社会的包衣组织,随着满族君主制的建立,皇属包衣牛录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的制度化改革,内务府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国家官僚政府之外、不受六部掌控、专事皇家事务管理、且完全由皇帝自主任命官员的皇家私属财政部门。(66)Jonathan D.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2.内库即皇帝的荷包,则有着独立的收入来源和支出体系。清代早中期,皇家的私库收入主要包括内务府皇庄及房租收入,人参、皮货的专卖,当铺生息,关税盈余,官员进献、议罚、籍没之财产,岁贡、各国贡物,及来自户部的拨款。(67)赖惠敏:《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年12月总第28期,第138页;祁美琴:《清代内务府》,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皇室的支出则包括皇室日用,内务府衙门办公费、官员差役人员薪俸,宫殿、苑囿、陵寝、寺庙的修缮,祭祀、筵宴、节庆及出巡,赏赐及抚恤等。(68)Preston Torbert,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23-125;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24页;祁美琴:《清代内务府》,第148—163页。虽然,与官僚政府的收入相比,皇室金库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内务府的存在为皇室干预国家事务提供了制度上的自主性。尤其随着统一战争结束、清廷成为全国性政权,18世纪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内务府赋予皇权的非正式渠道成为皇权控制国家的重要手段。
康熙末年,通过派遣包衣充任获利最丰的税关监督,内务府开始控制原本由户部奏销的部分财政收入,开启了皇室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干预。清代早期,负责征税的各税关监督本是由汉人进士和各部满洲郎官中选取。至1685年前后,内务府包衣开始进入税务行政领域。1686年,内务府官员桑格被派往江苏的浒墅关。正是在桑格任内,“盈余”作为结算的一个项目开始出现于关税账目。终清一世,海关和内地关税盈余以“余银”的名目成为内务府税收的一部分。(69)罗丽达:《清初国家财政利益上的宫府之争及赵申乔的遭遇》,载《新史学》6卷3期(1995年9月),第31页。尽管雍正元年大部分税关交还地方管理,但内务府仍然获得了崇文门税关的监督权。乾隆时期,大部分在雍正朝交由地方督抚监管的税关又重新回到内务府的掌控。内务府通过派遣官差与笔贴士,控制了户部32处税关中24处的管理权。(70)何本方:《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2月,第4—5页。户部所属的税关中岁收较多的缺分全都由内务府包衣垄断了。(71)陈国栋:《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利益分配(1684—1842)——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载《食货月刊》12(1),1982年,第25页。
其中,内务府对税关的影响尤以粤海关为大。原本由两广总督兼任的粤海关监督一职,自1751年开始便由内务府包衣垄断。(72)陈国栋:《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利益分配(1684—1842)——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第20页。此后,几乎所有粤海关监督均为皇室的包衣奴仆。(73)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由于与内务府的密切联系,粤海关承担了诸多为皇室金库敛财的职责。粤海关每年以三万两为度,办进贡物四次,分别为“年贡”“灯贡”“端贡”与“万寿贡”,分别在新年、元宵节、端午节及皇帝的生日时办进。(74)陈国栋:《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利益分配(1684—1842)——粤海关监督的角色与功能》,第22页。粤海关还为内务府采办贡品,传办方物,代为出售人参、东珠、玉石等物。贡品多为广东特产及新奇的舶来品,比如紫檀木器、玻璃灯屏、金银丝线、鼻烟、珐琅器、洋钟等。(75)何本方:《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第6页。
英属东印度也注意到了乾隆年间粤海关监督职权范围的增大,与粤海关针对外商的各项附征的增加,有着密切的联系。雍正元年,曾有除崇文门外,“各关税务俱交地方官管理”。(76)《清史稿》卷125,《食货》6,第3677页。英商注意到,由于有朝廷撑腰,粤海关监督的权力日渐增长,渐渐超出了两广总督的控制范围。(77)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1, pp.182、250.英商还注意到,监督肩负着为皇帝在广州办贡的职责,而行商正是监督采办贡品的工具。(78)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13.1834年鸦片战争前,一本介绍广州城的小册子也揭示出粤海关监督与内务府的密切联系:“监督来自皇室的成员,由皇帝直接任命”。(79)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4, p.29.
尤其是乾隆时期,在“盈余银”“额外盈余银”的名号下,榷关的各项加征成为推高这一时期皇室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粤海关之税课“有正额,有盈余”。 经过康熙年间的两次题减,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粤海关正额从9万多两下降到了4万余两,而乾隆初年,仅盈余银一项便高达85万余两。(80)《粤海关志》(二),第971页。乾隆十四年(1749),要求不仅正额需要完纳,而且还要上缴盈余,盈余以雍正十三年(1735)为准,作为比较。(81)《粤海关志》(二),第991页。一时间盈余银数额骤降至18万余两。由于这种固定盈余银的方式既无法实现督促作用,又不能使中央的税收得益于日渐增长的对外贸易,乾隆十九年,又恢复了与上年比较的做法。(82)戴和:《清代粤海关税收的考核与报解制度述论》,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6页。
虽然对盈余银报解数额的要求几经变迁,长久以来,盈余即是正课。盈余银短征,监督不仅面临“扣俸”,而且还要“依限完缴”,“限满不完,即著革职监追。如监追后仍复不完,永远监追,其子孙代赔之项,亦令依限完纳”。直至倾家荡产“扣抵请款”。(83)《粤海关志》(二),第973-974页。尤其是1754年盈余银数额不能少于上年的规定,更是对粤海关税负的升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盈余银两有较上年短少者,需向户部奏报“短少缘由”。(84)《粤海关志》(二),第981页。各税关银两需“奏报盈余之后方准考核具题”。(85)《粤海关志》(二),第986页。由于盈余银的短征会直接威胁到监督的俸禄和晋升,盈余银水涨船高,成为商民税负增高的主要诱因。尽管部分盈余银输往户部,然而,正是从盈余银中粤海关支销了内务府的备贡银。这一始于乾隆三年(1738)的经费项,每年以3万两为基准。乾隆二十九年(1764),办贡经费增长的条件下,办贡经费每年又增加了2.5万两。(86)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第101页。
乾隆时期,一些内务府包衣充任监督、盐政肥缺的地方,又出现了所谓“额外盈余”银。比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长芦盐政西宁便奏称,在正额盈余银两解交户部后,“尚有盈余银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二两一钱三分四厘”的“额外盈余银”解送到京由圆明园查收。(87)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奏为长芦盐政呈解天津关正额盈余银两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卷号: 05-0282-035。浙海关、天津关均先后有额外盈余银解交内务府的记录。(88)何本方:《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第7页。
乾隆年间,粤海关税入逐年加增。乾隆六年(1741)税银为29万6千余两。乾隆七年(1742)税银为31万7千余两。(89)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乾隆十四年(1749)税银为46万6千余两。(90)粤海关博物馆编:《粤海关历史档案资料辑要(1685—194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7页。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粤海关税银高达117万2千余两,几为乾隆初年的四倍。(91)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第10页。乾隆年间,粤海关税入的猛增,显然与此一时期新征税项目的加增有关。乾隆年间,税关监督遭到抄家、不能全身而退的比例之高,揭示出作为“肥缺”的粤海关监督完纳税额的压力之大。粤海关之税收主要来源于外国商船。以1757年一只英国商船为例:总货物税为2565两,可见1950两规礼所占税负比例之高。(92)H.B.Morse,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5, p.59.18世纪中叶,无怪乎英商的抗税斗争达到高潮。在抗税未果后又祭出了派遣洪任辉强行北上投递诉状的险策。
四、结语
通过梳理洪任辉诉状中6%附征和1950两规礼的由来和演变,本文揭示了既往洪任辉事件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在既有传统国家统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经费的控制仍然有限,中央财政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实则加重了地方的税负。1950两规礼便是火耗归公改革后,粤海关归公火耗之外另有火耗一例证。另一方面,6%附征和1950两规费的不可言说性还揭示了皇权在依托于官僚制的同时,凌驾于官僚制之上的特权。(93)Philip A.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88; Philip C.C.Huang,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而清廷对洪任辉事件的处理则恰好印证了洪任辉事件牵涉的清廷制度的问题之深,以至于清廷采取息事宁人、避重就轻的态度。由此可见,既往研究仅就清廷档案所做出的防范夷民勾结、不使宁波变为第二个澳门、减少基督教的威胁等观点,难免有以当事人避重就轻的说辞为依据、反果为因的嫌疑。一言以蔽之,洪任辉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最后的结果都一以贯之地反映了18世纪中叶清代传统国家治理的根本制度性危机。
近年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学者已经深刻地指出,当遇到挑战时,旧制度有诸多自我调节机制以确保旧制度能够渡过难关。正是因为这些自我调节机制的存在,旧制度得以长期维系;在这一框架下,危机或挑战没有削弱、反倒是强化了旧制度的韧性。(94)He, 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pp.24-36.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尽管其诉求涉及清统治制度层面的顽疾,但洪任辉事件并不具有对清政权造成系统性危机的影响。(95)在孔飞力看来,鸦片战争也远非中国传统国家衰落瓦解的标志,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的崩坏不应该早于太平天国运动结束的1864年。参见: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10.洪任辉事件之后,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开始全面管制外商来华贸易,使广州一口通商的制度得以固化。作为外来挑战的洪任辉事件不仅未能迫使清廷做出开放通商、关税上的让步,反倒固化了清廷既有的以政府高度干预为特征的保护性通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