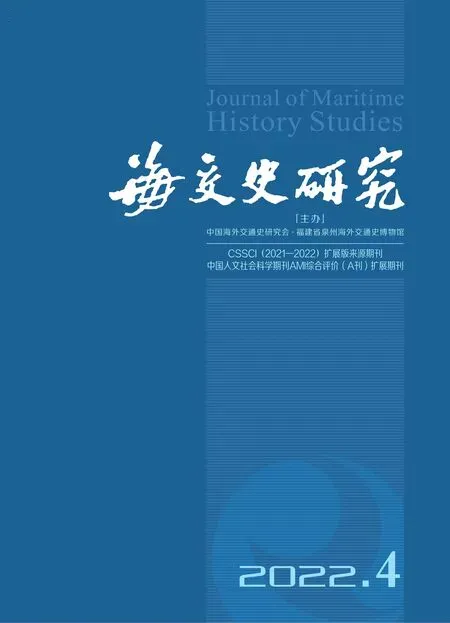布琮任:《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
2022-10-08黄泓熙,陈贤波
近年来,在欧美学界“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下,清朝国家治理的“多元性”和“帝国性”已经日益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而,不管对“新清史”持有什么样的评价意见,相关研究所投注的地理空间,更多地放在内亚大陆而非海疆世界,相对忽视皇朝的海洋政策、关怀和意识,应是全面理解清帝国统治体系的一大缺失。这也就不难理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青年学者布琮任(Ronald C. Po)的新著《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以下简称《海不扬波》)开宗明义提出“海上新清史”的必要性,认为“与其不断强调清皇朝是一个内亚皇朝,倒不如把它理解成一个执意平衡中亚边陲和海域疆界的大帝国”(第37页)。
布琮任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其博士学位论文改写后以The Blue Frontier: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为题于2018年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探讨的主题便是18世纪清朝的海疆治理思想和举措,已初步显现出作者有意对话和修正“新清史”的学术意识。相对而言,《海不扬波》从清朝测绘海疆到巡防造船,进而从《海错图》追寻海物、鱼翅的生命历史,再到清人渡海的诗文,更类似于作者的论文随笔集。全书正文除“前言”外,收录了6篇主题文章,作者自谦为“研读海洋史时的一些观察和心得”(第44页),但旨在“在可见的学术成果上补充、重构和提倡一些新看法,务以开拓海洋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第236页)。
《海不扬波》的“前言”以《海上新清史的探索与可能》为题,表达了作者对海洋史研究如何有助于重建清朝帝国治理架构的认识。作者指出,清代中国在欧美列强纷起进侵之前,并非漠视海疆的“陆权国家”,问题在于过去的研究忽略它“在十八世纪的筹海方略”(第31页),18世纪的清朝在海洋上同样表现出“帝国性”。“新清史”的重点,一方面强调清朝的“多元性”,即清皇朝之所以称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是因为满人技巧性地运用多种策略,成功治理不同边疆种群和以汉人为核心的文化圈,一方面强调其“帝国性”的开疆拓土历史,以至于建立起幅员辽阔的亚洲国家。不管如何,相关研究均疏于考察清朝的海疆经略,“特别在十八世纪的中、后期,清政府基本上没有忽略海洋作为一个促进交流贸易的纽带(frontier)角色,这种管治取径与看待中亚丝路圈的重要性大致相同”(第36—37页)。故此,作者所提倡的“海上新清史”希望呈现的便是海域于清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或可称之为“海洋帝国性”(第43页)。
在“前言”之后,本书的第一个主题是“测绘海疆——十八世纪清代有关内海与外洋的论述”,主要探讨的是清朝海域空间的认知。相较于明代地图,清代绘图质量更高,描述更加准确且详细,很多绘有海洋的地图已经明确地标明“内海”和“外洋”的范围。作者指出,清朝区分“内海外洋”并无统一客观的界定标准,不同于西方海权思想观念下的海域认知,了解清朝的内外洋观念务必从文献的具体情景出发。综合而言,作者提出以“主观且微观”“从大统治出发的宏观角度”“海军巡哨的视角”“地方管治的角度”四种理解方式进行解读。在“主观且微观”的视角下,内外洋是某些海洋著作撰述人的主观划分,这种划分标准可能基于撰者的认知边界,或者心理距离的远近,相对模糊。“大统治的宏观角度”相比前者则清晰明确得多,皇朝管辖之内便是内海,中央控制不到或者无意控制的便是外洋;“海军巡哨的视角”则是统治的微观角度,凡海盗、贼匪等反动势力的藏身之处便标注为“外洋”,此视角基本没有超出内海的范围。“地方管治角度”所提供的视角则展示了中央为了避免地方官对边界事物相互推诿而进行的细致划分。
第二个主题是“伐木造船——康雍年间在台的战舰修造与樟木采办”。作者指出,相较于明代修船则例,清代专门制定了详细的船只修建指导细则。为了保障战船建造的物资条件,清廷设有对应的军工料馆负责采购原料。通过地方志、外国公使记述、大臣奏疏等材料,作者梳理了清代台湾樟木产业和清朝在台伐木造船的沿革。可知在清代战船制造格局中,由于海盗猖獗和海防海巡的开展刺激着战船制造的需求,地理和物产条件优越的台湾逐渐被统治者重视,成为重要的造船原料供应地,并相继开办新造船厂。由于台湾当地大量的樟木位于深林之中,砍伐行为屡屡受到原住民抵制。雍正时期朝廷制定约束伐木人员的法令,避免与原住民出现更多冲突,促进了台湾伐木造船业的整体发展。
本书第三个主题是“建威消萌——清代东北的海洋军事化”,主要是针对学术界有关清代海洋史在区域上侧重于南部沿海而发的。在后金时代,明将毛文龙占领皮岛并且频繁骚扰后金的后方,成为当时明代牵制后金军队重要的军事力量。这使得后金统治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后方的这块战略要地,因此在入关前清朝就意识到东北海域的战略地位。几番波折拿下皮岛后,高度重视东北海域的清政府便在此处布下重防。由此入手,作者首先介绍了该片水域的山东水师、盛京水师、直隶水师所处的地理情况与其清初的发展沿革,指出由于满人不善水战,水师中的满族精锐逐步被撤换,东北水师大部分的管理职务与主要成员基本由汉族的将领和士兵充任。黄渤海海域的水师都大致经历了顺治、康熙时期的筹建开拓期,雍正及乾隆前期的巩固期,以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海防策略的转变以及海防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变革的转型期。作者还发现,水师中存在多种海神信仰,神庙中供奉的内容不仅涉及佛、道教中有关海洋的神明,还有一些被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神灵。这些神灵不仅仅在海上商业和民间渔、航业等生计上有着重要地位,也为清代水师的运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仰资源。
第四个主题聚焦于清宫藏海物图绘——《海错图》,探讨的是“清代学人对海洋物种的想象与书写”。《海错图》全书4册,分藏于北京和台北故宫,其学术价值近年来备受研究者关注。作者指出,《海错图》是中国古代海洋博物学的一朵奇葩,有其深刻且延续的发展渊源,其内容形式可与唐代吕元守的《蟹谱十二种》、明代赵之谦的《异鱼图》、杨慎的《异鱼图赞》、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等著作相比照,其思想文化则表现了在中国古代存在上千年的“化生说”以及“药食同源”等传统思想。作者将法国学者龙德莱(Guillaume Rondelet)1558年出版的《鱼类历史全志》这部欧洲海洋博物学奠基之作与《海错图》进行一番比较,认为用某个时期中极具西方色彩的“博物”“科学”等概念对漫长的中国历史进行总结,以及西欧人具有“海洋性”而中国人具有“大陆性”的传统观点,都有失偏颇。从今天的学科视野来看,《海错图》所涉及的学科非常广泛,除了能够为海洋史以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材料,也是食物学、食材史领域的重要著作,“《海错图》的成书,理应是一个结合海洋博物学、饮食文化和市场化的结果”(第166页)。
第五个主题探讨的是食材史中鱼翅的物质文化史。时至今日鱼翅依旧是一种较为名贵的食材,其长盛不衰的原因不仅仅是生态因素造成的稀缺,也有各个时代上层阶层以及文人为之赋予的社会文化性。作者指出,在现有文献中鲨鱼鱼翅扮演珍稀菜肴的角色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宫廷。到了明代,消费鱼翅成为一种追求身份的潮流,明中叶就已出现从国外进口鱼翅的情况。清代对鱼翅的记载更加丰富,如袁枚的《随园食单》、李代楠的《醒园录》等文人作品中,对于鱼翅的食用、药用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通过梳理中国人食用鱼翅的发展过程,作者意在将鱼翅放于“物质文化史”“中国饮食史”“人海关系”“奢华消费”等框架下讨论,认为鱼翅“不只是鲨鱼的翼鳍,而是一种富含另一种象征意义的海洋珍品”(第204页),对于食用者来说,“隐喻着一种征服海上霸王的感觉”(第205页)。
最后一个主题探讨盛清时代的海洋诗文,选取的主要是由福建航向台湾的渡海诗文作品。作者以17世纪正值黄金时代的荷兰风格鲜明的“海洋画作”作为引入,认为海洋在中国诗文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众多的含义,从诗文中可观察文人在渡海过程中经历变化无常,生发无尽感悟。除了描述一路所见和所感以外,还有一些托物言志的诗文“是中央透过士大夫群,彰展其帝国性的一种微管道”(第229页),也能瞥见当时的文人普遍相信海与风都由对应的神灵掌管,由此可见有关海神、风母等原始信仰在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根深蒂固。
概括来说,《海不扬波》一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取径,即更加注重王朝国家视角下的海洋经略与一般学人、普罗大众的海洋活动两者之间的平衡,从而引入诸多物质文化史新议题,拓宽了海洋史研究的视域。在行文上,作者有意让该书在行文和注释方面“没有依从一贯的学术惯例”(第229页),这使得全书的语言更为生动流畅,不至于如一般学术论文严肃枯燥。在行文架构安排上,作者每于一个主题开篇都由某一相关事物引入,旁征博引,既展示了作者较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也有助于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受众。不过,由于不依照严格的学术惯例,部分引文出处失于简略缺失,容易产生误会,亦在情理之中。至于对相关主题内容的分析,往往浅尝辄止。
稍让人遗憾或可进一步讨论者有二。本书所揭橥的“海上新清史”主要对话的是欧美学界的“新清史”研究潮流,但失于对近数十年来有关清代海疆治理研究成果的细致考察和关照。诚然,过去有关清代中国史的讨论明显带有以“陆地”为中心的观察视角,但学者对海疆、海域、海贸、海上人群、海洋信仰、海洋物种等问题的研究已经累积了数量可观、细致深入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多不在“新清史”研究的范畴之下,自然亦非“新清史”研究者对话的对象,但同样揭示出清朝国家治理在陆地之外的海洋面向。经过二三十年来的努力,说时下的清代中国史研究忽视“海洋”的面向,未免言过其实。若果如此,本书旨在扭转“新清史”的偏差而追求的“研究新意”可能就大打折扣了。此其一。
二是本书相关具体议题,如对聂璜《海错图》的研究,同样失于对话已有的研究成果。尽管作者也意识到该图绘背后的“博物学”脉络,强调不宜简单地进行中西比较,但须知《海错图》中许多海洋物种知识,正是源于西人东来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全球史背景下的“知识环流”。由此入手,或更能引出清代中国之于“亚洲海洋”甚至“全球海洋”的互动缠结。又如本书虽也花了很大篇幅论说《海错图》表达的中国古代“化生”思想,但须知北京故宫博物院2014年影印出版的《海错图》中已收录有王祖望先生《<海错图>物种考证纪要》专节论述“《海错图》是一部比较集中反映中国古代‘化生说’生命观的图志”(参见《清宫海错图》,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