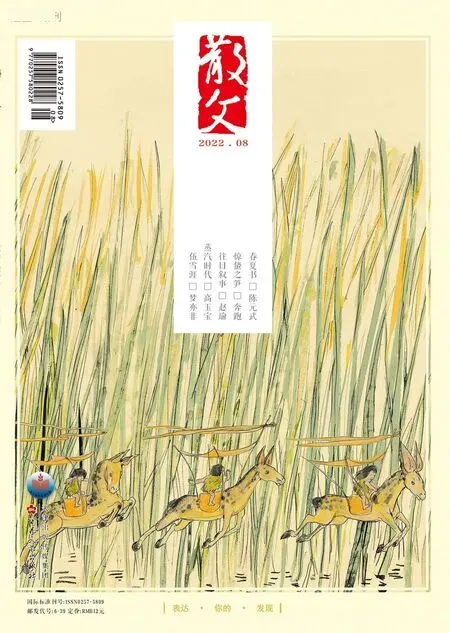人文的湖水
2022-10-05许超
许超
每周,我都会选择一天,去绕湖行走,通常是周末的早晨,那时候,身边会有很多晨跑者,但我不跑,跑步会止于身体,而散步于湖,会和湖形成某种默契,会有无声的对话。
一个人和一个湖的对话,其实很实在。就像鱼在湖里游,就像水草在湖底摇曳。一个湖,在人为的充满秩序的世界,仍然可以游刃有余地传递自然的野性,这是独特的存在主义。我好像瞬间明白了徐志摩和他的康桥。关键就是那柔波,一瞬间,物和人就建立了联系,而且是深刻的恒定的物我相合的联系。


下午四点钟左右,看外面雨停了,执意去看湖。岸边的楝树,在风中摇晃着楝果,而楝树形神兼备的时候,应该是四月,站在楝树下,紫色的楝花,形成吉光片羽的氛围,人会有难以言传的奇妙的满足。

湖边的蓼,好像丝毫没有受到气温骤降的影响,蓼花坚定地开。送别的人会把它们写在诗里,我甚至觉得,写出“枫叶荻花秋瑟瑟”的白居易,如果是在白天,他一定会换写蓼花。枫叶荻花在深秋会显得形销骨立,而蓼花虽然低矮,却给予人向上的感觉。
再力花也是。我常常疑惑,也是不满——如此美丽的植物,名字怎么会如此常俗?每一次路过,我都会叹息这个名字如何配得上它。不如就命名为“桨花”吧,得形得神,桂棹兮兰桨,渡万千目遇之人。
人在湖边走,冷风冷雨相伴,思维没有办法活跃,但是会显得纯粹,许多时候,纯粹,就是一种力量,能够使人获得某种本源性的启示,如同窄门。这是《路加福音》里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窄,是另一种纯粹,是另一种冷。冷和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激励。
有一周多没来看湖,觉得自己身上多了怨气,甚至是戾气。
不要起誓。在湖的身边如果一定要抒情,那也只能借用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我听到我的灵魂在喊我。而他的灵魂是——朱丽叶。是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抒情就来自莎翁,莎翁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抒情诗人。歌德说他翻开第一页,从此就是莎士比亚的人了。我觉得我也是。相对于其他抒情的苍白、庸俗和虚假,莎翁的抒情是多么多彩、独特和真诚啊!
雨大了起来,游湖的人纷纷撑起雨伞,而我要去菜场,有一些菜,在喊我。
只是想念,十一月月末的清晨,来见湖。
六道木正开花,花色洁白,花形如檐铃,这是一只只低悬在大地屋檐下的铃铛。石楠在每日霜露的浸染中,叶片愈加红艳。而高处的栾树,已经卸下周身的环佩,很少有人再像秋天那样深情地望向它,如果美太恣肆,就一定很难持久吗?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阿姨从我身边快走而过,我听到她的手机里传出一句歌词:“如果爱情不能再来。”呵呵,如果爱情不能再来……你就到湖边等。临水自照,一个人,也许会慢慢学会爱上自己。
荻和芦苇在岸边比邻而居,它们将絮穗高扬如旗帜。湖边有三位工人在修剪蔷薇,湖中有九条船,船上有十一位工人,在打捞水草。
阳光已经打在远处的明城墙上,新的一天,我们不是要去和生活战斗,而是要学会如何在生活里生活。
最近在湖边,也许是因为气温低,会常常想起白居易的那句“心忧炭贱愿天寒”,只此一句,就可见诗人心灵的广厦,如果这广厦里不是住着“仁慈和悲悯”,白乐天又怎能如此伟大地传递出卖炭翁的心理呢?
去上班,因为太早,一路上几乎只有清洁工,他们将梧桐的叶子扫到路旁。尽管有时也会被偶过的车辆携风旋起,但是叶子已经飞不太远。居然会在龙蟠中路遇到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有些吃力,车斗里装满了煤球,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唐朝的那位卖炭翁。在他拐弯的时候,一个煤球从车斗里滚了出来,也许是因为滚落的声音小,也许是因为老人耳背,他没有发现,我也没有来得及提醒,那样的一个煤球,就成了这座城市里孤独的煤球。
一路上都在想煤球,我上一次看到煤球是什么时候?还是小时候吧,父亲在院子里做煤球、蜂窝煤,我在旁边打下手,一个上午就能打半院子的煤球,然后让煤球接受太阳暴晒,晒结实了,再把煤球摞在厨房的拐角。看着那一摞摞煤球,我会生起不小的满足感,仿佛看到它们在煤炉里燃出光,看到锅里的肉和白菜豆腐们一起沸腾,那飘出的香味真是太馋人。
父亲和母亲早已迁居进城,他们的大儿子为他们提供了宜人的小区,住上了很大的房子,但是,他们的厨房里好像还是有煤炉,以及为数不多的煤球。我甚至认为,有煤炉的厨房,才是完整的厨房。那里有耐心,有对时间的耐心,有对食材成为美味的耐心。煤炉之上飘荡的香味,太诱人,太令人回想。
我不知道今天早晨所看到的那些煤球的去处,它们当然会制造出火与光,但是它们能不能燃烧出温情与记忆?包括那一个失落的煤球,在城市,在日渐明朗的城市,它那么黑,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认出它了吧。
所有的事物都是湖水的身外之物,包括湖水本身。在湖边,我只能想起,而且是又一次想起三十七岁的宋人苏舜钦。那一年,他获罪免官,面对浩渺的太湖水写下了《水调歌头·沧浪亭》。
下午的第一节课,学生在昏睡中醒来,其实,这样的状态很适合走进这首词,在迷茫中顿悟,在坚定中彷徨。有一只臭虫在教室的窗帘上,引起了他们的骚动,臭虫或静或动,静一会儿动一会儿,那只臭虫的学名叫柑橘格蝽,用手捏它,会有刺鼻的臭气,所以,我一般是用木棒夹住它,然后连木棒一起扔掉。当我知道它学名的时候,很是纳闷——怎么用了那么美好的词去修饰它?
“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是这首词下阕的最后两句。“刺棹”,就是划船。刺棹,应该是苏舜钦的独创,着一“刺”字,情绪全出。我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来说这首词,而且只是练习题里的词,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们,今年,我也是三十七岁。
这个年龄,很多时候都是处在“无语看波澜”的状态。尤其是面对湖水时,面对湖水的黄昏时分,当湖旁“夜上海”的灯光亮起,你和诸事隔离,波澜自惊,这种无语也是欢欣。那个时候,三十七岁的苏舜钦,在沧浪亭,他看到的湖水是清还是浊呢?
晨起翻书,刚好是一篇好文章,文字虽长,但是用小火熬出来的,就像熬米粥,每一粒米都有清晰的翻滚,都有自己的姿态,米与米之间有着悠长的气息。文字能做到这样,真是有难度,尤其是成名之后,还能保持一贯的步调,不像有些人,有了声名之后,就开始火急火燎,方寸都乱了。
六点十分的时候出小区,小区门旁的台阶上摆了一排菜,卖菜的老奶奶几乎每个周末的早晨都出现,她固定地蹲在那些青菜、萝卜、菠菜和芹菜前。青菜是两元一斤,芹菜是七元一斤,她说完芹菜的价格,还补了一句“上土的”。土和水真是好,你看,芹菜可以长在土里,也可以长在水里,长在水里的叫水芹菜。
风有些凉,凉中见爽。湖面幽微,有不能辨别的鸟在湖面上练习飞翔,湖水中的鸟影是模糊的。唐朝的杜牧见过水中清澈的鸟影,他在《九日齐山登高》的首句就是:江涵秋影雁初飞。大江包含了秋色的影子,那大雁的影子也一定会投射在江水中吧。同样,两百年之后,北宋的王安石,站在太湖恬亭上,看到了“水涵幽树鸟相依”,相依之鸟在镜子里,诗人对镜,更是孤人。
柳叶降落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地面上已经落了一层,有些飘到了湖里。三只麻鸭“嘎嘎嘎”地在草丛中觅食,因为距离岸边近,你能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慌张急切以及窃喜。
去买点早餐,小豆要吃煎饺,大豆要吃一个菜包一个肉包,还要一杯豆浆,这些都是昨天晚上订好的。我要循湖往回走,在湖腰处,我将遇到大片的铜钱草。
在湖边,我常常想到一个人,王荆公。
清溪路尽头,右转至海军指挥学院,即是半山园,半山居士晚年的居所。隔了一千年的时间,而在空间上,我们仅仅相距一千米。这也是我常常想起他的重要原因。我会感觉我现在走过的地方,在一千年前,他也骑驴驻留过,我们在某个奇妙的层面,有过重叠。
以前读介甫先生的诗文,说实话,少有共鸣,总觉得他理性多而感性不足,太刻板,太执拗了,知识的渊深反而阻滞了才情的挥洒。
毕竟,政治改革的风雨不同于生活中的风雨。比如,这两天,南京人都在等雪,好像雪不来,就感觉被雪欺骗,感情上无法接受。而雪不来,一定有它的理由。我们都在想雪,这就是感性的生活。所以,我喜欢拗相公从江宁离开,及至叶落江宁的时段。
钟山只隔数重山。两行排闼送青来。我站在湖边,抬眼可望紫金山。紫金山就是原来的钟山,它还是千年前的样子吗? 半个月,断断续续读完《王安石传》,我发现,我们起码有两个同样的优点:一是物质贫乏,时忧柴米油盐;二是固执,非我意者,皆睥睨之。
是耶非耶,外面似乎不在飘雪,而有雨滴声从檐而落。
春天应该是真的回来了,身旁的万物都在谋划。
窗外传来沙哑而又清脆的声音:“乌龟壳、老鳖盖、长头发、旧家电……”声音渐远,然后又变得清晰。根据经验,收购者应该是从13幢和15幢楼之间的那条略显狭窄的通道折了回来,在那阳光少驻的地方,他一定加快了速度。
毕竟阳光普照,带着暖意,那声音像是破土破雪而来,所以有沙哑,也有清脆。春天,在光线上写满了新意,那些旧物事要被陆续收藏。
昨晚,有一个旧群被通知解散,大家有所不舍,还有人喊:解散了,我以后到哪里卖油!油,是菜籽油,是她父母经营的小油坊的作品。早晨醒来,发现群主邀请我加入新群,群只是改了名字,可能也有极个别的同志不再被邀请,也有——比如我的同事梁国元,即使被邀请,他也无法应答,他在去年10月的车祸中不幸离开。而我还记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楼查房的间隙,他向我深情地分享二十年前他入职时的新鲜趣事。如果他在,今年就应该退休了。
长头发和乌龟壳老鳖盖旧家电们聚在一起,它们会谈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只有在春天,才被允许想起。你想啊,冬天,大家都紧捂着自己的壳啊盖啊,谁肯轻易丢弃它们呢?
上午去看一个朋友和她新诞下的宝宝,本以为月子中心很远,却原来就在住家的隔壁,石门坎128号。
阳光,照耀每一个坎。
湖水,也一同被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