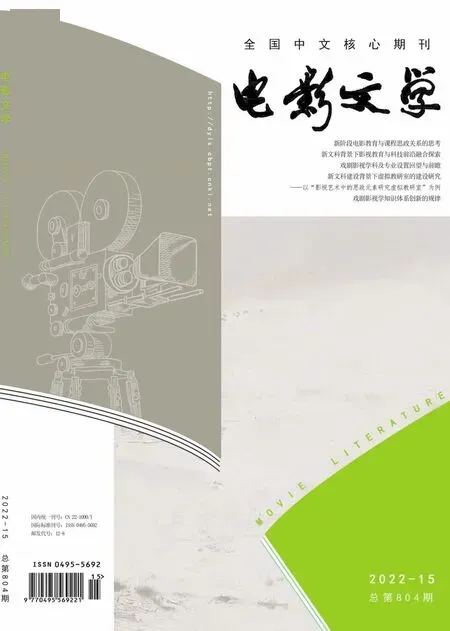王家卫电影与现代镜语下的东方思维
2022-09-23徐昕
徐 昕
(青岛电影学院,山东 青岛 266520)
“东方”不仅是一个方位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有别于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中、日以及古埃及、印度和波斯一带起源的文化,被统称为东方文化,体现着东方人独特的、富有诗性的思维方式与日常行为系统。这也就使得,尽管电影艺术诞生并兴盛于西方,但电影人同样可以赋予其东方烙印,这既包括了在内容上,电影人对本土风情地貌的细腻捕捉,对本地人精神世界的细致关怀,也包括了在形式上,对东方美学概念如“意境”“物哀”“风骨”等的充分运用。导演王家卫出生于上海,五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原本以平面设计为专业的王家卫开始以编剧身份踏入影坛,最终凭借执导《旺角卡门》让观众记住了他的导演身份。随后,其《春光乍泄》《东邪西毒》等电影更是频频获奖,逐渐树立起了独具一格的表达风格,也让世界观众以一个不同于内地导演提供的视角来观照东方世界。王家卫电影之所以能引发国内观众的共鸣和赞誉,与其风格的东方化,与其文本和影像中体现出来的东方思维,尤其是中式思维是密不可分的。
一、王家卫电影的东方哲理思维
在王家卫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其在对情节和人物关系的设计上,流露出的东方哲理思维。
一是圆融整一思维。东方哲学被认为是原始思维的延伸,而后者则是一种混沌型的,倾向于从整体上来认知、把握对象的思维。在原始人看来,如若对对象的观察与表现是部分性的,那么这一对象依然是陌生的,是令人感到不安的。这一思维有两大特征,其一便是“物我不分”或“物我同一”,即模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其二则是强调人与人,人与客观外物乃至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与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转化或相互激发情感的关系。即使是在人们逐渐加深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后,依然会以这一思维来进行思考或审美创造。这种整体思维既存在于银幕内电影中人的意识中,也体现在导演本人对剧情的处理上。如在《一代宗师》中,当武林门派林立,各自都有不传之秘时,宫羽田则表示:“拳有南北,国有南北吗?”他对女儿宫二也曾有过学武有三重境界的教诲,即“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人被纳入国家、天地与众生这一整体之中。并且,在王家卫电影中,人物故事常常呈现割裂的状态,如若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它们其实存在共通之处,“它们总是勾搭连环、纠结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拆解、难以廓清,表现出一种普适性和不可分析性,只有在其圆融整一的有机联系之中才能做出完整、全面的把握”。如在《重庆森林》中,人物生活于鱼龙混杂,犹如一个微缩版世界的重庆大厦,看似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彼此不认识,没有交集的人们在这里擦肩而过,正如警察223何志武所说:“每天你都有机会与每个人擦肩而过,你也许对他们一无所知,但他们将来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知己或朋友。”他和金发女杀手之间的露水情缘,与警察663和小吃店阿菲的恋情,看似毫无关系,但是都可以被纳入生活富有随机性,人沟通有困难性这一主题下。而人将感情与罐头和小吃,将自己与大头针、无脚鸟等建立联系,663把漏水的房子形容为“房间哭了”等,也是一种“物我同一”思维的体现。
二是超验与非理性思维。如前所述,东方哲学保留了原始思维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了一种对彼岸世界的观望,以及对于神秘、超验,难以实证者的不排斥。人们在不以怪力乱神为主流之余,也并不认为理性与逻辑可以指导一切。如在“中国美学中的‘天籁’‘作诗如悟禅’‘顿悟’‘妙悟’等范畴和命题都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也是西方理性主义美学所无法清晰阐明的、难以理解的”。王家卫也有意为电影涂抹一层非理性色彩,其并非为宣扬官能体验或迷信,而只为间接地表现人物处境或思绪的复杂,试图激活观众的“妙悟”。如在《东邪西毒》中,欧阳锋每日看皇历,看上面各种宜忌事项,“有血光,忌远行”,“冲龙煞北”云云;又如自称自己命书上有一句话“尤忌七数,是以命终”等,在电影中,与之相关的字幕或人物对此的喃喃自语反复出现。这些关乎岁星神灵的话语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欧阳锋本人以杀人为买卖,本身就是为他人制造混乱与灾祸者,他对皇历与预言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似乎处于将信将疑间,他对日期与皇历的关注,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饱受妒忌煎熬后内心的极度孤独和茫然,同时这些非理性话语也能帮助生活在当代的观众进一步向电影中的时空靠拢。
二、王家卫电影的东方道德思维
王家卫电影中,还体现着较为鲜明的东方道德思维,尽管他并不会直白表露本人的道德判断或追求,但是却往往让人物成为道德主体,在叙事中演绎着中华文化中的道德内涵。
这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人物在两性情感关系中“发乎情,止乎礼”的自我道德约束。“发乎情,止乎礼”出自《诗大序》对《诗》的解读,其原本讨论的是关于诗、乐、舞等艺术创作中的起点与目的,情感与理性的比例问题,其后被引申为某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指导,即主张人物在情感萌生之际,有必要以理性进行调和节制,最终达到一种理想的“以理节情”,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状态。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人们普遍性地认可这一道德观,以确保秩序的稳定。这体现在王家卫的电影中,主要便是人物因婚姻或其他人伦关系,强行抑制自己对他者的感情。例如在《花样年华》中,苏丽珍与周慕云因为各自配偶的出轨而相识,在接触中也渐渐对彼此产生了感情,但两人因为已婚的身份而始终自我控制,提醒自己和对方“我们不会像他们一样的”。王家卫以大量的镜头表现了人物内在欲望的萌芽,同时又饱受内心的道德束缚,担心邻里流言蜚语,因而处于痛苦挣扎之中。也正因为彼此给对方留下了保守、克己、被动的印象,因此直到最后两人都多弄到了一张船票,却都心存疑虑,担心对方不愿意接受“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带我一起走”的邀约;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代宗师》中,叶问与倔强秀美的宫二彼此不打不相识,产生了情愫,但是叶问已经有妻子张永成,而宫二则要为报父仇而奉道独身,两人始终只保持友谊,直到宫二临死前才对叶问表白:“喜欢不犯法,可我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在《东邪西毒》中,即使是个性离经叛道的黄药师,在爱上欧阳锋的嫂子之后,也选择远遁。在东方思维中,“自我意识对伦理世界的维护,建立在心与身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上,心虽然是善性的能动或自为的表现,但身又有情欲的冲动,二者之间存在一种‘乐观的紧张’关系”,人物在欲望与道德伦理间的博弈,人物形象因克制而发散的魅力,正是王家卫电影反复触动观众之处。
除此之外,还有人物坚守正义底线,或是秉承某种行侠好义、济困扶危的道德理想。与古希腊神话中诸神胡作非为、纵情任性不同,早在孟子时代,“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观念就已被提出,而《史记》中亦有了对“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者的褒奖,这些道德理念深切地沉淀于民族心理中,成为一种在进行是非判断时的稳定思维。在《一代宗师》中,投降日寇,担任奉天协和会会长的马三无疑就是放弃正义底线者,宫二立誓要杀死马三,这既是为父报仇,也是为国除害。与之相对的,叶问宁可出走香港也绝不投日,原本家境富庶的他表示:“现在国难当头,困难人人有,穷一点也没什么。我这个人喝惯了珠江水,这日本的米,我吃不惯。”而一线天更是深入敌后锄奸,成为“一代宗师”。在《东邪西毒》中,东邪黄药师与西毒欧阳锋都算不得侠,只有从乡下刚出来闯荡江湖的洪七甘愿为一个贫苦得只剩下一头驴子和一篮鸡蛋的村姑出头复仇,即使最后身受重伤,失去了一个手指,他也毫不后悔。而洪七行侠仗义的回报便是,相比于黄、欧阳、慕容等人的终日痛苦,只有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在此,王家卫书写的是自先秦两汉时便已深入人心的思维:让人超越生理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拥有充盈的精神世界的,绝非武功,而是高尚的道德。
三、王家卫电影的东方审美思维
正如学者指出的,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是西方的舶来品,西方的艺术经验与理论成果对中国电影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电影人在经受中国传统美学多年的哺育之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电影中糅入中国美学的精粹。而东西方在审美思维上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古典美学的基础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便是模仿,而从《诗》《乐记》《礼记》上生发出来的中式审美则是与模仿论不同的言志论:“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美学理想上,模仿论趋于写实、再现、逼真,言志论趋于写意、表现、境界。”如在绘画中,当西方画家采用焦点透视法来再现对象时,中国画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并不严格地遵循固定视角与物体间的客观比例。又如在文学中,以“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采薇》),“黄河流水”“燕山胡骑”(《木兰辞》)等营造出未必真实存在的意象空间,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完成某种情志或理想的表达。
电影艺术亦是如此。王家卫在电影中践行着对意象的营造,力图实现王夫之所说的“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的理想目标,其电影中的景物,往往是综合了光影、构图以及色彩处理后的情愫表达。如在《东邪西毒》中,桃花在夜里静静地站在波光粼粼的水中抚摸着一匹黑色的马,让人备感怪异。而欧阳锋则身处沙漠之中,举目皆是黄沙,空气干燥之极,一片苍凉之景,并且“沙漠的那边是另外一个沙漠”,炽烈阳光透过旋转的鸟笼照在欧阳锋脸上,使得他的脸显得时阴时阳,这又引发观众某种焦躁、畏惧的情绪。而在对人物关系稍加了解后,观众便能意识到,前者情欲的无处释放,后者关闭内心,情感高度荒漠化的状况,都借由景物得到表现。又如在《一代宗师》中,宫二在皑皑白雪中练拳,与马三生死相搏时也是天降大雪,火车站白气蒸腾,这固然与宫家原本就在东北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人物一身黑衣,置身于极寒、冷硬的景观之中,宫二心坚如石,虽九死而无悔的意志,与马三之间情义的断绝得到衬托。在这里,客观的外部意象实际上都承载了超越其原有能指的意义,观众自然而然地便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与审美经验,产生更加广阔和深远的遐想。
此外,王家卫还一直以电影来展现东方思维中根深蒂固的对含蓄蕴藉的推崇。“中国审美意识上的含蓄观念,可以追溯到‘周礼’的委婉性和《周易》的尚象性,并成为儒、道、禅美学共同推崇的审美理想。”其电影中的画面、形象往往包含了丰富的、暗示性极强的意蕴,吸引着观众去探求、交流。如在《花样年华》中,苏丽珍即使是在家里,也总是身着紧身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妆容也十分精致,这固然显得人物身姿优雅,气质过人,但实际上这是不便于日常生活的,而王家卫正是以这样的形象设计委婉地暗示人物的心灵世界:苏丽珍始终尽力维系着自己端庄克己、优雅从容的形象,身处狭窄的居住空间,又穿着修身旗袍,其肢体活动大大受限,同时受到限制的,还有她对周慕云的感情,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更换不同颜色的旗袍呈现自己的情绪。与之类似的还有《阿飞正传》中,伴随苏丽珍出现的时钟和栅栏,赌徒出门前与旭仔几乎一模一样的对镜梳头动作等,都是含蓄的,具有解读空间的设计。在此不赘。
四、王家卫电影东方思维的多重启示
当中国人急于走向世界,却在运用中式元素上不无误区,或是在坚持个性还是追逐票房间摇摆不定的当下,王家卫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对于王家卫对东方思维的阐释,我们无疑是要给予肯定的。毋庸讳言,人们身处全球化进程之中,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则来势汹汹,在数十年中几近建立起某种指向文化趋同性的霸权。同时,国产电影中也不乏为达到票房目标,过分重视感官刺激而轻忽民族精神内涵的平庸潦草之作,使得国产电影在与西方电影的竞争中更显弱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产电影显然有必要规避被西方同化,保持自身在美学表达上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也有必要避免其他人夺走对于东方风情或华夏精神的定义权,同时让民族电影产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维持一种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其次,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的是,王家卫电影浸润了东方思维却是非“东方主义”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人就开始了有关于电影“民族化”的探讨,希望建立起某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传统。就目前的作品来看,一般来说,被认为电影具有鲜明中式标签的电影,或是表现出了某种旧式的诗情画意,如费穆的《小城之春》,吴贻弓的《城南旧事》,以及霍建起的《秋之白华》等,在这一类电影中,观众能较为直接地看到人物身处一种静美悠然,情韵绵长的古典审美景致中;或是如个别第五代导演,为了打入国际电影市场而或多或少地迎合西方人猎奇心理,在电影中大量复现了一些中式民俗甚至是伪民俗,加深了其他国家观众对中国的“他者”想象和落后偏见。
而王家卫与前者截然不同,他能够让电影中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来展现东方思维,包括凸显人物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空间上的阴暗逼仄、嘈杂喧嚣,人生存状态的漂泊不定、颠沛流离,以及在与异性交往时的躁动不安、充满隔阂等,这也正是王家卫电影很早就能以一种“世界性”得到外部认可的原因之一。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后现代主义是谈及王家卫电影时难以回避的特征之一,他正是将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与自己文化积淀中的东方思维进行了结合,并未自然主义式地呈现现代都市人生活的各种苦闷无趣之处(如娄烨的《苏州河》等),亦不曾兜售某种苦难景观,而是通过如声画蒙太奇,颠覆线性叙事等手段让原本并不舒心适意的现代生活具有了某种值得人品味的诗情。尽管我们并不能说王家卫电影就代表了“民族化”的方向,但其中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确是对电影“民族化”的一种补充,而其关注现代都市,融会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向,对于部分倾向于通过回看古代或凝望乡野来完成“中式”书写,很容易滑向“东方主义”陷阱的电影人来说,无疑是有启发的。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王家卫电影还基本上实现了对经济规律与艺术规律的兼顾,原本极富个人色彩与诗性气质的东方思维,能够被他纳入商业美学实践中来,尽可能避免赢得口碑失去票房的窘境,这也是值得有意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人借鉴的。只要对王家卫电影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已被好莱坞商业片确立起的三项原则,即明星制、类型片与大片厂制度,都是王家卫乐于接受的。如他不仅热衷于选用明星,让如梁朝伟、张曼玉等知名演员贡献出具有可识别性的,让观众热议不休的表演,还善于在特定角色上,如《旺角卡门》中的乌蝇、《重庆森林》中的阿菲等,挖掘出本业并非演员的明星的表演潜质,实现了明星与影片的相互成就;又如在表达上的特立独行中,王家卫依然注意保留电影基本的,能发挥娱乐效果的类型特征,如《东邪西毒》《一代宗师》中精心设计的动作场面,《花样年华》中缠绵悱恻的两性纠葛,以及人物让观众赏心悦目的外形等。这也就使得人们普遍认可:“看他(王家卫)的影片是一种享受,既有帅哥美女主演,也有他们彼此之间的演技大比拼,再加上导演强烈的新浪潮的电影风格,使观众不论是在感官或思想上都有惊喜,是现在极少数拍片兼具娱乐与艺术价值的导演。”
毫无疑问,王家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电影“作者”,其电影中各基于王家卫本人生命体验和思想的特征,乃至其无剧本创作,超长拍摄周期等特立独行的拍片方式,都是他人难以复刻的。但其电影对于东方思维的继承,其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处理,依然对当代中国电影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